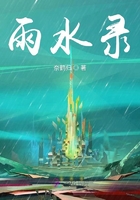简直毫无征兆,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们躲到了屋檐下。张德贵把脑袋伸出去,瞧了瞧天空,然后问我,为什么会下大雨?我把目光从天空移到他硕大的脑袋上,看到了他头发上的雨水,然后又看到他的脸上有雨水。后者跟泪水没什么区别,这使张德贵看起来相当悲伤。他就像在哀求我告诉他一个合理的解释。多么可惜,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这个艰难的问题。之前我只是希望能追随他的目光看到一些我所没看见过的东西,结果没有。下这么大的雨,天上连只鸟也没有,他的头上也没有鸟窝。我是说,他的头上如果有一顶帽子我可能就不这么说了。我到底要说什么呢?我说,张德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下雨。
是这样——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很多,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下雨,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突然雨就停了。但这并不带代表我们知道的东西就很少。我们知道玉米地里长了许多狗屎瓜。这是一种很小的瓜,形状和花纹与西瓜无异。区别在于,它只有拇指大小,而且熟透了之后很柔软,很香。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这种瓜叫什么名字,于是我们给它起了名字,狗屎瓜。我们决定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
就在昨天,我们带着许多狗屎瓜到学校,我们问胖子,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说着我们就取出一个让胖子闻了闻。胖子被香气所陶醉,但并没有闭上眼睛,而是摇头晃脑地盯着我们的狗屎瓜看。之所以摇头晃脑,是因为张德贵不停地摇晃举着狗屎瓜的手臂。
这是什么?胖子请求我们告诉他狗屎瓜是什么。我们不会告诉他的,所以我们就笑了。我们被胖子的无知弄得相当开心。我们因为有许多胖子这样的无知者而感到庆幸。他们混沌未开,蒙昧可怜,而且永远没有摆脱的机会。他们甚至还请教了无所不知的老师,老师也对着狗屎瓜摇头不语。
这场大雨确实是我们始料未及的。电视上播送天气预报的那个女的没有提及,这让我们对她的好感大打折扣。多年以来,张德贵对她的乳房啧啧赞叹,认为它们并不适合于哺乳,因为那样的话,婴儿会窒息而死。也不适合张德贵用手去抓,因为他的手抓不住,他认为就像自己无法单只手抓住篮球一样。也许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原因就是长大,起码等待手越长越大,当它有了足够的长度和宽度,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抓住篮球了,顺便抓住那个女的的乳房,像揪衣领那样揪住她的乳房,我们要鼻尖顶这鼻尖责问她:你,是不是想把婴儿都憋死,嗯?如果她胆敢不承认,说不是,那么我们就不放过她。如果她承认,说是,那么我们就为婴儿报仇雪恨。
回到这场大雨。在到来之前,我们也没有看见燕子低飞、蚂蚁搬家;咸肉没有滴卤,张德贵的奶奶也没嚷着刀疤疼。张德贵的奶奶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她说的话除了张德贵的爷爷就没人听懂。不过在张德贵出生前三十年,张德贵的爷爷就被一场洪水冲走了。有的人说他被下游的一棵倒在水里的大树的树枝给袢住了,没能到达大海。也有人说,他根本就没漂远,尸身出现在张德贵家门前那个水塘里,一到夏天就散发恶臭,三十年来总是如此。更多的人说,她到了大海,而他因为没有见过那么宽阔的水面,被活活给吓死了。总而言之,张德贵的爷爷死了,三十年前就死了。三十年后的张德贵在屋檐下躲雨,因为伸出脑袋看天空,脸上有了雨水就像泪水,很悲伤的样子。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为他在想念他的爷爷。张德贵的奶奶每天都要唠叨许多,我们听不懂,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她是希望我们不要打架,不要下河。现在我恍然大悟,她是希望我们帮着她到海边看看她的丈夫,告诉后者,她还活着,她都活腻了,而且早就不想活了。那回胆结石手术,她就打算死在医院的,但结果还是被人拖了回来,成了预报天气变化的工具。这种耻辱真的让人受够了。
在屋檐下,我们站累了,被眼前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搞得目瞪口呆,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因此我们感到绝望极了。后来张德贵建议我们坐下来,可是除了身后的墙壁,什么也没有。当然,我们可以敲门,让这户人家搬出一条足够两人乘坐的条凳给我们。或者我们被邀为上客,在这户人家吃一顿饭,然后挤在厨房的柴草堆里过上一夜,到了明天,雨一定会停的。这正是我们的经验,无论当天发生了什么,睡上一觉,到了眼睛再次睁开,就什么也没有了,什么都过去了。我们对自己说,真好啊,又是一天。
没有坐的,我们只好看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如注的暴雨从天空倾泄而下,激溅在屋顶上,屋顶笼罩在一层水雾之中。然后雨水顺着瓦楞不懈地流淌,在屋檐和地面之间制造了一面绝对垂直的水帘,水线与水线之间保持着平行关系。这些来自房顶的雨水和直接落在地面上的汇聚,使地面一片金黄,相当鲜艳。它们向低处急速流淌,消失在屋后那片低矮的鸡冠花丛里。我总认为鸡冠花是一种非常忧郁的花,它没有花朵那种司空见惯的轻盈和香气,却有着沉重的肉身。不是吗,也不知道它怎么回事,肉乎乎的,以至于都不像植物。它们的颜色也不好看,红,却不是鲜红火红粉红和其他什么红,而是紫红,甚至就是紫色。像在暴雨中淋湿的人那冻得发紫的嘴唇。张德贵的爸爸就有这样两片嘴唇,那么厚那么紫的嘴唇在我们所见过的人里面是没有第二个的。
很难想象这样的嘴唇能摁在什么样的女人身上。也就是说,关于张德贵的妈妈,只是个概念,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也许在张德贵出生前五十年,她就走了,比张德贵的爷爷走得还早。据我所知,她走的那天晚上,天十分黑,但有月光,有月光也很黑,也就是说,与其说她是趁着当晚的月光走的,不如说她是趁着黑走的。在那个黑暗的夜晚,张德贵家还点着一盏灯,就放在桌子中央,它将黝黑的桌面照出了亮光,但却照不到它的底座那块巴掌大的地方。张德贵说,他的妈妈之所以点着那盏灯是考虑到她的儿子将来怕黑。确实如此,张德贵很怕黑。此外,她还想通过点亮这盏灯,好让张德贵的爸爸夜里醒来时,可以直接发现她走了,免得他糊里糊涂像平时那样夜里起来撒尿连眼睛都不睁开一下。
他总是机械地爬起、走向粪桶、返回床铺,一系列过程由于熟练,根本不用担心会碰着什么撞着什么。事实上他夜里起床撒尿不仅不睁开眼睛,而且也没有醒。对张德贵的爸爸而言,起床撒尿根本不会中断睡眠,反而只是睡眠的一个配件,是睡眠的一部分。正因此,张德贵的妈妈点亮灯完全是多此一举,或者完全是为自己走掉制造一个神秘气氛。张德贵的爸爸是通过第二天早晨的光线发现她不复存在的。他总是起得很早,总是能听到鸡叫,他扛着锄头经过那些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的鸡叫,趁着早凉要到地里刨出一块来,然后等太阳升起来再回家吃老婆烧的早饭。隔着老远,他就可以看到晨光之下自家烟囱里那柱袅袅炊烟。那一天他没发现炊烟,而是推开门后发现桌上那盏灯已耗尽了油灭了,枯萎的灯芯上方缭绕着可疑的青烟。这个嘴唇又紫又厚的糟糕男人,老婆注定是要走的,不遵从命是不行的。可他居然像个孩子那样嚎啕大哭。
我说,张德贵,雨如果停了,我们去哪儿?
他说,你说呢。
我说,我看到他们就想死,不想回家。
他说,那我听你的。
说来奇怪,当我们进行这番讨论的时候,雨就突然停了。我已说过,我们根本不知道雨会停,而且这么突然,一如之前不知道雨会突然下起来一样。
于是我们像事先约定好的那样同时脱掉了鞋子,拎在手里,趟着村道的烂泥向村口走去。一向板实的村道彻底被雨水浇透了,让我们的腿脚深陷其中。烂泥像泥鳅一样从我们的脚趾间不断地逃了出来。为了免于滑倒,我们互相搀扶。我看见有一个大妈站在门前看着我俩,她与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后来,她渺小得就像一个诱人的猎物——如果有一把枪就好了。
我们终于来到了村外的田地里。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玉米地全被收割了,而且被拖拉机耕犁过了,泥土以大块大块的卷曲的形状裸露在我们面前。但我们并不甘心,怀着侥幸心理走了过去,希望在其中还能找到狗屎瓜。我们不愿意失望,但我们不得不失望,一个狗屎瓜的影子都没有。只有螳螂、蚂蚱和年幼的癞蛤蟆在泥土间跳跃。无数条蚯蚓在泥土上方蠕动。偶尔一只老鼠探出头来,转眼就不知去向。
怎么办?张德贵问我。
在他提问之前,我本来想说我们回家吧。但既然他问了我,我就作出了相反的决定。
我们继续往前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