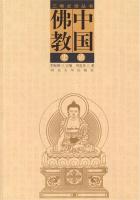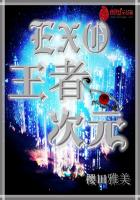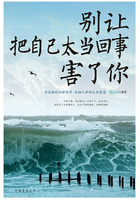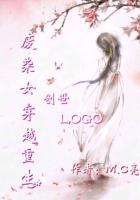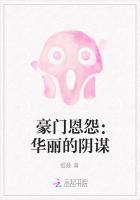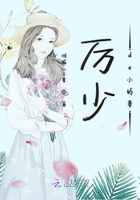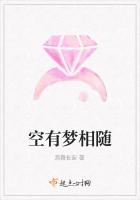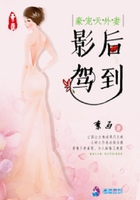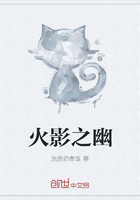心斋之学以安身标宗,知安身即知止至善,又以身为与天下国家,整个合为一物,虽与吾人前文所论不尽合,然其以天下、国、家、身为物,亦格物之物之所指,则固的然而无疑,同于吾人之说,以异于朱子、阳明之以物为事者也。唐君毅此说颇有引心斋为同道之意味。当然我们亦可看出,此一评论乃是针对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这一心斋之见解而发,而对于心斋之安身说的义理系统并无全面深入之剖析。
参诸上述历史上对心斋格物说的种种评说,那么,我们究竟应如何看待淮南格物说呢?要而言之,在淮南格物说当中,“格物”不再是一种观念模式,更不是对外在知识的追求方式,而是一种身体力行的道德实践,其特色在于强调工夫必须“真真实实在自己身上”、“实实落落在我身上”。就此而言,淮南格物说反映了心斋思想之重视力行实践的性格特征。其次,心斋突出了“身”在《大学》文本中具有“立本”的重要地位,以安身释格物,而所谓的“格物”事实上已被“安身”所取代,因此淮南格物说实质上就是格物安身说,而其格物说的独特意义及其历史地位也正可由此而显。再次,心斋之所以对“安身”问题如此关切,突出了“安身”所具有的“立本”、“端本”之意义,以为由此便可贯穿和打通整部《大学》的义理结构,但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将《大学》的义理问题作学理化的训解,而在于强调个体之身与整全之身对于人来说所具有的根本意义,而这一思想观念的形成当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有一定关联。最后须指出,心斋安身说的一个理论贡献是,“身”作为一种“个体”存在,不论此“身”是仅指“形骸”还是含指“心灵”,它具有了先于心意知物之存在的根本地位,是所有物的“根本”(“物之本”)。因此必须先肯定“身体”,然后良知才有着落,这一对“身体”问题的强调和揭示,无疑对于我们重新了解和把握心学运动的整个义理走向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足以使我们改变历来仅从抽象的形上问题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明代心学历史的研究态度。
从历史上看,除了明末刘蕺山、清初全祖望对此说有比较深入的评述,事实上心斋的格物安身说在当时以及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并不为大多数士人所取,甚至包括他的一些得意弟子。如罗近溪对淮南格物的“安身”说就表现得相当冷淡,在其格物论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对淮南格物说的正面评论。由此亦可看出,淮南格物说的一套诠释理路,与所谓正统儒者的言说方式未免格格不入。
究其原因,正在于心斋并不擅长将问题学理化,同时也与他的知识结构有关。然而在今天看来,这也正是淮南格物说的魅力所在。
另须指出的是,对于心斋的“安身”说,是否有政治学解读的可能。在我看来,此说与其“明哲保身”论是有非常重要之关联的。
事实上,“明哲保身”说的提出乃是有其社会政治背景的,主要是由于心斋目睹了嘉靖初年在“大礼议”政治风波中发生的官员集体被杖事件,因而引发了心斋的这样一种议论:“身且不保”,则修齐治平何从谈起?这便是心斋“明哲保身”论的核心观点,其中显然含有政治角度的考量。由此看来,我们不能否认心斋安身说的另一层重要涵义:它是作为一种现实政治的应对措施而被强调的。关于心斋在社会政治层面抱有何种问题意识及观点主张,我们将在下一节有较为详细的考察。
(第四节 学与政
一 政学合一
以上几节我们主要探讨了“良知见在”、“日用即道”、“淮南格物”、“安身立本”等心斋思想中的一些基本的概念设置、观念叙述,重点则在揭示心斋思想的基本精神趋向,从中可见其思想与阳明心学所展现的义理方向是基本一致的。我们讨论的重点显然侧重在“学”的层面,即主要分析了心斋思想在其学术构建中的几个主要环节,然而心斋的学术关心远不止于此。他对重构阳明心学的理论体系及诠释体系,固然没有多少兴趣,在有关良知心体等问题的抽象论证方面也显然并不擅长,这一点与龙溪等人有很大的不同,然而他借助于依靠良知便可改变自己、改变现实这一心学的基本观点,对于政治参与、社会参与如何可能等“政治”层面的问题倒是有着很大程度的关心。反观他早年的“天坠压身”之梦以及拜见阳明时有关“天下”问题的讨论、次年所做出的轰动一时的京师讲学之行为,都似乎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预示着心斋思想的发展方向不会止足于纯学术层面,而必然致力于摸索和探讨这样一个基本的心学课题:良知理论与社会政治如何能达成一种理想的结合状态,并由此推动理想的“政学合一”、“万物一体”、“人人君子”的社会发展进程。
事实上,所谓“基本的心学课题”,若放在宋明儒学的发展历史乃至放在整个儒学历史的背景中来加以考量的话,无疑地这也正体现了儒学的一个基本的中心关怀:儒家士人的伦理生活及其道德理想如何在社会、政治方面呈现其意义?只不过在阳明所推动的心学运动的过程中,这一儒学课题在良知理论的激发下被重新唤醒,并且形成了一种良知观念模式下的政学合一论。例如王心斋就曾明确指出:“学外无政,政外无学。”有“万物一体之仁”,遂有“万物一体之政”。尽管他并没有在学理上作进一步的展开。江右王门的中坚人物欧阳南野则反复强调:“政学本非二事。”“为学为官,本非二事。”“无政非学,无学非政。”另一位江右王门的重要人物邹东廓也颇为关注政与学的关系问题,常有一些精彩发言,这里仅举一例:“夫学与政,非二物也。以言乎修己,谓之学;以言乎安人,谓之政。政弗本于学,是谓徒法,徒法则己弗修矣;学弗达于政,是谓徒善,徒善则人弗安矣;是学与政之支也。”这是从政必须本于学,学必须达于政的角度,论述了政与学的彼此联结的一体关系,这个观点在阳明后学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然而这些观点其实在阳明那里都有渊源可循,且看下文:
子礼为诸暨宰,问政,阳明子与之言学而不及政。子礼退而省其身,惩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恶也;窒己之欲,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己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趋也;惕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己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己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举。叹曰:“吾乃今知学之可以为政也已!”
他日,又见而问学,阳明子与之言政而不及学。子礼退而修其职,平民之所恶,而因以惩己之忿也;从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己之欲也;顺民之所趋,而因以舍己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己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己之蠹也;复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己之性也;期年而化行。叹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为学也已!”
他日,又见而问政与学之要。阳明子曰:“明德、亲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亲其民,亲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体也;亲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礼退而求至善之说,炯然见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学所以为政,而政所以为学,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这篇文章的整体脉络非常清楚,前两段分别讲了政在学中、学在政中的道理,第三段则是说“学所以为政,而政所以为学”的最终依据在于良知。换言之,阳明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在良知学的意义上,政与学完全是可以合一的。同时,他又以《大学》的“明德”、“亲民”作为论述的一个主要取径,以“明明德”为学,以“亲民”为政,以“止至善”作为政学合一之目标。这一思想在其晚年的《大学问》中亦可得到充分的印证。若以这里的“明德、亲民,一也”的说法为据,则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阳明已有了“政学合一”的观点,只不过尚未以明确的语言,将此点出。到了王龙溪那里,才明确地提出了“政学合一”的思想口号。他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政学合一说”,该文不长,全文如下:
君子之学,好恶而已矣。赏所以饰好也,罚所以饰恶也。
是非者,好恶之公也。良知不学不虑,百姓之日用同于圣人之成能,是非之则也。良知致,则好恶公而刑罚当,学也而政在其中矣。《大学》之道,自诚意以至于平天下,好恶尽之矣。
“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意之诚也。好恶无所作,心之正也。
无作则无僻矣,身之修也。好恶公于家,则为家齐,公于国与天下,则为国治而天下平,政也而学在其中矣。昔明道云:“有天德可语王道,其要只在谨独。”独知无有不良,能慎独,则天德达而王道出,其机在于一念之微,可谓至博而至约者矣!
其中“学也而政在其中”、“政也而学在其中”也正是标题所示的中心思想:“政学合一”。其论证过程并不复杂:一方面,良知就是是非之心、好恶之公,是人人所同具的,每个人只要真诚地做到了致吾心之良知,以自己的良心去行事,就能正确地处理“刑罚”等这类政事,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学也而政在其中”;另一方面,如能按照儒家经典《大学》所展示的实践工夫的次序,从“诚意”工夫一直到“平天下”,时时刻刻不忘以是非之则、好恶之公来应对,便可实现身家国天下的修齐治平,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政也而学在其中”。在此论述过程中,龙溪强调的“公”的概念也很重要,显然这是源自阳明的良知即是“公道”、良知之学即是“公学”这一重要观念。在阳明看来,由于良知具有“公是非、同好恶”的品格,所以致其良知就能做到“视人犹己,视国犹家”,最终实现“万物一体”的社会理想;而在龙溪看来,由于良知是是非之公、好恶之公,所以致其良知就能做到“公于家”、“公于国”、“公于天下”,最终就能实现“政学合一”。可见龙溪与阳明的论述基调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将“公”置于良知的观念基础之上。也正由此,龙溪最终强调,无论是为政还是为学,其中的关键则存乎“一念之微”。所谓“一念之微”,也是龙溪袭用阳明的一个哲学用语,意指“良知”或“独知”、“良知一念”。意思是说,人的一切行为能否实现自身的价值,其关键就在于能否做到按良知行事。日常事务以及做人为学,虽然非常纷繁复杂,然而真正做起来,却只要按照人心的一点良知去做,即可无往而不胜,这就叫做“至博而至约”。在龙溪看来,只要能够做到“慎独”,切实地把握住“一念之微”,“则天德达而王道出”,意谓最终就会实现王道政治。可以看出,龙溪完全是按照良知理论来论述学与政的一体关系,换言之,学与政在良知观念的统领下必能实现完美的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龙溪对于程明道“有天德可语王道”一语的引用。经初步查阅龙溪文集,结果发现龙溪曾几次三番地加以引用,而“天德王道”连用,则更是屡见不鲜。依明道之意,上承天命而具备了天赋道德品性的天子才有资格施行王道政治。所谓“天德”,乃是指上天赋予人的一种德性,这里特指天子所具有的一种道德品性,所以明道又有“君德即天德”之说。然而在另一审视的角度下,则亦可这样来解读:理想的王道政治是建立在“天德”的基础上,若无天德则不可语王道。由此便会引发一个问题:实现王道的关键何在?明道的答案是:“其要只在谨独。”在明道看来,“天德”作为一种道德品性,是内在于人心的,借用《中庸》的概念,也就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的“独知”,因此若要最终实现王道政治的理想,其关键却在如何把握自己心中的“独知”,即便作为天子也应当由此做起。换言之,儒家的王道政治或外王理想的实现,其关键并不在于制度法典等外在事业的建设,关键仍然在于如何依靠道德的力量来转化成事业的建设。没有道德的政治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道德的缺失,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王道政治。可见,道德与政治的结合才是实现外王理想之前提的思路,与龙溪所强调的“政学合一”的观念模式———在良知理论的统合下才能实现学与政的完美统一———是基本一致的,这也是龙溪为何喜用明道此语的缘由所在。
应当说,政治与道德的一体化,道德经常被政治化,而政治又经常被道德化,这是儒学历史上不断出现的现象,甚至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究其根源,也许可从孔孟的“为政以德”的“仁政”观念找到原因。然而政治的实现毕竟离不开外在的行为礼仪、制度典章的设置和推行。这里我们可以举程伊川的两段话作为例子,首先须注意的是伊川提出的“四三王”之说:
子(指伊川)曰:“三代而后,有圣王者作,必四三王而立制矣。”或曰:“父子云三重既备,人事尽矣,而可四乎?”子曰:“三王之治以宜乎今之世,则四王之道也。若夫建亥为正,则事之悖谬者也。”伊川是说,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后世若有“圣人者作”,以三王之法的根本精神为据而另创一法,亦当是时势之必然所致,未为不可,这叫做“四王之道”。当然更为理想者,应是孔子所欲建立的“百王之通法”。伊川的另一段话则显示出他对于三王之治的实现抱有一种乐观的态度:
三代之后,有志之士,欲复先王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不备。故典法尚存,有人举而行之,无难矣。可见在伊川看来,复先王之治的条件,第一是法典,第二是人(这里不是指重要性的排序)。依上述“四三王”之说,“法典”可以是“四三王而立制”的“四王之道”,“人”则是指圣王或有志之士。但是在这一套经世之学的设想中,并没有提及个人的心性修养或道德实践对于实现王道是否具有关键性作用等问题。就此而言,伊川的外王政治的设想与明道的“有天德可语王道,其要只在谨独”之说,在思路上不尽一致,这也可能与伊川身历五朝、长期置身于政治旋涡之中、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牵涉甚多的个人经历有关。不过归结而言,伊川认为当今之世欲恢复三代社会只是一种理想而非现实,故其有云:“三代之治,不可复也。有贤君作,能致小康,则有之。”由二程再回到明代心学,透过上述所列心斋、南野、东廓、龙溪等人的有关政与学关系之问题的观点表述,我们可以发现宋明儒者的一个中心关怀是外王政治及经世济民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新近出版的******先生的两部巨著在“理学与政治文化”的分析框架下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述。他在谈到泰州学派问题时,曾这样说道:
如果我们承认“致良知”之教与“觉民行道”是阳明思想的一体两面,那么他的真正继承者只能求之于王艮所传的泰州一派;这似乎是一个最接近事实的推断。所谓“觉民行道”是余氏相对于“得君行道”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颇具睿识,他用以解说阳明良知之教的另一重要面相在于“通过唤醒每一个人的‘良知’的方式,来达成‘治天下’的目的”,余氏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