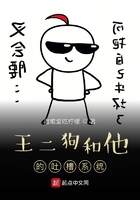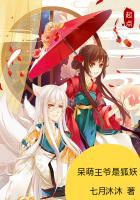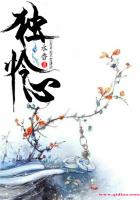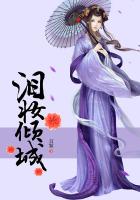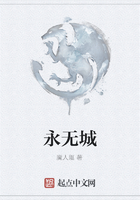今岁春,得见夫子…… (夫子)于祥所出以质之夫子者,多见许可,益勉以弗生退阻。临行,谆谆复以“体认动而无动,静而无静”为言。退而思之,涣若发蒙,于前所谓志帅、致知、立诚、主静种种工夫,一旦会归于一,真有怡然理顺之乐……是以拜别以来,无日不体此意,必求无负于夫子之教。虽无大益,亦幸无甚损。可见,张履祥在见蕺山之前以及见蕺山之后的这段时间多于心地用工夫,走的是心学一路。然而,此后的几年张履祥的学术路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起自何时、何因不得而知,只是它确实发生了。首先是他对阳明心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姚江以异端害正道,正有朱紫、苗莠之别。其敝至于荡灭礼教……姚江“良知”之学,其精微之言,只“吾心自有天则”一语而已。夫人性本善,以为天则不具于吾心不可也。然人之生也,有气禀之拘,有习染之迁,有物欲之蔽,此心已非性之本然,故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夫子之圣,必至七十,然后从心所欲不逾矩。亦谓天则未能即此心而是,故须好古以敏求耳。今未尝学问之人,而谓吾心即是天则可乎?将恐虽无物欲之蔽,犹有习染之迁,而气禀之拘,将必不免矣。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君子之道鲜也。姚江大罪,是逞一己之私心,涂生民之耳目,排毁儒先,阐扬异教。而世道人心之害,至深且烈也。“良知”之教,使人直情而径行,其敝在于废灭礼教,播弃先典,《记》所谓“戎狄之道”也。基于对心学的这种认识,他将所有有心学倾向的观点都掀翻在地,因此,他对师学的信仰必然发生动摇。蕺山学派的主旨在张履祥这里几乎不复存在。他在《书某友心意十问后》中说:
窃谓“诚意”二字,“意”字不必讲,只当讲“诚”字。在学者分上,还只当讲求所以诚之之方,而实从事焉。
在《甲申冬问目》的第一条中记载了当时张履祥对“诚意”的认识。
后来他自己对这段认识做了检讨:
欲知善之为善,不善之为不善,非自格物,何以知之?从“诚意”说起,是习于姚江而不察也。张履祥自然知道“诚意”是刘宗周晚年的宗旨,他在这里其实是借着自我批评来批评刘宗周的“姚江习气”。他对蕺山“诚意”之旨其实是反对的,因此常常对“诚意”二字有意回避。他在给刘宗周的孙子刘子本写的一篇序中便单提“慎独”而略去“诚意”,在《告先师文》中,他又说:
先生起而立诚以为教,本之人极以一其趋,原之慎独以密其课,操之静存动察以深其养,辨之然的然以要其归……盖世儒之为教也,好言本体,而先生独言工夫……这篇祭文说刘宗周“立诚以为教”,独不言“意”字,很可能是有意回避。其实,刘宗周虽然强调工夫,但只是反对只言本体,并未完全舍弃本体之说。从这里看,张履祥似乎只抛弃了“诚意”而继承了蕺山“慎独”之说,然而这里面所提到的“慎独”,也不是刘宗周所说的“慎独”,而是朱子的“慎独”说。他在《备忘》二中谈及了他对刘宗周“慎独”的理解:
世人虚伪,正如鬼蜮。先生立教,所以只提“慎独”二字。
闻其说者,莫不将“独”字深求,渐渐说入玄微。窃谓“独”字解,即朱子“人所不知,而己独知之处”一语已尽,不必更著如许矜张。吾人日用工夫,只当实做“慎”之一字。文中对刘宗周的“慎独”做了朱子学的理解,当然不是刘宗周本意。
可见,张履祥其实把蕺山学派慎独诚意的两个宗旨都抛弃了。他在《备忘》一中也婉转表达了对刘宗周“姚江习气”的批评:
癸巳,韫斯以予《初学备忘》质之裒仲,裒仲曰:“山阴先生不脱姚江习气,吾是以不敬山阴。考夫看来不脱山阴习气。”
韫斯述其言告予,予答之曰:“吾于先生之学,未能得其万一,况敢言脱乎?”然未尝不服裒仲之知言。吴裒仲是吴蕃昌的弟弟,也是信奉程朱的学者,他说张履祥不脱山阴习气,其实就是说他不脱姚江习气,说明张履祥那时仍有心学的影子。不过从他的反省看,不敢言“脱”,只是表示对老师的尊敬,他的本心还是要完全摆脱心学,回到程朱那里。
除继承了刘宗周整齐严肃、深沉内敛的程朱作风外,张履祥还继承了刘宗周的人性论。他和刘宗周一样,反对离气言性,认为不离人心而有道心。在《言行见闻录》三中记载着张履祥初见蕺山时对人性的看法以及他后来的认识:
先生尝问履祥:“人心道心,平日如何体勘?”对曰:“心之本体只有仁义礼智,所谓道心也。自夫目之遇色,耳之遇声,口之遇味,鼻之遇臭,四肢之遇安佚,而后人心生焉。人心渐重,则道心渐轻。窃谓危微精一,用力全于姤、复之际。”先生曰:“心一而已,人心之外,别无所谓道心。此心之妙,操存舍亡。存则人心便是道心,舍则失之。其流至于禽兽,亦是此心为之。所以工夫要一,一者诚也,至于一则诚矣。”……祥当时犹分声色臭味之类为人心,而不知声色臭味之各当其可,即为道心也。其势出此入彼,我欲仁斯仁至,亦无渐重渐轻之数也。在《备忘》中里,张履祥又说:
古之言性者纷纷,至孟子而始定。后儒言性者又纷纷,至程子而始定。程子、孟子一揆也。或疑程子兼言气,孟子只言其理,是殆未尝举孟子言性处思之也。若“形色天性”,及“口之于味”、“仁之于父子”处,何尝遗却气来?有友人以文字相质驳先儒“气质之性”之说。张履祥在其书后批注云:
好议论先儒而申己说,世之为良知之学者,无不中此病。
此人在习中转移而不自知,更说甚性?且去将“信而好古”一语仔细思之。
又接着说:
孟子说个“形色”,是发前圣之未发;程子说个“气质”,是又补孟子之未发。此友未之或思耳。不离人心而有道心是张履祥、陈确以及黄宗羲的共识,甚至是对师说唯一的共识。不过,张履祥的观点与刘宗周也稍微有点不同,这主要体现在对告子的态度上。刘宗周在《存疑杂著》中说:
告子累被孟夫子锻炼之后,已识性之为性矣,故曰“生之为性”,直是破的语。只恐失了人分上本色,故孟夫子重加指点,盖曰“生不同而性亦不同”云。孟夫子已是尽情剖露了,故告子承领而退。可见,刘宗周对告子“生之为性”的观点还是有所肯定的,只是认为他说得不究竟罢了,而张履祥对告子却只有批评:
告子论性,最足惑人,为害最深。由其言食色是性,而仁义礼智非我固有之也。其与荀卿“性恶”,相去一间。荀卿只为见得血气心知之险,而不知有仁义礼智,故便以为“性恶”。告子“生之谓性”亦不出血气心知,特未说到险处耳……告子“无善无不善”之论,遂为释氏之前茅,故至今犹有祖述之者。张履祥是蕺山门下由王转朱的一个代表,从他的这种转变可以看出当时的学风渐趋笃实。然而,由于张履祥墨守程朱,毫无创见,使得他给人的感觉较刘宗周更为古板生硬并有些暮气,缺乏灵性。梁启超评价张履祥说:“依我看,杨园品格方严,固属可敬,但对于学术上并没有什么新发明,新开拓,不过是一位独善其身的君子罢了。
当时像他这样的人也还不少,推尊太过,怕反失其真罢。”2.陈确陈确,字乾初,浙江海宁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卒于清康熙十六年(1677),长张杨园7岁。明亡前夕由祝渊介绍拜刘蕺山为师。陈确自幼聪颖过人,他的父亲又是一个对他相当爱护宽容的人,使得他天性毕露,书法篆刻、洞箫弹棋无所不精,为人也相当超迈。在师事蕺山之后,“一切陶写性情之技,视为害道而屏绝之”,但其个性难改,才情难抑,难免灭于西而起于东,他在学术上的标新立异和攻击性,恐是其自性中的才情受到压抑而产生的变相表达。
黄宗羲在给陈确写的第一篇墓志铭里对陈确有这样的评价:
先生天才绝出,书法篆刻擘阮,洞箫弹棋蹙融,杂艺经手便如夙习。居丧,书孝经百卷,体备晋、唐。截竹,取书刀削之成冠,以变汉竹皮冠之制。其服也,不屑为唐以下,突兀遇之寒田古刹之下,不类今世人也。其学无所依傍,无所瞻顾,凡不合于心者,虽先儒已有成说,亦不肯随声附和,遂多惊世骇俗之论。而小儒以入耳出口者嚣然为彼此之是非。先生守之愈坚,顾未免信心太过,以视夫储胥虎落之内,闭目合眼,矇瞳精神者,则有间矣。夫圣贤精微要渺之传,倡一而和十,悉化为老生常谈陈腐之说,此先生之所痛也。陈确的个性可见一斑。在这篇墓志铭里,黄宗羲虽以陈确为蕺山“高弟”,然仍谓其“学无所依傍”。其实,陈确虽推倒不少先儒成说,但对于孔、孟、陆、王、蕺山等人他仍是极力维护,推崇阳明“知行合一”之说,而多惊世之论,这也是心学应有的特点,因此,陈确学风仍属心学一路,并非完全“无所依傍”。
黄宗羲在给陈确写的第二篇墓志铭中,认为“(陈确)于先师之学十得之四五”,是正确的。他得于先师的是由“证人社”发展而来的“省过会”组织以及人性论,他石破天惊的《大学辨》也是由蕺山对《大学》的怀疑而来,是师学与《大学》冲突的产物。
如果说张应鳌和黄宗羲是以绍兴、宁波两地的证人书院作为蕺山学派道场的,那么陈确的道场应该是省过会。省过会是他的弟子许大辛等在1649年成立的,依据的便是蕺山《人谱》中改过迁善的“证人”之法,但由于单独的自省有时会如“狂者自医其狂”,因此,省过会便同刘宗周的方法又有不同,它要求会众每日自记言行得失,并公之于众,即借助别人的眼睛对自己的过错进行省察,而不只是像“讼过法”中那样要自己祭起一个高高在上的鉴临者。这是使他人成为自己的一面镜子,让自己对自身的过失有更为清楚的认识。“他人”是人格结构中超我的外化,这说明人们意识到来自于自身内部的超我并不能完全胜任对行为和意识的有效监控。省过会成员多是陈确的子侄或学生辈,陈确自然就是该会的导师。他在《诸子省过录序》中说:“此吾向者山阴先生之教也。”在肯定学生们的做法的同时,他又告诫弟子们知病与治病不同:
诸子苟未施对证之药,而泛泛焉惟过之省,省过而过滋多。
犹病者能自言其病……彼非不知病之审也,然而不愈,则未尝有治之药也……知病矣,而不能求良医以治之,与不知病同。
知治之法矣,而不能节饮食、慎起居以养之,与治非法同。同时,他又区分了“偶感之疾”与“养成之病”的不同:“偶感之疾,勿药而自愈;养成之病,不治将日深。”陈确给出的方法就是以相反的手段“对治”。然而善治者,不如善养者,一个人想要远离过错,不能单靠别人的纠察,“古之君子不畏众而畏独”,因此要注重培养元气,“盖人之元气固则百邪无由入也,学者之天理全,则百过无从生也”。“培养元气”之说源自于蕺山。从对知过改过的重视程度看,陈确应该是一个道德严格主义者。
陈确的人性论大抵继承蕺山的说法而略有不同。他的观点大抵是:人只有气质之性,气质之性便是善,此善性需后天扩充方可成就。他在给刘汋的一封信中说:
来教谓“止就气质言,便万有不齐,安得遽谓之善”,此蔽于习闻习见,而未尝一反而思之,故云耳也……大抵兄所谓气质,指习气说,正宋儒之所误认者。习自相远,以习为性,何翅千里!先生所谓“人只有气质之性”,谓气质亦无不善者,指性中之气言。性中之气,更何有不善耶!阳明亦云:“性之善端在气上见,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如是,则虽曰“气质即义理”,亦无不可,犹云“性即理”也。可见,陈确是真正继承了刘宗周“性只有气质,义理者气质之所以为性”的观点,相反,刘宗周的儿子刘汋的不以气质为善,实有背于家学。陈确批评刘汋以“习气”为“气质之性”的倾向其实是刘宗周中年时期在《论语学案》里表达的观点,晚年的刘宗周对此已经不再坚持,而是主张气质之性便是善了。既然气质之性便是善,那么善是不是现成的呢?当然不是,否则恶从何来?陈确认为,虽然气质之性本是善的,但必须“扩充”才可以“成性”。他在《性解》(上)说:
“尽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盖人性无不善,于扩充尽才后见之也。如五谷之性,不艺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种之美耶?…… 《易》“继善成性”……继之,即须臾不离,戒惧慎独之事;成之,即中和位育之能…… (从来解者)至所谓“继善成性”,则几求之父母未生之前。呜呼!几何不胥天下而禅乎!又在《知性》中说:
今学者皆空口言性,人人自谓知性,至迁善改过工夫,全不见得力,所谓性善何在?恐自谓知性,非孟子所谓知性者也。
孟子本知性于尽心,正为时人言性终日纷争,总无着落。谓性有不善,固是极诬,即谓性无不善,亦恐未是实见,不若相忘无言,各人去尽心于善。尽心于善,自知性善,此最是返本之言,解纷息争之妙诀也……所谓尽心,扩而充之是也。苟能充之,虽曰未尝知性,吾必谓之知性;苟不充之,虽自谓知性,吾岂谓之知性者哉!盖陈确虽然仍是性善论者,但反对凭空说性善,认为必须“扩充尽才”,“继之”方能“成之”,工夫不可或缺。如此,他一方面在肯定性善的基础上,否定了善的当下即是,另一方面也是试图堵住将工夫转向先天的倾向。
然而,正如刘汋所说,人的气质毕竟存在先天的差别,那么依气质而有的人性是否也应该有差别?这是陈确无法回避的事实,而刘宗周本人对此并没有直接回答。陈确在《气禀清浊说》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气之清浊,诚有不同,则何乖性善之意乎?气清者无不善,气浊者亦无不善。有不善,乃是习耳。若以清浊分善恶不通甚矣……清者恃慧而外驰,故常习于浮;浊者安陋而守约,故常习于朴。习于朴者日厚,习于浮者日薄。善恶之分,习使然也,于性何有哉!故无论气清气浊,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矣。
故习不可不慎也。“习相远”一语,子只欲人慎习,慎习则可以复性矣,斯立言之旨也。这里陈确不慎用了“复性”一词,与前所谓“继善成性”之旨相背,然而他的意思仍是很清楚的,与刘宗周对此问题的看法并无大的不同。性只是善恶,无关清浊,这是解答这个问题的关键。那么恶缘何而起呢?陈确和刘宗周一样,将恶归因于“恶习”,他们无疑对环境给人施加的影响有着深刻的体会。
和人性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人欲。由于陈确是一个自然人性论者,认为气质之性即义理,因此,他不会对因气质而有的人欲持彻底批判的态度。他说:
欲即是人心生意,百善皆从此生。止有过不及之分,更无有无之分……贤人君子,于忠孝廉节之事,一往而深,过于欲者也。顽懦之夫,鞭之不起,不及于欲者也。圣人只是一中,不绝欲,亦不纵欲,是以难耳……山阴先生曰:“生机之自然而不容己者,欲也;而其无过不及者,理也。”斯百世不易之论也。
又说:
人欲不必过为遏绝,人欲正当处即天理也。如富贵福泽,人之所欲也;忠孝节义,独非人之所欲乎?虽富贵福泽之欲,庸人欲之,圣人独不欲之乎?学者只时从人欲中体验天理,则人欲即天理矣,不必将天理人欲判然分作两件也。虽圣朝不能无小人,要使小人渐变为君子。圣人岂必无人欲,要能使人欲悉化为天理。君子小人之辨太严,使小人无站脚处,而国家之祸始烈矣,自东汉诸君子始也。天理人欲分别太严,使人欲无躲闪处,而身心之害百出矣,自有宋诸儒始也。君子中亦有小人,秉政者不可不知;天理中亦有人欲,学道者不可不知。明末清初之际的许多思想家将晚明的败亡归罪于阳明心学释放出了人欲这只猛虎,使得名教不能范围人心,导致世风日下,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