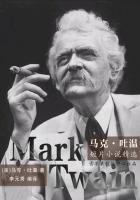笑了一阵之后,桃子好像不经意地说起:“大哥,建明,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如果你们还想参加我们公司的话,动作要快喔。因为从下礼拜起,公司的赢利不错,股份要涨到二万块钱一股,这礼拜五是最后一班车。”
臧建明朝我看了一眼,意思说老大你拿主意,我不管。
这女人无事不登三宝殿,臧建明一定漏出去说我们手里有几万美金,这女人是只闻到腥的猫啊!
桃子给歪嘴他们解释东海公司的性质,说今后的股息还是按百分之十的月息发放。
我点起一支烟,作为一个当家人,每天把钱拿出去,对钞票的观念跟刚来时有所不同。我们装修公司辛苦一个礼拜,所赚也就是一二千美金,一到月底,房租交掉就所剩无几。如果真像桃子所说的,一万六和二万之间的那四千美金的差距,对我来说还是很令人心动的。我现在手上的钱还够买三个股份,如果按照臧建明的说法,再有百分之十的回扣可拿,那这笔钱应该是很可观的,可以对我们日益浩大的开支贴补不少。
可是,我心里总有一丝疑惑,倒不是对东海公司,最近当地的中文报纸都纷纷扬扬地报道对公司负责人的访问,成篇累牍地探讨赚钱的新理念。连雇我们做装修的主顾也在说准备辞了职去东海上班了。看来这台巴子还是有点门道的,否则不会这么多人都是傻瓜。
我的疑惑是这个女人,我总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她,但我死活想不起来。数了数我认识不多的上海人,部队里有几个,全是男的。家乡地方上有一些六十年代支内的大学生,全是半老的阿姨了。深圳?那是个人来人往的城市,但在我的记忆里找不出相像的面孔。
那种相识像是在梦里,讲不清道不明。有点像前世的记忆,在一片模糊的人群中有一张脸,眼光和你一碰撞就隐入灰色的背景,你苦思冥想,却捕捉不到这道眼光是几生几世前曾跟你相遇过。
“老大。”我听见栾军在叫我,一激灵醒过神来,看到房间里的人都朝我看着。臧建明道:“等你拿主意呢,买还是不买,至少给桃子小姐一句回话,人家老远地跑了过来。”
我抽着烟没接声。
栾军问道:“桃子小姐,听起来不错,但总觉得好得不像真的。你确定我们把钱交给你,什么时候想要都可以拿回来吗?”
桃子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叠空白的申请表:“这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我们签了字就是正式的法律文件,在美国,法庭就认你的签字。如果到时候要不回来,你可以上法庭告我们公司。”
栾军道:“我们连一个英文大字也不识,还能去告谁?我只是想确定钱交到了保险的地方。不怕问你一句:桃子小姐,你自己有钱放在公司吗?”
桃子说:“不瞒你说,我所有的钱都放在公司里了,不止一个股份。”
大家都不做声。
我对歪嘴使了个眼色,我们一起来到楼下车库里。歪嘴说:“真有这么好的事?”
我道:“臧建明唠叨过好几次了,你看怎样?”
歪嘴道:“太好的说法总使人想起陷阱,但也难说,这世界上什么事都有可能,我们一年前还在福建小地方混日子,谁又能想到今天来了美国呢?”
“那你的意思是试一试啰?”
“我们需要钱。”
我沉默不语,我不能把对桃子的疑惑告诉歪嘴。
“老大你在想什么?”歪嘴问道。
“如果公司在文件上弄什么花样呢?我们可玩不过他们。”
歪嘴嘴巴一牵,做了个开枪的手势:“那就端了他们。”
回到客厅,我拿出支票,开了四万八千美金给桃子,买三股公司股票。我和歪嘴在车库里商量好,过一个月就拿回来,先赚他个几千美金再说。
桃子请大家去ABC餐馆吃宵夜,那儿的牛筋面不错。
我们已经打好主意等那笔钱取回来要怎么用。我们还需要一部汽车,也许买一部卡车,对我们装建筑材料有帮助。我们的家具也要换了,现在用的都是街上捡来的,或是车库拍卖便宜买来的。还有,美国的各种电动工具很多,如电锯、电锤,价钱也不贵,拿了钱这些基本的工具都要买一套。
臧建明买了套西装,桃子每天早上过来接他去东海上班。他不是个做体力活的人,让他去东海也好,至少我们的钱有只眼睛给看着。
第一个礼拜臧建明拿了张四千八的支票回来,存进银行没问题。我们也放心了不少,这几天没接到什么活,于是我带了歪嘴和栾军上海奥德练枪去。
栾军和歪嘴都是第一次试射乌兹,打得非常过瘾。我又把他们介绍给杰米,一起到中国饭馆去吃了午餐。
吃完饭由我驾车送杰米回靶场,也许是午餐时多喝了几瓶啤酒,我有点飘飘然的感觉。在进入靶场相邻的停车场时和一辆老式的美国车轻轻地擦了一下,也不完全是我的错,那车拐弯时太急了一点。美国车停了一下,突然高速后退,差一点撞到正想开门查看的我。那车在我们旁边停下,车门一开,走下来四个二十来岁的拉丁美洲人,都穿着肥大的裤子,反戴棒球帽,颈间挂着粗大的金链。开口说车被撞坏了,要一千美金的修理费。那辆车锈迹斑斑,车身的颜色都看不清了,只怕扔在路边也不会有人要,哪值一千美金?再看我们的车,头灯碎了,左面的挡泥板全都凹了进去,防撞杆也掉了下来。我心中憋了一腔的怒火。杰米正跟那些人交涉,我拦住他,从皮夹里抽出一百美金,要就要,多一分钱也没有。
为首的家伙不接,坚持要一千美金。我叫杰米走开,把一百美金收回皮夹。转身坐进汽车,正想离去。一转脸,却看见一支大口径的手枪逼在我的左上方,离太阳穴只有几公分远;另有两支手枪对着车里的歪嘴和栾军。
我双手放在方向盘上一动不动,脑子里紧张地思索着:这家伙会扣动扳机吗?说不定,这家伙一脸的凶狠和野蛮,眼睛里隐含杀机。那只近在我眼前的手稳稳地握住枪柄,我连他指甲里的污垢都看得清清楚楚。
杰米见状想过来劝解,却被另一个拉丁美洲小子用枪逼住,大声喝令他双手抱头,转过身去。
我的酒全部醒了,我做梦也没想到会被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制住。我的本能告诉我这个关头绝不能心存侥幸,不能反抗,甚至不能做一丝引起对方怀疑的举动。在这么近的距离里,那大口径的手枪一扣扳机什么都完了,子弹可以把整个天灵盖都掀掉。我倒担心栾军会不会冒险出手,他是侦察兵出身,学过反擒拿。但我们三人都坐在车里,乌兹枪在后车厢里。还是一点胜算也没有。
逼在头上的枪口移开了一点,那家伙做手势要我出来。
我跨出车子,心想是不是一出车门就突然快速下蹲,给那小子来上一记扫堂腿,想法把枪夺过来?但完成这套动作再快也得二秒钟,另两个家伙完全可以对歪嘴和栾军开枪,我可不想他俩才来美国就送命。罢罢,死活都是天意。我决定不到最后关头不轻举妄动。
我两手平举,使拿枪的家伙不致误会,慢慢地走出汽车。
一出汽车脑袋上就狠狠地挨了一下,那家伙又用枪柄在我锁骨上狠命一敲。当我痛得弯下腰时,他把我按在汽车的车头盖上,伸手在我裤后兜里取出皮夹,抽光里面的钞票,随手把空皮夹扔出老远。我的眼睛余光看到另外两个家伙也对歪嘴和栾军如法炮制。
这些家伙割破我们车子的前胎,临走之前还用枪管在我腰眼儿上狠命一搠。耳朵里只听见四扇车门摔上,美国车踩足油门,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
“你还好吗?”我晕眩地抬起头来,看见杰米、歪嘴、栾军都朝我看着,眼光里透出焦急的神色。我慢慢地直起身,锁骨痛得像断了一样,头还是晕乎乎的,我一移脚步,便一脚踩空差点摔倒,歪嘴一把扶住我。
“你流血了。”我恍然听到杰米说道。伸手往头上一摸,满手的血,眼睛也被淌下来的血糊住了。
“到我的宿舍去,我可以用冰块给你止血。或者,你要不要我召救护车?”
我要杰米别大惊小怪,又叫人来换车胎。歪嘴拿毛巾包了一袋冰块,用一件衫子捂住我的伤口,等车胎一换好就走。
回去由栾军开车,我半躺在后座,大家一片沉默。
到旧金山时,栾军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狗娘养的,此仇不报就不是人养的。”
我疲倦地回答道:“怎么报?旧金山这么大,去哪儿找这些家伙?”
坐在前座的歪嘴转过头来:“我记下了他们的汽车牌照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