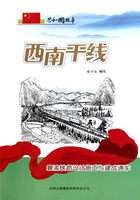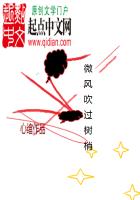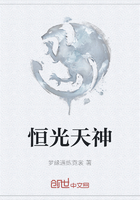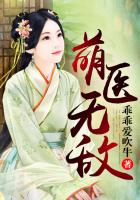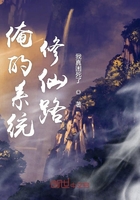这符合我心目中的戏剧美学要求:必须跟展现的目的保持一定的距离,使这个目的在时间或空间移动。一方面,舞台上表现出的激情应该相当有节制,不应孩碍观众的觉醒;另一方面,应该让消散,这是我采用的譬喻,按高乃依的术语来讲,就是喜剧幻觉的消散。应当让观众处在人种志学者的地位:人种志学者深入到一个落后社会的农民中间,起先他几乎把农民看作物,然后在研究的过程中他的看法渐渐改变了,最后领悟到,在研究农民的同时,他研究和发现了他自己。
在我看来,世界造人,人造世界。我不仅想在舞台上塑造性格,而且想指出客观环境在一定的时刻决定着某某人的成长和行为。我曾想用另外的剧名,例如:《输者赢》,但这个剧名缺少事物的另一面,在我看来也是同样重要的一面,即:《赢者输》。我着意描写一个真实存在的情境,如实笔录一个世界的死亡。我调遣人物,借用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通过这些人物暴露无遗。当我谈到我们时代的暧昧,我的意思是想说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时刻准备获得自由,又同时陷入最严惩的战斗。我写过一些剧本,其主人公和结局都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取消了矛盾。《魔鬼与上帝》就是一例。但是在我们生活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对一个像我这样的作家,除了写批判列宁主义的东西之外,很难写别的东西。如果一个主人公最后不再生自己的气,那么从头到尾看他演戏的观众也很可能调和他们的疑问,消除未解决的问题。
9.演员与悲剧
演员与逢场作戏的喜剧角色正好相反,当喜剧角色工作结束的时候,他重又变成了像其他人一样的人,而演员却无时不在“表演着他自己”。这既是一种令人赞叹的才能,也是一种不幸:他成了这一才能的牺牲品,他永远不知道他真正是谁,也不知道他是否在表演。
布莱希特的戏剧创作理想是使观众像一队突然遇上一群原始土著的人种学者,当他们走近的时候,他们才突然恐惧地想到,这些野蛮人正是我们自己。观众正是在这时成了作者的合作者:他既认出了自己,但又感到陌生,他好像成了一个他人,这时他面对作为对象的他自己而使自己存在,他看着自己,但并不扮演自己,因而他在理解自己。
我希望观众能以证人的身份从外部来看我们时代这个怪物,同时他又是参加者,既然他也在创造着这个时代。此外我们的时代又具有某种独特的东西,我们知道,我们将受到未来的评判。
我不仅想在舞台上表现性格,我还想提示,客观环境在一定的时候支配着个人的成长及其行为。……以前我写过一些剧本,其中的主人公与结局都以某种方式取消了矛盾,《魔鬼与上帝》就是这样。然而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资产阶级社会里,像我这样的作家除了写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很难写别的什么。如果主人公在最后不再与自己过不去,那么看他表演的观念也就可能缓和他的疑问以及尚未解决的问题。
而《懂事的年龄》和《延缓》还只不过罗列了一些虚假的、扭曲的、不完全的自由,描述了自由的疑难,只是在《最后的机会》中,真正自由的条件才会得到阐述……马蒂厄体现了那种彻底的无约束性,黑格尔称之为恐怖主义的自由,而这实际上却是反自由。他与《苍蝇》开头的奥雷斯特很相似:轻松自在,毫无束缚,与世界没有关系。他并不是自由的,因为他没有介入。……他感到自己被排斥在正在发生的事件之外。……马蒂厄,他是无动于衷的自由,抽象的、无所作为的自由,他不是自由的,他什么都不是,因为他总是在外面。……布吕内则体现了严肃精神,他相信那些超验的价值,这些价值被铭刻在天国里,清晰可辨,就像事物那样独立于人的主观性。他认为世界与历史都具有一种支配了他的行为的绝对意义。他介入了,因为必须有一种确信才能生活,他的介入不过是消极地服从于这种需要罢了。他没有花多少力气就摆脱了忧虑。他并不自由。人可以自由地介入,但只有当人为了自由而介入时,他才是自由的。
悲剧是命运的一面镜子。在我看来,要写一出自由的悲剧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古代的命运无非就是被颠倒的自由而已。奥雷斯特在犯罪之前和之后都是自由的:我描写了他是如何身受自由的折磨的,就像俄狄浦斯为其命运而痛苦一样。他在此铁拳之下挣扎,然而他必须以杀人告终,他必须承担其杀人的罪行,并带着罪孽走向彼岸。因为自由并不是什么超越人类条件的抽象能力,而是最荒谬、最无法逃避的介入。奥雷斯特将继续他的路途,他依然是无法辩解的,毫无理由的,他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像一个英雄,也像任何人一样。
我想探讨的是与命运的悲剧相对立的自由的悲剧,换句话说,这个剧本的主题可以这样归纳:当一个人面对他所犯下的罪行,他是如何自处的,哪怕他承担了一切后果与责任,哪怕这个罪行令他本人感到恐惧。……显然,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与唯一的内在自由原则不相符合的,某些大哲学家如柏格森等人,他们就试图在此自由中找到摆脱一切命运的根源。可这种自由总是理论上的、精神上的……作为意识上自由的人,他可以达到超越自己的高度,可只有当他重新确立了他人的自由,只有当他的行为导致了某种现存状况的消失,并重新恢复了应该确立的状况时,只有这时他才能在境遇中是自由的。
问题并不在于知道为什么我们是自由的,而在于了解什么是自由之路。在此,我们完全同意黑格尔的说法,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那么任何人都不可能是自由的。……我们现在的,也就是当代的具体目的就是人的解放,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人的形而上学的解放,使之意识到他的彻底自由,让他明白他应该与趋于限制自由的任何现象作斗争。其二是人的艺术的解放,通过艺术作品促进自由人与其他人的相互沟通,并由此使人们处于同样的自由气氛之中。其三是政治与社会的解放,被压迫者与其他人的解放。
如果我在客体意义上把他人的自由作为目的,那我便侵犯了他人的自由。如果我以自己的自由作为目的,那么这都必然要把所有别人的自由都作为自由来要求。在我选择我的自由时,我也要求他人的自由,然而当我进入行动领域时,我就不得不把他人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显然,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个二律背反,但正是这个二律背反构成了道德问题。我将在我的《道德》论著中考察这一二律背反,但我现在就应该看到,一种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却对矛盾大感惊异的思想正在彻底衰败。
“我们从未像在被占领时期那么自由”,这句话是与海因里希这个人物相对立的,海因里希这个客观的叛徒成了主观的叛徒,后来又成了疯子。从奥雷斯特到格茨经过了7年时间,其中还有抵抗运动的分裂。
矛盾并不在观念里,它在我的存在之中。因为我所说的这种自由也包含着所有人的自由。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我不能完好无损地置身于所有人的纪律之下。我不能独自一人是自由的。
或者道德是句无聊的空话,或者它就是集善与恶于一身的具体总体。因为没有恶的善是巴门尼德的存在,也就是死亡;而没有善的恶则是纯粹的非存在。回收否定的自由,并将之与绝对的自由或通常所谓的自由一体化,这和主观的综合一样是与这种客观的综合一致的。我希望读者能够理解,这丝毫不是尼采那种善与恶的彼岸,而毋宁说是黑格尔的扬弃。这两个概念的抽象分裂仅仅表明了人的异化。无论如何这种综合在历史境遇中是难以实现的。所以,今天一切不愿明确承认自己是不可能的道德,无一不在骗人,使人更加异化。道德对我们来说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不可能的,道德问题即由此而产生。而行动则必须在这种难以超越的不可能性的条件下赋予自身伦理的规范。应该从这个观点来考察诸如暴力问题或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对于经受着这种分裂,并不得不有所要求,又有所决定的意识来说,一切漂亮的反抗,一切拒绝的呼喊,一切符合道德的义愤全都显得是陈旧的夸夸其谈。
10.论艺术作品
作品绝不局限于画成的、雕成的或讲述出来的客体,如同人们只能在世界的背景上知觉事物一样,艺术表现的对象也是在宇宙的背景上显现的。作为法布利斯的历险的背景,是1820年的意大利、奥地利和法国,布拉奈斯神甫观测的满天星斗的夜空,最后还有整个地球。如果画家画给我们看一角田野或者一瓶花,他的画幅是开向整个世界的窗户;这条隐没在两边的麦田中间的红色小道,我们沿着它走得比凡·高画出来的部分要远得多,我们一直走到另一些麦田之间,另一朵云彩底下,直到投入大海的一条河流;我们把深沉的大地一直延伸到无穷远,是这个大地支撑着田野与符合目的性的存在。结果是,创造活动通过它产生或重视的有限几个对象,实际上却以完整地重新把握世界作为它努力的目标。每幅画,每本书都是对存在的整体的一种挽回。因为这是艺术的最终目的:在依照其本来面目把这个世界展示给人家看的时候挽回这个世界,但是要做得好像世界的根源便是人的自由。然而,由于作者创造的东西只有在观众眼里才能取得客观的现实性,因此这一挽回过程是通过观赏活动这一仪式——特别是通过阅读仪式——得到认可的。现在我们能够更好地回答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了:作者作出的选择是召唤其他人的自由,他们各有要求,通过这些要求在双方引起的牵连,他们就把存在的整体归还给人,并用人性去笼络世界。
我们同意康德的说法:艺术品没有目的。但这是因为艺术品本身便是一个目的。康德的公式没有说明在每幅画、每座雕像、每本书里面回荡的那个召唤。康德认为艺术品首先在事实上存在,然后它被看到。其实不然,艺术品只是当人们看清它的时候才存在,它首先是纯粹的召唤,是纯粹的存在要求。它不是一个有明显存在和不确定的目的的工具:它是作为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提出来的,它一上来就处于绝对命令级别。你完全有自由把这本书摆在桌子上不去理睬它。但是一旦你打开它,你就对它负有责任。因为自由不是在对主观性的自由运行的享用中,而是在为一项命令所要求的创造性行为中被认可的。这一绝对目的,这一超越性的然而又是为自由所同意的、被自由视作已出的命令,这便是人们称之为价值的那个东西。艺术是价值,因为它是召唤。
如果我向我的读者发出召唤,要他把我开了个头的创举很好地进行下去,那么不言而喻的是我把他看做纯粹的自由,纯粹的创造力量,不受制约的活动。我怎么也不能诉诸他的消极性,就是说我怎么也不能试图影响他,一上来就把恐惧、欲望或者愤怒等情感传达给他。当然有些作者一门心思想引起这类情感,因为这类情感是可以预见、可以控制的,也因为他们掌握了屡试不爽的手段,有把握引起这类情感。但是,同样真实的是,人们因为这一点而责备他们,如同人们从古时代起就因为欧里庇得斯让孩童登上舞台而责备他那样。在激情里面,自由是被异化的,自由一旦贸然投入局部性的业务,它就看不到自己的任务:产生一个绝对目的。于是书就成为维持仇恨或欲望的一种手段,如此而已。作者不应当去寻求打动人,否则他就与他自己发生矛盾;如果他有所要求,那么他就必须只是有待完成的任务。从这里就产生艺术品的这一纯粹性质,这一性质对艺术品来说是主要的,读者应该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
11.音乐与欣赏
我从来也不认为音乐是适合于音乐厅里演奏的。当你从电台或唱片中欣赏音乐时,应该是独自一人;或者它是由三四个朋友一起演奏。听音乐时,如果被一大群也欣赏音乐的人包围着,这是没有意义的。音乐的创作是用来被每个个体独自欣赏的。
我觉得贝多芬对我来说是最伟大的音乐家,其次是肖邦和舒曼。现代音乐中,我很喜欢三个最著名的无调音乐家:舒恩伯格、贝格和韦本;特别是贝格和韦本,例如《纪念一个天使的协奏曲》,当然还有《伏采克》。对舒恩伯格的喜欢稍为差些,因为他学究气太浓了。我喜欢的另一位音乐家是巴托克(Bartok),我是1945年在美国的纽约发现他的。我以前并不知道他。巴托克曾经是、并且仍然是我很喜欢的音乐家。
除此以外,我也很喜欢布雷兹;他并不是天才,但他有很大的才能。你可以发现我的爱好很杂。我也喜欢古典音乐:蒙台维第、格苏阿多那一时代的歌剧。我非常喜欢歌剧。
我甚至写过一部奏鸣曲。它有点像德彪西的作品,但我已记不太清楚了。我也喜欢德彪西和拉威尔的作品。
我可以发现类似米雷尔·维昂、波里斯·维昂妻子等这些人,很懂得爵士乐,因为她们自己演奏爵士乐。她们有资格谈论它,而我没有。在大战之前,我听过许多爵士乐——也是一些很好的爵士乐——但是,我确实只是遇到什么就听什么。现在,波伏瓦和我仍然听爵士乐:例如我现在非常赞赏的塞伦诺斯·蒙克(Thelonious Monk),还有查理·派克(Charlie Parker)、查理·明格斯(Charlio Mingus)……1949年我在巴黎遇到派克,他告诉我,如果有时间,他想到巴黎音乐学院来学习。如果我在电台里听到演奏爵士乐,我通常不能辨认出这是哪位音乐家演奏的,除非是派克和艾灵顿。当然,对于蒙克,你可以从最初的几个和音中把他辨认出来……但是,仅仅如此而已。然而,我认为,对音乐真正有修养的话,就应该知道从古典的到非常现代的音乐,这其中当然包括爵士乐。
坦率地说,我一点也不知道流行音乐。我偶尔听到一些流行音乐,我也不能说我不喜欢。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即每个演奏员在演奏时,并不太关心其他人在干什么。我认识一些搞流行音乐的人如巴阀克,他是米雪尔和波里斯的儿子,我觉得他有一张唱片非常好。但是,我得告诉你——你问我爵士乐,因为你自己演奏爵士乐——对我来说真正有价值的音乐是古典音乐。
很奇怪,在我的书里没论及音乐,我想这是因为我所知道的与大家没有太大的区别。当然,很久以前我曾为勒内·莱伯瓦兹的书写过一篇序,他是我认识的极少数音乐家之一。但是,在这篇序里,我谈得更多的是音乐中的意义问题,而不是音乐本身,而且这篇序显然也不是我写的最好的文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