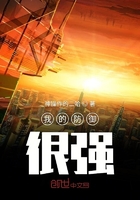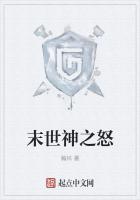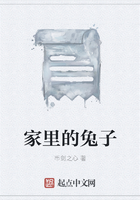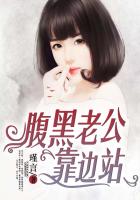第二节 海派文学因缘内涵: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如果说儒家文化在现代“运交华盖”,那同为传统的佛教在近、现代却呈复兴之势。这决定了现代作家与佛教文化的关系比较融洽,谭桂林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颇有心得:“为了把现代作家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我把它们归纳为信念型、修养型、研究型、实用型四个类别。”【17】就多数海派作家而言,修养与研究型均不适合他们,因为海派作家大体上是市民作家,他们的佛教文化心理处于民间文化层次,稍有研究心得的是施蛰存与徐讠于,但他们也谈不上有造诣。就信念型而论,海派作家也未到佛教徒或居士的境界,他们当中没有人是丰子恺或许地山,他们只是像普通的中国人一样笃信因缘等;另外,也有作家以实用的态度取佛教文化入文学,如叶灵凤等人。
海派文学的佛教文化题材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中国人的因缘心理,二是佛理与人欲的冲突,三是皈依佛门或忏情度己或弘扬佛法。下文将论述海派文学的因缘心理,并试图探讨因缘的多重意义。考虑到关涉因缘心理的文学是海派文学的重头戏之一,且因缘是佛教的一个核心范畴,故,以这类作品作为代表来阐述海派文学的佛教文化主题便不算以偏概全。至于其他,后文会有论述。
海派作家创作的佛教题材小说,当然不能脱离现代都市语境,这也是论述海派佛教文学的关键所在,忽略这一点,就看不到海派佛教文学的独特性。
一、持市民立场的因缘书写
先看一段短文。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青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地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人被亲眷拐了,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个年青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张爱玲散文《爱》只有短短的三百余字,韵味却悠长。如果拿掉最后一段,这篇短文仍然完整,而且,主题似乎更为多义。首先,这是一个人生悲剧,主角的人生起点看起来不错,后来的她却一直走厄运。她人生不幸的另一个理由是,在她的少年时期,她有过一个十分不起眼的爱情故事;事实上,要把它称为爱情故事十分勉强,但对她来说,它已经是全部。她把这一点光当作全部人生的亮点,这衬托出她人生的暗淡。其次,就女性主义者看来,它是一个女性悲剧,她是传统社会里中国女性不幸的一个缩影。张爱玲对该故事的解读不是女性主义的,她走的是中国人熟悉的一条老路:缘。在芸芸众生中,他为什么就是她要见的人?在无限的时间中,她凭什么碰巧见着他了?这一切皆有因缘。张爱玲对故事的阐释在强化主题的同时,其弊端是掩盖了故事的其他所指;不过,它所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作家的注解暴露了她对爱情、人生的真实看法,它有助于读者直指作家的本意。
循着因缘去看张的作品以至海派文学、特别是痴男怨女型小说,就能发现这一类故事有不少被作家纳入佛学因缘的范围。《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与范柳原一开始很难说有情缘、姻缘,尽管七妹宝络的相亲使得他们有了相识、相知的机会。离婚回到娘家的白流苏很难在白公馆立足,她得抓住青春的尾巴把自己嫁掉,范柳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后者仅满足于玩,这又是白流苏所不希望的。他们在香港玩“太极推手”,结局却是他们结婚了,原因很简单:“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在小说的结尾,张爱玲再一次落入自己的圈套:“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将凡俗叙事与因缘结合在一起常常是张爱玲的拿手好戏,这一点,台湾学者林柏燕认识到了,但他的原文无法看到,陈炳良在《有关张爱玲论著知见目录》中略有介绍。林基本上对张爱玲持否定态度,陈在文章里概述:“他指出张氏的男女世界只有丑恶,同时‘时代感’显得薄弱。他认为(1)她的题材意识往往不脱‘醒世姻缘’的窠臼,(2)……”【18】“他”指的是林柏燕,这里所说的题材可能是主题,也有可能是指张小说的题材跟《醒世因缘》多有类似。无论是哪一种意思,显然,林意识到张爱玲在处理男女爱情、婚姻题材时常常有一种倾向,即把发生的事实归之于因缘。不过,林的批评显然褊狭,因为他的落脚点是“时代感”、“大题材”,毫无疑问,他站在“宏大叙事”的立场上来看张爱玲,这难免会忽视张爱玲的民间性、日常性,更何况她小说中的因缘含义已超越古代小说因缘书写的佛教范围,具有时代特性。除张爱玲,其他作家如施蛰存在《黄心大师》、《塔的灵应》、徐讠于在《花神》、《痴心井》、《鸟语》等中也以因缘来演绎故事,在小说里,因缘是人物命运转向的内在因素。其实,最喜欢以因缘来敷衍故事的是旧海派小说,这些消闲文学主要为满足市民消费而生产,所以,以普通中国人所信奉的宿命论——因缘来阐释人生际遇很能迎合市民的文化心理。新海派基本上延续旧海派为市民的文学理念,其佛教题材小说是高度市民化的文学。这决定了海派文学因缘内涵的传统性,因为一方面,虽然现代社会急剧变化,但沉积在底层的文化有较强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社会新思潮不可避免地渗透到都市日常生活的各角落,把握时代信息的文学因缘因而又有一定的现代意义。
因此,海派作家的因缘心理小说与其他作家的同类小说有所区别。一是笃信佛学的作家,他们对因缘的理解往往有较为高深的佛教含义,如丰子恺的散文,许地山、废名等人的小说有着浓厚的佛教文化色彩。与他们的作品相比,海派文学主要阐发一种普泛的、散布于民间的因缘心理。再就是,以启蒙姿态出现的新文学家往往在因缘书写中否定因缘,如鲁迅在小说《长明灯》中将佛教包括因缘在内的迷信思想当作中国的传统大加挞伐。鲁迅对佛教文化的态度在新文学家中有代表性,有学者说:“鲁迅不仅以佛教思想中一些有益的东西为武器,用来批判封建儒家文化,也不仅试图通过运用佛教净化人的道德的方法、方式,来为完成改造国民性的任务服务;在鲁迅那儿,更具意义的是,他还从佛教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精神养料,这种汲取对鲁迅的人格形成是很重要的。”【19】许多作家可能不及鲁迅深远,但现代精神是一种过滤器,能为作家所用的佛学思想,作家以它来塑造自己、国民;在无名氏、周作人看来,佛学还可以用来建构中国现代新文化体系。反之,如果佛学思想不吻合现代精神,作家就对它予以嘲讽、批判,宿命的因缘观当在他们的否定之列。反观海派作家,他们并没有因为因缘的反科学性就颠覆因缘,作为市民作家,他们在文化启蒙的自觉方面有所欠缺。
在对待佛教文化方面,海派作家中也有态度不够明朗的,如施蛰存。他是一个注重文化反思的作家,在创作上,他对佛教的介入并非单纯的民间立场,换言之,他是一个有着文化精英意识的海派作家。有人以为施蛰存的佛教题材小说“揭穿佛教文化中的某些神秘性”【20】,譬如他在分析《塔的灵应》时,就认为塔的灵验源于一系列事实的巧合,它们戳穿了佛教因缘观的神秘面纱,因缘遭到质疑、调侃。但施蛰存并没有完全站在现代立场上,即便在《塔的灵应》中,小说也有不少的以科学来解释却不能令人信服的碰巧。为什么两个小孩碰巧就在池水沸腾时来到塔边捉促织,而这两只促织又碰巧钻入塔基下?为什么基石碰巧就被他们搬开了?少年男女为什么就碰巧在塔里面?这些碰巧可能都是天意。这么说来,小说存在有两种倾向:科学在解构因缘心理,而佛教文化又遮蔽了科学的光芒。再如,《黄心大师》是一个较为通俗、有一定传奇性的小说,但他又在探讨佛教文化,它似乎是一个专门研究佛教文化的小说。以上分析能说明,施蛰存对因缘的关注虽然有一定的启蒙意识、精英化倾向,但他的小说仍未脱离海派市民文学的范围。
二、海派文学因缘心理溯源
海派作家之所以重缘,在于他们成长在中国文化圈内,而中华民族是一个讲究缘分的民族。台湾有学者指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缘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在世俗传说中,缘是各种人际关系的最方便的解释。……传统中国人这种将各种人际关系都解释成缘的态度,可以称为‘泛缘主义’。”【21】显然,这个传统延伸到了现代与当今,换言之,自古及今,中国人的内心藏着一个“缘”字。它是中国人阐释人际关系的基础,如丰子恺在《大账簿》中说:“我仿佛看见一册大账簿,簿中记载着宇宙世界上的一切物类事变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因果果。自原子之细以至天体之巨,自微生虫的行动以至混沌的大劫,无不详细记载其来由、经过与结果,没有万一的遗漏。”【22】代代相传的“因缘”思想类似于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不过,他认为集体无意识“是指遗传形成的某种心理气质”【23】,因缘不能归属到遗传的范围,中国人是在后天环境里不断地被熏染才接受这一理论的,因此,“缘”的心理是一种“集体意识”。但是,它有时似乎处于无意识状态,不受意识的控制,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脱口而出:“缘分!”这里不打算对“缘”究竟是意识或无意识做过多纠缠,但因缘对中国文学的作用确实与荣格集体无意识的功能相似,他认为集体无意识可以外化为作品或者说有时候创作过程是集体无意识活跃的过程,中国人普遍信仰的“缘”,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也有这种功效。余斌在《张爱玲传》里提到,《爱》的故事是胡兰成讲给张爱玲听的,如果这是真的,那她就有双重身份:读者与作者;从她听故事到构思再到表述,“缘”极有可能处于中心地位,至少在构思和表述阶段就是如此。由此可见,民族心理对她创作的制约非常明显,“缘”的意识在《爱》的创作中处于积极状态。
中国人的因缘心理跟佛教有关。“缘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一种命定或前定的人际关系。”【24】所谓命定也就是天定,古代中国人信仰“天道”。天定如何演变为缘的?显然,这是佛教传入中国才有的结果。因缘是佛教的一个核心教义,“佛法的最大特色,便是缘起或缘生之说的开创”【25】。它强调“缘法”,即世间万物是相互转化的,有因即有果,如佛祖言“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26】。这种因缘观跟中国人的“天道”观有很大差异,天道观强调一切天定,而因缘果报论则认为人的善或恶行会影响乃至决定他的未来。大约是佛教为了在中国求得生存、发展的缘故,具体在什么时候已很难确定,天命论被佛教接受,成为佛学的因缘观之一点;换一句话说,中国人所说的缘分常常就是人看不见的“天”力所为。所谓前定,可能也包含命定,但范围更为宽广。譬如因缘果报,人做善、恶事,一定会有报应,神明是裁判并最终来确定赏罚。因果报应在佛教有三种方式:前生业,今世报;现世报;三生业报,总之,人的所作所为都会在后来有回应。古代中国人有很强烈的三界观念,因缘果报不仅局限在人世间,如《红楼梦》所载,林黛玉本是一棵绛株仙草,她感激神瑛侍子之恩德,来到人间以一生的眼泪来报答贾宝玉。由上文所论可知,中国人的因缘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当时外来佛教相融合的产物;从哲学角度看,因缘说是一种宿命论,尽管它不忽视人为,但天或神明还是处于核心地位。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可能是因缘说的一个通俗而又经典的注解,人为可能是因,但起决定作用的因是天、佛,在它们的掌控下才有人世间的果。
肇始于佛教的因缘说成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它是佛教徒以及相关文人不懈宣传才有的结果。以文学宣扬佛学始于六朝,有人说:“六朝以来,志怪小说中一部分‘释氏辅教之书’,专门宣传佛教徒因果报应的说教,竭力宣传佛教经典、佛像的神奇作用。”【27】到了唐代,涉及佛学因缘说的小说已经不少,如唐前期的小说集《冥报记》、《纪闻》中有很多宣扬佛法、昭示因缘果报的故事。在宋、元时期,除文人小说外,话本中有专门“说经”的“小说”,对此,有学者说:“它是通过敷衍佛教经典以及与此相关人物的故事,使之形象化、文学化,以达到弘扬、宣传佛理的目的。”【28】这一类小说对佛学大众化、通俗化的作用是巨大的。说书与其他方式一起促使佛学在古代中国人的内心沉淀下来,从而使佛教因缘观念成为中华民族一种稳定的心理结构。
明、清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同时,佛学思想也随处可见。不过,与佛学思想有关的小说创作显然已不再将宣传作为主要功能,因为佛教文化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小说里因缘的彰显大抵出于佛教文化心理。除《西游记》外,《红楼梦》有着浓厚的佛教意味,贾宝玉跟薛宝钗、林黛玉之间的金玉良缘、木石前盟是小说的中心;有的小说还直接取名为“某某缘”,如《醒世姻缘传》、《再生缘》、《镜花缘》等。从以上一系列小说能看出,中国人的因缘心理制约着明清小说的创作走向;这一股势头延续到现代,因缘对海派的小说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海派文学的因缘写作还得益于文学自身的传承。旧海派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余波。在古代,小说不是文学的正宗,小说是游戏、是消遣,旧海派的不少小说家也是本着这个目的写小说的。至于新海派的小说观念,恐怕也未脱旧海派的窠臼。有的作家如张爱玲是一位与旧海派有着密切关系的作家:第一,她多次在文章里谈到这一派小说,甚至不讳言自己偏爱张恨水的小说;第二,她的进入文坛跟周瘦鹃有关,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就发表在他主编的杂志《紫罗兰》上,从此,张爱玲横空出世;第三,她还把近代小说《海上花》由吴方言翻译为国语。张爱玲还喜欢明清小说,在《天才梦》里,她说《西游记》是她小时候的课外读物;在《论写作》中,她提到第一次看《红楼梦》时她才八岁;另外,她多次在散文里提及如《醒世姻缘传》等明清期间的长篇小说。总之,与明清小说、旧海派文学有联系紧密的新海派,肯定能感受到明清以及旧海派小说中因缘的普遍性存在,这对他们的创作在无形或有形中能起到一定作用。
显然,海派作家与佛学因缘观的结缘途径,并非单一。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里有学者提及,佛学精神渗入到现代文学有四种途径:家学与生活环境的熏染,近代维新派大师的直接师承,古典文学情趣的浸润,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所论可谓较为全面,但是,要是将海派小说也加以考察,就会发现,海派文学的佛学思想之来源是该专著所论无法容纳的。首先,近代维新派大师的直接师承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影响要去除,海派作家跟维新派大师没有多大联系,至于日本传统文化,他们所知可能不多,对欧美文化他们倒是接触比较多。再看古典文学情趣,他所言的古典文学偏重晚明性灵派文学,但是,就现在所知,许多海派作家对晚明小品并没有浓厚兴趣。最后看家学与局部环境的影响,海派作家直接面对的是佛学的复兴,这种情形肯定对海派文学产生影响。但海派文学与佛学之渊源还有其他,这已在上文有比较透彻的论述,在现实生活中,因缘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从文学的发展看,与因缘发生关系的明清小说是一个源头,这两股力量作用于施蛰存、张爱玲等海派作家,从而使因缘在现代文学中续写过去的辉煌。
三、新旧杂陈的因缘书写
如上文所论,中国人的因缘观是一种宿命论,与佛教密切相关,它强调人世间的一切是天定或神明确定,如《醒世姻缘传》里的三世恶姻缘、《红楼梦》里的金玉良缘,在鸳鸯蝴蝶派小说如《唐祝文周四杰传》里,天赐姻缘是一条人际关系准则。但是,由于西学东渐,科学思想在中国广为流传,这也就意味着因缘的宿命色彩、佛教内涵不再是铁板一块,故而在现代小说里,因缘的文化意义是多种多样的。张爱玲小说《怨女》里的银娣,对自己的婚姻很不满意,对丈夫的弟弟倒是有情,而对方也有意玩弄她。有一次,她在寺庙的佛像前,他来了,于是,他们在佛面前调情,她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因为今天在佛爷跟前,我晓得今生没缘,结个来世的缘吧。”银娣所说的“缘”是本义,符合“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逻辑。又如,徐讠于《花神》里的阿福也相信缘法,以为他的命运转变皆有因缘。在《倾城之恋》中,作为作家的张爱玲没有将自己隐藏在幕后,尤其在对白流苏跟范柳原姻缘的评价上,她直接跳出来,对它指手画脚。到底是谁要成全白流苏、从而发动战争?是天意,还是不可理喻的世界?胡寄尘《抄袭的爱情》是一个很有趣的短篇小说,命运中好像有一股引力把爱情男女牵引在一起;缘可能是命,当然,缘也有可能是一种并不具有宗教意义的碰巧。在这两处,天意只是一种可能,可见,在他们对因缘的界定中,宿命的成分在减少。小说《半生缘》从《十八春》改写过来,根据张爱玲的好朋友宋淇说:“《半生缘》这书名是爱玲考虑了许久才决定采用的。……《半生缘》俗气得多,可是容易为读者所接受。”【29】这一段话里说她拟了不少书名,最终确定用“半生缘”,它尽管俗,但中国读者喜欢,其实,张爱玲也应该喜欢。在《半生缘》中,因缘既不是宿命的,也不是半宿命的,佛教意义上的因缘几乎只剩下一个外壳,它里面装的是新东西。譬如在世钧跟曼桢之间,缘分就在于他们都对对方一见倾心,这是一种难以说清的契合状态,这就叫有缘。由于世钧在第一次看见曼桢时就喜欢她,所以,他用心接近她;而她不但不躲避,而且还靠上去,因此,他们的缘分从实质上讲就是一种好感,也正是这种奇妙的心理而非天力促使他们互相吸引;但如果不细究,缘分似乎还是佛所赐,其实,它基本跟佛无关。《塔的灵应》讲述了一个显灵的故事,如果放生池中的水沸腾,佛塔必定倒塌,显然,这二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真有因果,那也是另有因缘。行脚僧因怀恨往池中倒生石灰,池水沸腾,两小孩抓促织搬掉部分塔基从而导致塔坍塌,所以,所谓因缘,似乎只不过是人为。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这两件事恰巧同时进行?难道真有因缘在作怪?以施蛰存的学养、对佛教的态度,他应该另有用意。单就因缘而言,一方面,小说剖析了佛教所谓的因缘是怎么来的;另一方面,从行文语气看,小说在肯定必然性的因果关系的同时,并不排除世界上还有并无必然性的联系,它们看似神秘,其实纯粹是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的巧合。因此,施蛰存的独特性在于,他以科学理性完成对因缘的反动,其精神是启蒙的。
从上文所论能看出,因缘的文化内涵在不同的小说里各异,因缘的多义性表明海派作家感受到传统的心理结构在西学的冲击下已经有所松动,即宗教的神秘性受到科学的压挤;而在施蛰存那里,文化心理则产生突变。这里所说施的心理有巨大的变化,并不是说他反佛教文化,而是说他能够站在现代的立场上审视佛教,从而使宿命的因缘心理产生逆变。尽管张爱玲对五四的启蒙理想颇有微词,这可能源于作为时代女性的母亲让她失望,所以,她对五四知识分子的精英化并无认同感;但就她所受的教育、所处的时代而言,她不可能不持有科学观念,这是她部分地消解因缘神秘性甚至将它拉下神坛的根本原因。因此,海派文学的因缘内涵已具有时代特色,它切实地传递民族文化心理变化的信息,体现时代精神向文学的渗透;而因缘原有的文化意义则在不同程度上遭到消解,其神秘面纱被撕开。
毫无疑问,海派作家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了因缘的神秘性,所以,对因缘的书写往往会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的文化意韵。在他们的小说中,作家往往专注于世俗书写而很少进入宗教层面,小说展示的是一种脱胎于宗教而又少有宗教意味的因缘观。因缘叙事的变化在明清有过一次。此前,文学关涉因缘大体上是宣传,所以,说经故事就是世俗化经书;事关因缘的明清小说走出怪圈,获得文学独立的品格,佛学因缘说是民族心理,是作家看人生、世界的哲学,因此,在多数作品,因缘往往成为一条暗线,但它的文化含义没有改变。在《花神》、《倾城之恋》、《鸟语》小说,还有旧海派不少作品如《啼笑因缘》、《脚之爱情》等在内,世俗化叙事得以进一步加强,因缘的宗教色彩进一步被淡化。在《茉莉香片》中,言家与冯家是远亲,前者是生意人家,后者为累代贵族,言子夜在给冯家几个女孩补课时跟冯碧落一见倾心。这大约类似《半生缘》里世钧与曼桢之间的心电感应,由于难以解释,中国人往往将它归结为因缘,以为是看不见的命运之手在操控的缘故。张爱玲也将它视为因缘,在言家提亲遭到拒绝后,小说有这么一句话:“那绝对不能够是偶然的机缘,因为既已经提过亲,双方都要避嫌了。”但是,这一对男女没有切断联系。有学者说:“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缘可以分为两类:缘分与机缘。前者是一种长期之缘,后者是一种短暂之缘。”【30】这两种缘都是因缘,在小说中,言子夜与冯碧落有长期之缘。可是,他们有情缘而无姻缘,冯家以言家不是诗书礼乐之家为由笑拒,而言子夜、冯碧落则在暗中缠绵。碧落求子夜托人到父母面前疏通,但子夜年轻气盛,不肯屈尊;子夜出国留学,希望碧落一同出走,可碧落没有勇气;此恨绵绵,碧落与他人婚后早逝,言教授活得似乎也难尽如人意。从有情缘到无姻缘再到情思不尽,《茉莉香片》中不见明清小说的“如来佛”之手,取而代之的是巧合、是人事,这是一种地道的尘世书写。如果说《茉莉香片》叙述了一个良缘未成的故事,那么,在《金锁记》基础上改写的《怨女》则讲述一个孽缘竟成的故事。《怨女》之所以事关孽缘,在于银娣与二公子的婚姻完全是一次人钱交易,后来的事实也说明这完全是一场恶姻缘。她的姻缘始于功利,又在****与利欲的逼压之下,这使得她与丈夫的结合成为一次冤家聚首。叙述中对因缘宗教性的规避使得男女故事有了现代内核,支撑其小说的不只有现代乱世背景、都市日常生活,一种既旧又新的生活逻辑往往起重要作用,这也是张爱玲等人的小说有别于明清小说的关键所在之一。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因缘叙述并未脱尽佛教意味,如银娣在佛面前的表白。事实上,如果完全剔除佛学底蕴,那因缘就没有存在的支柱,那它可能就是反因缘了。
海派文学的因缘书写能折射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换言之,现代性是介入现代小说因缘书写的潜隐力量。有人在《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一文里,从“意象化空间:场所与地域”、“新传奇”两个方面论述她创作的现代意义,如在前一个方面,作者说:“张爱玲就这样,在对‘内室’、公寓和街道等意味不同的场所的描述中,意象化地呈现出一个参差不均地分布着‘传统’与‘现代’各种因素的地域空间——‘半新旧’的社会生活的一个景观。”【31】因缘含义就像上海的空间,也处于新旧杂陈的状态;从叙事来看,在对因缘的操作中她尽量从人事方面进入,逐渐摆脱佛教的无边法力;最能体现现代性一面的是,张爱玲对社会上人的负面“缘起”有所批判,其中,最为她所不满的是门当户对的婚姻观。读《茉莉香片》,笔者首先把聂介臣看做张爱玲的父亲,聂传庆是她的弟弟,《茉莉香片》跟她幼年时代不幸的家庭生活应该有着密切联系。不只言子夜与冯碧落是门第观念的受害者,聂传庆才是最大受害者,碧落嫁到聂家是清醒的牺牲,而聂传庆呢?“屏风上又添上一只鸟,打死他也不能飞下屏风去。他跟着他父亲二十年,已经给制造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残废,即使给了他自由,他也跑不了。”这是张爱玲为弟弟写得最好一段文字,当然也包括像弟弟一样的牺牲品。另外,在她的许多小说里,人物一律是不挣扎的,而且,她对他们的人生态度不置可否。由于《茉莉香片》带有传记性质,这可能触动了作家的伤痛,因此,她对聂传庆的同情十分真切,对子夜的负气与碧落的顺从在理解的基础上给予一定程度的批判。以上所说的人力是姻缘有无的关键因素之一,建立在聂传庆人生悲剧基础上的、对人的因素所做的批判加强了因缘的现实意义,这是她对五四人的解放的继承,当然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延续。其他如施蛰存《塔的灵应》里的科学精神、徐讠于《鸟语》中的人文精神无不体现出海派文学对现代文学传统的传承。由此能看出,在海派文学中,作为一个古老的词汇,一方面,因缘仍在释放它本来的能量;另一方面,它又焕发出一种新的活力,展现出与时代同步的一面。
上文比较多地论述因缘的现代一面,其实,将传统引入现代,这也是传统文化心理所导致。现代社会的现代生活,或许有它的内在逻辑,但小说仍以因缘来解释世事变幻,如《倾城之恋》里的战争是一个重要因素,可小说对战争的认识停留在宿命层面上,又如《塔的灵应》像似在传达“纯属巧合”,可过多的巧合串联在一起似乎又关涉因缘。总之,现代生活乃至科学思维都掺杂有因缘成分,这反映出作为中国人深层心理的因缘仍在主导作家对生活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