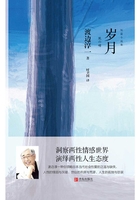我又把刘沙的事情说了。我说:“现在都变成组织交代的任务了。”他说:“去年我也碰到过一件这样的事,是个文艺生,是从艺术专业考进来,再转过来的。也是金书记打了招呼。她还考得不那么差,五十二分,我想想她不能跟别人去争保研的资格,也不能去争奖学金,就把她放过去了,六十分。”我说:“她真能搞文艺吗?真能搞文艺那也就算了,还可以在表演上为学校做点贡献,也勉强算个说法。像刘沙这样的,他能打排球?”他说:“我们学校的体育学院、艺术学院就是两条下水道,多少乱七八糟的人都以术科的成绩考进来,然后转院到这边来了。高考分数线可以降一两百分呢。你说一般的人能搞到这样的机会?后面有两个字在操纵着,一个‘钱’字,一个‘权’字。”
我叹一声说:“太恐怖了。你说那个刘沙吧,他爸爸要把他的名字塞进那支得了冠军亚军的排球队去,那容易啊?考术科要排球老师点头通过,那容易啊?当然,说不容易是对平头老百姓不容易,有钱有权的人还是容易的,真的像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他爸爸是关云长,他要过那几关还不容易?现在中国只有一个高考公平一点,是穷孩子翻身的唯一机会,还被权贵撕出这么大一个裂口来了。”他说:“前任舒校长的儿子早几年也是这么进来的呢,从体育学院录了,马上转到商学院。说起来吧,学校的自主招生可以把录取分数线降到一本线,那也比别人低了三四十分吧。可这个不读书的儿子降了这几十分还不够,只能走体育学院这个渠道。他的儿子其实是个体育盲,怎么能通过术科考试?那一年就增加了一个新的科目:南拳。”陶教授握拳做出拳击的动作:“南拳。一个科目至少有七个人报才行,就来了七个人报,那六个都是来陪考的。南拳科目设了那一年,第二年就取消了。一个考试科目就是为他一个人设的,还下了文件的呢。”
陶教授长叹一口气,说:“舒校长他还是全国著名的教育学专家呢,道理一串一串糖葫芦似的呢,到了事情面前就作废了。”我说:“有这事吗?”他说:“那我编个故事哄你?”又说:“我还听说,有家长为了儿子能以体育特长生降分录取,转了七个弯找关系,花了二十多万,搞定了。这是考学生还是考家长呢?”我说:“真有这些事吧,肯定是不好,可也能理解。一个人如果不能确定自己碰到了同样的情况能够淡定,他最好不要抱怨,要怨也只能怨自己没有那个能力。他当校长他儿子连个大学都不读?或者要他不讲那些伟大的理论?都不行。道理不讲铁定是不行的,事情不做也铁定是不行的。这是世界上最公开的秘密。”他说:“唉,现在太多的人都用价值理性来说,用工具理性来做。前年他儿子毕业,学校临时定一条,去下面支教一年可以保研,不受成绩局限,现在都在商学院读研呢。我看他将来要读博的,还可能当校领导。以后就是他们接班了。”
我用筷子敲一敲菜碟,说:“吃啊,怎么不吃了!”他说:“想一想,饭都吃不下了。看来关系网的局面就这么形成了,铜墙铁壁。天下算定了是他们的,我们的儿女怎么办呢?聪明点可能努力拼杀还有条缝钻上去,也可能缝都没得给你钻,铜墙铁壁。”又说:“那两个学院都这样操作十几年了,把我们麓城师大的名声都搞臭了。新上来的卢校长想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阻力很大呢。不要说那两个学院,校领导都有人反对,说是要为改善办学环境留下空间。这空间留给谁了?老百姓?”我说:“那么长一条利益链,是谁想剪断就能剪断的吗?可以推想改革是件多么艰难的事。”
陶教授端起碗说:“那我还是吃吧。”又说:“说起高考被撕出裂口,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裂口,就是重点大学的自主招生。去年一个大学同学请我吃饭,我说十几年没联系,怎么突然就请我吃饭?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没事。我就去了。去了看到他带了一个朋友来了,那人儿子报了我校的自主招生,问我面试老师有熟人没有。我只好说去问一问。其实我没有问,后来知道我们学院是刘教授去的。那小子后来过关了,同学提了烟酒来送给我,还要给我一个购物卡,说是他朋友的心意。烟酒我推不掉只好收了,购物卡坚决不要。”我说:“那小子后来招到哪个学院?”他说:“法学院。”我说:“自主招生说是要给有特长的学生一个机会,这些机会最后都被谁拿走了?有几个农家子弟?要我说,高考只能裸分录取。委屈了一个两个钱钟书不要紧,委屈了千千万万百姓子弟就不行。”他说:“有人还在呼吁取消高考,历数了十几条不是,说这根指挥棒罪恶滔天。如果哪天把这个裂口又撕开了,那才是真正的罪恶滔天!到那天不要说普通老百姓,我们普通教师的子弟都岌岌乎殆哉!”
他招呼我吃菜,说:“我们的儿女,是学霸就杀出一条血路,不是那就待在社会下层,就这两条路。你还好,儿子还在老婆肚子里。”笑一笑:“也可能还潜伏在你自己身上的某个阴暗角落,这件事还远。我儿子过两年就要读中学了,压力一年年上来了。我羡慕你呢。”我说:“我羡慕你呢,现在社会上的缝还有那么多,拼了命还可以钻进去,到我儿子那一天,那就真的是铜墙铁壁,无缝可钻了。”又说:“有时候我也不怪学生不诚信,考试搞点小动作。说到底他只是个小动作,抓到了是要开除学籍的,真的不忍心抓他。搞大动作的人,从来就是毫发无损。”陶教授默默地吃饭,不再说话。我不知道他是为这种局面担心呢,还是为自己儿子的前途担心。于是也默默吃饭,不再说话。
两个星期以后考试结束了。刘沙卷面成绩是四十三分,按百分之七十算是三十分。看来金书记的担忧不是凭空而来的,他真的非常了解这个学生。平时成绩三十分,他交了两次作业,都是九分。我相信这不是他自己的成绩,也只好算了。第三次是顾莉帮他做的,零分。这样他的总成绩是四十八分。我到金书记办公室把这个结果告诉了他,金书记说:“就差那么一点,提上去算了。”我说:“上了五十我就提上去了,这叫我怎么提?要不我把成绩单交到教务办,要教务办的人去改。”他说:“那怎么行?这是任课教师的权力。”我说:“我们有什么权力?这些人是谁搞进来的?说他会搞运动,为学校的比赛做了贡献,那也是一个说法。除了运动关系,他还能运动什么?要是他家里给学校捐了几十万,那也是一个说法,捐了吗?可能捐了,但不知捐到谁那里去了。”
金书记连忙挥手说:“这些话没有扎实的证据就不要随口说啊!”我说:“那就说成绩,碰见这样的学生,还要放他过去,想死的心都有了。”他笑了说:“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有这种心情?我也是没有办法呢,上面有人打了招呼呢。”我说:“上面是个什么人啊!要不这样好不好,让他先挂着,下期补考,我交代他暑假认真看书,补考我一定让他过。这样的学生,不能让他太舒服了,他那么舒服,我们当老师的就太……”我想说“太没尊严”,又不想刺激金书记,就说:“就太……太不舒服了。”金书记说:“小聂,你这么认真,我觉得很好,很欣赏,我觉得一个人就应该认真。可是,上面交给我的任务,我也得认真完成吧?能不能体谅一下我的难处?你看呢?”我再也说不下去,于是说:“书记是领导,我就不看了,书记怎么看那就怎么看。反正他也不能跟别的同学去争奖学金和保研名额,反正他终归还是要毕业的。”他说:“毕不了业,烫手山芋砸在手心,不好受呢,你们当老师的又感觉不到烫。帮我了个难吧!”又说:“只能给他六十,不能多给,多给了连我都不会同意的。这样的化生子,已经太便宜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