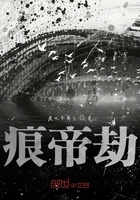下雨了。三关道上,泥浆横流。大水从山坡上冲涮而下,沟底就成了洪流肆虐的世界,声大如雷。
一踏上石门关口,常谷丰就被洪水的声音震撼得浑身发抖。他站到道边的岩石上,把手电光打向沟底,看到了水面上那些令人心悸的漂浮物:椽木,家什,还有黑乎乎一跳一跳的人头。这使他觉得自己夜走石门关肯定是做对了。
大水四五年来一次,可人们如果不是为了有意向洪水叩求解脱,你甚至连一根草枝也看不到。分明是有人把洪水看成了告别人世的借口。这是一种推卸--谁先做鬼,谁就少了一些为先去的人坠泪、掩埋的责任。
常谷丰磕磕碰碰地顺路前行,临近三更时,敲开了庄子里唯一一家渗出微弱灯光的门。
开门的石担盯着来人空空的两手说:粮食呢?杜金原没给?他说着,身子一晃,咚的一声靠到门扇上。
常谷丰说粮食?粮食就会有了。
石担一愣:是常书记?我还当是豫蓝回来了。
常谷丰思谋了一会,才反应过来,随即骂道:都到这种时候了,杜金原还有兴头搞女人,这不是趁火打劫么?去,把你媳妇领回来,粮食,我给。日奶奶我豁出去了,明儿夜里,十二点,你来公社,腰里揣个口袋。
常谷丰匆匆离去,又贼一样敲开了几家的门,贴着耳朵告诉人家:日奶奶,我豁出去了,我要造反了,明儿夜里……
领受到机密的都是他认为真正到了绝路上的人家,最后自然要叮嘱:不要外传,传出去就没你的了。他担心去的人多了,粮食不够分不说,还会虚造起声势来。
这天夜里,常谷丰离了石门走土门,天放亮前,又出现在铁门关。
雨住了。低伏的云翳渐渐升高。石门关几天来弥漫着的阴郁似乎就要消失了。雨后的凉爽使这些在鬼门关前踱步的人们清醒了些。
豫蓝直到天亮才回到家中,一晚上耻辱的代价已由半斤粮减为二两,但这仍然使她兴奋得几乎撞倒自己的男人。她告诉他,因为她的曲意逢迎,杜金原很高兴,已经发话了,今儿、明儿、后儿晚上他还要她,也就是说,至少还有三天,她和石担将比别人活得有信心。
她似乎已经不再担忧自己人格的降低了,甚至也不再害羞,她的同情心很大一部分也被驱逐出了心室--那些受她排挤的女人和她们的亲人将如何度日,是死是活,她已经无法顾及。屙屎的不为拾粪的操心,花朵儿不为蜜蜂着急,这也是天经地义的。
石担神情漠然地扭过脸去。她明白他的意思,赶紧跑向锅台,生火做饭。饭熟了,两个人相对无言,哗啦啦把麦粒儿汤朝肚子里灌去。
灌完了,他喘着气说: 以后你不要再去了。
她一惊:你怎么又说这种话?
他说我这话不对么?你好像很想去似的,你给我过来。
她不动。
他说你以为我饿得没力气了,不是男人了?
石担过去,抱住她,突然觉得她依旧是自己的--一个可以让别人随意践踏的自己的女人。他又说:
豫蓝,我是说我去搞粮食,哪怕偷,哪怕抢,我不能让你养活我,我是个男人。
她气得胀红了脸:你又想什么歪门邪道了,不能,你不能去偷,抓住会打死的。
他冷笑一声说:打死了好啊,你就可以嫁个有粮人,就不用受罪了。
豫蓝在他怀里哽咽起来。她感到委屈,如果不是为了丈夫,她也许早就不甘凌辱、饮恨九泉了。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用情专一的良家妇女,她最怕的就是丈夫嫌弃,而不管她的受辱是丈夫弱小的结果,是迫于生计的无奈。她对石担常常怀着一种深沉的歉疚,小心翼翼而又毫无根据地提防着他的厌恶。只是没想到,嫌弃和厌恶早已发生了。
石担拉她坐到炕沿上,生硬地说:脱鞋。
她脱了,又要解扣子。
他拨开她的手说:我来。
她揩着眼泪,朝他微微挺起胸脯。
他说我要不是你男人呢?
这问题太奇怪,她以为是他想逗她转悲为喜呢,就勉强笑笑说:我就掰断你的手指头。
好,你掰。他伸出手去。
她不动,依然别别扭扭地笑着。
石担说我的意思是我假装强奸你,你反抗。
她说我不。
他说我们试验一下,以后你对杜金原也这样。
豫蓝不吭声了。
石担又说:听我的,你把我当成杜金原。
她摇头。而当丈夫动手动脚时,她却忍着眼泪,死命地挣扎起来。她的确想试一下,可她毕竟是个孱弱的饿过肚子的女人,尽管躲上躲下,挡来挡去,弄了个满头大汗,衣服裤子还是被石担扒掉了。她喘着气,赤条条地仰躺在炕上,没有了一丝力气。
石担不满意地说:你怎么让我脱掉了?
豫蓝说你是男人,你力气比我大。
杜金原也是男人,是男人就能把你脱掉?他吼道,反抗啊,再反抗啊。
豫蓝咬住嘴唇,扭过脸去,泪水漫溢而出。
啪的一声,她的光身子上重重挨了丈夫一巴掌。
你呀你,石担叫起来,你就是这样一个货色,怪不得杜金原死粘着你不放。
我……我没力气了。她唏嘘着,发现丈夫陌生了,一瞬间什么都变得虚无了,跟过去不一样了,连死着还是活着都不知道了。
她哭了很长时间。
石担冷坐着,慢慢地就后悔了:干什么呀,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难道别人强加给他们的灾难还不够烦恼么?
别哭了,豫蓝别哭了。他把她搂在怀里,又是舔他的眼泪,又是揉她的胸脯,那种让她似曾相识的怜爱重又出现了。
她把头埋进他怀里,听那心跳的声音,竟又成了世间最美妙的音乐,闻那熟悉的汗味儿,仿佛也是世间最香最甜的。依旧是自己最可信赖的男人,依旧是她的世界她的肉。肉贴肉,心贴心,她在泪水中感受着幸福和甜蜜,又一次陶醉了。
干脆,不吃不喝,不散不离,就这样躺着,一天,一年,躺到永远,死去,死去。这样的死是美好的,理想的,色彩斑斓的。但等她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时,丈夫却推开了她。
石担说他想把今夜去公社领粮的事告诉尕秀阿爷,再让阿爷把杜光宗拽上。石门关的人能多活一个算一个,日后也少些寂寞,也可以互相帮衬着再度难关。
他一走,豫蓝就又开始伤感了,眼泪喷涌而出,大起大落的抽搐搞得她腰都疼了。
这时马灵验来了。她听到了哭声,以为死了人,一头闯进来,就想把整筐整箩的祝福倾倒给这个哭断了腰的人。而对豫蓝来说,马灵验的出现,是一个非常适合诉说衷肠的机会,她把什么都说了,包括石担的去向--公社要分粮了,石担去通知尕秀阿爷了。
马灵验万分惊愕,忘了所有的吉利话,抬起屁股紧紧张张地走了。她来到村道上,见人就问:
知道不知道?今晚上公社要分粮了。
都说不知道。
而那些知道的却一律地守口如瓶,他们不敢说话,不敢出门,惟恐自己说漏了嘴,惟恐别人从自己脸上觅到受宠若惊的秘密,甚至也不去亲友家串通,做媳妇的忘了自己的娘家,倒插门的忘了自己的亲阿大,另了家的忘了自己还有一个一奶喂大的兄弟。更加残酷的是他们浑然不觉,还以为常谷丰对自己的关照,能够证明他们比别人更加可怜,而可怜又是带来殊荣的前提,于是就留恋着可怜,也希望自己永远可怜。
沟底的山水还在咆哮,但对他们已经不是死亡的召唤了。
马灵验不知道这些人的想法,她只知道见人就问:
今晚上公社要分粮了,知道不知道?
都说不知道。但紧接着就都知道了。
马灵验挨家挨户走遍了石门关,之后循着常谷丰昨夜的路线,径奔土门关,天擦黑时,又蹒跚在去铁门关的路上。于是,就在午夜将临时,三关地方的所有人家都知道今夜常谷丰要大显神通了。马灵验见人就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果然就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我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代表常谷丰来向你们传达胜利消息……
悄无声息的萤火虫在荒野里闪烁。大山的黑影突然升高,赫然逼到惨白的月亮上去了。群星远逝,灯光泯灭,一切来自近处和远方的监视都被大夜遮去了。人群和欲望在寂静中涌进--从三关道上,从死的藩篱中涌向公社,涌向黯夜中几乎要放声大哭的常谷丰。
石门关后庄的马明善死了,他是从家里一直爬到干滩的,可他没有爬到跟前,他已经有半个月没吃到一粒粮食了。杜光宗的阿妈也死了。她在公社院子里领到自己的那份粮食后,紧紧抱着,以为她已经给儿子准备好了活下去的一切,就坐在地上,往后一靠,闭上了眼睛,安详得像经过整容后躺在了透明的水晶棺里。
从来没有像今天晚上这样,让常谷丰感到一个干部的尊贵。老百姓感激他,哭的,下跪的,唤他做爷爷的,说他是菩萨的。他不停地拱手作揖,向每一个领到粮食的人说一句:掺些东西慢慢吃,吃完就没有了。但他知道自己说也是白说,三关地方能吃的树皮、白胶泥已经光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掺了。
知青豫蓝也和别人一样给常谷丰跪下了,跪下后就听马灵验带头唱起来: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接着马灵验又喊: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她把万寿无疆前面的限定词省略了,让所有人都觉得是敬祝常谷丰万寿无疆。
豫蓝也在跟着喊,喊着就挤进人堆,拿到了分给自己的半布袋粮食。
马灵验喊够了又唱起来: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豫蓝左右顾盼着往回走,在川流不息的鬼影般的人群里,寻找自己的丈夫,可碰到的却是一张张随时都想吞下整个地球的獠牙交错的大嘴。她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拔腿就走,却又被和那些嘴挤在一起的一双双凄哀浑浊的眼睛摄住了。她犹犹豫豫回过身去,心惊肉跳地提起了自己的口袋,把粮食朝那些瘮人的大嘴和那么多颤抖的手倒去。
她说慢慢吃,一点点吃,别把自己吃死了。
她看到自己的口袋空了,那些嘴也就闭上了,而眼睛却绽放出一朵朵灿煜的花朵来,亮晶晶的,是夜色中悄然落在花瓣上的露珠,是苦难里由心潮掀起的人情的泪滴。终于海珍媳妇可以蠕动了,那张嘴一抖,便颤悠悠喊了一声:
好妹子,我给你下跪了。
豫蓝慌乱地扶住她:海珍呢?
死了。
哦,他也死了。豫蓝想着轻叹一声说:那你快去吧,兴许这会还能领到你的一份呢。
豫蓝说罢就走,听到黑暗中有个声音在呼唤她。她感觉那是鬼魂的声音,这鬼魂还在人体内,想拼命挤出躯体,飞升而去,于是就挣扎着喊起来。她快步走过去,走向一个朝她摇着胳膊张着嘴的人。刚到跟前,一双虬枝般的手就把她撕住了。
她说杜宝得,你就再忍一会吧,粮食就会吃到嘴里了。
杜宝得顿时变得异常平静,因为他认出她就是自己曾经活埋过的那个男人的女人。
他说我忍,你别害怕,我忍,快扶我走啊,唉,婆娘起不来了,她也饿倒了。豫蓝,亲妹子,快扶我走。
其实豫蓝早就扶住他了,可他的腿硬是被黄土拽着提不起来。豫蓝赶紧蹲下,把他背起来,腾腾腾地朝前跑去。她感觉他轻飘飘的,就像一具裹着人皮的骨架。
可是粮食已经没有了,最后一捧也让常谷丰捧进了石担的布袋。
豫蓝放下还在微弱喘息的杜宝得,从丈夫手里刁过布袋,抓出一把粮食就往杜宝得嘴里塞去,又喊一声:水。
常谷丰端来了水。
杜宝得的腿渐渐打直了,仿佛卸去了浑身沉重的铅块,摇摇晃晃地挪动着脚步。
这时傻愣着的石担才发现豫蓝空着两手,吼一声:你的那份粮食呢?
豫蓝浑身一颤,愕然不知所言。是啊,她的粮食哪去了?倒进了那些黧黑的吞云吐雾的海口?可是她和石担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