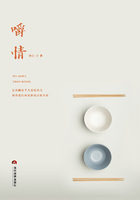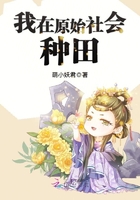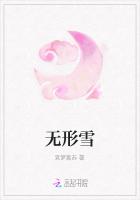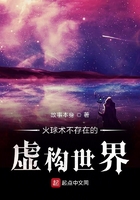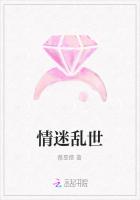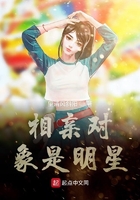1935年10月19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当时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最后一段路程,到达陕北苏区边沿的吴起镇(今吴旗县城)。毛泽东与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跟随第一纵队先到吴起镇,彭德怀跟随第二、第三纵队尚在吴起镇以西的地区。但是这时有敌军追在红军后边,敌先头部队已经到了吴起镇西边的唐儿湾、刘家亭子一带,其中一个团正在向吴起镇北面迂回。
当天晚上,中央在吴起镇召集第一纵队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与敌人骑兵作战的问题。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这里已是陕北苏区的边沿,我们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要把“尾巴”切掉,这一仗必须打,而且一定要打好。
会后毛泽东发电报给彭德怀,要他立即赶到吴起镇商讨作战事宜。第二天,彭德怀到吴起镇见到毛泽东和林彪,具体研究了敌情、地形和红军的作战部署,确保给进犯的敌骑兵以坚决打击。随即由彭、毛、林3人签署了一份电报,向一、二、三纵队发出战斗命令。彭德怀连夜返回前线亲自指挥作战。
10月21日早晨,第一纵队在正面,第二纵队在左翼,利用塬上深沟设伏,在吴起镇西北地区同敌军先头部队骑兵一个团打响,经过数小时激战,将该团击溃。红军乘胜追击,接着又在齐桥和李新庄之间分别把另外两个团冲垮,敌军狼狈逃窜,人仰马翻,乱作一团。红军俘虏敌官兵700余人,缴获战马100多匹,迫使敌军停止追击,远离了苏区。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的激动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不禁诗兴涌动,写下了这首赞扬彭德怀的六言诗。彭德怀回到毛泽东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毛写的这首诗。诗的第一句,恰好是他和毛、林在战前签发的电报作战命令中的一句话。当他看到最后一句时,觉得胜利不应归功于他个人,随即拿起笔来,把“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仍将诗稿放回原处。
原始手稿没有保存,又没有立即登载报刊,这首诗初时便只有经过口头转述,不胫而走。到了后来,由于受彭德怀政治际遇大起大落的影响,又使它呈现时隐时显,忽明忽暗的迷离状态,平添了许多传奇色彩。
这首诗最早见诸报端,是1947年8月1日,离写作时间已有12个年头。当时在冀鲁豫解放区部队的《战友报》第三期版上,以《毛主席的诗》为题(因这首诗原来没有标题)刊登了出来。虽然编者在注释里把这首诗误写为出自在腊子口毛泽东发给彭德怀的一份电报,但这张不报,仍然不失为这首诗第一次公之于世的珍贵文献。
1959年2月6日,《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写信给毛泽东,请他校阅并准予在该刊发表这首诗。信中说,诗是该刊读者抄录来的,还说这首诗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为庆贺彭德怀率兵攻占腊子口写的一份电报。
不料毛泽东看到信后,于2月15日复信给《东信》月刊说:“记不起了,似乎不像。腊子口是林彪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
毛泽东“记不起了”,这是可能的,因为写诗的时间已经过去20多年,加上来信又把写信的地点误为腊子口,致使他只是想到腊子口战斗的情况,未能去想其他战斗的情况。当然也有可能是出于别的原因。但是,不论这封复信出于什么原因,它使这首诗的历史价值一落千丈,是毫无疑问的,好在1957年那时候,这封复信没有流传出来,未产生太大的影响。
1957年《解放军文艺》4月号(距毛泽东复信的时间仅一个多月),仍然发表了这首诗。使这首诗在社会上得到空前广泛的传诵。
遗憾的是,1959年夏天,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被诬为“反党集团”的头子,这首诗自然也就没有人再加传诵。甚至在1963年出版的和1976看再版增订的《毛主席诗词》一书,也都没有收入。
销声匿迹20年,到1978年12月,彭德怀冤案获得平反,这首诗才在黄克诚悼念彭德怀的文章中重新见诸报端,再放光彩。
1981年12月,《彭德怀自述》一书问世,彭在书中为了驳斥加强于他的莫须有的罪名,为了澄清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是“三七开”的指责,详细介绍了毛泽东当时写这首诗的情景,《彭德怀自述》这本书曾经畅销290多万册,被译成英文俄文等传播国外。从此,“彭大将军”成了彭德怀的专用称号,这首诗也传向各国。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结,疑问还没有彻底解放。在1984年评审《中国大百科全书》彭德怀条目初稿时,有的提出,在历史档案中发现毛泽东给《东海》月刊编辑部的复信,为了慎重起见,这首诗应否写入该条目,必须作进一步的查证。
事后,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力平查阅了全修权的回忆文章(刊载于《中共党史资料》第2辑第186页),证明这首诗是毛泽东在吴起镇打退敌人骑兵后写的。接着,又写信询问杨尚屁,并附上伍修权的文章和毛泽东给《东海》月刊的复信。杨尚昆答复说:“这首诗是毛主席写的。有的。气魄也是毛主席的,是在入吴起镇前打马家骑兵后(写的)。”并且认为可以写进大百科全书条目。
在这以前,1983年6月15日,彭德怀传纪编写组访问王震时,也谈到了这首诗。王震说,在1947年8月,彭老总指挥西北野战军打完沙家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36师以后,在前东原召开族以上干部分。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亲临会场,向大家祝贺胜利。毛主席特别高兴,在会上讲话高度赞扬彭老总的指挥才能。会议休息时,毛主席兴犹未尽,提起笔来重新书写了《唯我彭大将军》那首诗。
经过这样取证,于是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已将这首诗收入。虽然是作为没有经过作者校订的、生前不愿发表的作品,列入“副编”,但确认它出于毛泽东的手笔已无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当中央决定为彭德怀等人平反的消息传到成都,四川省委立即派省劳动人事厅副厅长张振亚赶到成都殡仪馆,将彭德怀的骨灰盒运回了成都。
12月16日,被发落到资阳县武装部任副部长的景希珍正在公社蹲点搞民兵冬训,突然接到县武装部值班员的电话,要他连夜赶回县城,等待接听北京第二次给他打来的长途电话。
次日晚11点钟,北京的长途电话来了,是军委办公厅秘书傅学正打给他的。傅学正告诉他,三中全会决定要为彭德怀开追悼会,要他和綦魁英近日到成都军区报到,尔后一同去北京。
此时此刻,景希珍再也控制不住悲喜交迸的泪水,他仰望着繁星点缀的苍穹,环视着绵亘叠嶂的群山,发出内心的呼唤:彭老总,苍天有眼,山河有情,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您啊!您的沉冤昭雪了!您在九泉之下也该快慰地笑一笑了!12年前,是我和綦魁英为吊唁您的亡灵去北京。彭老总啊!今生今世,我们和您算是铁打成一块了,荣辱与共,这是缘分啊!
当景希珍赶到省军区时,被发落到内江军分区的綦魁英也赶到了。
成都军区已派人前来,向景希珍、綦魁英传达军委办公厅打来的紧急电话:中央定于12月24日召开彭德怀同志追悼会,要他们二人立即去省委联系,把彭德怀同志的骨灰运回北京。
此时,省军区已把二人的飞机票买好,定于下午1点40分起飞。
时间十分紧迫。
景希珍、綦魁英和成都军区的同志马上直奔省委。
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书记鲁大东、杨光等人已给中央组织部挂了电话,得到答复后,确定省委和军区领导全部参加向彭德怀同志骨灰告别仪式。
于是,一个紧争电话通各,30分钟后,省委和军区领导同志全部赶来了。在省委会议室举行了向彭德怀骨灰告别仪式。段君毅亲手将骨灰盒交给了景希珍和綦魁英。二人将一块红绸子覆盖在骨灰盒上。
此时,时间已近晚上6点钟。乘客为起飞时间来回改动议论纷纷,推测景希珍和綦魁英一定是负有“特殊使命”的“特殊人物”。
在飞机起飞运行一小时后,一个陌生人来到前舱,向景希珍和綦魁英审视了一番,问:“你们二人是不是成都军区的?”
“是啊,什么事?”
“父们带的东西呢?”
“什么东西?”景希珍和綦魁英警惕地打岔道。
“你们带的东西,你们还知道!”
“我们没带什么东西!”
“我是这个机组的负责人。”陌生人这才将一份北京拍来的电报递过来。
二人看完电报,说:“是的,彭老总的骨灰在这儿。”
这位负责人神色庄重地点点头:“好。你们到首都机场后不要下飞机。”
首都机场。等飞机上的乘客全部下机后,军委办公厅的王承光登上了飞机。他紧紧地同十多年未见的景希珍、綦魁英握手、拥抱,个个热泪盈眶。
王承光告诉他俩:“飞机还要起飞,到西郊机场去,这段算是专机。”
飞机再次起飞,很快在西郊机场降落。
在机场上举行了简单的仪式:景希珍、綦魁英抱着骨灰盒肃立在机舱门口;副总参谋长迟浩田、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以及彭梅魁、张春一、彭康白、王素红、王焰、傅学正、孟云增等人分站两排迎候;彭钢上舷梯接过骨灰盒,随后缓缓而下,两侧所有的人脱帽致哀。
随后,车队直奔八宝山革命公墓冲破了那片森严可怖的“禁区”,《安魂曲》洗礼般地荡漾在人们的心头。
“同志们:
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为彭德怀同志举行追悼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举行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元帅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致悼词。悲哀低沉却又字字落地成雷的四川乡音在这个亿万人民所仰慕的圣地回荡。
这是1978年12月24日。历史抹去尘埃,终于揭开了这一页。
逝者的遗体虽然早已化作了灰烬,但悬挂在大幕中央的他的那幅遗像--那倔强的有棱有角的方型脸庞,那三角欣似的喉骨,那宽厚的总是紧闭着的微微向下弯曲的嘴唇,那深沉有力且蕴含着几分忧郁的眼眸--一切仍是这般清晰,永恒地垂立于天与地之间。
为了这一天,他以坚挺的身躯、不屈的头颅向命运抗争了十多年!同邪恶搏斗了十多年!对光明期盼了十多年!
邓小平在悼词中历数了彭德怀一生“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的卓越的贡献,”和他曾担任过党政军许多重要职务之后,这样评价说:
“彭德怀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忠诚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彭德怀同志是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直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怀念和爱戴。”
听到这里,参加追悼会的人怎能不为彭德怀同时也为自己露出一丝欣慰的微笑呢?自然,人们无法回避地会由此联想到1959年夏天在庐山发生的故事;人们在无限悲痛和牵魂动肠的感念中更加对这位历史的殉难者发至肺腑地钦佩和敬仰:在这尊刚正不阿、犯颜直谏的脊梁和风骨面前,可以剥出那让人失笑的迷狂,那叫人切齿的鄙劣,那使人扼腕的怯懦和麻木,那令人轻蔑的圆滑和世故。
1959年的彭大将军,正处在他人生的辉煌期。然而,他那从幼年的苦难中埋下的倔强,他那从几十年残酷战争中养成的疾恶如仇人刚烈,他那由于逆境多于顺境而滋长的桀骜不驯的睨视群小的怪脾气,统统都随着他巨大的声望而毫无遮挡地表现出来。也许正是由于他的性格的缘故,即使瞬息万变的战争也没能给他注进一点阴柔、韬晦、善变、克己、忍耐等等中国传统的兵家机智。他像一块铸铁,不带丝毫弹性,注定他必在重压下断裂--撇开历史的必然性,一个人的性格,往往会影响以至注定着一个人的命运。
一些善良的人们总不免这样遗憾地认为:彭大将军若是不上庐山也许就没事了。
其实,即使彭德怀不上庐山,甚而1959年在庐山不发生那场大风波,中国日后的灾难和彭德怀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个人遭遇也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是,彭德怀上了庐山。于是,历史在1959年的庐山实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像但丁所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彭德怀也有类似的话:我彭德怀不出来,难道叫李德怀、张德怀出来吗?
尽管他的“出来”像闪电似的,只在庐山的夏日云雾中乍然一亮,便很快熄灭了,但他毕竟在那重重迷云之中勇敢无畏地燃烧了自己,成了他一生中最光辉夺目的一次闪耀!
一位诗人说--
他的不幸,恰恰是他对人民的忠贞!
他的悲剧,又恰是他生命中特殊光彩的一页!
历史,永远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