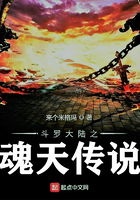成绩贬值的现象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现象和美国大学的理念息息相关。前面提到的宽恕制度就是一例。当然这一问题不仅在美国的高校普遍存在,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界都有同样的问题。其中一个说法是由于担心坏成绩会使学生失去学业上的上进心而造成非常消极的后果,因而老师避免给成绩欠佳的学生一个坏成绩。不管怎样,不可否认的是教育质量普遍下降,教育普及和大众化放松了对教学质量的控制。教学质量的放松直接导致教师对学生的要求的降低。就此现象,《波士顿环球报》的专题文章和罗若夫斯基教授的论述可供我们参考和对比。弊病之五:重研究而轻教育。
前文理总院院长柯伟林教授曾强调,在哈佛大学这样一所综合的研究型大学,聘任的终身教授应该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杰出的学者和极度负责并且具有合作精神的同事。虽然教学、研究和合作精神是一位哈佛的教授应该具备的三大至关重要的素质,但是事实上,教师的研究能力和成就举足轻重,而和本科生的关系大多是比较疏远的。本科生与舍监(House Master)、高级教员(Senior Tutor)的关系更为密切。在很多大课上,教授根本不可能认得所有修课的学生,基本的教学任务都是由助教来承担的。
在研究型大学,教授(不管是短期的助理教授还是年资已久的终身教授)往往把研究当作首要任务,而教学位于其次。如果某一教授有学术成就,往往指的是他最近的新书的影响力和在某一研究领域内特有的突破,而不会提到他今年开的哪门课怎么受到学生的欢迎。当然,开课效果好,受到学生的青睐不会是坏事,但是从学术效益来讲,其影响力(或杀伤力)都不如刚出版的专著来得大。
美国高校重个人研究而轻教学的现象,和牛津一对一的导师制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强调研究和出版毋庸置疑,而现在二、三流的大学和小型的人文学院也一味强调教师的研究成果,其结果自然是学生遭到忽略。
由于哈佛大学是一个研究型的大学(researchuniversity),有重研究而轻教学的倾向,这是由来已久的通病。随之,文理学院成立了特殊小组来专门讨论本科教学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加强教学在教授教职中的比重。本科生修的大规模的中心课程大量聘用研究生担任助教,教学质量逐年滑坡。较为年轻的助理教授不仅有沉重的教学任务,更有出版著述的重压;同时学生的教学评估对晋升也有重大影响。资深教授忙于各类非教学、非研究的应酬而忽略了严格的教学传统,这导致评分标准的宽松,对学生要求的降低。成绩贬值和入学要求的贬值一样,也是机会均等的普及教育和贵族阶层的精英教育之间的矛盾。2005年10月,耶鲁大学以缺少指导教师、辅导国际学生更加困难为由,将该校的一位中国学生勒令退学,此事被指为歧视中国学生并引发300多名学生集体抗议。为此,耶鲁大学组成了专项委员会,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并于2006年3月提交了详细的调查报告。我们暂且避开此事的前因后果不谈,单就学校的调查报告来针对目前美国的高校存在的问题做一些分析。调查报告提到评估问题,其中提到:“评分贬值的趋势也许会使学生误以为教师对其评价很高。”这一现象已经道出了高校内部对学生的评价和外部的市场需求相左的严重性。
弊病之六:学费和其他各类费用昂贵而导致师资和生源比较局限,仅仅吸收社会中一小部分阶层的人。
历来,美国的常春藤名校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而亚裔进入常春藤名校的比例持续上升(20%左右),但是拉丁裔和非裔远远不足(under.represented)。其中有多重原因。美国常春藤名校的大门仅仅为富人敞开的说法未免过于简单化。在此,我觉得罗若夫斯基院长的回应颇有启发意义。他说,仅仅以生源的家庭经济情况来看待哈佛生源的家庭背景似乎无助于深入解答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换一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很多拉丁裔和非裔的学生其实早在进入大学本科之前,其受教育的条件和知识水准已经远远地落在同龄人之后,不管其家庭的经济条件如何,进入哈佛这类的常春藤名校是不可能的。因此,虽然学校为低收入的家庭提供全额奖学金,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学业和课外活动的能力本身就是家庭经济条件的折射。学习乐器,加入足球队,参加社区活动并担当领导角色,无一不需要家庭的支持和引导。最近在萨默斯校长的倡议下,大幅度增加了对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优秀学生的资助,从而增强了生源的文化、阶层和家庭背景的多样性。
这一现象在萨默斯上任以来虽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为进哈佛的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全额资助依然无法解决上大学之前基础教育的巨大差距,出于经济原因,很多学生早在上高中之前已经远远落在同伴身后。
对这一弊病的阐述最为突出的是2007年出版的丹尼尔·戈尔登的专著《录取的代价》。
弊病之七:大学的高层管理机制过时。
从管理机制来看,近年来最为突出的是最高层管理机制陈旧、过时。前任校长萨默斯和文理学院教员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冲突从一方面暴露了董事会不能及时直接介入校方行政事务的弊病。民主制度要求任何执政者的权力都有其底线,总统如此,高校校长也是如此。在谈到美国高校校长的权力限度时,高校董事会这个概念在中国的高校行政中依然非常生疏。
克尔在2000年发表的论文列出了21世纪的研究型大学面临的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挑战。其中之一就是以外来成员为主的董事会成员是否依然具有足够的机动性、敬业精神和智慧来引导巨型大学的领导层具有足够的能力来回应挑战。不管将来哈佛校史和美国研究型大学史对萨默斯五年执政哈佛做何等评介,有一点是难以否定的,而且印证了克尔的论断的明智,即哈佛大学的最高决策层———七位董事会成员在萨默斯和文理学院资深教授的冲突中,由于缺乏直接的了解,缺乏近距离的干涉和调节,缺乏体制上的便利的应急措施而使这种本来轻微的冲突和意见扩大、加深以及恶化,以至于升级到了无法调解的程度。三百年前管理地方性小学院的董事会的结构和运作机制在21世纪的今天显然已经过时,克尔所谓的挑战无疑不仅发生在哈佛,而且近几年美国高校纷纷出现的校长被迫辞退的例子无疑也说明最高领导层的机制需要随着高校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更换。
以上罗列的这些弊病远非哈佛独有,这更说明现行的高等教育制度面临的困境和巨大挑战。
从“教授即为大学”的角度来讲,一方面,教授是大学的主持者,承担各类要职,招生录取、上课(重视研究生的课,大课有助教承担主要的负担),负责博士生的大考和指导论文,甚至帮助学生求职、晋升等等。大学运转的每一环节无一不和教授的重要角色息息相关;而另一方面,教授,尤其是资深教授往往倾向于重研究而轻教学,没有时间兼顾各方职责。高校为了适应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高等教育产业化使得很多根本的理念逐渐丧失,并使其失去了人文素质的熏陶和引导。
中国的高等教育和高校的管理制度面临进退维谷的巨大挑战。为了解决当务之急,很多校长和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纷纷前来哈佛和美国其他名校,探求世界一流大学办学的成功经验。其实,中国高校的很多问题具有普遍性,中国有,东亚其他国家有,欧美的高校也不乏其例。可以说,中国高校面临的诸多尖锐问题,在哈佛或是其他常春藤名校都能找到其对应面。关键的不同是中国高校在中国的体制中存在和发展,而美国的大学多为私立大学,管理机制透明,经济来源独立,于是就能在挑战面前随时应变和更新,不断完善高等教育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