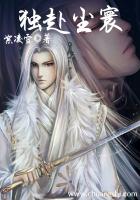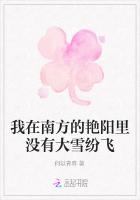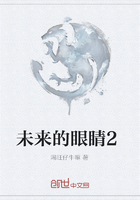杜诗的“诗史”之说最早见于晚唐孟棨的《本事诗·高逸第三》:“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孟说强调了杜诗获得“诗史”称号的两个理由:一是杜诗记载了因安史之乱所引发的许多社会时事,二是杜诗善于通过诗歌把时事表达出来。孟说虽然简略,但已经涉及了杜诗的内容和技巧两个方面。宋初宋祁的《新唐书·杜甫传》云:“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此说强调杜诗善于用长篇排律反映时事,侧重杜诗以诗载史的艺术技巧,是对孟说杜诗技巧方面的具体化。蔡居厚的《蔡宽夫诗话》:“子美诗善叙事,故号‘诗史’。”中国诗歌向以抒情诗为大宗,以叙事诗为次,蔡说明确说出了叙事的艺术手段是杜诗与史相通的原因,是对杜诗善叙事的艺术技巧认识的深化。《瀛奎律髓汇评》引无名氏谓杜甫“以史笔为诗”,即以撰史的笔法作诗。叶梦得的《石林诗话》评《述怀》、《北征》诸篇云:“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固古今绝唱也。”宋王正德《馀师录》卷上引《步里客谈》陈长方云:“老杜作诗,笔力可方太史公。如郭元振宅等诗,便是与之作传。”这是说杜诗可以为人物立传,而史传文学正是以人物传记为主的,这就把杜诗的“史性”探讨的越来越具体了。黄彻云:“子美世号诗史,观《北征》诗云:‘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史笔森严,未易及也。”溪诗话》卷一。这种把具体的年月日写进诗中的写法是诗歌史中少见的,在杜诗中也是极少数,黄彻却以此赞扬杜诗具有史笔的精确性,这是把诗当作史的极端化认识。另一些人则偏重于杜诗的内容。如(宋)谢逸在《故朝奉大夫梁州使君季公行状》中赞季公“尤爱杜子美,以谓唐之治乱,备见于此。”陈岩肖云:“杜少陵子美诗,多纪当时事,皆有据依,古号‘诗史’”,又云:“非特纪事,至于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无贵贱,亦时见于吟咏”。认为杜诗不但记载国之大事,而且还无所不包地记录了各地的风土人情,是比史书还要详尽的“诗史”。刘克庄引“三吏”、“三别”等诗后谓“新旧唐书不载者,略见杜诗”。这是强调杜诗具有补史的功能。但宋人对诗史说的最大发展是把史所承载的思想道义赋予了杜诗。如胡宗愈云:“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夫、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切,学士大夫谓之诗史。”杜诗不仅反映了作者的行事、悲乐,更反映了诗人忠君、崇贤、斥恶的思想,前者是诗家数、后者则是史家数。黄庭坚云:“老杜文章善一家,……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文天祥曰:“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以其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杜诗在纪事之中暗寓惩恶扬善的春秋笔法。黄彻甚至认为杜诗中的称谓如“杜曲”、“杜子”、“甫”、“杜陵”等都是“寓诸褒贬”的春秋笔法。溪诗话》卷一。宋代还出现了一些杜诗注本就明确标明以史解杜。如《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黄氏补千家注杜工部诗史》等。宋人对杜“诗史”的理解自内容取材、艺术技巧向思想道义的扩展是正确的,因为杜诗的确不仅多纪事、善纪事,而且对君臣将帅贤能宵小进行“抑扬褒贬”;但渐渐地,宋人过于夸大杜诗的“史”性而有意忽略杜诗的“诗”性,完全以读史的方法来解读杜诗,这势必会出现穿凿附会的弊病,引起世人的抵触和反感。如刘攽《中山诗话》记载丁谓以杜甫《侧行赠毕四曜》诗中“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回答宋真宗“唐时酒价几何”的提问,这本是文人雅士的机敏,不可当真。但在《诗话总龟》等书中,此事竟成了杜诗为“一代之史”的证据。王嗣奭在《杜臆》中指出,杜甫此句不过是用北齐卢思道之成语,“诗家不拘也”。若果真以此认为杜诗中的“三百青铜钱”是唐时的酒价,那就错了。《猗觉察杂记》卷上也载有以杜《盐井》诗而见当时盐价和商贾所贩之息的事,并称“使后世有考,真‘诗史’也”。又如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云:“李光弼代郭子仪入其军,号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曰:‘三军晦光彩,烈士痛稠叠。’前人谓杜甫句为‘诗史’,盖谓是也。非但叙尘迹摭故实而已。”语中所引诗句,出自杜甫《八哀诗》。这两句诗主要是表示李光弼深得军心且是军队的灵魂,一旦故去,则旌旗移色、三军痛悼,和“号令不更而旌旗改色”的传闻毫无关系。文学的形象生动性毕竟和历史的客观真实性是不同的,以史解诗是有限度的,越过了限度,是要出错的。当时的沈洵在《韵语阳秋序》中就说:“杜子美之诗,世或称为诗史。……虽比物叙事,号为精确,然其忧喜怨怼、感激愤叹之际,亦岂容无溢言?”在沈氏看来,杜诗字里行间有太多的个人情感,不符合史所要求的对时事的客观再现,因此杜诗不能称之为“诗史”。这是宋人对“诗史”称号的反思,当然这种反思仍然是完全以“史”的标准来衡量“诗史”的错误思维的另样发展,但毕竟我们听到了不同的声音,说明了这个称号并非神圣不可侵犯,是可以质疑的。因此沈说本身无可取之处,但他启发了后人对“诗史”内涵和外延作进一步的探索、界定。
明人杨慎就对“诗史”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以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杨慎的批评带有很强的个人情感色彩,缺乏说服力。首先,宋人对诗史的理解是包括纪事、技巧、思想在内的多个层面,而纪事只是诗与史相联系的表层原因,技巧、思想的相通才是杜诗被称谓“诗史”的深层原因。杨慎眼中的宋人“诗史”观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其次,他认为杜诗“直陈时事”的诗“类于讪讦”是“下乘末脚”,依据杨慎的意见,则“三吏”、“三别”即属此类。这是对诗歌中“赋”的手法的贬抑,忽略了“赋”法本身是做诗的一大传统。第三,杨氏认为“诗史”是完全可以代替历史的,这是对“诗史”说的片面理解。多数宋人还是在诗的基础上来理解“诗史”的,并非杨氏的狭隘。杨慎的批驳虽然破绽很多,但他强调诗与史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各有特征,诗要含蓄蕴藉、史要直陈质实,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尤其对那些完全以诗证史、以史解诗、忽略杜诗文学性的杜诗研究者是一剂猛药,虽有矫枉过正之嫌,还是对“诗史”的探讨作出了贡献。王夫之讥笑《石壕吏》“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辛辣的嘲讽那些赞美杜诗谓“诗史”的人是“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可闵者”。他评价李白的《登高丘而望远海》诗:“后人称杜陵为诗史,乃不知此九十一字中有一部开元天宝本纪在内。俗子非出像则不省,几欲卖陈寿《三国志》以雇说书人打匾鼓,夸赤壁鏖兵。可悲可笑,大都如此。”白诗虽也写了“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动荡、民生凋敝,但多为想象之景,与杜诗亲见亲闻的“诗史”是不能比拟的。但王夫之却硬说“诗史”的桂冠只有李白适合,杜甫是当不起的,这就不仅是强词夺理,更有信口雌黄的意味了。王说是紧承杨慎“含蓄蕴藉”的论诗观而来的,但他的批评尖刻,更加过激,不但叙事诗,即使小说这种叙事文学也都被他一并抹倒,而且还挟带着人身攻击的火药味,多数人不赞成他的意见。四部馆臣在《杜诗捃提要》中说:“明唐元竑撰……自宋人倡诗史之说,而笺杜者遂以刘昀、宋祁二书据为稿本,一字一句,务使与纪传相符。夫忠君爱国,君子之心;感事忧时风人之旨,杜诗所以高于诸家,固在于是,然集中不过数十首耳。咏月而以比肃宗,咏萤而以比李辅国,则诗家无景物矣;谓纨绔下服比小人,谓儒冠上服比君子,则诗家无字句矣。元竑所论,虽未必全得杜意,而刊除附会,涵泳性情,颇能会于意言之外。……胜旧注之穿凿远矣。”显然明朝的杜诗注家唐元竑是以诗人的眼光来涵咏、注解杜的“诗史”的,而四部馆臣则再一次在理论上支持了杨慎,强调了诗才是杜甫“诗史”的首要特性,并指出了以史注诗的弊端。反对“诗史”说的一方经过了明清两代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努力终于使他们的批驳渐趋严密完善、具有了较强的说服力。元明清三代支持“诗史”说的一方仍然是多数派,但他们的诠释基本上承袭了宋人。明陆时雍《唐诗镜》评《喜达行在所三首》云:“三首中肝肠踪迹,描写如画,化作记事,便入司马子长之笔矣。”杨伦《杜诗镜铨》评《草堂》一首云:“以草堂去来为主,而叙西川一时寇乱情形,并带入天下,铺陈终始,畅极淋漓,岂非诗史?”这是说杜诗善于纪事,故称“诗史”。王嗣奭《杜臆》评杜之《八哀诗》,以为“此八公传也,而以韵语记之,称为诗史,不虚耳”。认为杜诗善纪人故称“诗史”。《杜臆》评《忆昔二首》云:“公俱不讳,真诗史也。”这是说杜诗具有史书秉笔直书的特点,故称“诗史”。仇兆鳌《杜诗详注》评“用古体写今事”的乐府诗《前出塞》、《后出塞》云:“大家机轴,不主故常,昔人称‘诗史’者以此。”侧重杜诗写“今事”的内容。元人宋无《杜工部祠》诗云:“诗史孤忠在,文星万古传。”清人吴乔云:“杜诗是非不谬于圣人,故曰诗史,非直指纪事之谓也。”即使直书其事的《哀江头》和委婉而讽的《宿昔》因也是“是非不谬于圣人”,故也可称诗史,并批评:“用修(杨慎字)不喜宋人之说,并‘诗史’非之,误也。”这是强调“诗史”中所具有的忠君、抑扬褒贬的伦理意义。但明清评论家对“诗史”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杨伦《杜诗镜铨》引邵子湘评《悲陈陶》、《悲青坂》云:“‘日夜更望官军至’,人情如此;‘忍待明年莫仓卒’,军机如此。此杜所以为诗史也。”浦起龙《读杜心解》之《读杜提纲》云:“史不言河北多事,子美日日忧之;史不言朝廷轻儒,诗中每每见之。可见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两说都认为诗可以反映国民的情绪,可以形象地记录世人的心态,杜诗是“安史之乱”前后唐人的心灵史,它反映的深度及对潜在的隐患的敏感度都是史书所不及的。这实际上是说“诗史”比单纯的“史”有着更大的优越性,而这种优长正源于“诗史”所具有的抒发性情的诗性,这就在事实上承认了兼具“诗”、“史”两长所形成的“诗史”的第一性仍是它的“诗”性,而非“史”性。这种论断要比杨慎等人的批驳令人信服。(清)何永绍为姚文燮《昌谷集注》所作“序”云:“诗之有史也,自杜少陵始也。少陵生天宝末,所为诸什,一一皆以天宝实录系之,后人读其诗如读唐史然。故史不必系之以诗,而诗则皆可系之以史者。盖文人才子感时寄兴,以愤发其不得志于当世之意。然少陵之称史也,是以史自见者也,故后人亦尽见其为史也。”何说以为诗可兼史,而史不可兼诗;并且认为诗史可以借助个人情怀反映世运,以达到载史的作用,这样就明确地把杜甫的包括叙事诗在内的所有诗作都看作“诗史”,它是对杜甫诗的整体的称谓,并非只是对于杜诗中的叙事诗而言,这正是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诗史”。这种看法抓住了杜诗心系家国、关注社会民生的内核,是通达而恰切的。然而他又说杜甫是以史臣的自觉来作诗的,则是一种臆测,并且姚文燮亦承其弊说:“世称少陵为‘诗史’,然少陵身任其为史也。”
可以看出自唐末两宋到元明清关于杜诗的“诗史”解读、辩驳史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首先,中国诗话用语的模糊性使后学难以揣摩一些术语的含义,同时也为后学进一步的探讨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例如“诗史”自孟棨提出,却没有明确的界定。第二,对术语的理解往往由笼统走向具体,由肤浅走向深入,但常常要经历一个走向极端的曲折过程。宋人对“诗史”的理解包括了内容、技巧、思想三个方面,但也走向了“以史解诗”的极端,引起了明清人的强烈不满和批判,但反对方为了恢复“诗史”的诗性也走向了极端,他们把叙事诗贬得一无是处,并且连“诗史”的桂冠也要从杜甫的头上摘走。杨慎、王夫之即是此类典型。第三,经过长期的发展论争,会出现一个比较通达的相对接近客观真实的结果,但这一结果必须建立在对论辨双方观点合理成分的吸收的基础之上。何永绍的“诗史”观即是如此,他把诗性放在第一位,同时承认了诗史的合理存在,抓住诗史的本质,把诗史的范围扩大至整个杜诗。第四,论说者通过向史的靠拢或疏离在有意识的提高或降低诗和诗人的地位。支持“诗史”说的学者不断地挖掘杜诗中“史”的特点:诸如记时事、立传的诗歌内容,善叙事的笔法,善善恶恶、忠君爱国的伦理道德都备受学者的关注。结果杜诗由“小道”被提升至“史”的高度,相应地杜甫本人也渐渐的由诗人被抬升至具有“史臣意识”的以诗作史的无冕史学家了。“诗史”的称号使杜诗和杜甫像跃过了龙门的鲤鱼一般成了龙凤,再也不同于一般的诗作和诗人了。当然这一跃历经晚唐至清朝近千年的漫长时间,可谓艰难异常,一如诗人饱经忧患的一生。当然那些不喜欢杜诗的学人如接近神韵一派的杨慎、王夫之等为了损抑杜诗也是从剥夺人们称誉的杜诗中的“史”性入手的,他们认为含有史性的杜诗是下三滥的货色,是不能算作诗的,至少不是好诗,并进而摘去杜甫“诗史”的桂冠,使杜诗重新回到诗赋的队伍中去,那么杜甫自然也只能降格恢复他诗人的身份了。正反两方虽目的迥异,但却都在借史作伐,反映了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重史轻文”的传统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