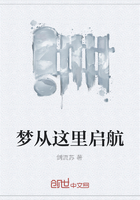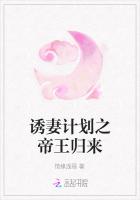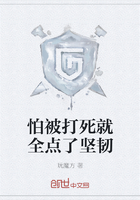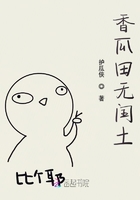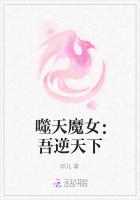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杨业与潘美(小说家笔下作“潘仁美”)并非有仇。陈家谷口逼杨业进军,后又将接应部队撤走的人是王 而非潘美。按《宋史·王 传》,王 字秘权,开封浚仪人,其父王朴,曾任后周枢密使,因上筹边之策而名噪一时。王 虽系名门之后,本人也有战功,但其为人“性刚愎”,“以语激杨业,业因力战,陷于阵, 坐除名,配隶金州”。
那位在小说家笔下坏透了顶的潘仁美(潘美)并没有那么坏,至少,他在陈家谷口并没有算计杨业,更没有像通俗小说或电视剧里所描写的那样,按兵不动,射杀杨七郎。倘若说他在这次战役中有什么过失的话,那也仅是因为他误信了王 之言而已。
惟其如此,所以,宋太宗赵光义在事后处理参战人员时,仅把潘美降三级使用,而对负有主要责任的监军王 则“除名,隶金州”,刘文裕“除名,隶登州”。
二、杨业共有七个儿子,而不是八个。
小说《杨家将》和电视剧《杨家将》中,杨业共有八个儿子,这也不完全对。据《宋史》记载,杨业共有七个儿子,他们是:
杨延朗、杨延浦、杨延训、杨延环、杨延贵、杨延彬、杨延玉。
其中杨延玉随乃父征战,于陈家谷口一战殉国,其余六子,延朗为崇仪副使、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并为殿直(官名)。
这七个儿子除杨延玉战死外,余皆善终。并无流落番邦、身死奸臣之手一说。
三、杨六郎应为杨大郎,杨宗保应为杨文广。
在“杨家将”的传记中,杨府男性主角,除了老令公杨继业以外,最有名的就是杨六郎和杨宗保这父子二人了。
这两个人物也非历史之本貌。
杨六郎者,杨大郎之谓也。他是杨业的儿子杨延朗(后改名为杨延昭),这没错,但他却并非杨业的第六个儿子,而是长子,他卒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宋史》上说他:“智勇善战。所得赏赐悉犒军,未尝问家事。出入骑从如小校。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行阵。克捷推功于下,故人乐为用。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惮之。”
杨宗保,应为杨文广。
《宋史》记载,文广系杨延昭之子。他字仲容,“以班行讨贼张海有功,授殿直”,北宋赫赫有名的范仲淹宣抚陕西时“与语奇之”,曾把他收为部下,后又随狄青南征,最后官至定州路副都总管,迁步军都虞侯。
“杨家将”既然半真半假,扑朔迷离,那么“杨门女将”呢?
“杨门女将”纯属子虚。
中国古代虽然向有“男尊女卑”的传统,但女将女帅倒也并非没有。
据《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记载:王莽新王朝天凤元年(公元14年),山东琅琊就出了个奇女子,此人名吕母,后来成为统领一方的女将军。《后汉书》上说:“吕母之子为县吏,犯小罪,宰论杀之。吕母怨宰,密聚客,规以报仇。母家素丰,资产数百万,乃益酿醇酒,买刀剑衣服。少年来酤者,皆赊与之;视其乏者,辄假衣裳,不问多少。数年,财用稍尽,少年欲相与偿之。吕母垂泣曰:‘所以厚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县宰不道,枉杀吾子,欲为报怨耳。诸君宁哀之乎!’少年壮其意,又素受恩,皆许诺。其中勇士自号猛虎,遂相聚得数十百人。因与吕母入海中,招合亡命,众至数千。吕母自称将军,引兵还攻,破海曲,执县宰。”
吕母以后,有名的女将还有隋末唐初的平阳公主。据《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记载,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平阳公主逃到户县,散家财招纳南山的亡命之徒,得到好几百人以响应李渊。又派遣家奴马三宝招降义军领袖何潘仁,与他合兵一处,攻克户县。接着又陆续收降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人,连克周至、武功、始平等县。“勒兵七万,威振关中”。
李渊渡过黄河以后,平阳公主领精兵一万与李世民会师渭北,并开设幕府,俨然行军主师“分定京师,号‘娘子军’”。
这些都是见诸信史的。
十分遗憾的是,在小说和电视剧里轰轰烈烈的“杨门女将”,正史中却连点儿影子都没有。
《宋史·杨业传》中只收录杨业及其子延昭等七人,和其孙文广一人,并无一字提及女眷。
倘若杨门女将确曾有过的话,那么,专收“义妇节妇”之事迹的《烈女传》也会记载。
但我们仔细地查找了《宋史·烈女传》,该传共收近40名“奇女子”,她们是:
朱娥、张氏、彭列女、郝节娥、朱氏、崔氏、赵氏、丁氏、项氏、王氏二妇、徐氏、荣氏、何氏、董氏、谭氏、刘氏、张氏、师氏、陈堂妻、节妇廖氏、刘当可母、曾氏妇、王袤妻、涂端友妻、詹氏女、刘生妻、谢泌妻、谢枋得妻、王贞妇、赵淮妾、谭氏妇、吴中孚妻、吕仲洙女、林氏女、童氏女、韩氏女、王氏妇、刘仝子妻。
没有一个人出自杨门。
“杨门女将”纯属子虚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千万莫把文学当成历史。
吴三桂谋反乃是被康熙皇帝所逼
康熙年间的吴三桂,实力声望功业权势,尚可喜不能比,耿精忠更不能比,动则要从长计议,暂不动他为宜。云南苗蛮杂处,形势复杂,吴三桂长居此地,情况熟,底子厚,继续治理也不是坏事。另外,用八旗换防,路途遥远,复杂艰险得很。况且所有对吴三桂忠诚度的怀疑均系猜测,并无真凭实据,贸然强行撤藩,恐不能令人心服。
讲得很有道理!可以说,绝大多数朝臣对马上撤吴,都是投了反对票的,包括大学士索额图、图海等重臣显臣,只有刑部尚书莫洛、兵部尚书明珠等少数人主撤,但那时的大事件并非议会制多数表决通过即可,反对者多也没用。
康熙力排众议,大手一挥,撤藩之奏一律恩准,三藩同撤,马上行动!众臣愕然,这可是他们认为的下下策啊!吴三桂们更是愕然,绝没想到,当初的如意算盘,结果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皇上怎么能这样?圣明何在?
谁让你们认识不到狡兔死的道理呢?这么多年了,还执迷不悟。就说你老吴,历来同类者,要么再占个自家独立山头,要么交出一切安当钓鱼公,有几个两头摆、走中间路线能成功的?明代沐家?毕竟是少数,何况条件还不一样,人家和皇上啥关系!
还想打小算盘?一般的皇上也就算了,可现在你们面对的可是那千年一帝,能不与众不同吗?
什么轻率冒进、意气用事、偏狭固执、独断专行,一样不少,都端出来让你们瞧瞧,不要以为咱康熙大帝只想做个高大全平面的人,他也渴望多层面、多棱角、有立体感的,这样更有魅力嘛。
只是这次,康熙大帝另一面表现得不是时候。军国大事岂能儿戏?他想得太单纯、太幼稚了,纯稚得让人不可理解,简直匪夷所思。
他对实际情况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更未静下心来设身处地感受一下三藩们的真实想法,迫切、冒进、固执、专断,完全占据了他的大脑,竟天真地以为,只要他的圣旨一到,他们马上会卷着铺盖回老家,困扰朝廷十几年的问题立刻就解决了。
也许有人会诘责,这分明是对康熙大帝的诬蔑之词,圣明之君岂会如此?史书上明确记载,康熙大帝曾经说过:“三桂等蓄谋已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
怎么讲呢,这清史类的东西,一旦针对帝王,向来都是极尽文过饰非、颠倒黑白之能事,圣祖尤甚。
人家尚可喜,明明率先提出撤藩在前,大乱中至死未叛在后,对大清那个忠诚,日月可鉴也,怎能说蓄谋已久?再说吴三桂,前面分析了,哪有的事,就是狂贬他的清史书上,其实也找不到任何真凭实据的。
咱们还是继续往下看,一切更加豁然也。
耿精忠暂且不提,且说吴三桂,接到皇上恩准撤藩的圣旨,简直当头挨了一棒,可想而知那是啥滋味。热血疆场上的出生入死、云贵高原上的苦心经营、荣华在手的富贵人生、权势在握的叱咤风云、昔日君主的皇恩浩荡、今日圣上的恩断义绝,等等,犹如过电一样,在他脑海中闪现,内心翻江倒海、痛苦不解、委屈愤怒、犹豫彷徨。
手下那帮随着他西讨南征的铁杆文臣武将们,更是震惊愤慨!既然皇上如此绝情,干脆反了得了,咱兵精将勇,怕他啥?老吴本还在徘徊犹豫,今见部属们拥戴,反复衡量后,也下定了起义的决心。
其实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别看朝廷现在话说得好,对撤藩工作也抓得紧,事无巨细,周密安排,力求给吴三桂们一个最温暖最舒适最可靠的安乐窝,可一旦真撤后,地盘没有了,兵权也无了,像吴三桂这等风云人物,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呢?古往今来,政治上过河拆桥的事情太多了。
老吴有否此种想法,不得而知,反正决心已定时,他是自信满满的。比较一下,他以为自己文韬武略天下已无双,将士们又是百战之锐、忠心之辈,要是起兵无不从命;所据云南也是经营多年,地险财富;另有一批过去的老部下如现任陕西提督王辅臣等虽已调走,却可作为外应。
简说老吴的文武之才:四个女婿胡国柱、夏相国、郭壮图和卫朴,都是一时才俊,或文或武或文武双全;另外武有吴国贵、吴应期、马宝、王屏藩、张国柱、高得捷等,文有方光琛、刘茂遐(字玄初)等,个个顶呱呱。
再看朝廷,皇上年方二十,乳臭未干,不堪大任,过去平定中原的名将大都凋零,剩下的及新起的一代岂是他的对手?其实老吴主观了点,事后也证实,康熙是没啥大本事,可清军新一代统帅有厉害的角儿,八旗依然很强,绿营同样不弱。另外,他也忘了,时间如果让人家凋零,自己与老部下们十一年来不也要走同样的路吗?
还有一点,绝对不能忽视,那就是满汉之争。明亡清兴至今不过三十年,大陆抗清之火被扑灭也只在九年前(1664年),汉人的故国之思岂能说忘就忘?就连做汉奸已很久的吴三桂,手下不也有胸怀反清复明之士?他的女婿、臂膀之一胡国柱就是。
而正是这种客观存在的民族之争,不仅让三藩内部凝聚力更强,也是日后大乱爆发初期,虽然发动者是为人所不齿的昔日背叛者,大江南北的汉人响应者仍众的原因之所在。
切入正题。这边吴三桂们真的开始磨刀霍霍了,而康熙那边却还浑然不知,全力做着撤藩的前期准备工作,好几万人呢,漫漫长路,线路怎么走,沿途怎么接待,到目的地后又怎么安置,浩大的工程啊。
康熙忙得不亦乐乎,其间有很多专门御批,足以体现他对撤藩之事的重视与对被撤之众的关切,但从他的着眼点来看,倒能明确一个真相。
原来他忙了半天,没有一件触及假如吴三桂们有啥异常如何防范的问题,虽然《圣祖实录》之类书上有不少事后弥补这方面不足的大帝语录及其他相关言辞,但根本找不到能够证明当时朝廷哪怕有一点实际举措的证据。
这也侧证了康熙当初决定三藩同撤时,想的就是那么简单,认为圣旨一到,一切OK,大臣们想这想那,还分几步走,纯粹多虑。什么“撤亦反,不撤亦反”,事后遁词也。
吴三桂们谋反之箭已在弦上,岂能不发?经过一番精心谋划,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终于正式反了!
老吴也从此进入了人生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他前不见古人后不知是否有来者的奇诡人生也至此奠定。
大清子民为何钟情于鸦片
八股文、小脚女人、鸦片,近代中国三大陋习。三大陋习中,八股与缠足乃中国传统文化,只有鸦片属于完整意义上的舶来品。鸦片起先是药品,后来在中外人民的“集体智慧”下,演变成天朝上下的最爱。在此前后,英国人往天朝输入过钢琴、饭叉、睡衣、玻璃、钟表甚至上帝等各种洋玩意儿,但天朝人民并不怎么接受:1674年,英国商人来华,流泪赔本大甩卖,只卖了11匹布;1699年,英国的毛织品来华,东印度公司大班发现,没有中国人想买它;刀子、钟表,赔本能卖出去一些;钢琴、刀叉,赔大本也没有人买;至于睡衣、睡帽,更卖不出去了……
按有些中国学者的解释,英国商品卖不出手,乃是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对资本主义廉价工业品具有天然的抵抗能力。但是这些学者解释不了,为什么对于鸦片,天朝人民就没有天然抵抗力了。相反,天朝人民热烈拥抱鸦片!与此同时,当时的英国并不禁烟,因为英国臣民并没有迷上这玩意儿。鸦片战争前后,每年流入英国本土300箱鸦片,成为城市中下层阶级的麻醉剂。但是英国政府及民众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因为面对众多酒鬼,几个鸦片鬼似乎太微不足道了。当中国鸦片正泛滥的时候,英国的海岸缉私队也没闲着,50艘快船6000名缉私队员在英伦三岛周围忙着禁酒呢。在白酒与鸦片面前,英国人选择的是前者,中国人选择的是后者。而日本,与中国同样的条件下,也没有拥抱鸦片。所以,鸦片应该还有一个民族偏好因素在内,这是我们不好意思承认的。难道说,鸦片,天朝人民就爱这一口?
近代中国到底出了多少烟民,从来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黄仁宇先生说过,中国向来缺少数字化管理,所以我们只能像民间百姓分萝卜那样撮堆算:1836年,有外国人估计中国有1250万人在吸食鸦片;1838年,林则徐认为有400万人;1881年,赫德估计为200万人;1890年,有人提出为1500万;1906年,有人提出为2000万。不管具体多少吧,估计天朝百姓与鸦片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中国的诗词中,甚至把鸦片称作相思草。天朝人民相信一种传说:印度在栽种罂粟时,把相思相爱的一对男女捆绑在一起,当两人的性冲动达到最高潮时,用利刃刺穿他们的心脏,让他们的鲜血流出,浇灌给罂粟。也许,这是天朝人民为自己离不开鸦片所想象出来的最佳理由吧。当然,鸦片有诸多好处,治病祛痛这是众所周知的,精神迷醉也是众所周知的,还有人把它当作睡觉的催眠药、采花时的春药、延年益寿的长寿药。甚至有人认为,鸦片适合中国人的体质。除了以上原因外,鸦片在中国的风行,还有经济方面的因素,因为天朝人民后来干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凡是能种鸦片的地方,都种了。鸦片在中国的普及与推广,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红薯和玉米:鸦片生产的利润极高,鸦片的产值和利润远高于一般经济作物,比红薯、玉米、棉花等强多了;种植鸦片的劳动强度相对来讲比较小,妇男老幼皆能干;鸦片具有货币功能,而且能够保值,这种货币,除了不会贬值外,携带起来还方便、安全,所以旅行者和商人宁愿带着鸦片上路而不愿意直接携带容易引人注目、吸引歹徒的钱银,甚至天朝各地赴京赶考的举子也往往携带鸦片以支付一路上的食宿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