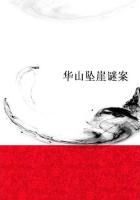“埃米尔,”厄苏拉喃喃地说。她过去不曾意识到这个宝宝也有名字。埃米尔照例穿得像在极地过冬。尿布、橡胶卫生裤、连体裤,层层叠叠;外套各种毛衣,衣服上无数蝴蝶结。厄苏拉对婴儿并不陌生,她和帕米拉一样,都曾像爱护小狗小猫小兔子一样热情照看过泰迪和吉米,她又是帕米拉孩子们的好阿姨,但阿波亚德太太的这个孩子,在讨人喜欢的程度上似乎略逊一筹。托德家的婴儿身上是奶香、爽身粉香和干爽衣物的清香,小埃米尔身上却有一股隐隐的腐臭。
阿波亚德太太在旧得走了形的大手袋里摸了好一会儿,手袋看上去也和她一样,是跨越欧洲,从另一个(厄苏拉显然一无所知的)国家远道而来。终于,阿波亚德太太一声长叹,在包底摸到了钥匙。宝宝仿佛感应到了自家的门槛,在厄苏拉怀里蠕动起来,似乎在做着变身的准备。它张开眼,显得很不高兴。
“谢谢你,托德小姐,”阿波亚德太太说着抱回孩子,“很高兴跟你聊了几句。”
“我叫厄苏拉,”厄苏拉说,“叫我厄苏拉就行了。”
阿波亚德太太踌躇半晌终于腼腆地说:“我叫艾丽卡。E-r-y-k-a。”两人门挨门住了一年,从没像此时这样亲密过。
门一关,宝宝照例哭开。“她不会是在用针扎它吧?”帕米拉在信中问。帕米拉的孩子个个心平气和,“都是到了两岁才野起来。”她说。去年圣诞前,她又生了个男孩,取名杰拉德。“下次好运吧。”厄苏拉见到她时说。她坐火车北上看望新生儿,一路舟车劳顿,与一火车赶往训练营的大兵同路,大部分时间在乘警车厢度过,很受了一番调戏言语的轰炸,一开始还觉得有意思,后来也就没劲了。“算不上是彬彬有礼的完美骑士。”好容易抵达目的地时,她这样对帕米拉说。路途最后一段的交通工具是一架驴车,很有时光倒流、甚至到了外国的感觉。
可怜的帕米拉被这场假惺惺的战争和关在一起的男孩们搞得没精打采,“感觉像在男校里当护士长。”珍妮特又是个“懒姑娘”(还喜欢无病呻吟和打鼾)。“人们总以为本堂神父的女儿断不至如此,”帕米拉写道,“当然,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先入为主。”春后她逃回芬奇利,自从夜半空袭开始后,虽说不愿与希尔维同一屋檐下,她又带着一窝小崽子回到了狐狸角“避风头”。在圣托马斯医院就职的哈罗德被调到了前线。医院的护士之家几周前遭轰炸致毁,五名护士死亡。“每天晚上都像在地狱。”哈罗德说,见识了轰炸现场的拉尔夫也说过一样的话。
拉尔夫!对了,拉尔夫。厄苏拉都快把他忘了。他刚才也在阿盖尔路,炸弹爆炸时他还在吗?厄苏拉挣扎着四下里看了看,仿佛这样就能把他从废墟里找出来。四下无人,只她一个,被圈在炸断的木梁柱所组成的牢笼之间,空中的灰尘,落在地上,落在她嘴里、鼻孔里、眼睛里。不,警报拉响时拉尔夫已经离开了。
厄苏拉已经不再与海军部的恋人同床共枕。战争的打响让他心里突然充盈一种愧疚。他们必须终止恋情,克莱顿说。比起战争对他的要求,肉体的诱惑应该放一放——仿佛她是为爱情而毁了安东尼的克娄巴特拉。就算没有“暗藏情妇”的危险,世界看来已足够精彩。“我是情妇?”厄苏拉说。她从没想过要去争取一个红字,那个符号应该属于两性世界中更活跃的女人。
天平倾斜了。克莱顿做出了选择。自然并不坚定。“好吧,”她平静地说,“如果你想的话。”此时她已开始怀疑,克莱顿神秘外表之下其实并没隐藏着一个别样风采的他。他其实不难了解。克莱顿就只是克莱顿——他是莫伊拉,是他的孩子,是日德兰半岛,仅此而已,虽然未必以这个顺序
呈现。
虽然分手是他促成的,他反倒生了气。难道她毫无感觉?“你很冷静。”他说。
她又没有“恋爱”过他,她说,“希望我们还能做朋友。”
“恐怕做不了了。”克莱顿说,似乎已经为既成的往事追悔莫及。
尽管如此,翌日她还是为失恋哭了一天。她对他的“喜爱”似乎不像帕米拉想的那么无足轻重。接着她擦干泪,洗净头发,拿上一片涂博维尔肉酱的吐司和一瓶1929年的上布里昂葡萄酒上床去了。葡萄酒被随随便便扔在伊兹梅尔伯里路家中的高级酒窖内。厄苏拉有伊兹家的钥匙。“能找到什么就拿。”伊兹曾经这样说。于是她照办不误。
多可惜呀,厄苏拉心想,不能再与克莱顿幽会了。战争其实给他们之间轻率的举动行了方便。灯火管制最合适不轨的结盟,轰炸终于爆发,又为他不回沃格雷夫与莫伊拉和女儿们待在一起提供了取用不尽的借口。
可她反而同德语班上一个男同学开始了一场开诚布公的关系。上完第一节课(Guten Tag. Mein Name ist Ralph. Ich bin dreizig Jahre alt.大家好。我叫拉尔夫。我三十岁。),两人就来到南安普敦大道上的卡尔朵玛咖啡馆,那时街边堆的尽是沙包,谁也看不见咖啡馆里的他们。两人同看轰炸灾情地图时,发觉竟在同一幢楼里上班。
离开教室——坐落在布卢姆茨伯里区某楼三层的一间逼仄的房间——时厄苏拉才发现,拉尔夫原来是跛子。是在敦刻尔克受的伤,他不等她提问就主动说。站在水里等去大船的小驳船时被射中的。他被一个福克斯通的渔夫拖上船,少顷渔夫脖颈中弹。“清楚了吧,”他对厄苏拉说,“再没必要谈这事了吧。”
“不,当然没必要,”厄苏拉说,“真残忍。”关于敦刻尔克,她当然在剧院的时事片里看到过。“牌虽然不好,但我们打得很精彩。”克莱顿说。疏散部队后她曾在白厅遇见他。他想念她,他说。(他似乎又有些动摇,她想。)厄苏拉决意要若无其事,说自己还有报告要送到战时内阁办公室,拿牛皮纸信封当铠甲一样护在胸前。她也曾想念他。她觉得此事万万不能让他知道。
“你升入战时内阁了?”克莱顿刮目相看。
“只是向次长的一个助理汇报情况罢了。其实也不算什么助理,只是个跟我差不多的‘姑娘’。”
她认为谈话已经太长,至此应该结束。他凝视她的眼神令她想要投入他的怀抱。“我得走了,”她朗声说,“外面还在打仗呢。”
拉尔夫是贝克斯希尔人,有些许刻薄,是个左倾的乌托邦主义者。(“社会主义者难道不都信乌托邦?”帕米拉说。)拉尔夫与克莱顿截然不同,后者现在想来,职位实在太高,权力实在太大。
“被共产党追求?”莫里斯在“圣墙之内”遇见她时,问。她觉得自己遭到了审讯,“要是被人知道了,恐怕对你不利啊。”
“他又不是共党内部的什么重要人物。”她说。
“还是不妥。”莫里斯说,“不过至少他躺在床上聊天时不可能透露他们战舰的位置了。”
这话什么意思呢?难道莫里斯知道克莱顿的事?
“你的个人生活不完全是你一个人的,尤其打仗的时候。”他面带反感地说,“而且,对了,你究竟为什么去学德语?你这是在期待侵略,为欢迎敌军做准备吗?”
“我还以为你担心我是共产主义者呢,原来你以为我是法西斯主义者。”厄苏拉生气了。(“真是个浑蛋,”帕米拉说,“他不过是害怕自己受到影响,面子上不好看罢了。倒不是说他就有道理。他就从没有过
道理。”)
从井底这个位置,厄苏拉看见自己和阿波亚德太太房子之间,那百无一用的墙已经完全消失。穿过坍塌的房梁和折断的木地板,她看到一条裙子,软绵绵地挂在晾衣架上,钩住墙上的挂镜线。厄苏拉从印着蔫黄玫瑰的墙纸上认出,这是底层米勒家的挂镜线。那天傍晚她还在楼梯上见拉维妮娅·内斯比特穿过这条裙子,当时裙子还是豆汤绿(绵软程度相当),现在却变了一种炸弹灰,且从一楼迁徙到了底楼。距她头部几码远的地方落着她自己的烧水壶,那是个咖啡色的大东西,在狐狸角时,足够烧一家人的茶水。她从手柄厚厚的绕线上将它认了出来,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天,由格洛弗太太绕上去的。一切事物都脱离了它应有的位置,包括她自己。
对,拉尔夫来阿盖尔路了,两人喝着啤酒,吃了些东西——面包和奶酪。接着她做了昨日《镜报》上的填字游戏。近来厄苏拉为看近物,不得不买了一副老花镜,戴起来相当丑。买回家才发觉,这副老花镜,和内斯比特两小姐戴的款式一模一样。难道她的命运也跟她们一样?她打量壁炉上镜中的四眼,这样想。她会不会也落得老姑娘的下场?话又说回来,戴上红字是否意味着不可能再是老姑娘了?昨日午休时,她在圣詹姆斯公园吃三明治,一个信封悄悄来到她的办公桌上。她一见是克莱顿的笔迹(他写得一手好看的斜体字),写着自己的名字,就连信带信封一起撕得粉碎,扔进了纸篓。后来,当所有事务员都像鸽子一样围着送茶车躁动时,她捡起碎纸,把信拼了回去。
我的金烟盒找不到了。你知道是哪一个——由家父在日德兰战役后赠予。你不会恰好见过吧?
你的,C。
反正他从来不是她的,难道不对吗?相反,他一直属于莫伊拉。(或是海军部。)她把信扔回纸篓。烟盒就在她包里。他离开她后过了几天,她在床底下发现了它。
“你在想什么?”拉尔夫问。
“没什么,相信我。”
拉尔夫在她身边躺下来,把头搁在沙发扶手上,穿着袜子的双脚插进她大腿之间,看起来仿佛睡着,但每回她对他说话,他都喃喃地做出反应。“罗兰与奥利弗?你说填‘圣殿骑士’怎么样?”她问。
昨天她在地铁上时发生了一件怪事。她不喜欢地铁。轰炸以前她去哪儿都是骑车,但现在满地玻璃碴、碎石块,骑车不方便了。为了忘掉坐地铁的事,她在地铁上做《镜报》的填字游戏。大部分人来到地下都感到更安全,但厄苏拉不喜欢被关起来。前几天才有一颗炸弹落在了地铁口,轰炸的气浪和火焰顺着通道进了地下,结果相当惨烈。不知此事是否登了报,这种事情公布了,对士气不利。
地铁上,坐在对面的一个男人突然凑上前来——她也就向后缩——对着尚未完成的填字格点了点头,说:“您真厉害。我能给您我的名片吗?有兴趣的话,请来我的办公室。我们正在招募聪明的女孩子。”一看你就知道是个规矩人,她嘲讽地想。男人在格林公园下车时,对她轻点帽檐行礼。名片上的地址居然在白厅,她把名片给扔了。
拉尔夫从烟盒里抖出两支烟,一一点燃,递给她一支,说:“你是不是特别聪明?”
“差不多,”她说,“所以我干情报,而你只能画地图。”
“哈哈,不仅聪明,说话还有意思。”
两人在一起很自在,不像恋人,倒像有多年交情的朋友。两人都尊重彼此的个性,从不相互苛求。因为都在统战室工作,相互之间很多事不说也都明白。
他用手盖住她的手背,问:“你好吗?”她说:“非常好,谢谢你。”他仍像战前一样,保有一双建筑师的手,战斗未曾损伤它们分毫。他曾在皇家工程队做土地侦测,幸免于战争的交锋,整日研究地图、照片,没想到竟然也被迫上了战场,在漂满油污和血水的海里蹚行,被四面八方的机枪扫射。(后来他终究忍不住又就此多说了一点。)
虽然轰炸很残忍,他说,但它也有它的好处。他觉得未来有希望(不像休和克莱顿)。“有些破地方炸了也好。”他说。伍利奇、西尔弗顿、兰贝斯、莱姆豪斯全数被炸,战后都要重建。这是个机会,他说,我们可以建造简洁的现代化楼房,配备齐全设施——一个玻璃钢筋、空气澄澈透明的社区,告别维多利亚式的脏乱,成为未来的圣吉米尼亚诺。
厄苏拉不赞同这种现代化塔楼群的办法,如果让她来规划,她将在未来建立各种花园城市,许多舒适的小屋和充满野趣的花园。“你真是个保守的老东西。”他满心喜爱地说。
当然他也爱老伦敦(“哪个建筑师不爱?”)——雷恩诸教堂,恢宏的私人宅邸,高雅的公用楼宇——“伦敦的石建筑。”他说。一周有一两个晚上,他在圣保罗大教堂当巡夜,“必要时”时刻准备上房,保护教堂不受燃烧弹侵袭。那地方火灾隐患极大,他说——老木材、锡材,到处都是,屋顶平坦,楼阁众多,还有许多黑暗的角落早已没有人记得。他应《英国皇家建筑院刊》上的一则面向建筑师的广告,当了防火志愿者,因为他们对“楼体各层结构等相关知识更为了解”。“需要我们相当敏捷。”他说。厄苏拉担心他的跛腿无法应付。她看见他在各种楼层平台上和被人遗忘的黑暗角落里被熊熊烈火包围的样子。守夜是件快活事——大家下棋,长谈哲学和宗教。她想拉尔夫必定喜欢这工作。
不过几周前,他们才一起惊恐万状地目睹了荷兰城堡被大火烧毁。起先两人到梅尔伯里的酒窖去拿酒。“干吗不住到我家来呢,”伊兹开拔美国前,曾顺口说,“正好可以帮我看房子,对你也安全。我想德国人绝不至于炸到荷兰公园区来。”厄苏拉觉得伊兹过于高估了纳粹德国空军的投弹精准度。再说,如果真安全,她自己为什么掉转尾巴逃走了?
“谢谢,不必了。”她说。那房子太大,而且空落落的。不过她仍然拿了钥匙,偶尔去房里搜刮一通有用的东西。橱柜里有厄苏拉存着以备走投无路时自保的罐装食物,当然,还有整整一个酒窖的酒。
两人打着电筒在酒架间巡逻——伊兹走时,拉断了房子的电力——厄苏拉从架上抽出一瓶看来相当高级的Pétrus(柏图斯干红葡萄酒),对拉尔夫说:“你觉得这个配炸马铃薯饼和午餐肉怎么样?”话音刚落,空中响起可怕的爆炸声,两人以为房子中弹了,立即扑倒在酒窖坚硬的石板地上,拿手抱住了头。这是近来去狐狸角时休反复强调的一个做法。“千万保护好你的头。”他打过仗。她有时会忘记这一点。架上所有的葡萄酒都摇颤起来,倘若这些拉度酒庄(Chateau Latour)和滴金酒庄(Chateau d’Yquem)的好酒纷纷雨落,那些玻璃碴像榴霰弹一样,砸在两人身上,后果不堪设想,厄苏拉回想起来不禁一阵后怕。
两人跑到外面,看见荷兰城堡化为一片火海,火舌吞噬着一切,厄苏拉心想,千万别让我死在火里。请上帝让我死得干脆些。
她相当喜欢拉尔夫。有些女人会为爱情而困扰,她没有。与克莱顿在一起时,她因一种爱的可能性而不断受到诱惑。而与拉尔夫之间一切都是直截了当的。然而那不是爱,更像是喜欢一条狗(当然她绝不会把这话对他说的,有些人,或者说很多人,并不了解人与狗之间那种情感的高度)。
拉尔夫又点了一支烟,厄苏拉说:“哈罗德说吸烟对人体危害很大。说他在手术台上见过不少肺叶,像从来没扫过的烟囱。”
“吸烟当然有害,”拉尔夫说着,为厄苏拉也点了一支,“但被德国人轰炸、扫射也是有害的。”
“你有没有想过,”厄苏拉说,“比如过去一件很小的事,一旦被改变,我是说,比如希特勒一生下来就死了,或者小时候被绑到——呃——比如说贵阁会(贵阁会(Quaker),又称公谊会或者教友派(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主张和平主义和宗教自由),在那里长大,那现在一切都会不一样了。”
“你觉得贵阁会有可能绑架小孩吗?”拉尔夫随口问。
“假设他们知道将要发生的事,当时也许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