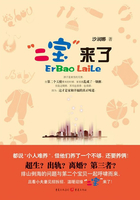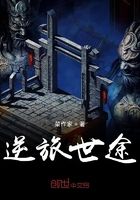人生第一次,她感到了惶恐。不会有人来救她。阿波亚德太太晕头转向的鬼魂肯定不会来的。她将在阿盖尔路的地窖里孤独地死去,只有《肥皂泡》和无头的拉维妮娅·内斯比特陪伴左右。假设休在这里,或者泰迪,或者吉米,或者就算只是帕米拉,也一定会排除万难把她弄出去,把她救活。他们会管她。但这里谁也不会管她的。她听到自己哭泣起来,声音仿佛一只受伤的猫。她是多么可怜呀。她像可怜别人一样,可怜起自己来了。
米勒太太刚说完“要不大家都来杯热可可吧”,米勒先生就又担心起了两个内斯比特小姐,厄苏拉受够了地下的幽闭,主动提出去找,刚起身,就听见“嗖——”“嗖——”一发高爆速炸弹登场了。接着是一声炸雷般的巨响,仿佛地狱的围墙咔嚓裂开了,所有恶鬼倾巢而出。周遭出现巨大的负压,仿佛要把她的内脏——肺叶、心脏、脾胃甚至眼球——从她身体里吸出去。礼赞这永恒的最后一日。就是它了,她想。原来我将这么死。
寂静中突然响起一个声音,一个男人的声音,几乎就在她耳边:“振作一点,小姐,让我们想办法帮你出来,好吗?”厄苏拉看得见他的脸,又脏又汗,好像是掘了三尺地才找到她似的。(她觉得实际上很有这个可能。)她惊讶地发觉自己竟然认得他。这是她部里新来的防空指挥官。
“您叫什么名字,小姐?能告诉我吗?”厄苏拉嗫嚅着自己的名字,但她知道自己说得太含糊。“厄丽?”他确认着,“不是?那是玛丽?
苏西?”
她不想死后被称为苏西。不过,名字这东西真的重要吗?
“宝宝。”她喃喃地对指挥官说。
“宝宝?”他突然警惕地说,“您有孩子?”他直起身,朝身后的谁嚷了几句。她又听见了其他声音,这才明白周围有很多人。仿佛为了证实她的观察结果,指挥官说:“我们都来救你们了。煤气工已经关掉了煤气,我们即刻就会转移你们。别担心,苏西,您刚才说您的宝宝?是抱在手里的那种宝宝吗?是小小的吗?”厄苏拉想到埃米尔,想到他像炸弹一样沉(房子爆炸的那一刻,谁是那个轮到抱他的人呢?),她准备说话,却再一次发出了猫受伤一般的呜鸣。
头顶上方,什么东西发出咯吱吱的沉吟,指挥官捉住她的手说:“没事了,我在这里。”她对他,对所有前来救她出去的人们,都感到莫大的感激。她想休也将多么感谢他们啊。想到父亲,厄苏拉哭了,指挥官马上说:“嘘,嘘,苏西,没事了,我们马上就出去了,就像从螺蛳壳里挑肉那么简单。然后就有茶喝了,怎么样?不错吧?很期待吧?反正我很期待呢。”
好像下雪了,她的皮肤隐隐感到了一粒一粒针尖般的冰凉。“真冷。”她含糊地说。
“别担心,绵羊抖两下尾巴的工夫,我们就出去了。”指挥官说。他费事地脱下大衣,盖在她身上。本没有多少空间让他干这件好事。他碰到了什么东西,又兜头撒下一片碎渣来。
“啊。”她突然感到翻江倒海的紧张,但很快平静下来。树叶伴着沙土、灰尘和死人的灰烬一起飘落下来。突然间她置身于一片山毛榉树叶之下。树叶散发着蘑菇和篝火的气味,还有一丝甜滋滋的气味。那是格洛弗太太烤的姜饼的气味。比地沟和煤气味好闻多了。
“来,姑娘,”指挥官说,“加把劲,苏西,千万别睡过去。”他的手在她的手上握紧了,但厄苏拉正看着别处,阳光下,一只晶莹的东西正在转圈。是一只家兔吗?不对,是野兔。一只银色的小野兔,正在她的眼前慢悠悠地转着圈。多叫人沉醉啊。这是她见过的最美丽的画面。
她从屋顶飞身进入黑夜。她在玉米田里被阳光曝晒着。在田间小径上摘野莓。与泰迪玩捉迷藏。多好玩的小家伙,有人这样说她。说话的人自然不是指挥官咯?接着雪下起来了。夜空不再高悬。夜空像温暖的海洋,向她聚拢过来。
她向昏迷飘移过去。她想对指挥官说一句话。谢谢你。但说不说并无所谓。什么都无所谓了。黑暗降临了。
美好的明天
1939年9月2日
“别生气,帕米,”哈罗德说,“家里怎么这么静?你把孩子们怎
么了?”
“卖了。”帕米拉打起精神,开玩笑道,“买二送一。”
“你今晚应该住下,厄苏拉,”哈罗德好心劝道,“明天那种日子,不该独自一人待着。你就当这是医生的命令吧。”
“谢谢,”厄苏拉说,“但我有安排了。”
那天早些时候,她在肯辛顿高街做战前最后一次疯狂购物时买下一条黄色绉纱茶裙。她将它穿起来。茶裙上规律地印着飞燕图案。她喜欢,觉得穿起来很漂亮,或者说觉得梳妆镜内照出的各部分很漂亮。为了照到下半身,她必须站在床上。
透过阿盖尔路淡薄的墙壁,厄苏拉听见阿波亚德太太正用英语与一个来去毫无明确规律、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男人争吵——也许他正是神秘的阿波亚德先生。厄苏拉只在楼梯上与真人打过一次照面,当时他情绪欠佳,瞪她一眼就继续走了,也没有打招呼。他身量高大,面庞红润,有一点让人联想到猪。厄苏拉想象他站在肉铺柜台后面或者大力拖动酿啤酒的麻袋,觉得都很合适,但据两个内斯比特小姐说,他其实是干保险的。
与之一比,阿波亚德太太显得又黄又瘦,每当她丈夫出门,厄苏拉就听见她拿一种自己听不懂的语言唱忧伤的歌。听起来是某种东欧话。卡夫先生教的世界语此时该派多大用场啊。(当然得在人人都说它的基础上。)尤其那段日子,伦敦突然拥入许多难民。(“她是捷克人,”内斯比特小姐们终于告知,“以前我们可不知道捷克斯洛伐克在哪儿。真希望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厄苏拉猜想,阿波亚德太太一定也是个想在英国绅士怀中安然度日的难民,没想到却找到了暴脾气的阿波亚德先生。厄苏拉决定,一旦听见阿波亚德先生打起他的太太来,她就去敲门制止,虽然还不清楚具体的制止
办法。
随着隔壁的争执到达顶峰,阿波亚德家的门被重重摔上,争吵声静了下来。可以听见进出动静极大的阿波亚德先生,咚咚咚咚跺着楼梯下去了,边走边甩出一通脏话,关于女人和外国人。被迫偃旗息鼓的阿波亚德太太恰好既是这个,又是那个。
一种不满的酸楚,连同水煮卷心菜令人作呕的气味,从墙壁那边渗透过来,叫人消沉、难耐。厄苏拉希望她隔壁的流亡者充满灵性和情怀——为追求文化生活而来,不愿她是被虐待的保险职员的妻子。虽然这种荒唐的希望对隔壁的女人不大公平。
她从床上下来,在镜前微微旋转,觉得茶裙的确很合身。她快三十岁了,但还保持着年轻人的身材。何时才能发展出希尔维护士长般饱满的腰腹呢?有孩子的可能性如今看来越来越渺茫。她抱过帕米拉的孩子——抱过泰迪和吉米,她记得那种怜爱与惶恐并存的感觉,那种誓死保卫的本能愿望。假若是自己的孩子,这感觉会强烈几分?也许会强烈得难以承受。
在约翰·刘易斯百货喝茶时,希尔维曾问她:“你从来没有很想抱窝的感觉?”
“你是说像母鸡那样?”
“‘职业女性’。”希尔维的语气仿佛职业和女性二字不该出现在同一场合。“老姑娘。”她又深思熟虑地加上一句。母亲如此费心地刺激她,厄苏拉感到莫名其妙。“你大概是不会结婚了。”希尔维总结道,似乎说厄苏拉的生命等于就此结束了。
“‘不结婚的女儿’真有那么糟糕?”厄苏拉恣意享受了一番这个诱人的可能性,说,“简·奥斯丁就认为不错。”
她从头上脱下茶裙,只穿胸衣、丝袜,无声地走到水池边,在水龙头前接了杯水,又搜刮出一片奶油饼干。这是典型的监狱伙食,她想,对即将到来的日子是一种很好的历练。除了在帕米拉处吃的蛋糕外,她早上只吃了一片吐司。她本希望晚上与克莱顿一起吃顿好的。他约她在萨沃伊饭店见面,两人绝少在这样的公共场合私会,她心想不知会不会发生戏剧性场面,抑或他只是想谈谈这场依然戏剧得过了分的战争。
她知道明天英国就要宣战,虽然在帕米拉处装了傻。克莱顿把许多不该说的都说给她听了,原因是反正两人“都签署了秘密行动协议”。(她则什么都没告诉他。)最近他为两人的事又动摇起来,厄苏拉对他究竟会采取什么动作心中无底,也不清楚自己希望他怎么做。
他邀了她出去喝一杯。要求以海军部文件的形式,在她暂离办公室时神秘出现。厄苏拉不止一次疑惑究竟是哪个精灵在送这些字条卡片。您的部门即将接受审计。卡片上这样写。克莱顿喜欢文字游戏。厄苏拉但愿海军密报部门的水平千万别像克莱顿一样拙劣。
助理职员福塞特小姐看见躺在桌上的文件,惊慌地看了她一眼。“奇怪呀,”她说,“真的要接受审计?”
“有人开玩笑而已。”厄苏拉说着,沮丧地发觉自己正在脸红。这些表面无辜实则放荡(甚至下流)的字条里有一种与克莱顿不符的东西。我发觉铅笔不够用了。或者,您瓶中的墨水是否充足?他如果学过皮特曼速记法,或者行文风格更谨慎些就好了。完全停止这种递字条的游戏自然更好。
萨沃伊的门童侍候她走进门,克莱顿已经在开阔的大厅等候。他没有陪她向底层的美国酒吧走去,而是上二楼来到一个套房。整个房间似乎都被一张大床占据了,床上装点了许多枕头。噢,原来我们是为了这个来的。
她想。
中国绉纱裙看来有失时宜。她也后悔在里面穿了皇家蓝丝长裙——她最好的三件晚装之一,克莱顿很快就会把它脱下来,假设他还顾得上。丰盛大餐已然泡汤了。
他喜欢替她脱衣,喜欢看她。他说“像雷诺阿”。虽然对美术知之甚少,她想这至少比说她像鲁本斯好。或者毕加索。他赋予她对裸体的一种习以为常。莫伊拉则是个以法兰绒及地长裙裹体、做爱必须关灯的女人。厄苏拉有时候怀疑克莱顿也许夸张了他妻子的刻板。有一两次,她想到要长途跋涉去沃格雷夫看看那饱受非议的妻子是否真是个灰头土脸的女人。问题是,假设亲眼见到莫伊拉(她想象她更为鲁本斯,而不是雷诺阿),莫伊拉便不再是想象,而成为现实中的一人。厄苏拉将无法再毫无负担地背叛她。
(“但她本来就是现实中的一人,”帕米拉不解,“你的逻辑太狡
猾了。”
“没错,我心里是明白的。”厄苏拉在休吵吵嚷嚷的六十大寿春庆上承认道。)
由套房望去,从滑铁卢桥到国会大厦和大本钟之间的泰晤士河尽收眼底,河面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变得影影绰绰。(“紫蓝色的一小时。”)她只隐约辨出了像手指一样在黑暗里指着天空的克娄巴特拉方尖碑。不见了伦敦往日的灯火闪烁。灯火管制开始了。
“二房里有人占着,还是我们的事见得天日了?”厄苏拉问,克莱顿正打开一瓶在缀满汗珠的小银桶里等了许久的香槟。“这是为了庆祝?”
“为了永别。”克莱顿说着,也走到窗前,递给她一杯酒。
“永别,我们的?”厄苏拉很纳闷,“你把我带到上等宾馆,准备了这么多香槟,就是为了结束我们之间的事?”
“对和平的永别,”克莱顿说,“对我们所熟知的世界的永别。”他向窗外暮色中辉煌的伦敦举了举酒杯。“为了终结的开始。”他沉郁地说,又仿佛突然想起似的补充道:“我已经离开莫伊拉了。”厄苏拉吃了一惊。
“那孩子们呢?”(只是顺便一问,她想。)
“都离开了。生命短暂,不该为不快乐的事活着。”厄苏拉想这天晚上伦敦城里不知有多少人在说这句话。虽然说话的环境也许不那么考究。虽然有些人说它时,不是要破釜沉舟地抛弃,而是要更珍惜身边人。
厄苏拉突然感到一阵意想不到的惶恐:“可我不想嫁给你。”她说完才意识到自己的确极其反感嫁给他的念头。
“我也不想娶你。”克莱顿说,厄苏拉还是感到了一阵失望。
“我在艾格顿花园租了房子,”他说,“我想也许你会愿意一起来。”
“你是说同居?不清不白地住在骑士桥区?”
“只要你愿意。”
“天哪,你可真大胆。”她说,“你的事业怎么办?”
他无所谓地“哼”了一声。这么说,他新的日德兰半岛将不是这场战争,而是她这个人了。
“你答应吗?厄苏拉?”
厄苏拉透过窗户凝视着泰晤士河。天黑得几乎看不见河水了。
“我们应该说句祝酒词。”她说,“海军里是怎么说的——‘祝情人和太太老死不相往来’?”她将自己的酒杯碰在克莱顿的酒杯上,“我饿了,我们去吃饭吧!”
1940年4月
门前街上汽车喇叭声大作,打破了周日早晨骑士桥区的宁静。厄苏拉想念教堂的钟声。战前那些习以为常的小东西,如今变得弥足珍贵。她真想回到从前再好好诚恳地去感受一遍。
“为什么要按喇叭呢,”克莱顿说,“我们的前门不是有一个门铃嘛?”他向窗外望去,“假设我们在等一个三件套西装绷得鼓鼓囊囊像圣诞知更鸟一样的年轻男性的话,”克莱顿说,“那么他已经到了。”
“听起来是他,”虽然厄苏拉现在、过去都从未觉得莫里斯“年轻”过,但与克莱顿相比他或可算个年轻人。
休要过六十岁生日了,莫里斯勉强自己来接厄苏拉去狐狸角庆祝。与莫里斯共挤一辆车这还是第一次,虽然未必是一次好的体验。两人很少单独相处。
“他有汽油?”克莱顿说着,高挑起眉毛,虽然是问话的语气,但并没有疑问的意思。
“他还有司机呢。”厄苏拉说,“我早知道莫里斯会趁战争捞一大笔的。”“什么战争?”帕米拉听了一定会问。她被“抛弃”在了约克郡,“与六个男孩和一个珍妮特困在一起,后者不仅是个无病呻吟的人,还是个彻头彻尾的fainéante(懒骨头)。真没想到本堂神父竟有这样的女儿。真是懒到家,只有我一个人整天跟在我的和她的儿子后面跑。这出避难的闹剧我真是受够了,我打算尽快回家去。”
“他要是不捎上我,怎么好意思开着车出现在家里。”厄苏拉说,“莫里斯在谁面前都要做得滴水不漏,就是自己家人也一样。他要面子。此外他全家人都在狐狸角,今晚正好接他们回伦敦。”莫里斯把埃德温娜和孩子们送到狐狸角过复活节。厄苏拉怀疑关于战争他知道些平常人不知道的消息——也许复活节期间伦敦会出乱子?莫里斯肯定知道许多其他人不知道的事。然而复活节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她又想也许这次拜访只是单纯为了让孙儿们去看看祖父母。菲利普和海泽尔是两个相当乏味的孩子,不知两人与转移到希尔维家那些活蹦乱跳的孩子(1939年9月,英国为避免德军轰炸殃及太多儿童,进行了一场妇女儿童大迁徙。约有80万儿童从城市被转移到不易被轰炸的偏僻乡村,寄养在当地人家中)相处得如何。“回来时车里肯定很挤,又是埃德温娜,又是孩子们,他居然还有个司机。不过,还是将就一下吧。”
汽车喇叭又响起来。厄苏拉存心不理。她想象克莱顿穿起军官制服(戴上所有奖章、绶带)紧随她身后,叫莫里斯看看这个在各方面都比自己高出好几级的男人,该多么叫人惬意。“你可以一起来,”她对他说,“我们只要不提莫伊拉和孩子就行。”
“是你的家吗?”
“嗯?”
“你刚才说,‘他不好意思出现在家里’,那里是你的家吗?”克莱
顿说。
“是,当然。”厄苏拉说。莫里斯在人行道上不耐烦地来回踱步,她敲打窗户引起他的注意,然后举起一只手指,比了个“一分钟”的口型。他对她皱了皱眉。“都是这么说的嘛,”她转身道,“大家提到父母的住处,总是用‘家’这个字。”
“是吗?我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