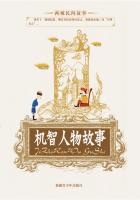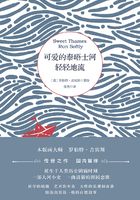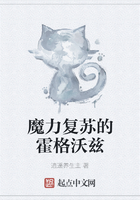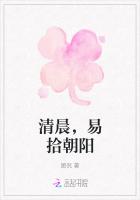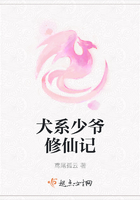派来的人说,想不到民间的大会如此有序;又跑回去重开证明,恢复老婆的名誉;总梦见新疆那块地方,总是在那个地方;那片广袤深厚的大地,从来没有欺骗他们。
这是2008年的12月17日,在大批上海支边青年到新疆四十五周年之后,他们的纪念大会终于举行。会场是在有关部门指定的市郊体育馆,会议进程得到有关方面的密切关注。而大会组织者,恰恰是当前在阿克苏振臂一呼的几位代表人物。
全国知青返城潮的发起者丁惠民也特地赶来,并宣读贺词:“在这里,我丁惠民要说的是,去新疆的支边知识青年,是全国知青群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么多年的功过是非,今后,历史自有评说。”
有时候想,干脆再回去吧
参加纪念大会的这些人,已经从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了返城回沪的退休者。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户口、工资、医疗等方面的诉求,他们还被视作“不安定因素”。会后,一位派来负责监控大会的干部私下说:“想不到民间召集的大会开得如此文明有序。”或许,这是一次迟来的纪念,但对每位当年的上海青年来说,就像回到了四十多年前:没有尊卑贵贱,在时光中沉淀下来的,只是相似的境遇和共同的情感。
安康有个当年一起到新疆去的朋友,他因为老婆不是上海人,不容易回来,又不打算离婚,就找熟人办个证明,说老婆死掉了。证明是真的,事情是假的,他老婆还好好的。两个女儿跟他到上海来,把户口报上。他老婆其实也一起来了,但来了以后名不正言不顺,已经没这个人了,怎么办?时间一长感觉不对,后来他跑回新疆原来的单位再去开证明,恢复老婆的“名誉”。当初像他老婆这种情况的不能报进户口,现在政策变了以后可以报了。
在周敦福的家里,他拉开旧柜子的抽屉说:“我基本的证件都在这里,都在这个袋子里。这是我一家的户口,我的职业写的是‘无业’,没单位的。回上海没有给我安排过单位。”周敦福属于他们这个群体中的一类人。
同时,他们本人的身份就被简称为“369”,意思是一个月拿369块的生活保障金。尽管开始户口不起什么作用,但拿了户口的,在团场那边就已经除名。最后回来没办法,上海怎么安置呢?一个月发给369块生活费。
他们退休后医保的问题,看病有一定比例的报销,但是要拿到新疆的原单位去报。收入本来就低,用句通俗的话讲:“吃了饭不能吃药,吃了药不能吃饭。”在这个背景下,兵团后来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医保工作站,方便回来的退休职工报销医疗费,不用再拿回新疆去报了。
当许多人惋惜老上海的建筑正在消失的同时,实际上,确实还有不少人正在急切期盼着旧弄堂的动迁,以便有望改善自己一直以来糟糕的住房条件。
在笔者前去寻访时,周敦福从他阴暗的老屋里出来,站在弄堂口指着外面说:“我们这条街都要动迁了,动到那边的几条马路。我们搬到哪里去,这个还不清楚。像我回来的时候有房子住,现在就比人家差了。我们当中能买得起房的有几个?而且不是靠自己买得起,是靠子女比较有出息。还有的通过动迁加上贷款买房子,这是很少的。有些人回来赶上动拆迁,有的动拆迁已经过去,就没房子,只能用那点收入租房子了。”
上海市民的居住条件大概在90年代普遍开始改善,原来住在棚户区的,很多都是靠动拆迁实现翻身。从新疆回来的张依璞、李德娣夫妇,还住在四十多年前离家时父母的老房子,那么小,只有等动拆迁,但是他们家那一片还没有等到动拆迁的消息。
张依璞甚至说:“有时候想,我们回来干什么呢?我们在新疆那边后来已经过得挺好了,回到这个房子,家庭矛盾出来了,生活上困难了。有时候确实在想,干脆还回新疆去吧。虽然那边房子卖掉了,但十来万块就能买套房子,上海呢,十来万块只够买几个平方。”
我妈说了,多挣点钱到上海买个房
在南疆库尔勒附近的开都河畔,姜步宏在农二师21团任副政委直到退休。他是1966年夏天最后一批进疆的上海青年,也是他们当中最后一批在职的。在办理退休手续后他也是要返回上海。
走在场部外面的土岗上,姜步宏说:“起初21团的上海青年有一千二百多人,都退休了。退休的在这里每月拿一千多块,两口子两千多,生活没问题,挺舒服。有的回不去了,大部分是因为房子问题。在我们库尔勒买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二三十万。在上海呢,要多少钱?还要看是内环、中环,还是外环。”
笔者在场部的家属区见到了徐佩君,她退休前是统计员。当年由于出身资本家,她主动报名进疆,后来嫁给山东籍的老职工。四个儿女都留在团场务农,其中一对双胞胎女儿,姐姐种辣椒,妹妹养牛,每年有不错的收入。大女儿小时候跟着回过上海,但记不住了,大了以后再没回过。按政策可以有一个子女回去,把二女儿的户口落在上海了。但是她人还在这里,回上海以后,觉得还是新疆小伙子好,又跑回来结婚了。
养牛的二女儿坐在方桌旁边说:“我户口在上海,肯定以后我们儿子要在那边上学。在这里多攒点钱,到那边毕竟要有个窝。像我妈说的,多挣点钱,到上海去买个楼房。”
把外孙送回上海去读初中,看来是全家人的一个计划和希望。大人问这个男孩:“你知道外婆他们当年为什么要来新疆吗?”他回答:“我想应该是让新疆变得更美丽吧。”像是准备好的答案。
笔者从她家走出不远,同样是个平房小院,在葡萄架下坐着白振杰、韩培芬夫妇。虽然女儿一家在上海,但是他们夫妇俩已经不大向往城市生活了。
韩培芬说起来:“直到现在回去见了我大哥,大哥还在讲我,‘当年你就那么傻,我从火车上拉你下来,你就不下来,你咋想的吗?’我也不吭气,反正一切都在那里面了。我们在上海没有房子,也不能回去,孩子条件再好,住一起时间长了也不行。最主要的一点,儿子在这个地方,反正我们在新疆四十多年了,都习惯了。”
丈夫白振杰接话说:“在哪儿都是待。我跟她讲了,在哪儿都一样,非要回北京、上海吗?”
家人一年聚两三次,我们几十次
对于这些回到上海的昔日支边青年来说,定期聚餐是一种保持交流的方式。逢到固定的日子,同一团场或同一连队的人在酒楼里聚餐,大家按惯例AA制,轻松又平等。他们碰杯的祝酒词常常是:“开心啊!”“健康啊!”
在餐桌旁,一位男士笑道:“我和家里面一年最多聚两次三次,跟他们一年最起码几十次吧。”
在座的有一位老职工的女儿,她说:“他们是寻开心。我爱人那个时候十六岁,我十二岁,但是辈分不一样,他们一来支边的时候,我们学生都要集合在路两边,要欢迎‘叔叔阿姨’。他们不断地来,每隔几天就要欢迎一次。
坐在她旁边的女士取笑道:“后来她嫁给‘叔叔’了,就跟我们一样了。”
大家一二十人围坐在餐桌旁,应笔者的请求,他们每人用一句话说出了自己曾经在兵团的岗位——
我在新疆是农工,主要是管啤酒花和种水果。
我们连队是种水稻,我打了十六万多斤,那时候最红的,我是水稻班班长。
让我领导一个木工班,木工班班长,那是我的最高职务。
我是赶大车的。四套马的车子,两根鞭杆。好长的鞭杆还在家里面放着。
我在农一师机关幼儿园当老师。
我最高职务在武装值班连当排长。
我在团场医院当护士。
我曾经的最高职务是连里的会计。
……
说到兴头上,他们当中一位曾经在师宣传队的女士起身离桌,大家就围拢来,在旁边唱起了《达坂城的姑娘》,那位女士拉着丝巾跳起了热情欢快的新疆民族舞。从这歌声和舞步里,让人感受到包含着那么多难忘的情感。
唱的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说起来,他们从十几岁远离生长居住的城市,到反差那么大的地方,像兄弟姐妹一样集体生活在一起,有着太多共同的悲欢,别人可能是难以完全理解的。
安康重病住院的那次,最多的一天来了五六十人看他。医护人员对他说:“安先生,您肯定以前是当大官的。”安康说:“我当什么大官呀,就是个退休职工嘛。”人家说:“你瞎讲,每天来看你的多少人,把我们都吓死了,一般当官的也没有这么多人来看呀。”安康说:“你们不可能理解的,我们都是一起在新疆支边的。”听到安康病了,确确实实有很多人来,因为他迷迷糊糊的,有的跑过来看了以后,甚至放声哭起来。
2009年,因小区的活动室改做它用,安康组织的唱歌会就只能搬到他家的一室一厅中。房间小了,参加的人却没有减少,连床上都坐满了。这些人里,除了少部分有能力改善境遇的,大部分靠不充裕的退休金生活。但一进门,听到他们放声高歌的是,《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唱罢一曲,安康把手从钢琴上缓缓抬起,然后随着余音放下来。或许,他用这种方式已经圆了他学生时代的音乐梦。他说:“实际上我们在一起唱歌是一种精神寄托,每个人都有不尽如意的生活状况,在外面在家里不开心的话,到这里一唱把什么都忘了。”
张依璞、李德娣夫妇也手捧歌本坐在其中。大家都知道,他们自己没有生育,收养了一个维吾尔族女儿。第二天,笔者从又窄又陡的木楼梯上去,来到他们夫妇从新疆退休回来后住的阁楼。四十多年前,他们也是从这样的弄堂阁楼走出家门,远赴边疆的。
坐在床边的李德娣翻着相册说:“这是我女儿,一百天的照片。女儿的结婚照在这里。三十岁了。女婿也是新疆回来的子女。”
笔者随同他俩去了一趟女儿家,要挤公交车坐十几站。夫妇俩卖掉了自己在新疆的房子,省吃俭用帮助女儿女婿在上海还一部分房贷。
他们的养女张嵘说:“像我爸妈和我这种情况的很特殊。我是维吾尔族,应该说就算在上海人里有收养情况的,也不可能是我这个民族。别人有时候会觉得他们傻,不理解。当我自己有了女儿,也养了女儿以后,就觉得,生一个小孩子容易,疼那么一阵子就生下来了,但是培育孩子长大成人,走上工作岗位,然后成家立业,这真是爸妈一辈子的心血。”
在自己居住的社区活动室里,余加安每周定时义务教歌。这位昔日的团场文艺骨干仍然发挥着特长,教唱得十分认真卖力,仿佛又找回了当年的良好感觉。
余加安说:“回来三十年了,就像打的烙印,没有办法擦掉。一提新疆,我还是新疆人;但是在新疆那边说起来,你是上海人,就这样。”
在杨清良夫妇的家里,午饭摆上了桌,像通常的上海人一样,菜是许多个小碟子。但他拿出了新疆出产的伊力特酒,握起酒瓶说:“来,喝酒!这是我们新疆的伊力特。我们在一起,这些新疆回来的朋友聚在一起,那肯定要这样的—老杨,来杯伊力特!”妻子朱静华在旁边说:“他哪里像个上海人,对这个白酒情有独钟。”
杨清良夫妇俩返城以后辗转各地做生意。当初是响应号召,好儿女志在四方;后来是独自创业,老大不小再闯四方。他们靠自己加倍的努力,逐渐成为生活中的赢家。他们办的“喷喷香”食品厂,做巴基斯坦松子,手剥松子。为了做这个买卖,杨清良又到了新疆喀什。从喀什到边境口岸红其拉甫,又走上那条上海青年参加修建的翻越帕米尔高原的中巴公路。
朱静华说:“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新疆十八年的生活历练,很可能我也就平平淡淡地等待下岗,等待退休。但是从新疆回来以后,我想不会一辈子就这样的,我要抓紧做事情。”
当年选择继续留在兵团的王祖炯,通过刻苦写作改变了命运,一步步在做文教和宣传的岗位上提升自己。他在《兵团日报》任副总编时,几乎走遍新疆各地。王祖炯指着家里摆的照片说:“这是我,骑着马,天山主峰托木尔峰就在背后。在新疆走到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无意中听到上海口音的人说话。这些人撒在天山南北,不定在哪儿你就发现了,见到了,他们都很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