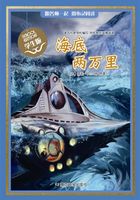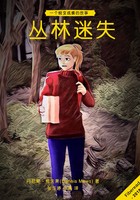折腾了一晚上,两个警察都累了,不打麻将就犯困,也不知道如何收场才好。真金不怕火炼,这小伙给打成这样愣是一声不吭,不愧好汉一条。到了三更时分,周麻子家的王管家来敲门,讲这事不要闹大,闹大了名声不好,给两位两个银元,把人放了算了。有台阶下自然是好事,两个警察打开押犯人的小房间,两脚把葛正才踢醒。其实这小伙根本没睡着,哪里睡得着。警察叫他起来,赶快出去,不然要收栈房钱。周耀元的管家看到葛正才走出警察所,才回去报告主人。
警察把葛正才带走后,周耀元才发觉这件事来得有点蹊跷。他转身问他的小老婆,你看见那个姓葛的拿白丝你当时咋不吭声?小老婆说,我只是在窗口远远看到他鬼鬼祟祟的样子,背了个麻袋溜出去,我怕夜黑眼花没看清,所以没跟你讲,要是今天过秤时茧丝没少那么多,哪会对他起疑心呢?这时周耀元才怀疑他的小老婆在其中做了手脚,偷偷卖掉一担丝讲做丝的手脚不干净。于是周耀元赶紧叫王管家去给警察打招呼,连夜放了葛正才。并给警察两个辛苦钱,别跟警察结梁子。
这事就这样解决了。周耀元也没扣葛正才的工钱,葛正才还继续到下一户人家去做丝。警察打人也挺讲究,剥了你的衣服打,别把你衣服打烂了给你拿到证据;也不往脸上打,旁人看不出来。后来在街上碰到,彼此还交谈两句,就像不咸不淡的远房亲戚,也不亲热,也不冷淡。后来还碰到周耀元的小老婆,不止一次两次,那女子仍然生葛正才的气,不跟葛正才说话,一辈子不原谅这个做丝的。
后来的情况是,葛正才入了大刀会,一面给人家种地,一面跟周三立学打拳。当年周三立的长拳,曾打遍江南无敌手,溧阳大刀会成员十之六七是他的徒子徒孙。周三立不但拳脚厉害,而且眼睛凶,一眼就看出葛正才是可造之才。周三立在茶楼上喝茶,见葛正才拿扁担挑了一副空络绳朝这边走,依然穿短衫打赤脚,腰里系一根细麻绳。周三立叫人把葛正才带过来,葛正才是认得周三立的,朝老人打躬作揖。他见过周三立端坐在太师椅上,那是在周家祠堂前的一排旗杆底下,两旁是人声嘈杂的看客,中间是打拳比武的弟子。
“人家叫你葛小妹对不对?”周三立把玩着茶壶盖问年轻人。
“没错。”这是葛正才头一次走进茶楼雅座,脚上的牛粪渣掉在硬木地板上。
“为啥这么叫你?”
“不知道。”
“你愿意跟我学拳么?”
“我愿意。”
当晚就举行拜师仪式。葛正才带了两个礼包来,一个是蜜枣,一个是红糖。南货店总是拿粗黄纸包礼包,拿细麻绳系礼包,中间夹一块正方的红纸头,以示欢天喜地。葛正才跪在周三立家的明堂前,给周三立磕了三个头。周三立明确表示,这个是关门弟子,以后不再收徒弟。
这时的周三立已年过七旬,虽白发白须但精神矍铄。按理讲,这个老人再收十个二十个徒弟也没事,人家都是徒弟教徒弟的,师父在不在场,师父讲不讲啥,都无所谓的,可周三立不肯当这种挂名师父,他收的徒弟,全是他本人手把手教出来的。老人见好就收,并非多多益善。按理讲,二十岁的人学打拳虽然比六十岁的容易学到手,但远不及童子功来得扎实,顶多学到七八成,能应付个耍赖的痞子,劫道的强盗,就算学出来了。
可奇怪的是,也不大看到周三立教葛正才学拳,也不大看到葛正才在祠堂前用功习拳,但葛正才的功力却日渐增长,推手时一搭手就知道。起初谁也不把他当回事,三年后连大师兄应对他也感觉吃力。周三立只教了葛正才三年工夫。这三年中,更多的时间是周三立给葛正才读书而不是授拳。最初是周三立读给葛正才听,后来是葛正才读给周三立听。三年中只读那三卷书,日日之乎者也的连大师兄也不听懂。
讲周三立伯乐识马并非阿谀奉承。其实周三立看出葛正才身条匀称是习武的料倒是其次,主要是他知道葛正才对动作的记忆有过目不忘的本事;究竟是如何知道的,谁也闹不清楚。周三立所教的动作,葛正才当场做一遍两遍就牢记不忘,有时看一眼就记得牢,每日夜间就一个人在松林里苦练两个时辰。而周三立教他读书,他居然识得了字,也听得懂意思,这就更加神奇。起初是每句话周三立读一遍讲一遍,后来是葛正才自己读,葛正才读一句,周三立讲一句。三年中翻来覆去就读那三卷书,一老一少乐此不疲,好像越读越来劲。只要葛正才来,总是先读书后习武。读书时总是大声朗读,摇头晃脑,像和尚念经般抑扬顿挫。
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
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感而后应,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
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大至则多奇巧;以礼饮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乱,大至则多奇乐;凡事亦然,始乎谅,常卒乎鄙……
读了就讲,讲了也听不懂,就像听天书堕入云里雾里。旁人都觉得奇怪,自己肯定没听懂这不用说,懂了就不会觉得奇怪,不明白的是,看葛正才的样子,好像他是能够听懂的,没听懂的时候,他会问师父问题,而他问的问题,旁人也听不懂。后来就见怪不怪,习拳的照样习拳,聊天的照样聊天,不在意他们师徒两个读什么讲什么。这世上的事,搞不懂的多,搞得懂的少,不是样样事情都要搞得懂;有时候是你没心思搞懂它,有时候是你没本事搞懂它。“凡事亦然,始乎谅,常卒乎鄙。”这句话是啥意思?你不懂,我也不懂,师父讲了也不懂,不懂就不懂呗,可偏偏葛正才听得懂,这就奇了怪了。
当年葛正才跟潘尧最铁。潘尧是湖北佬,家住乌鸦山北麓的麻园村。早年葛正才到麻园打短工,潘尧把他带到自己家里吃住,两个人一见如故。后来才知道潘尧也是大刀会的,舞起刀来寒光点点一脸煞气。葛正才给潘尧讲那档子事,只是喝酒时闲话两句,讲他挨过一顿打,是给周城镇两个警察打的。后来有一天,潘尧叫来七八个人,叫葛正才一起去周城警察所。潘尧对他讲,给你出口气是小事,弄两杆枪才是正经事儿。葛正才明白这件事的严重性,抢警察所的枪就是跟官家对着干。他拿起烟锅抽烟,一面抽烟一面琢磨。抽完烟,磕掉烟灰,站起身来,点点头,同意跟潘尧一起干。当晚他们就杀了那两个警察,抢了警察的枪。一不做二不休,葛正才敲开周耀元家的门,大步走到周耀元的烟榻室,当着他小老婆的面,一刀捅死周耀元。
那个女人吓得直哆嗦,张开嘴巴却喊不出声音来。葛正才捅了周耀元掉头就走,没伤那个女人。盗亦有道,葛正才后来杀人如麻,但从未杀过一个女人。打南渡的时候,主要是抢当铺。溧阳人讲:“金南渡,银张渚;蚀了本,归戴埠。”南渡有钱人家多,又挨着京杭国道,警力配置强于其他乡镇。战斗进行至胶着状态时,有人肚子饿了,七手八脚吃了街头一个老汉的一锅烘山芋,给葛正才知道了。拿下当铺后,葛正才叫人给那个老汉的锅子里倒一锅铜板抵山芋。十年前你采访那些见过葛正才的老人时,他们十有八九提及这件事。
潘尧比葛正才大两三岁呢,但他明白葛正才有智有勇比自己强,所以力主葛正才当头领。开始就十来个人,就两条枪,后来便挨个村子搜缴武器。有钱人家往往有几杆枪的,你大刀会单凭大刀片子奈何不了他们,现在你把他们的枪都搜走,他们没了武装力量,而你却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你得这么干,就得这么干。
那是在乌鸦山东面的一个村子里。你找村里年岁最大的老人,人家不知道你有啥用意,看你一个北方女子,也算面善,也就搭理了你。结果你问的那个热心老婆婆,领你去一个老房子。一位八十五岁的儒雅老翁从竹椅里站起来,一条黄狗猛地扑到你身上,把你吓得直哆嗦。幸好你身上没啥异味,那黄狗嗅完你的胸和腿,就朝你摇头摆尾好喜欢你。那位老人的父亲做过郎溪县的县长。郎溪县你知道么?太平天国的一个著名军事会议叫建平会议,就是在郎溪召开的。一八六〇年四月十一日,忠王李秀成于攻克建平镇的当日,开会明确作战方案,拉开二破清军江南大营的序幕。郎溪县城的所在地就是建平镇,离这儿七十五里地。老人承认见过葛正才,但明显讨厌讲这件事。还是那个老婆婆热心,她说她也见过葛正才,屈指算来,当年她虚岁八岁。
原来你问的是葛小妹啊,怎么不早说呢?葛小妹长得漂亮,小嘴巴,大眼睛,白皮肤,女孩子若有他那个样子,就能找到好人家。葛小妹骑一头毛驴,问我在塘里捞啥。我说这塘里有好多鱼好多虾还有好多枪,葛小妹叫人找来一个大脚盆,叫几个会水的下水摘菱角,摘红菱,摘乌菱。水性好的就潜入水中摸蛳螺摸河蚌,没想到会摸出一捆长枪来。我小时候人家就叫我快嘴婆,见到啥就讲啥,不会讲半句掖半句,不然心里难受。葛小妹来我们村的前一天晚上,我看见他们家──老婆婆指了指那位儒雅老翁──用油纸把枪捆起来扔塘里,就给葛小妹讲了,害得这老头见到我就讨厌我,三十年不跟我说一句话。葛小妹走到他们家,在他们家吃饭,就在这个老房子里吃。葛小妹搛芋头塞到我嘴里,还拍了拍我的脸,蛮喜欢我。后来我才晓得,葛小妹是来我们村找枪的,没费劲就找到了。村里人都说我嘴快,说我泄了王乡绅家的秘密。其实也不能全怪我,人家摘菱角摸螺摸蚌,就是我不讲塘里有枪,也会给人家摸到。他们家──老婆婆再次指了指那位儒雅老翁──好笨,哪能把枪藏到水塘里?除了枪,葛小妹还拿走不少书,全是他们家的书。那位儒雅老翁刚才还挺客气,挺健谈的,可一讲到葛正才的事就沉默起来,不说话了。还是快嘴婆婆好,她领你去下一个村子找一位九十五岁的老人,那老人不但见过葛小妹,还跟葛小妹一起破城放监,神气过一阵子呢。可惜这位老人已经耳聋,一句话也听不到。于是快嘴婆婆又领你去下一个村子,你就碰到了云将奶奶的二姐,那老太太讲到葛小妹的人要腐化她,要拉掉她的花裤子,她说她是葛小妹的亲戚,她的奶奶跟葛小妹的娘是堂姐妹。葛小妹闻迅赶来,把那人训了一顿,没给他腐化成。
云将的叔公在前面拿砍刀给你开路,你走在撒网顶的密林深处。如今山里人也是烧煤气,没人上山砍柴了,山上的树木也不许随便砍伐,绕山有高速路,山上也修了柏油路,所以没人走山间小道了。原先的麻石道儿,全废弃在荒草中。何况你要找的葛正才母子的墓在半山腰,原本就没路往那边走。云将的叔公叫啥名字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知道云将姓田,那么这个老人也应该姓田,叫田什么就忘了。当时是记在采访本上的,采访本给丢了。
你在暗无天日的密林走了半晌,以为田叔公找不到那两个坟头了,以为今儿白跑一趟没指望了,可田叔公却胸有成竹,只默默砍伐竹藤草木往前走,没半点犹豫。二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走到葛正才母子的坟墓跟前。当年田叔公毕竟年过七旬,爬这趟山自然感觉吃力,坐到柏树底下拿烟锅抽烟。你好怕起火烧了山林,田叔公说没事的。那烟末子就落在枯叶上,愣是着不起来。
眼前是两个高高的坟头,这已经使你觉得奇怪。葛正才母亲的坟在上头,葛正才的在底下靠右;小孩行孝心给大人抱脚呢。坟前有烧纸的痕迹,应是当年清明时节留下的。坟前的那块空地,也是有人定期割刈杂草的。你觉得奇怪,便问田叔公谁来这里扫墓,可田叔公竟摇摇头,他也闹不明白。田叔公抽了烟,有了精神,四周察看一番,才发现有一条路往底下通山涧。下山的时候,他领你走山涧回泥面岗。这条路不但好走,而且风景不错,有好几道没人看到的漂亮瀑布,有好几种不同的鸟叫声音,你在溪水间的石头上跳来跳去,还在水潭边捧到一条穿条鱼。
现在你才明白,年年给葛正才母子上坟烧纸的是葛正才的养子李宗祥。显然田叔公是知道李宗祥的,甚至知道李宗祥年年去扫墓,但没对你透露这个秘密。田叔公过世后,田叔婆只知道大窑路二弄五十七号有个叫李宗祥的人知道葛正才的事,但不知道她以前认识的那个火生伢,也就是葛正才母亲带大的那个抱来的男孩,就是李宗祥;甚至不知道火生伢是给潘尧带走的。田叔婆也见过葛正才,也见过潘尧,田叔公给葛正才当差时,田叔婆去麻园给田叔公送过她自己绱的鞋子自己缝的衣服,见到葛正才正在给房东人家栽秧哩,见到潘尧在谷场上教半大男孩习拳。解放前李宗祥担心他养父的仇人找他报仇,解放后又怯于承认自己是土匪的养子怕惹事生非,哪里想得到**********以后,会有人写文章讲他养父是农民领袖,给写到新县志里。
**********那么乱,没事还要给你找事,你父亲杀人如麻,造反派不打死你才怪。开始是学生娃娃折腾,号称红卫兵保卫毛主席,抄家烧书摔瓷瓶剪旗袍给男的戴高帽子给女的剃阴阳头,穿大闸蟹一样押几十个特务叛徒工贼异己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呼口号揪头发浩浩荡荡游街,武斗是后来的事。假如你给人家知道你的真实身世,你是九头鸟也在劫难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