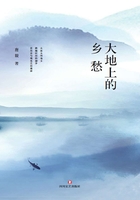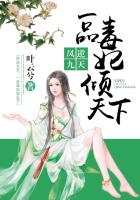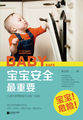如果说1920年代末茅盾的以《蚀》和《虹》为代表的“历史小说”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是“世界革命”的“宏大叙事”在中国的史诗式展开,那么卢卡奇(Georg Lukács, 1885—1971)有关马克思主义和小说的论述似乎为我们观察两者间的“接轨”提供了不乏启迪的连接点。这里主要指卢卡奇在1930年代中叶旅居苏俄时期写的《历史小说》(The Historical Novel)一书。此时卢氏已经皈依马克思主义,似乎已经否定了他早年在《心灵与形式》(Soul and Form)或《小说理论》(The Theory of the Novel)中代表欧洲人文传统的文学观,而较为自觉地运用无产阶级的历史意识作为小说分析的武器,且多少受到当时斯大林时期的文艺政策的影响。据《历史小说》中的一个主要论点,1848年革命浪潮席卷欧洲之后,随着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堕落,自19世纪初以来在小说创作中代表其历史进取的“现实主义”已经寿终正寝,如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的《沙浪博》(Salammbo)所显示,小说已沦落为作家主观表现和炫耀技巧的道具。在此同时,正如卢氏所热切期待的,由于无产阶级的历史意识走向成熟,“现实主义”小说应当焕发其青春,通过表现新阶级的革命意识把握历史前进的脉搏。
卢卡奇的这一论述对于茅盾及其所处的中国境遇有投亮之处。茅盾开始创作小说恰在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失败、共产主义运动坠落低谷之时,因此他对当代史追忆的叙述自觉地追求“时代性”,颇如当年的卢卡奇力图以世界历史“进化”的普世性作为真理的依据,继续推进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然而在具体的中国境遇中,这种普世化的过程,诚如“茅盾”这一笔名的偶然命名方式所暗示,他的早期小说写作同他的存在意识、浪漫情结和身份危机,同城市文学传媒和文学生产方式,同民族救亡的命运和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纠结错缠,呈现极其紧张的冲突与最终走向伦理与美学整合的过程。
卢卡奇认为,西方“历史小说”诞生于19世纪初,是受赐于法国革命的现代现象。以前的现实主义社会小说所描写的,是一种抽象时间中的历史,人作为个体的存在,其意识是先验的、超然的。法国革命与随之而来的拿破仑王朝的兴衰,首次使历史成为一种“群众的经验”。长期的社会动荡和战争,唤醒了各国的民族意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生活在共同的时代氛围中,历史事件与集体记忆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意识到自己与其所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现在,假如像这样的经验和那种认识——整个世界都发生同样的动荡——相联系,这就必定大大增强了那种感觉,即感到有这么一种可唤作历史的东西,感到它是一种不断的变化过程,最终感到它给每一个个人的生活带来直接的作用。”
同时革命增强了群众的历史主体意识,如法国革命中主动投入的军队与高唱《马赛曲》的群众,共同体验和分享一种民族情感,由是产生了民族的内心生活。这样的革命过程已经无形中拆除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界限,同时使社会底层的农民、小资产阶级等分享这种自豪的民族意识。“他们第一次感觉到法国是他们自己的国家,是他们自己创造的祖国。”“因此,在这种群众的历史经验中,民族因素一方面和社会改造的问题相联系,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联。这一对于历史发展特征的增强的意识开始影响到经济条件和阶级斗争的判断。”
卢卡奇是历史进化论的忠实鼓吹者。他关于历史小说的论说本身是“历史精神”的螺旋式开展,体现出强烈的当代性与意识形态。据他的叙述,欧洲启蒙思潮到法国革命一脉相承,代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方向。拿破仑一世之后,由于王政复辟,各国封建势力卷土重来,使历史进程暂遭挫折,但从反面证明了“历史必然性”。当然卢卡奇把马克思的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模式和阶级斗争理论看作历史发展的最终归宿,指出从法国大革命到1848年革命,资产阶级为自己制造了历史困境和反讽,即自己不再革命,而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卢氏这番诠释的历史局限是明显的,不仅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行将消亡的预言并未兑现,也表现出他对历史精神的理解——从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发展到后来的民族主义和阶级意识——历史前进的方向似乎愈益狭窄。尤其当他以阶级利益作为历史小说的批评标准,遂对19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偏见。
但与一般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卢卡奇没有陷入经济决定论。他的论述根植于德国浪漫主义哲学背景中,重视精神在历史中的开展与实现。他固然强调人受到经济、文化等社会条件的制约,同时也着眼于自觉的阶级意识对于历史创造的主动性。在这方面卢卡奇似乎更倾心于黑格尔的关于“世界精神”的说法。像马克思一样,他也批评了黑格尔的这种说法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上本末倒置,然而又称赞这种精神“体现了历史的辩证发展”。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精神否定自身,并必须克服自身,为自身的目的设置对立的障碍:进化……在精神中……是一种无休止的、艰巨的否定自身的斗争。精神所欲达到的是实现自身的理念,但它也给自身隐藏了这一理念,并在自身疏离中充满欣喜和满足……此时精神的形式已经不同于原来的形态,变化不仅在事物的表层上发生,而且在理念的内部发生。得到修正的正是理念本身。”或许正由于那种对于精神形式的内在演变的探究,使卢卡奇的《历史小说》在美学形式的诠释方面包含许多创见,远胜于某些将文艺简约为政治工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这里所谓的“接轨”,如果放到1920年代末中国的场景中,似将卢卡奇纳入了中国小说“现代性”的视域。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于民族危机而担当救国大业的说法,我们耳熟能详。史家常喜征引鲁迅所说的,“这革命的文学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但有趣的是,在“别国”的卢卡奇那里,中国人找到了同道。其实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基本信条,如人类理想的终极历史目标、评判作品的道德取向以及强调文学的济世功能等方面,与中国传统“文以载道”的观念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而卢卡奇的《历史小说》在以1848年为界强调“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断裂而呼唤无产阶级创造自己的历史小说,却包含着危机感,其中亦暗示他与正统马列主义的紧张关系。在宣称资产阶级腐朽衰亡的同时,另一方面对于小说中所反映的处于进步时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实即自18世纪以来欧洲启蒙思潮的那一番追本溯源,也多少针对当时苏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条化、公式化倾向及其意识形态的贫乏。卢卡奇的那种与小说俱来的危机感,可见于更早的《小说理论》(1920)。据他的追述,写作该书的最初冲动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焦虑中虽然也盼望大战能促使沙俄和封建德国的垮台,但对于人类文明的终极命运不禁黯然神伤,疑虑重重。
茅盾开始踏上文学之途,依稀地已将人类解放作为终极目标。1921年他接掌《小说月报》在文坛崭露头角时,已投入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成员之一。至20年代末,他的政治和美学立场几经蜕变,逐渐脱略了达尔文式的社会进化观或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式的地理、种族的文化观,进而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所武装。茅盾在20年代的文学之旅并不限于理论批评的领域,对阶级意识的一番体认来自于时代冲浪的实践。他在1926年掷笔从戎,赴广州参加北伐,次年7月至武汉,投入革命的“大洪炉”、“大漩涡”。但是,1926年3月发生“中山舰事件”之后,国共逐渐分裂,蒋介石乘机铲除异己,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茅盾因病滞留在牯岭山上,一时从前线退却,由此奇特地造成他的“脱党”,后来在上海卖文为生,在《小说月报》上以“茅盾”的笔名发表《幻灭》、《动摇》、《追求》(《蚀》三部曲),一举成名,却成为职业小说家。
茅盾的早期文学之旅比卢卡奇更惊心动魄,更富浪漫戏剧性。正是他的革命实践,尤其是那些载入史册的事件,如他所亲身经历的“五卅”和“北伐”,在他的历史意识的形成中、在他对小说动力的追求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痕。对于茅盾来说,事件不光成为他的小说主题,如何使事件得到可歌可泣的再现,成为锻炼其小说艺术的铁砧。围绕着事件,情节得以波澜壮阔地展开,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类型得以塑造。但同时事件被赋予某种悲剧的神圣性,却蕴含“历史必然”的目的。为茅盾所处理的事件,仿佛是民族的嘉年华会,眼泪和鲜血也无法阻止巨大欲望的凝聚和宣泄。那是一种“公共记忆”通过祭祀仪式般的艺术再现,使之成为永存于民众记忆中的历史丰碑。
然而,事件的悲剧性给作者带来道德的负荷,且如此强烈,以至生命中出现不能承受的时刻。极富吊诡的是,茅盾的处女作《蚀》及其稍后的《虹》,属于“革命加恋爱”的小说类型。与小说描写的那些轰轰烈烈、风云诡谲的历史事件——前者的1927年“大革命”,后者从五四到“五卅”——形影不离的,是一系列“时代女性”。如静女士、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梅行素等,皆有沉鱼落雁之貌,或娇媚幽怨,或飒爽英姿。这几部小说不光风靡当时,近年来也一再受到学者的眷宠,相形之下,许多茅盾后来的作品为之逊色不少。
看来茅盾写这类不乏市场效应的“江山美人”小说,乃一时之沉溺。写完《蚀》三部曲,即深悔其“颓唐”;嗣后发表《虹》意味着某种自我救赎,即摆脱梦魇而走向光明,其实通过“时代女性”的表现作者已建构了一套表现“时代性”的象征系统,这在1934年发表的《子夜》中得到验证。小说中“时代女性”不再作为主角,乃以全景式的气势批判地展示了社会生活的长卷,个人被贴上阶级的标签,其命运服从于历史的自我完善的意志,由此预言中国资产阶级的短命。《子夜》为文学史家一致推为反映社会真实和本质的“现实主义”杰构。它无疑表现了作者技巧上的成熟:类型的转折表明,凭借“描绘”的现代技巧,小说更成为一种“话语”;同时更表明意识形态上的成熟:担纲主角的是“历史”,主宰了史诗式叙事的内在动力。但尽管属于“过渡”形态,这些“革命加恋爱”小说,无论放在现代小说的谱系中,抑或放在作家的思想脉络中,却别具魅力。
很难想象如果小说不写男女之情,是否能不断生产繁殖。远的不说,“革命加恋爱”受惠于晚明“情”潮泛澜,亦接续了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的流风余绪,然而“为情而死”的才子佳人不得不置身于民族解放的革命伟业,却由不得在情网里几番挣扎。虽然“革命加恋爱”并非由茅盾独创,但他的史诗式叙事似乎汲源于“爱欲与文明”的古老传承,尤其是《虹》所开创的革命英雄“成长小说”类型,至1950年代更被发扬光大,产生像《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聂耳》等小说和电影。据王斑《历史表述的升华》的研究表明,对革命洪流中男欢女爱的描写,在历史哲学、崇高美学、性别政治和浪漫抒情之间所体现的张力,千姿百态,可歌可泣。
在某些作家那里总有些难解的谜,或许正是这些早期作品,构成茅盾的“蒙娜丽莎之微笑”。有关“时代女性”的创作动因及其义蕴,与他本人的政治史和罗曼史错综纠葛,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虽然,如本书所着眼的,比起同期的类似作品,这些小说最为酣畅而诡异地表现了作者对于中国小说现代性的执著追求。就形式方面来说,其文脉的复杂犹如革命漩涡的激流,但当“时代女性”最终通过幻美的虹桥走向革命,茅盾也在混沌中廓清自己的欲念,将形式与历史整合。尽管美学为之付出了代价,但不致付之东流,更确切地说也为革命“现实主义”铺垫了爱欲的河床。不管怎样,这些早期创作标志着茅盾由革命转向文学的终生选择,使之成为今日之茅盾,如王晓明譬喻的,犹如“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 不无反讽的是,这一选择却也决定了他暂时的政治放逐,或如传统文人式的多舛命途——他早年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直至身后方真相大白。
茅盾在20年代文学思想演变的脉络及其表述形态,由于政治上和理论上的不确定性,不可能达到卢卡奇《历史小说》般的清晰程度。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民国宪政与其说是立基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础石上,毋宁是理论先行,建立在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对西方政体模式的想象和选择上。不消说长期以来军阀当权,祸乱相寻,使宪政的实行困难重重;1927年之后,国民党政变导致蒋介石“党国”政治,共和宪政愈陷于艰难。其时国共双方都以“革命”为号召,争夺正义和正统合法性。茅盾的写作也须臾离不开“革命”,但它的意义远非明确的,有时“革命”如烟幕弹,闹不清姓共姓国。即使在30年代左翼作家笔下,“革命”的意义受党内形形式式路线斗争的制约,和毛泽东的农民革命相距甚远。茅盾的文学观从科学立场、启蒙理性到接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学说,某种程度上乃是五四以来激进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的逻辑延伸,“革命”更取决于一种道德立场,似乎从一开始就认定了资本主义及民国现存秩序掘墓人的角色。
如果卢卡奇合乎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所称颂的那种“世界历史性人物,即时代的英雄,应当被认作先知——他们的言行足以体现时代的精神”,那么茅盾也庶几当之。在共产主义阵营里,作为从事文学的,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曲折和磨难,但两人都始终忠实于自己的信仰和事业,虽然像卢卡奇在激烈的派系争论中“常常抓住机会撤回或修正先前的一些看法”。“二战”结束,卢氏回到祖国匈牙利,在后斯大林“解冻”时期,他担任过短命的纳吉政府的文化部长,纳吉随即被捕和处死,他遭到流放。直至1967年被重新接纳为共产党员,此后他的著作陆续在西方世界翻译出版,因其与正统马列主义的“异端”倾向而得到重视。尽管在国际上声誉日隆,但在本土被年青一代视为过气人物。晚年卢卡奇则孜孜回溯、清理自己的思想道路,完成《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皇皇巨著,似乎在歌德和马克思之间为他的哲学认同找到了归宿。相比之下,茅盾在五六十年代也出任过文化部长,并未像卢卡奇忽起忽落,甚至幸存于“文革”之后。他的早期共产党员的一段历史,可说在政治上及信仰认同上与他性命攸关。终于在他的晚年写成了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对自己有了交待。他在逝世之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组织上也对他有了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