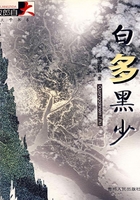从上述可以假定,知性趋向意识,本能则趋向无意识,因为所用的器具由自然造成,其适用的对象由自然提供,而且所获的结果也是自然原形,因此几乎不需要选择。在这情况下,表象内含的意识,每次刚刚出现,即为行为的实践所抵消。在此,行为与表象同等,也与表象同样重要。意识即使出现,它所照耀的与其说是本能,倒不如说是本能所显露的障碍。要言之,本能的不足、行为与观念的差距都会变成意识。由此观之,意识在此只是偶然;在本质上只强调本能的第一步,亦即强调从一系列自发运动踏出的第一步。反之,不足是知性的常态。蒙受种种反对,则是它的本质。知性的原初功能是制作无机器具,知性必须经过许多艰难,为这项工作选择场所与时期、形态与素材;而且,知性不会完全满足,因为新的满足又会产生出新的要求。总之本能和知性纵使都含有认识,但在本能中,认识也是当即显现的,无意识的;而在知性中,认识则是思考的,意识的。不过,这与其说是性质的差,倒不如说是程度之差。若只就意识而言,我们就会忽视知性与本能在心理上的主要差异。
要抵达两者的本质差异,可不必拘泥于明显照出这两种形式的内在活动的灵光,必须立即指向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对象,此对象是这些内在活动的适用对象。
马蝇在动物的脚和肩上产卵。这时,马蝇仿佛知道幼虫必须在马胃里成长,马舔身时,刚出生的幼虫会被带进消化管一样。膜翅类有使猎获物麻病的能力,它先以针剌猎获物的神经中枢,使其不能动弹,却不至于死。这方式很像博学的昆虫学者兼任熟练的外科医生一般。大概没有一种昆虫像常被谈论的小金龟子西达利那样无所不知了。这鞘翅类的甲虫,在名叫安特弗拉的蜜蜂所挖掘的地下道入口产卵。西达利幼虫一直埋伏在入口处,等待雄性的安特弗拉从地下道出来。安特弗拉一出来,西达利幼虫就咬住它,一直跟它到“蜜月飞行”的时候。雌雄双蜂交尾时,西达利幼虫就伺机从雄蜂移到雌蜂,静静等待雌蜂产卵。雌蜂产卵后,西达利幼虫就飞到卵上。卵在蜂蜜中,可助西达利幼虫成长。西达利幼虫不数日吃尽了卵,遂托身卵壳上,经历第一次变形。于是幼虫有了可以浮在蜜上的身体,现在开始吃蜜,吃完蜜即化为蛹,接着由蛹变成虫。西达利幼虫从孵化之初就仿佛什么都知道。它仿佛知道安特弗拉雄蜂会从地下道出来;仿佛知道蜜月飞行时有移至雌蜂的机会;仿佛知道只要吃些安特弗拉的蛋,以致变形,就可以浮身于蜜的表面上,而且可以杀死从蜂卵生出来的竞争对手。西达利自己仿佛也知道自己的幼虫懂得这一切。其中虽有认知,但这认知并不发达。在此,认知并未内化为意识,却外化为确实的步骤。昆虫显然不学而知某地某时某物存在或发生,并将其表象直接转化为行动。
若从同一观点考察知性,则知性也有不学而知的。但这种认知跟本能迥然而异。我们在此不拟重复哲学家在天赋观念上的陈旧论战,只想叙述大家都能认同之点。如幼儿可以立即了解动物永久不能了解的事物。在这意义上,知性跟本能一样,是可以遗传的功能,从而也是天生的功能。不过,此一天生的知性即使是一认知能力,在个别上也不能认知任何对象。刚出生的婴儿开始寻找母乳时,显示婴儿已知道还不曾见过的某种事物(当然是无意识的),但是天生的认知在此正是一定对象的认知,所以这不是来自知性’而是来自本能。总之,知性对任何事物都不会有天生的认知。如果知性天生就无任何认知,则知性非天生。知性既然一无所知,那到底能认识什么呢?——事物之外还有关系。刚出生的幼儿既不知特定的对象,亦不识对象的特定性质。然而,某天有人在这幼儿面前在某对象上加上某性质,在某名词上冠以形容词,这幼儿立刻就了解其意义。因而,幼儿自然而然就掌握了主语和属性的关系。这也可以用在动词所表现的普遍关系上,这普遍关系可由心智直接取得,所以一如没有动词的原始语言一样,语言可以不必表达此一关系。由此可知,知性已自然而然使用某物与某物的等值关系、所含与被含的关系、原因与结果的关系,亦即含蕴在主词、述词及动词(无论表现与否)所组成的文章里的关系。知性是否把这些关系当作个别的天生认知?这些关系是不能还原的关系呢?还是可归于更普遍的关系?这是逻辑学家的工作,然而,无论用什么方法来分析思考,最后总有一个或数个普遍架构。而且,心智(精神)自然而然使用了此一架构,所以心智对这架构而言拥有天生的认知。由此我们可以说,如果考察含有知性与本能的天生认知,则可知此天性认知在本能系趋向事物,在知性则指向关系。
哲学家在认知上建立素材与形式之分。素材系由原初状态的知觉能力给予;形式则是为构成认知体系在这些素材间所建立的关系总和。没有素材的形式,可以成为认知的对象吗?当然可以。因为认知并不是我们的所有物,而是我们习得的习惯。认知与其说是一种状态,不如说是一种方向。若然,则此为自然的注意倾向。学生知道要写分数,便在知道分子和分母之前先画了一道横线。以此观之,学生虽然还不知道分子和分母的数值,却已想起两者间的普遍关系。他认知了没有素材的形式。同样,我们常在经验以前,先知道一些架构,再用经验来填补,把习惯所承认的这两个语词用在这里。对知性与本能之别,我们可以给予较明确的公式。知性和天生这一点上是形式的认知;本能则包含素材的认知。
从第二个观点,亦即不是从行动,而从认知的观点可知,生命内含之力仍是有限的原理。这原理中起初有两种不同的认知方法共存,甚至可说有两种分歧的认知方法共存,而且互相渗透。第一种认知是在素材方面直袭特定的对象。这种认知是指“这儿有某物”。这两种认知不会个别袭击任何对象。这种认知是使某对象与其它对象、某部分与其它部分、某方面与其它方面发生关系的自然能力;也就是说,这只是从前提引出结论、从已知走向未知的自然能力。这种认知已经不说“是这个”,只说“如果条件是如此,则结论亦如此”。总之,第一种认知属于本能性质,哲学家以真言命题称之。反之,第二种认知属于知性,常以假言命题表示。这两种能力中,起初第一种能力似优于第二种能力。其实,如果这种能力分布于无数对象,则此能力必较优。但是,这种能力只适用于某特殊对象,但至少有内在而充实的认知。这种认知不显于外,而含蕴于可行的实际行动中。反之,第二种能力本来只有外在而空虚的认知。然而,正因为如此而有一种长处,那就是它有一个架构,可让无数对象交替放入。经由生命形态发展出来的力量是一有限之力,故在自然或天生的认知领域里,必须选择两种限制中的一种。限制之一是认知的外延;其二是认知的内涵。前者,认知是极其充实的,却限于一定的对象。后者,认知已无一定对象,因为此一认知是没有素材的形式,所以不包含什么。这两种倾向起初互相涵蕴,后因成长而必须分离。这些倾向都在世界中自求多福,分别抵达了本能和知性。
因此,知性和本能可由这两种分歧的认识模式界说,但此时已不从行动的观点,而从认知的观点观察。认知与行动在此只是同一能力的两种面貌,其实我们已经可以轻易看出,第二种界说只是第一种界说的新形式。
如果本能是利用自然性有机器具的能力,则本能无论对这器具或对其适用对象都必须含有天生的认知(当然是潜在的或无意识的认知)。因此,本能是对事物而言的天生认知。但知性却是制造无机——人为——器具的能力。某生物有了知性,就无需从自然获取有益于己的器具,因为这生物能适应环境,使自己的制作发生变化。因此,知性的本质功能是面临任何环境都能找到克服困难的手段。知性所追求的是最有益的东西,亦即最能切合已知架构的东西。在本质上,知性趋于所遇状况及其应付手段的关系。知性内含的天生倾向就是建立各种关系。这倾向还包含了某种对极普遍关系的自然认知。个别知性的固有活动都以这些普遍关系为基础,再从这基础来裁断较特殊的关系。因此,活动指向制作时,认知必然指向关系,这种完全形式化的知性认知比素材的本能认知具有数不清的优点。形式是空虚的,因此我们可以用无数的事物交替、任意地填补进去;甚至可以把毫无用处的东西填进去。形式的认知显现于世时,纵然以实用为目的,也未必局促于实际有用的事物。知性生物本身即内含自我超越的手段。
可是,知性生物并不像自己所期待,或自以为可能那样超越自己。知性的性格是纯形式的,缺乏必要的内容,以致不能置身于思索最关心的对象上。反之,本能有所希望的素材,但无法像知性那样到远处去探寻自己的对象。本能是不思索的。于是,我们触及了此一研究的重点。我们还要继续分析,以剔出本能与知性的差异,我们可以把这差异公式化。有的事物只有知性才能探求,但是只凭知性决不能发现这事物,只有本能才能发现,但本能决不探求遗事物。
知性的原初功能
在此必须先就知性的机构,探索其若干细节。如前所述,知性的功能是建立关系,知性所建立的关系具有何种性质,势须加以较明确的规定。如果认为知性是纯粹思索的能力,那不是观念模糊不清,就是失之于武断。如果这样,难免会把知性的一般架构释为绝对、不可还原、不能解释之物。我们天生就有自己的容貌;同样的,知性乃天生而具知性的形式。不错,我们须界说此形式,但也只能如此。因此我们不必去探寻这形式何以是这样的形式,而不是那样的形式。于是有人说,知性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也有人说,知性运作的共同目的是把统一导进复杂多样的现象中。可是,“统一”此语暧昧不清,比“关系”一词,甚至比“思考”一语都缺乏明确性,无法显现比“关系”等更多的内含。进而可以再反省一下,知性的功能与其说是统一,不如说是分割。如果说知性的活动是因为知性需要统一;知性追求统一只因为知性需要统一,那我们的认知已依存于心智的某种要求了,这要求也许跟现有者完全不同。如果知性采取别的形式,认知也就有所不同。如果知性不依存任何事物,那一切即需依存知性。如是则未免把知性抬得太高,而把知性给予的认知放得太低。知性一旦变成绝对,认知即变成相对。相反的,我们认为人类的知性常依存于行动的必要性。若能起而行动,知性的形式即从中导出。因此,知性的形式既不能还原,也不能解释。这种形式既然不能独立,我们也就不能说认知依存于知性。认知并非由知性所生,在某种意义上乃是实体的构成部分。
哲学家回答说:“行动是在有秩序的世界中进行的。此一秩序早已隶属于思考。行动以知性为前提,故以行动解释知性,犯了倒果为因的谬误。”如果这一章的观点是我们的决定性观点,他们的说法也有其道理在。如此,我们就与斯宾塞犯了同样的错误。斯宾塞认为,如果物质的一般性格可以还原为留在心上的痕迹,知性就可以获得充分的解释。仿佛物质内含的秩序就是知性本体!哲学可以试用什么方法追究知性与物质的真正起源到何种程度?这问题留到下一章再讨论。目前比较引起我们关心的就是属于心理学秩序的问题。我们所要讨论的是,物质世界中,知性较能适应的是哪一部分。要回答这问题,根本无须选用什么哲学体系,只要站在常识的观点上就足足有余。
先从行动谈起,并且把知性以制作为目的当做原理看待。制作完全以一般物质为素材;因此,若以有机物做素材使用,制作就不会理会形成有机物的生命,而把有机物当做无机物处理。在一般物质中,制作亦仅注意固体物。固体以外之部分皆因其流动性脱逸而去。若知性以制作为目的,则实体中的流动物只有一部分会逃脱知性之手,而生物中真正生命之物一定完全逃出知性之手。我们的知性是以无机的固体为主要对象。
只要逐一检视知性的能力即可知道,知性在处理一般物质——尤其是固体——时,最为轻松沉着。那末,一般物质最普遍的特质是什么?那就是广延。因有这特质,某一事物对其它事物而言是外在的;在该事物中,某一部分对其它部分而言,也是外在的。为了我们往后的运作,所有对象都可任意分割为许多部分,这些部分中每一个都可再任意分割,以至于无穷,这样做确实有益无害。但是,为了目前的运作,我们必须把正要处理的现实对象或分解所得的现实要素当做大抵已决定的事物,并视为惟一的单位来处理。我们谈到物质的连续性广延时,已经暗示物质可以随心所欲加以分解。然而,如所周知,这种连续性可归结于我们选择物质中所见非连续样态的能力,而这能力是物质给我们的。总之,一旦选择非连续性的样态,它就常以真正的现实物展现眼前,吸引我们的注意,因为我们现在的行动基准是来自此一非连续性的样态。以此观之,非连续性可以用非连续性本身来思考,也可以在其自体中思考。我们常借心智的积极作用来表现非连续性。反之,连续的知性表像勿宁是消极的,因为我们的心智拒绝把任何现有的分解体系当作惟一可能的体系。
知性只明白表现非连续性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