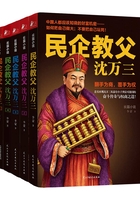又翻过一个年头,这年是1978年了,段东麒都二十八了,眼看着真的是要成老光棍了。两口子终日慌得都不敢看儿子的脸,最后他们商量着由段星瑞上趟山,到深山里找个穷人家的女儿做媳妇,实在不行就买一个下来给他做老婆。眼看着就要过三十了,三十了那就半辈子也过去了,活得还有什么意思?哪知道,段星瑞还没来得及上山给儿子找媳妇的时候,一个消息已经传到了安定县。****要大平反了。贺红雨的第一反应就是,活出头了,这辈子居然还能有活出头的时候。
儿子有救了。
平反摘掉帽子之后段星瑞又回了学校教书,还补发了一笔工资,段东麒也被安排了工作,去了矿上当了工人。这时候媒人们都纷纷踏进了她家的门槛来做媒来了。好像安定县里一夜之间忽然长出了这么多已经到了婚龄的姑娘们。以前她们都像种子一样不知道被埋到哪里去了。
介绍来的姑娘里段东麒看中了一个,是南街豆腐三的五女儿,刚满二十,名叫惠春爱。
贺红雨本来就对这媳妇不是很满意,因为她为什么不早点嫁给段东麒呢?就算她那时小,她的四个姐姐呢?还不是一个又一个地嫁给了外人?现在看着她家平反了,工资也补发了这才腆着脸送上门,说来说去还不就是图了个钱。那豆腐三又要了三百块钱的彩礼,贺红雨便觉得,这和卖有什么区别?段星瑞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块一毛钱,就要了三百块钱的彩礼,一年的工资。不过好歹就一个儿子,年龄大了,又是他自己看上的,贺红雨不好再说什么了,就捏着鼻子给他们办了喜事。
这年,还有件喜事就是贺家的老宅还给了贺红雨,因为贺家现在只剩下贺红雨一个人了。这样一来,娶了媳妇也就有了住的地方。贺家老宅已经破败了很多,柿子树和枣树都已经被砍了,只有那棵桃树这么多年里却又兀自长大了好多,已经浓荫匝地了。贺红雨走在这院子里的时候,便想起了父亲,老姨太太和贺天声。如今他们都不在了,只留下她一个人,把这空空的宅子也留给了她。她踩在青砖上的时候仍能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她甚至能听出贺天声一瘸一拐的脚步声。可是,他们都不在了,只有他们的魂魄还在这院子里久久飘荡着。她坐在桃树下久久地盯着那些虚空处看,就像是,他们还住在那里。有时候她看着看着,泪忽然就下来了。
她和段星瑞住在东厢房里,把西厢房给了段东麒一家住。正房做客厅,有人来了坐坐。唯独绣楼她没有动,一直上着锁。
段东麒在矿上上班,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段星瑞做了安定小学的副校长,白天去上课,晚上又被扫盲班请去做辅导。家里经常就剩下了婆媳俩。惠春爱自小就会编席子,嫁人之后照旧还编席子赚点零花钱。下午的时候,惠春爱在院子里编芦席子,编一张三毛钱,贺红雨在桃树下乘会儿凉,就到邻居家串门说话去。她说,我还给他们做?我做了一辈子还不够?伺候完这个伺候那个,我早晚要死在他们手里的。邻居就说,看着那媳妇倒也整天趴在灶台上做饭呢。贺红雨一声冷笑,撇着嘴看了一眼窗外,说,她倒想吃现成的呢,她挣下什么了?一看见我们家补发了工资就忙不迭地扑过来了——存心叫人小看。就她做的那饭?你去吃吃去,每天就喂猪打狗的。
她突然压低声音说,在娘家就没吃过个好的,什么都没见过,那来了我们家就是为着吃来了。吃了个罐头都攒着瓶子,回娘家的时候给她妈带回去。啧啧。邻居也拧起眉毛回应,啧啧。贺红雨磕了一只南瓜子,又说,慢不说她这么嫌贫爱富,就是她不嫌贫爱富,那儿子也不是她的,我这么多年怎么把他拉扯大的?1960年的时候脸都肿成脸盆那么大了,他爹还在大同的监狱里劳改,谁可曾照顾过我一指头的营生?谁看着我都觉得我活不了了,我还不是硬生生地活下来了?我熬到今天了她倒过来吃现成的?他婶,你说吧,天下还有这样的好事?什么都让她占了?可怜我两个闺女都没跟着我好活过一天。说着就扯袖子抹眼睛。
她现在最想念的反而是二女女,因为她知道,她欠她最多,而且再也补偿不了了。这么多年里二女女再没有回过家,生死未卜。女女一直就住在机床厂的单身宿舍里,没有再结婚,看样子是不打算再嫁人了。她开始还说她,后来知道没用了也就不再说了。当初女女嫁错人,也有她的一半责任。她还能说什么?让她再嫁错一次?
如果说遇到赵一海的时候女女回光返照了一次,那在赵一海之后女女就是彻彻底底地死心了。她把自己彻底堵死了。女女每天卡着点上班下班,出门买菜,回宿舍给自己做饭,就这样好几年也就过去了。这天,女女在路上突然又碰到了纪艳萍。纪艳萍的脸看起来忽然很生硬,她的脸是白的,唇是红的。她化了妆。那时候在一个县城的街头几乎看不到有人化妆。她们默默站着,正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时,纪艳萍突然说话了,赵一海回天津落户了,过段时间可能我也回天津了。听了这句话,女女宽容地笑着,把目光挪开了。这话听起来太陌生了,陌生得让她心酸。这样的话怎么能从纪艳萍嘴里出来?那样一个缜密得让人害怕的女人,可以把所有铁一样坚硬的秘密消化在自己的肚子里,把所有的事情不到最后一步都决不会说出半个字的女人,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除非,她,已经回不去了。
临走时,纪艳萍突然拉住了女女的一只手,她们认识二十几年了,这却是第一次,女女吓了一大跳,似乎握住她的,不是一只手。她的手冰凉苍白修长,像一尾粘湿的鱼一样落在了她的手上,跳跃着,喘息着,滑腻着。她牢牢地抓着她的手,悄悄地说,什么时候去我家吧。就在剧团的宿舍,你过去吧,啊?她用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叹词,啊?带些撒娇和祈求的语气,不依不饶地说出来了。她愈加慌乱地躲闪,纪艳萍却拍拍她的手,又说话了,你从小就觉得你比我强,比我漂亮,比我能唱会跳,可是,你真的不如我。我哪好意思和你说啊,现在我教你吧,我教你化妆,教你怎么穿衣服。我想起你那时候每天只知道穿绿军装就想笑……呵呵,你以为那就是漂亮?这句话带着挑衅直直扎到了女女最敏感的穴位,但她也笑,好啊,我哪天下了班就去找你去,你等着我。
女女是又过了几天才去找纪艳萍的。这几天里她特意向别人打听了一下。一个五分钟就可以走完的县城,想要忽略一个人容易,想要打听一个人却更容易。她才知道原来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只是她这几年因为忙于应付生活,竟一点都不知道。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她在潜意识里根本不想听到纪艳萍和赵一海的任何消息,如果他们过得好。事实上她真的以为他们过得好。
原来,剧团已经解散了,赵一海两年前就已经调回天津了,把儿子也带走了。那个曾经和纪艳萍一起在剧团的女人一边向女女描述一边皱着眉头,啊呀,你是不知道啊,她就生了这么一个孩子都不给他喂奶,她奶水足的和什么一样,就是不让孩子吃,让孩子喝羊奶。她是怕喂了孩子把乳房拉长了,身材就走样了。她那个孩子从生下来就没吃过她一滴奶,所以呀,和她一点都不亲,临去天津连哭都没哭一声就走了,就像没她这个妈一样。你说孩子都有了,还当自己十几二十岁地活,在胸罩下面垫那么厚的海绵,恨不得把胸挺到天上去。在我们剧团里,成天就是和这个男人那个男人眉来眼去的,恨不得把所有男人的眼睛都勾到她身上,都看着她。你看她走路那样,就像有拍电影的正跟在她后面给她拍一样,眼睛看着天上,不看人,和谁都处不到一起。其实人家赵一海啊,早看出她不是省油的灯,早不想要她了,回天津说是只能带一个家属,就把她放下,带着儿子走了。人家找了个借口说,回去以后活动活动,就把她调过去,傻子都能听出来这还不是骗人的?这不,人家回去以后,通过两封信之后就没信了,信也没有,更别说调动了。她还每天等着,人家说不来已经在天津又结婚了。她不把自己当这个县里的人,倒好像自己就是个天津人,迟早都要回天津一样。对身边的人从来都冷冷淡淡的,就急着想去天津。她这么等着自己也着急,这个人又特别心重,什么都不和别人说,我看她都不太对劲了。你别和别人说啊,你千万别和别人说。就我们剧团的人知道。她为了能调到天津,先是和我们团长睡,然后又和县委的什么书记睡,然后又和人事处的王处长睡。反正是和很多人都睡过了,结果都白睡了,也没见她去成个天津。女女静静地听着,一句话都没说。
第二天下了班女女就骑着车子来到了剧团的宿舍楼下。打听纪艳萍家太容易了。她随便问了个人,别人就指给她看,就那个窗户。声音里带着一点莫名的兴奋。她眯起眼睛看着指窗户的人,那人也看着她,目光明亮得像里面装了一面镜子。
她一步一步朝那扇门走去,周围的墙是灰暗的,颓败的,像舞台上的幕布一样在迅速地后退后退,灯火昏暗的舞台要开场了。她突然就有一种巨大的凄凉,几乎站立不稳。门开了,立在门框里的就是纪艳萍。一刹那,她以为是回到几年前她们住在学校单身宿舍的时候,那个晚上,她就是这样出现在赵一海的那扇门里,然后,她们四目相对了。她走进了纪艳萍的家里,四处张望着,她看到桌子上,柜子上都是厚厚一层灰,东西扔得到处都是。她想,一个女人住的家?纪艳萍很高兴的样子,说去给她烧水,打开了炉子又跑过来,把那天路上说过的那几句话重复了一遍,然后,很快的,她就把话题转向了她身上的衣服。她说,你看你,到现在了都不会穿衣服,你不能看着别人穿什么你就穿什么,不要跟着她们赶什么潮流,那时兴的衣服没几件是好看的。我那时候是因为家穷,没有人给我做衣服,我知道你们常在我背后说什么,那时候我就想,等着看吧,等着看以后吧,你们以为你们是什么,就你们那几件衣服就可以笑我?
女女没有说话,笑着看着眼前的女人。今天,她是第一次这么从容这么平静这么没有一点畏惧地坐在纪艳萍的面前。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今天来之前她就知道自己已经胜出了,她来,不过是看看她,看看她是不是真的已经和传说里一样了。来看看她像阳光下最后的冰雪一样最脆弱的高傲,看看她究竟坍塌成什么样子了。她真的垮了,无声地像雪崩一样地在垮下去。现在,她就在她的面前,当她想起自己的一切的时候,她突然明白她其实已经把这个女人垫在自己脚下了,因为,她连自己都不如。没有工作,没有男人,没有孩子。这些她都看到了,但是,现在,她为什么还是这么难过。她开始流泪,无声地,默默地。
纪艳萍坐在她对面,呆呆地看着她哭,一句话也不说。直到她止住哭声了,才小心地看着她,然后站起来,急不可待地拿过一只化妆盒,打开。她把那只弹扬琴的手伸进去,像是从箱子里取什么易碎的玻璃器皿。她极力忍住炫耀的口气,说,这是口红,这是眉笔,这是胭脂,这是香粉,这个可以擦在两腮。你看啊,我教你。她整张脸上都是波光闪烁的,像河底倒映着波光的石子,到处是波光,到处是水影。她举起一只口红向她做示范。她也不照镜子,就那么一圈一圈地在嘴唇上涂着。嘴唇越来越红,越来越厚,最后成了触目惊心的血色。
她一边慢慢涂一边看着女女,似乎女女是透明的河流,她在她的身体里可以看到自己的倒影。涂完了,她举着口红的手慢慢的,像只鸟一样垂了下去,有些颓然的,有些不甘的。她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地看着女女,其他的五官都暗淡下去了,只有这嘴唇却像木棉花一样燃烧着。她端庄地,严肃地让她看她的嘴唇,突然说,涂点吧,都八十年代了,给生活找点盼头。女人哪个是不爱红妆的。除非你不会。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挑着眉毛看了她一眼,开始描眉,打粉,抹腮红。女女看着她的脸一点点得鲜艳起来了,像一朵艳丽的植物在幽暗的空气里轰然开放。她一直坐在那里安静地看着她在那里给自己画,像坐在台下看一出戏剧。观众只有她一个人。其实,这几年里,她的观众就只有她一个人,如果没有了她在观看,她一个人在台上又有什么意思?她终究是孤独的,终究是落寞的,所以她最后还是要找到她。她不能没有她。她们之间隔了窄窄的一尺,却像有一辆火车呼啸着开过去了,每一节灯火阑珊的窗口里都是纪艳萍不同时期的脸。火车渐行渐远,面孔在变化变化,一直到最后,落在眼前这张脸上,再不动了。她喧嚣拥挤的嘴唇、眉毛和腮上的红晕都像站在一幅画里,在画里看着她笑。她不真实的近于可怖。
纪艳萍又站起来拉开了角落里的那张衣柜,刚一拉开柜门,就有衣服像水一样哗的汹涌而出。女女呆住了,她没想到她会有这么多衣服。衣服像花朵开败一样杂沓着残败着铺了一地,颜色互相浸染着,互相反射着,像块地毯。纪艳萍坐到了上面,她坐在一堆衣服上看起来小小的,像是这堆织物里生出来的婴儿。她拿起一件衣服,并不看女女,自顾自地说,看到了吗?这是用我以前的衣服改成的。又抓起一件,说,这件是我自己做的,这件也是。我从来就不管衣服有过时不过时的,我的旧衣服会比她们穿得更好看。你看看,你看看,这都是我自己改过来的。我把别人不要了的衣服也拿过来改,改成我自己的,这件衣服,看不出来吧,是拿男人的衣服改的。她正看着衣服的脸忽然抬起来了,无比清晰地对女女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超不过我吗?因为我比你用心。在上学的时候,在你们都笑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们都不是我的对手,你们算什么?我就知道有一天所有的男人都会喜欢我,就像在你和我中间赵一海只是喜欢上了我。她坐在那堆衣服上看着女女,就像在一条河流的中间遥远地寒冷地看着女女。
女女突然想说,那后来呢,那后来他怎么就离开你走了呢?突然觉得这是多么无聊啊,她宽容地笑着,什么都没有说。
女女说她该走了,纪艳萍突然又一把抓过她的手,这个你拿去用。是那只化妆盒。她又急忙抓起几件衣服塞到她手里,这个,这个,你都拿去吧,我多着呢。她的声音突然有些疲惫还有些哽咽。女女说,都给我了,你去哪里?她便抬起头,看着女女突然一笑,我能去哪儿?我去天津,过段时间就走了,你也许就再见不到我了。女女也笑,是啊,我怎么忘了,你是要去天津的。说完就往出走,纪艳萍也没再说什么。女女一步一步地下了楼梯,没有回头看一眼。走出好远了,她突然回头看了看那扇窗户,窗帘的水波里埋着一个影子,小小的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因为看到她回头,那个影子一晃就不见了。
第二天,女女上班之前突然掏出了那只口红,对着嘴唇细细地涂了一圈又一圈。然后再慢慢擦掉,唇上,唇周围却都留下了血一般的痕迹,像刚擦过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