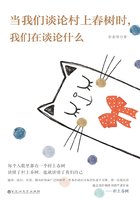民歌有时亦有偏于直白显露的不足,不似古典诗词那么蕴藉含蓄,耐人寻味。因而,在向民歌学习的同时,也要注意吸取古典诗词艺术上的长处,使二者融于一体,这也是探索诗的民族化上值得一试的。新诗经过20余年的发展,早已完全打碎了旧诗词的束缚。这时,回过头去,对旧诗词进行咀嚼,尽量吸取精华,其条件已完全成熟。稍后一点出现的阮章竞的叙事诗《漳河水》,便是在这方面所做的有成效的实践。
阮章竞,广东省中山县人,1937年来到太行山区,工作到全国大陆解放。他努力向太行山区民歌学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既有民歌特点又有古典诗词韵味的诗风格,创作过《圈套》、《妇女自由歌》等着名诗篇。1949年5月,他发表了长篇叙事诗《漳河水》。此诗叙述漳河边三位农村妇女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和解放后翻身的经过。荷荷、苓苓和紫金英,她们3人原先都希望能够有一位如意的丈夫。但是“断线风筝女儿命,事事都由爷娘定”,在封建包办婚姻下,荷荷嫁给一个富农,受尽婆婆丈夫的欺压;苓苓的丈夫是狠心郎,对她随意耍弄、打骂;紫金英更惨,过门半年丈夫病死,留下个“墓生孩”,从此守寡。
长诗的第一部就是3位女子对自己不幸生平的诉说,有如剪不断的哀丝愁缕,真是“声声泪,山要碎”;第二部写她们挣脱了封建枷锁,过上了自由幸福的新生活。《漳河水》是一曲妇女解放的赞歌,是以叙事方式写出的《妇女自由歌》。
《漳河水》因为也是采用了民歌的表现形式,在艺术上有与《王贵与李香香》相近之处。例如大量比兴的使用使诗的形象性特别加强,但它又有更为蕴藉的特色,因而抒情的意味更浓。如开头一段《漳河小曲》:
漳河水,九十九道湾,
层层树,重重山,
层层绿树重重雾,
重重高山云断路。
清晨天,云霞红红艳,
艳艳红天掉在河里面,
漳水染成桃花片,
唱一道小曲过漳河沿。
九十九道湾已甚曲折,复加以层层的山与路,山重水复,云烟缭绕,雾气茫茫,实在是一幅标准的水墨画。下面忽将水光染成一片红色,其中用个“掉”字,已见其奇,紧接着用“染成桃花片”来形容,更感奇崛、清丽。从诗的角度看,不断的复沓,层层逼近,婉转而又缠绵,蕴含着说不尽的情意。这段开头,通俗流畅,有民歌风;然诗情画意,水乳相融,又颇有古诗风味。这在写景的新诗中,不可多得。对新诗如何多方面的借鉴、吸收,以增强自己的表现力,也是有启发性的。
《漳河水》对叙事诗如何精细地刻画人物的心理,也有较好的尝试。《漳河水》的叙事方式,主要是通过诗中人物的直抒胸臆,因此人物既是诗所要描述的对象,同时又是抒情主人公。一方面有利于在叙事中抒情,另一方面在抒情中唱出了心灵深处的声音,因而有助人物形象的刻画。例如写紫金英的心理:
看尽花开看花落,
熬月到五更炕头坐,
风寒棉被薄!
灰溜溜的心儿没处搁,
水裙懒去绣花朵,
无心描眉额!
这里用极简练的诗句,把无所依托的寡妇的冷寂、空虚、辛酸、悲苦之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整个诗因为注意心理描写,而显得更细腻、精致。《漳河水》与《王贵与李香香》相比,除了保持着山野风姿,更为典雅一些。
比较重要的叙事诗还有田间的《赶车传》和李冰的《赵巧儿》。这两部诗的主题、题材有相近之处。它们分别描写了主人公蓝妮、赵巧儿遭受地主的蹂躏,后来得到翻身解放的故事。但《赶车传》不仅是表现妇女解放问题,它通过石不烂(蓝妮的父亲)赶车出逃,遇到共产党员金不换,在金的启发下后回乡与地主斗争,救出蓝妮,表明农民只有追随共产党才有出路。石不烂赶车寻求真理,多少还有点象征的意味。两部诗的风格,也属于“民歌体”。
《赵巧儿》更接近快板,不乏平易而优美的诗句,但总体上过于显露,一览无余。好的快板也是诗,但它毕竟与诗又有区别,如果不在学习基础上注重创造,就会影响作品的艺术质量。田间比较注意在学习民歌基础上形成自己一种新的风格。
在《赶车传》中,有些段落还可以看出这位诗人特有的急促的节奏中所含炽热的诗情。但《赶车传》的节奏不很流畅,它的诗句从二言到八言俱全,既踏不上格律性强的民歌、快板的节拍,又缺乏自由体新诗的“情绪的节奏”。人们读起来感到别扭,有损于诗的感染力,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弱点。此外,张志民虽未写像上面提到的这种长诗,但他以民歌风格创作了反映农民受地主残酷压迫、残害的《王九诉苦》、《死不着》等,也都是叙事性的。
文艺整风之后,作家和诗人们深入到人民群众中,接触到极丰富的生活素材,激发了诗情。这时,他们觉得首要的不是去抒发自己所受到的感动,而是赶紧去描绘群众的苦难以及他们的斗争、胜利和欢乐。学习民间文艺有利于表现人民生活、感情,他们去创造更多叙事诗,并取得丰硕的成果。叙事诗的成就高于抒情诗,是这一时期解放区诗歌创作的一个特点。
用民歌形式叙人民群众之事,作为一种创作风气,必然会影响到抒情诗。以往抒情诗运用得最普遍的是自由体,不可能全用民歌体来代替。因此,在抒情诗领域中,诗人的风格是比较多样的,还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一是在抒情诗中,歌颂的比重大为增加。第二,不少抒情诗也带有叙事的特色,虽然没有突出的人物形象、完整的情节,但往往歌唱的是“事”。第三,学习民歌、改变诗风是明显的趋向,不论这种变化是否都适合于每一位诗人,但主动地改变自己已成的风格,以便通过学习民歌来促进诗的民族化,使其更接近群众,这种愿望是值得肯定的。诗风变化过程中,难免会有不成熟的东西出现,甚至还会有失败,但为探索新诗的发展留下经验教训,也是有意义的。
本时期解放区最有影响的抒情诗人还是艾青和田间。艾青在1942年发表了《献给乡村的诗》、《向世界宣布吧》。后者以饱满的热情,歌颂解放区的生活,与《黎明的通知》、《毛泽东》等同属于一组诗。不久,他便开始进行表现解放区人民生活的尝试,并且还写了一些揭露德日法西斯、歌颂抗战胜利、歌颂翻身农民的诗。田间在这个时期相继写了那种短小精悍、形象鲜明、鼓动性很强的短诗。他还写了不少小叙事诗,往往抓住一些片断,以小见大地反映人民群众中的人物。其中5首名将录,描写聂荣臻、贺龙等几位将军,就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诗作。他还为根据地着名的子弟兵母亲戎冠秀写了长诗,即《戎冠秀》。晋察冀诗人群的其他诗人,也都相继写作不少较好的诗。既有保持饱满政治激情,又十分凝练的街头诗,也有着意学习民歌、具有清新活泼风格的诗。曼晴的《打野场》描写大生产运动的波澜壮阔,
打,
打,
打野场,
打了谷子打高粱;
东风里簸,
西风里扬,
簸扬的谷子金样黄。
像风吹麦浪一般,上下起伏,形成了跌宕,跳荡的画面,既表现了打场劳动的节奏,又表现了劳动者的欢乐愉快的情绪节奏。还有象陈陇的《地雷歌》,已完全和工农群众创作的民歌、快板一样明朗、晓畅、生动、活泼了。以工农群众的口语入诗,对整个新诗创作发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此时,即使是自由体的诗,其语言也很少再有那种欧化的洋腔了。
这时创作上较努力的诗人还有严辰、鲁藜、戈壁舟、肖三、公木等。他们也更多地在抒情诗上下功夫。有的诗人,象郭小川、贺敬之等,虽然这时成就还不突出,却为建国以后在诗创作上的成功做了准备。但总的说来,1942年以后解放区诗歌中,抒情诗的成就不及叙事诗突出。
解放区的散文及报告文学
在散文领域中,抒情性散文和议论性散文的成就也远不及叙事性散文。解放区作家曾就写作杂文的问题发生过争论。这个问题与“歌颂还是暴露”密切相关。一部分作家曾提倡杂文。
丁玲在《我们需要杂文》中批评了解放区不宜于写杂文、只应反映正面生活的意见,她认为:“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所有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则仅仅把杂文当作是暴露黑暗的手段,似乎杂文总是与“可怕的黑暗,和使人恶心的恶毒的脓疮”连在一起。因此,对新的时代环境中如何正确地运用杂文,未能给予正确的解答。罗烽自己创作的《嚣张录》,就常常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激情绪。
金灿然在《论杂文》一文中,也认为杂文的时代没有过去,而且当民族斗争白热化、阶级斗争正微妙曲折地进行着的时候,杂文这形式“正面对着辽阔的发展前途”。但他认为杂文不应只是暴露黑暗,也应“贯穿着一种对于光明的礼赞”。所以,要求“杂文的题材、内容、格式、对象等等的随着时代及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易,只有这样,杂文才能发展,才能适合于战斗的需要”。他还认为不能说讽刺是杂文的灵魂,杂文的灵魂是立场。在文艺整风运动开展以前,前一种主张曾有较大影响,但当时运用杂文暴露解放区的问题、讽刺革命队伍中的同志时,确有某些偏差,并未产生思想上、艺术上都有较高质量的作品。到了文艺整风开展以后,一些有错误偏向的杂文受到了批评,后一种意见便占了上风。当作家们深入群众,致力于表现解放区生活的光明面,要歌颂那“黎明的微光”时,在散文领域里,杂文便不发达,这就更显出报告文学的一枝独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