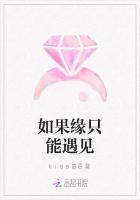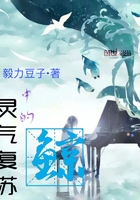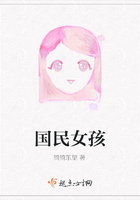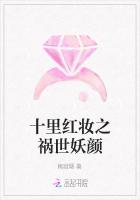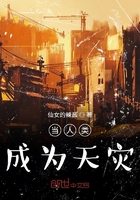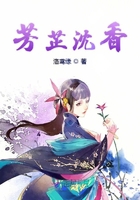王先生的小女儿送我们下楼,她在华东师大念中文系,一路上我们便交谈起来。她说,父亲的信念很坚定,他爱党,爱社会主义完全出自内心的真切感情。因为他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又到过不少西方国家,所以有比较、有体会。他从自己亲身经历中深深感到新中国好。是的,诗人的心已和人民牢牢绑在一起了,因此他由衷地唱出:《祖国,我是永远属于你的》。
我把你大块大块地
含在嘴里,
就像是洁白如玉的油脂一样,
生怕它溶化了,
因为你是属于我的!
看见有人用手指指着你讲话,
我就生怕你遭受伤残,
就像手指要戳进我的眼睛,
我是爱护眼睛一样在爱护你,
因为你是属于我的!……
原载香港《文汇报》1982年1月17日
布帆无恙挂秋风
———辛笛剪影
冰夫
一
辛笛是我尊崇的前辈诗人。不久前,一个春雨初霁的傍晚,他和我们中青年诗友在太湖洞庭东山访问。辽阔的湖面上,升腾起淡淡的薄雾。耸立在湖中的一座小岛,青色的山峦上,浮动着轻纱般的云影,恰如童话中仙山似的迷离神奇。就在小岛的远处,飘荡着无数小小的黑点。黑点越来越大。那是船,扯起篷帆,鼓荡着长风的船正在航行。此情此景,我不禁想起辛笛作于1934年的那首脍炙人口的《航》:“帆起了/帆向落日的去处/明净与古老/风帆吻着暗色的水/有如黑蝶与白蝶……”这首佳作,境界新颖,节奏感强,一种恬静、清晰的意象表现得多么自然,诗的格调明朗达观,富于哲理。
我第一次读辛笛的这首诗是在1948年深秋的上海,那时我在一家商行当实习生。同伴中有个姓刘的爱好文学的青年,他不知从那里弄来一本《手掌集》。我们深夜躲在堆杂物的仓库阁楼上,就着昏暗的灯光读这本诗集。也许由于我常常思念石头城外的故乡,所以非常喜欢《怀思》:“一生能有多少/落日的光景?/远天鸽的哨音/带来思念的话语;/瑟瑟的芦花白了头,/又一年的将去。/城下的路是寂寞的,/猩红满树,/零落只合自己知呢;/行人在秋风中远了。”读着读着,常常引起我孤独的旅愁和思乡的泪水。而我那姓刘的同伴,对《航》和《款步口占》《垂死的城》等诗赞不绝口。那时,《手掌集》陪伴我们度过无数个疲乏之夜。三十年以后(1978年)的春天,在上海作家协会诗歌组的一个座谈会上,我才第一次见到我爱慕已久的老诗人辛笛。他朴素的服饰,和蔼可亲的长者风度,声音有些沙哑的发言,在激动时挥舞手势所强调的纯真的诗人气质,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我们经常见面,在一起开会,谈诗,研讨时事,议论人生。去年5月,他应邀出席加拿大召开的第六届国际诗歌节之后归来,在“文艺会堂”一个六七个人参加的小会上介绍情况,说得极其平易简单,毫无修饰炫耀之词。倒是从他带来的一大叠影印材料中,我们看到加拿大的一些报刊,对他参加国际诗歌节活动作了一系列报导并介绍他的诗作。5月6日晚上,在美丽的多伦多城湖滨多元文化中心贝狄根厅举行诗歌朗诵会,来自中、英、美、法、德、意、西班牙、新西兰、智利、匈牙利等和东道国的诗人与各界人士纷纷参加。辛笛用英语和汉语先后朗诵了自己的八首诗作和艾青的《维也纳鸽子》与《柏林墙》,博得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二
辛笛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以创作优秀的诗篇而登上诗坛。他1912年生于天津,祖籍淮安,父亲是清朝末年的举人。幼年读私塾时,他就酷爱唐诗宋词,考进南开中学后,更醉心于五四运动以来的诗文。他曾说:“唐诗对我影响最大。我激赏杜甫、白居易、李义山的作品。宋代诗词中,我最爱苏东坡、陆游、周邦彦、姜白石以及清代的龚定庵等人。”他1931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更多地接触到西方文学,学习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诗歌,如英国湖畔诗人以及法国象征派,但对他写诗发生过较大影响的是现代派的艾略特、霍布金斯、奥登等。那时候,他经常到三座门大街巴金和靳以创办的《文学季刊》编辑部去玩,在那里结识了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卞之琳与何其芳等同辈诗人,并应邀为卞之琳主编《水星》月刊撰写诗稿。他还曾经为《大公报》和《国闻周报》翻译过波特莱尔的散文诗和莫泊桑、迦尔洵的短篇小说。“九·一八”以后,东北沦陷,民族危亡,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参加了清华地下党领导的外围救亡活动,在蒋南翔任总编、姚克广(姚依林)任副刊负责人的《清华周刊》,主持文艺栏的编辑工作。他在《垂死的城》中说:“暴风雨前这一刻历史性的宁静/呼吸着这一份行客的深心/呵,是谁/是谁来点起古罗马的火光/开怀笑一次烧死尼禄的笑———”据诗人的好友袁可嘉解释说:辛笛这儿说的尼禄自然是指独夫民贼蒋介石。辛笛在回忆清华园的这一段往事时,曾感慨地说:“总之,这已经是近半个世纪左右的故事,说是褪色的玫瑰也罢,但在回忆的烟云里,总还有一点余香犹在呵!”
1936年夏天,诗人“不愿待见落叶纷纷,径自与这垂死的城(北平)相别”,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英国文学。1937年艾略特来到爱丁堡大学接受文学博士名誉学位,举行莎士比亚讲座,辛笛当时直接听了他的课。另外,辛笛在英国还见到了路易士、史班德、缪尔这些受人称颂的诗人。这对他是个很大的鼓舞。可是这时诗人的心是充满了忧虑的,因为抗战的火焰已经燃起,日本侵略者在鲸吞着祖国广大的土地。诗人说:“谁能昧心学鸵鸟/一头埋进波斯舞里的蛇皮鼓/就此想瞒起这世界的动乱”。而在一个阴寒多雨而草长青的地方写的《门外》一诗,如果不是深深体验过羁旅异乡、尝遍寂寞之苦的滋味,是不可能描绘出这种独特深邃的意境的。
辛笛在1939年回国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教授。上海沦陷后,各大学停办,他改习银行业谋生。虽然没有投身抗战的伟大行列中,但他在上海闭门索居期间,除了和郑振铎徘徊于中西旧书肆外,心情是异常沉痛的:“伤心犹是读书人,清夜无尘绿影春。风絮当时谁证果,静言孤独永怀新”(《夜读书记》前言)。
抗日战争胜利后,诗人的“银梦在死叶上复苏,于是在工作的余闲,我重新拾起了文字生涯。”辛笛这时不仅参加反蒋反内战的中国民主同盟,从事民主运动,而且任《中国新诗》编委、《美国文学丛书》编委。艾青曾说:当时,“在上海,以《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为中心,集合了一批对人生苦于思索的诗人:王辛笛、杭约赫(曹辛之)、穆旦、杜运燮、唐祈、唐、袁可嘉以及女诗人陈敬容、郑敏等。他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采取了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画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中国新诗六十年》)近月,他们当时的代表作品已编成《九叶集》出版,在国内外引起热烈反应。四十年代的这许多珠玑作品,如今已沐浴在灿烂的阳光里。
三
今年春节前夕,辛笛从香港讲学回来,我曾去看望他。他拿出一叠剪报和资料给我看,并简单介绍了他去香港讲学的情况。去年12月底他应邀参加由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辛笛在会上宣读了《四十年代上海新诗风貌》的论文。中文大学教授余光中在会上宣读的论文题目为《试为辛笛看手相———〈手掌集〉赏析》,对辛笛的这本蜚声中外诗坛的诗集,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辛笛虽然在诗坛沉寂了近三十年,但是他过去写的诗一直在海外流传着。
辛笛曾说,他的诗比较讲究光色明暗的运用,有的诗用音、色的重复和变调来表达情绪和节奏。例如《杜鹃花和鸟》:“年年四月,勃朗宁譹訛怀乡的四月/雾岛上看见此花肥硕与明媚/(呵,迢迢亦来自古中国)/便招邀起我心中/故国故城里此鸟的啼声/你知道,悲哀同命/而我是一个道旁的哑者/依然倔强不低头/今天独在空山中无事奔跑/心乱翻成故意来寻/草地里的流泉水。”诗人用“此花”“此鸟”和自己“悲哀同命”。远在异国他乡,看见杜鹃花开,听见杜鹃鸟啼,发自内心的自问:“迢迢亦来自古中国?”因为在故乡江南的四月,杜鹃花开遍山谷,深山里不时风送着杜鹃啼归。诗人说:“感谢你多情告诉我也南来了/可是你与我一样而不一样/因为你是过而不留/在月明中还将飞越密水稠山。”辛笛,这个旅居异域的青年诗人之悲秋,运用古典诗歌中“等是有家归不得,杜鹃休向耳边啼”的意境,改造创新,赋予并不多情的自然景物以“多情”,而画龙点睛地突出一笔:“我这个海外行脚现代的中国人/对你无分东西都是世界”。谓“多情”而实无情,鸟的自在鸣唱实在是诗人悲哀而不“同命”的反响。这首蕴藉隽永、委婉动人的短诗,在技巧上运用声音的转折回响,形象的反照、迭变,达到了“状态出神,联想自由,沉思的活动溢满情感的色彩,旋律跃动不定”的艺术效果。
辛笛多次对我说:“诗,要从真情实感出发才能写得好。我认为:作为一个诗人,应该有‘七情六感’,才能写出好诗。我特别强调六感:真理感;历史感;时代感;美感;形象感;节奏感。一个诗人,如果缺少了这六感,或其中一个,都不能写出好诗。艾略特在著名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文章中提到,诗人创作总离不开他的传统,没有历史感的人不能写诗。我认为他讲得很好,但还不够,还应加上时代性、社会性才对。所谓时代性,就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为人民大众服务,鼓舞人民前进。”
辛笛经过两段沉默的时期(抗战时期在沦陷的上海闭门索居和建国后从事工业工作)之后,随着祖国春天的降临,他重新焕发了青春,寻找到了“失去的春花与秋燕”(《狂想曲》),恣意挥毫,纵情歌唱,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近百篇抒情诗和散文随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编定他的诗集《春韭集》,年内即将出版。王辛笛虽年已古稀,但精力充沛,他除了写诗外,正以部分时间翻译狄更斯的一部长篇小说。祝愿我敬爱的前辈诗人像太湖上鼓荡着雄风的金帆,疾飞迅驰。
原载《文汇月刊》1982年第4期
辛笛和掌上风景
秦松
我们已无时间品味传统
我们已无生命熔铸爱情
我们已无玄思侍奉宗教
我们如其写诗
是以被榨取的余闲
写出生活的沉痛
众人的你的或是我的
这是辛笛写在1948年的《一念》之间的几句话,《一念》在我看也可能就是从那时起,到今天的他的写作的注脚。他写此诗的心情,他自己说:“早上起来/有写诗的心情/但纸币作蝴蝶飞/漫天是火药味……”他在《一念》里的主张:
我们在生活变成定型时就决意打破它
我们在呐喊缺乏内容时就坐下来读书
但是,他并不主张读“死书”:
革命有诗的热情
生活比书更丰富
他在《一念》最后一段说:
如果只会写些眼睛的灾难
就呵责众人献上鲜花鲜果
当作先知或是导师供养
那我宁愿忘掉读书识字
埋头去做一名小工
这是他创作与生活的态度,今天还是有其现实的意义吧!
辛笛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反传统者,一个革命者,在创作与生活的深切内涵里,不是空泛的呐喊。他与他同年代的作家一样,也沉默了很多年。
爱好新诗的人大都喜欢辛笛的诗,并不太了解辛笛其人。有时作品和人是不能分开的,而被分开了。
辛笛的《手掌集》具有多面的象征性,写诗的和读诗的人都十分喜欢的。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过一本《珠贝集》,四十年代出版过一本《手掌集》,十年余才出版一本集子,不是多产,只能说是“少产”。《珠贝集》已湮没在时间的海洋里,只有《手掌集》还在一些人的手上。
一本《手掌集》已掌握了许多人的诗心。经过很多转折,曾经隔海影响过和间接的推动台湾和海外的诗运。
辛笛的手掌似乎有一种魔力,也有一种魅力。在海外大部分写诗的朋友,回去如果到了上海,都要去看看他,你不去看他,他也会来看你。他热心于诗,更热情款待写诗的人。令人感动,令人尊敬。
他在他那个年代,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之间,是一位可敬可爱的诗人,从现在向回看,更是如此。从一本《手掌集》,从《手掌集》里的几首诗,给人很深的印象一直到今天,辛笛有辛笛的独到之处。但是,在某一个年代,又是被忽视的诗人。知道的人并不多,流传也不广。
诗本来也就不像小说那样,可以到处流行。再加上历史的灾难,岂仅是辛笛,岂仅是诗人和诗的悲剧?所幸他的《手掌集》还是流传在与他有相同的手掌的人之间。
读过辛笛的诗很早,对辛笛的人所知不多,在我去夏回国前与他从未有过联系。在回国旅行访问的最后一站,到了上海首先接触到的就是他。他和另外一位徐钤先生到车站来接我们,令我意外地握到他的“手掌”,欣喜之余也感到不安,他已是七十岁的、高年的前辈。在中国的习惯应当称他是辛老、王老,我称他辛笛先生,很多的时候,都称王先生。辛笛本名王馨迪。1912年生于天津,原籍江苏淮安。
从车站与他相遇,在上海七天,每天都和他有数次晤面。一切都承他的照顾与安排。像他写诗一样的完整而美好。
满头白发、满面春风的辛笛,精力旺盛,话锋亦健,我们在盛夏的上海,茂绿的街路上走过很多趟,兴味盎然,我总过意不去,他意犹未尽。他在上海很多年,说着略带天津口音的普通话,偶尔也插上一点“外来语”。他之关心人和好客到了极致。和他一起好像读他的诗一样享受。
他的热情比许多年轻人还要热情,因之,令我想到,在上海如果未遇到他,不知将如何?他是一个真人,一个纯粹的诗人。我已经很多年不用“纯粹”这两个字,但是,遇到像他这样的人,不能不用,再没有其他适当的语言。
很奇怪,在国内像他这样亲切、坦诚、自然又自如的人,不是没有,好像不多。我是说,在国内确是有不少大大小小的文艺官。对我来说,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能“深交”,而能有深刻的认识,可以相通已经是难得了。
辛笛不仅能相通,而且能通到相通的深处。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语言,虽然他比我年长二十岁。在某些艺术观与创作观,超越了他同年代的人,也超越了时空,他给我这样一个可贵的印象。与他的作品得到了印证,什么人才能写出什么作品。辛笛是一个至性至情的人,我常常以此来要求别人,对于辛笛,他在这种性情上也是我的前辈。
在上海那几天,刚巧有一位居住在香港的写诗的老朋友,他先我而到,也是一位真人,我想写诗的人都应当是真人。真和真在一起,才是真的开怀畅快,有酒且乐,无酒也乐。我们欢聚数日,引发了辛笛的诗兴,比我两位少了二十岁的人更快。辛笛在他离开前赠他一首,又在我离开前赠我一首。不仅是他赠诗之可贵,是他创作的热情与活力更可贵。
诗人之外,他是政协的委员,也是上海作协的理事。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专业作家?我在国内遇到一些专业作家,比他要年轻得多,像我这样的年纪,有的比我还小,已是老气横秋令人难以想像,与辛笛成为一个对比。使我直觉地感到,搞文学的也有“当权派”。作家当权以后也是同样的出“毛病”。人不健康,如何要求作品“健康”?也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