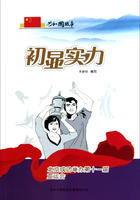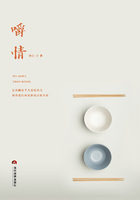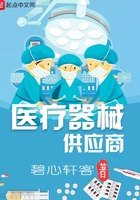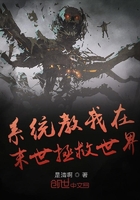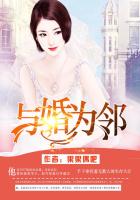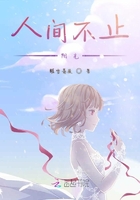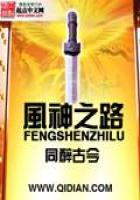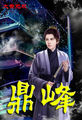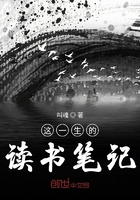1941年,正在大学里教书的辛笛老,突然转入银行界工作。这又是一次转折。其原因,因为他很少向人提及,至今仍使海内外关心他的人士不解。叶维廉发表于台湾《联合文学》第五卷第二期的文章中,对此也只是简单地写道:“1939年回国,任上海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教授。其后转在上海银行界工作。”并未道出其根由。辛笛老在最近和我的一次谈话中,才使我明白了事情的原委:“那时上海已沦为‘孤岛’。许多文化人都上了敌伪的黑名单。我是大学教授,又常常写诗,自然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为了免遭不测,不得已才转入银行界工作。”这次转折,也使他第一次暂时脱离了诗坛。但他并未沉寂。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他采取另外的形式,与当时隐居于上海的郑振铎(西谛)先生一起,为抢救祖国珍贵的图书典籍做了许多工作。那时,郑先生从福州路书肆中搜求到八九百种清代文集,却无钱购买。经过辛笛老的一番周折,终于得到银行的居停主人的慨然资助,才使这些清代文集得以完善地保存下来。这一时期,与其说是他告别诗坛,还不如说他在思想、艺术上的修炼和积聚,为以后的创作高潮的到来做准备。果然,“抗战胜利后,银梦在死叶上复苏”,他“才又拿起了笔,重新开始写下了一些新作”(《辛笛诗稿》《自序》)。这就有了至今仍令海外许多诗界人士难以忘怀的《手掌集》中的名篇佳制。他之成为“九叶派”诗人之一,也正是这个时期。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辛笛老的生活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正如《联合文学》那篇文章里所写到的:“1949年的政治变动,辛笛与夫人原已在香港并打算接管香港某银行;但当大部分人都往外逃的时候,辛笛和他的夫人反而向大陆飞,要为新中国献身。”在该文作者看来,也许是难于明白的,如果联系到辛笛老一贯的爱国思想,他之选择这样的道路也就不足为奇了。还是在那篇文章里,不是也记述过辛笛老对他说起过的,早在三十年代,他“跑到国外去念书”,虽然能“学新知,欣赏异国情调,但来了,空虚得很,走了千里万里,并不为异域的魅力所动容。我还是无法忘怀当时凄凉的故国河山”。更何况,到了四十年代末,他的思想和生活信念更前进了一步呢!
颇富有戏剧性的是,1949年在北京出席第一次文代会之后,辛笛老为了响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号召,要深入生活,投身建设事业中去,竟又一次来了个重大的转折,竟转到工业战线去工作。这一转便是三十多年,中国诗坛从此找不到他的踪影。但他也恰恰因为这样一转,远远地离开了文艺界这块最惹事生非之地,免却了后来许多人都遭受过的政治灾难。至于“文革”那是人人都逃脱不了的,但因为他那时已不是作家和诗人,故相对而言,他也比其他人少受了皮肉之苦。也因此,他这件“文物”,才得以保留下来。
我并无意在此叙述辛笛老的历史。历史是每个人都有的,而个人的历史和国家、民族的历史紧密地联系着,与时代和社会的兴衰际遇相关连。辛笛老的历史称得上是复杂而特殊的。命运好像是有意和他开玩笑:一方面,使他避开了无数个政治漩涡,“躲”过了许多人为的灾难,很有点“吉人自有天相”的意味;而另一方面,又硬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和他心爱的诗神缪斯分割开来,若即若离。而他个人的升降浮沉,似乎也从某一个侧面,反映了国运的异常及世事的变迁。我不知道,也不懂,这无论是对他还是对于中国诗坛来说,究竟是有幸或不幸,是“祸”还是“福”。但不管怎样,这种变幻无常的人生经历所造成的矛盾心态,是早已深深地刻印在他的诗作中了。叶维廉认为:他的诗“流露着当时知识分子的心境是这样的:一面要追求高洁的人性和纯粹的美,而保持一种倔强,一种固执,发出对高洁和纯粹的颂赞,一面又有些无奈。”此话颇有见地。其实,岂止辛笛老的诗是如此,如果将这段话移用来概括辛笛老一生的曲折变化,我以为也是非常确切的。
新加坡诗人原甸曾写过一篇文章:《辛笛是怎样活过来的?》。文中这样写道:“一定要乐观,他就是凭着乐观捱过了‘反右’,凭着乐观捱过了‘文革’……”其实,在我看来,这“乐观”之中还掺杂着某种苦涩的滋味,只不过,一般人难以品辨就是了。辛笛老曾经对我说过:“我对什么都很想得开。‘文革’时抄家,抄就抄吧,挨斗,斗就是了。我不是也活过来了么?”此话固然不失其豁达和开朗,不是也有那么一点无可奈何的意思在内么?
辛笛老从自己一生的经历中,“深深体会到‘做人第一,写诗第二’”。确实如此。纵观他的一生,诗诚然写得不多,但他做人却始终是堂堂正正,行得稳,站得直,从未对任何恶势力卑躬屈膝;虽然未曾有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壮举,也说不上大起大落,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爱国爱民,忧国忧民却始终如一、一贯到底。在这些方面,他的名声正如他的诗作一样,早已传遍海外。去年,我去新加坡开会时,许多诗界朋友纷纷向我询及他的近况,对他的为人和诗艺称赞不已。不知为什么,我当时竟突然会联想起中国大陆甚为流行的一句广告用语:“外转内销”。辛笛老于十年前的重新复出,固然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但以某种意义上说,也颇有点“外转内销”的意思。他虽然在大陆诗坛沉寂了几十年,但他的诗作和影响在港台乃至海外,却始终存在。他的作品在港台也时有出版,以至于当大陆要重新出版他的作品时,遍寻无获而不得不参照香港的版本。我因此而想到,倘若不是如此,他是否有可能在中国诗坛东山再起?
早就有人评价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是“价廉物美,经久耐用”。此话不免有点尖刻,却也道出了事实。辛笛老正是这样的人。去年夏末他因患老年性前列腺肥大症住院治疗,手术不很成功。出院之后,不得不在身上吊着一个塑料胶囊盛接尿液。而他却以七十七岁的高龄,忍受着痛苦不倦地工作着。我每次去他家里,都见到他不是在书写着,便是与友人亲切地交谈。他并没有因为年事已高或疾病缠身而就此放下诗歌创作,他也时刻关心着海外诗坛的发展,并怀念那些诗友。这种韧性和毅力确实是令人惊叹和感佩的。
无独有偶的是,辛笛老说他的一生总是在“勉力自持,只作成人生圆圈里的一点”。这和许杰先生说的“出发在人生,归着在人生”竟如出一辙。我想这绝非偶然的巧合。作为同一代人,他们有着大体相同的经历和命运,对人对事也有着相近或相似的看法,在文学创作和研究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他们身上,我们是可以学习到许多东西的。作为一个受益者,我写下这些,就算是学习心得吧。倘幸能公诸于世,或可有助于海内外关心他的人士和朋友对他们的认识和了解。
一九八九年三月三日
原载香港《星岛晚报》1989年4月11日
辛笛印象
王璞
见到辛笛先生不过一年之前,我才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那还是因为我跟他女儿圣思成了同学,别人告诉我:“她父亲王辛笛是三四十年代有名的诗人。”不久,我偶尔在一份杂志上看到辛笛的一首诗,是他一首应景的新作。老实说,没留下什么印象。现在我连那首诗的名字也记不起来了。一个人读过的无数篇文章、无数首诗中,能够沉埋心底、保存久远的毕竟只有很少很少的一些。我记得,当时我的一个淡淡的印象是:哦,三四十年代的诗人……
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四十年代”,在我,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被西方现代派文学冲击的大学生读者的词典中,近似贬义词。
又过了不久,我见到了辛笛先生真人。至今那第一次见面印象还历历在目。
在那间白天也需开灯的大屋子里,四处张灯结彩似的挂满了贺年卡。那些贺卡都用绳子牵挂在房间四面的墙上,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给这暗淡的客厅增添了一种奇异的气氛。我们这群来客都是学文学的,有谁随口提到某作家,辛笛先生就立刻兴冲冲地起身走到某一面墙边,信手取下一张贺卡,打开一看,正是那人赠与的。情况有如变魔术。后来我发现,对那些高高低低堆在、摆在、排列在客厅、卧室里的书与文件,这位当时年近八十的诗人也有同样惊人的记忆。在谈话中,他经常会突地起身,走过去随手取出一本书,正是那本他刚刚提到的作家写的。有时,甚至会翻开某一页指出其中某几行话来印证他刚才的言论或反驳对方的论点。信手拈来,位置之准,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他夫人却嗔怪道:“他的书报信件到处乱摊乱堆,还不准别人收拾整理,自夸是凌乱美。”
因此,初次见面,辛笛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学者,在他身上看不到诗人狂放不羁的谈吐,大起大落的情绪变化,风流潇洒的仪态,瞧着他身上那件中式对襟棉袄,一时间我很难将之与那位在爱丁堡大学聆听艾略特讲课的才子联想到一起。那时他从美国回来不久,他说,在美国住了半年心里总是不安,因为……因为那里收不到许多信。在上海就不同了,信多得邮递员向他家提出建议:何不跟楼下那家公司似的,改装一只特大号邮箱?圣思说他现在每日最大的乐趣就是下楼取信。辛笛听着我们如此这般地议论他。摇摇头,淡淡地笑。
他沉默,淡泊,温文尔雅。
然而有一天我们终于谈起了诗。
说着说着,辛笛又是不期然站起身来,从一堆书中取过一迭复印资料放我面前:“台湾《联合文学》刚刚发的。”他简略地说了这么一句。
那是美籍台湾学者叶维廉与辛笛谈诗的一篇长文。我信手一翻,骤然入目的几行诗句令我心里一震:年年四月,勃朗宁怀乡的四月/雾岛上看见此花肥硕与明媚/(呵,迢迢亦来自古中国)/便招邀起我心中/故国故城里此鸟的啼声
更有如下这几行:
阳光如一幅幅裂帛/玻璃上映着寒白远江/那纤纤的/昆虫的手昆虫的脚/又该粘起了多少寒冷/———年光之渐去。
我便不能释卷了。我不仅强行借走了这本复印件回家仔细研读,而且赶紧从箱底翻出《手掌集》,一首一首地吟读。至此我才知道:三四十年代中国不仅有沈从文这样的小说家,也曾有过辛笛这样的诗人。美国一位学者曾说:中国没有现代文学。我一度认同他的观点。现在我却想,那是因为他没读过辛笛诗,或是因为语言隔阂没读,就是在世界诗坛上,这样的诗句能有几多:
一生能有多少/落日的光景?/远天鸽的哨音/带来思念的话语;/瑟瑟的芦花白了头,/又一年的将去。/城下路是寂寞的,/猩红满树,/零落只合自知呢;/行人在秋风中远了。
还有:
船横在河上/无人问起渡者/天上的灯火/河上的寥阔/风吹草绿/风吹动智慧的影子/智慧是用水写成的/声音自草中来/怀取你的名字/前程是“忘水”/相送且兼以相娱/———看一支芦苇
我此时强烈的愿望是向每一位文学朋友介绍辛笛的诗。后来到了香港,我才知道,原来我这是少见多怪,港台几乎每一位写诗的人,不仅都读过辛笛,而且其中很多著名诗人都把他奉为一代宗师,承认是从他的诗中起步。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辛笛的诗在内地绝了迹,在港台是一纸风行,读辛笛的诗在文学青年中是时髦风雅的事。由于出版印数不多,找到一本辛笛的诗不容易,大家就辗转传抄,出现了很多《手掌集》的手抄本。
我觉得辛笛对于中国现代新诗的卓越贡献,在于他将中国古典诗的音韵之美,与西方现代诗的自由开放的形式糅合,把现代中文诗的语言幽远深厚的张力,拉至又一高度。辛笛最好的那些首诗,几乎每句诗都自成一个世界。每一句诗都让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意境,然后一个切换或是淡出,我们发现自己又被带入另一片天地,总是有新的惊喜,新的体验,新的思索。
我惊喜于辛笛诗句的声音之美,叶维廉与辛笛对话时提到了这一点,他说:“在我念你的诗的时候,特别感觉到一种声音,很丰富的声音,尤其在声音的转折里面感觉很丰富。”辛笛回应道:“这种味道我们李商隐的诗中得到很多。譬如反复咏味和通感。他有两句简单的诗,才十个字,令人低回无已:‘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春天在天涯做客,春天正是最美好的明媚时光,我却在外头做客,又偏偏日已高斜,黄昏了,令人情伤不禁。他又说:‘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莺在啼,啼是声;因啼而有泪,泪是水;水而能湿。泪湿什么呢?泪湿衣襟吗?泪湿最高花。湿是触觉吗?在诗中,我们感觉得到。虽然泪是通过视觉的,啼是通过听觉的等等,但我们感觉到,即所谓五官通感。”
这段话也说明他确实是在有意识地沟通中国古典诗与西方现代诗。可惜我无机会就这方面与辛笛深谈。一是因为我自知浅陋,还达不到与他谈诗的高度;二是因为每次见他都是来去匆匆,我们就多谈些日常生活琐事。我发现,凡是谈到文学以外的东西,他总有些讷讷,显然不大在行。经历了令人脱胎换骨的“文化大革命”,甚至到过了“五七干校”,他仍极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会做的饭菜只有一种,那就是鸡蛋炒饭。在干校时他不得不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平生第一次拿起了针线,这竟使他由衷地感叹人类的智慧:“怎么会想到在这样细的一根针上打一个眼来穿线,真妙!”
这便是诗人的真性情了。八十岁了,饱经风霜,他也这样兴致勃勃地爱着生活,他热心地倾听一切,参加一切,哪怕端上一盘菜,抹一抹桌子,他都贯注了极大的热情。看着他热情洋溢地做着给信封封上口、贴好邮票这类工作,我便想起他的诗句:今天独在空山中无事奔跑/心乱翻成故意来寻/草地里的流泉水/不想迎风会听到你重又当前/唤起我往梦重重里的梦/感谢你多情告诉我也南来了/可是你与我一样而不一样/因为你是过而不留/在月明中还将飞越密水稠山/我这个海外行脚现代的中国人/对你无分东西都是世界/合掌唯有大千的赞叹
这是辛笛五十年前在英伦写的诗句,五十年后,他仍然保留着年青时对这大千世界的赤子之心。尽管历经无数磨难,他仍然怀有这颗赤子之心热爱生活,热爱五光十色的世界。在他的目光里,仍然闪着孩子般的天真和好奇。瞧着他锲而不舍地与夫人抢读一本新杂志的老顽童神态,你会在心里叹道:这才是诗人,这才是一位真正的诗人!我祝他永远只会做蛋炒饭,我祝他永远向着一根针发出对人生的由衷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