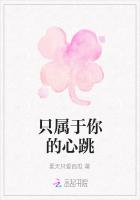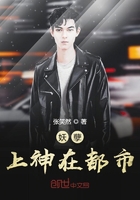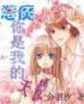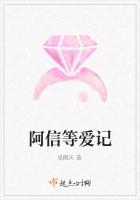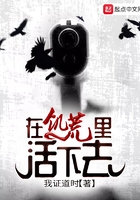这就是说,他和鲁迅(自树)都住在“张芝芳君处”,亦即留住“十六铺”。第二天上午,他们“乘车至高昌庙”,这高昌庙也就是现在的江边码头一带,即江南制造局近侧;随后他们又“同至十六铺”。这一来一去,都是在十六铺往南的线路上走,起点和终点都是十六铺,若无特殊情况,怎么也不会绕到十六铺以北的外滩黄浦公园这一带来。所以,我很怀疑周作人所记的“公园”就一定是黄浦公园。虽说当时正式的公园不多,但日记中的公园并不一定非正式公园不可。那时的江南制造局附近,有没有专供西人游乐的场所,包括一些有体育设施的场地(诸如网球场之类)呢?我很希望上海史专家能提供更多的资料。当然,上海确曾出现过“犬与华人不准入”这样的招牌,这一点是不再有疑问了。
我查《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在同年九月十日(阴历七月十九日)这一条中,只记了“至上海。宿张芝芳处”,未写明张芝芳住十六铺。所以,光看年谱,不查日记原文,就很难猜透他们第二天行走的线路了。
(写于二〇〇八年秋)
5、胡适之体有奇趣
在《文汇读书周报》的“书人茶话”上读到孙郁兄的《读诗法》(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三十日),颇获教益。此文所论的废名《谈新诗》,也是我十分喜爱的一本小书,我觉得,它与缪钺《诗词散论》、林庚《西游记漫话》,乃至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都属极简薄而极隽永的学术佳品,充分个性化而又充满创见。现在到处都是厚重而难读的“学术专着”,这样好看的书早已是稀见之物了。
但孙郁兄“不相信废名对初期白话诗是喜欢的”,并特别强调“胡适的白话诗多么苍白”,我对此难以苟同。回想从前,初读《尝试集》时,我也感到过这种苍白。但再读,就觉得其中有说不出的讨人喜欢处,就像儿童手中的玩具,看似平淡无奇,就是不舍得放手。再后来,就愈益发现它们的不一般了,我从浅近中读出了真切、朴拙而雅淡的趣味。
比如写于一九一九年的《小诗》:
也想不相思,
可免相思苦。
几次细思量,
情愿相思苦。
短短二十个字,竟出现三个“相思”,两个“相思苦”!但这不是词穷,而是故意为之。想来,他是要使全诗有一种回旋的节奏(这是从古诗学来的,《诗经》就是最好的范本);同时又能有一种“简单味”,一种很特别很熟悉的“滑稽”感。对这后一点,我只觉得好玩,只觉其美,却好久没能想透它的奥妙。
这种味道,在他最初的白话诗《蝴蝶》中,就已经有了: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一首短诗,用了两个“飞”,两个“上天”,两个“一个”,两个“孤单”。高明如胡适者,会看不出其中的重复?他的词汇真的那么少吗?这中间肯定有一种特别的美,它让胡适着迷,也让我们渐渐被吸引。
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这是一种童趣!只有孩子,才会这样不避重复,而大人只有在童心萌发时,才会有这种奇特的措词。
我后来研究胡适的文体,发现他所发明的中国早期的白话体,正是在不知不觉中受了西方近世儿童文学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胡适,传递到五四以后的几代中国文化人的笔下,形成了中国学界、散文界特有的浅近优美的文风(详见《上海文学》,二〇〇七年九月号,拙文《一清如水》)。胡适是以文入诗的,所以其诗美与他的散文、议论文之美,在源头上是一致的。
这里我想再举两例,来看看胡适诗体那独到的美。一九二四年,胡适为自己的爱情所苦,又作了一首有名的短诗,题目还是《小诗》,共四行:
坐也坐不下,
忘又忘不了。
刚忘了昨儿的梦,
又分明看见梦里那一笑。
后来他又删了前面两行,让它只剩了后面的两句了。但此诗最有趣的还是诗后的一段附注: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的猫“慢慢地不见,从尾巴尖起,一点一点地没有,一直到头上的笑脸最后没有。那个笑脸留了好一会儿才没有”。(赵元任译本页九二)
读完附注,再读读那两行诗,我们会读出爱情的滋味,会感到他内心孩童般的执着和苍凉,也会联想到古人的“才下眉头,又上心头”。这样的诗,我觉得是不苍白的。
在胡适的《尝试后集》中,还有一首一九四三年的译诗,那是他从十几岁时就开始喜欢并打算翻译的。原作者是美国诗人朗费罗,诗题是《一枝箭,一只曲子》。这是典型的儿童文学,从中我们更可发现胡适的趣味,和胡适之体的美妙所在。现就抄在这里,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望空中射出了一枝箭,
射出去就看不见了。
他飞的那么快,
谁知道他飞的多么远了?
我向空中唱了一只曲子,
那歌声四散飘扬了。
谁也不会知道,
他飘到天的那一方了。
过了许久许久的时间,
我找着了那枝箭,
钉在一棵老橡树高头,
箭杆儿还没有断。
那只曲子,我也找着了——
说破了倒也不希奇——
那只曲子,从头到尾,
记在一个朋友的心坎儿里。
(写于二〇〇七年初冬)
6、探寻“古籍整理”的源头
一九一七年七月六日,胡适留美归来途经东京,买到《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上有日本学者桑原隲藏的《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胡适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的读后感:
《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其大旨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末段言中国书籍未经“整理”,不适于用。“整理”,即英文之systematize。其所举例,如《说文解字》之不便于检查,如《图书集成》之不合用,皆极当,吾在美洲曾发愿“整理”《说文》一书,若自己不能成之,当数人为之……
在这里,胡适已开始留意“整理”一词,并将其转换成英语systematize,可见已注入了系统化条理化的意思在内,这也与他后来一贯提倡的“科学研究方法”相一致。此后,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又将“整理”归结为“索引式整理”和“结账式整理”。西语“索引”一词(index)音译即为“引得”,而对这种整理贡献最大者当推洪业(煨莲),他在一九三〇年发表了着名的论文《引得说》,并在一九三一到一九五一年间主持出版了六十余种中国典籍的“引得”,这些学术成果直到近年仍在被人使用。“结账式整理”则更为复杂,它包括对某一部书的“集注”,对此书版本史和接受史的清理,也包括对某一类古书的史的研究。一九二三年十月,胡适拟订了“整理国故计划”,邀集一班朋友参加,开出三十六种整理书目,并将各书的整理工作落实到人,初步选定的人中有马幼渔、刘文典、顾颉刚、沈尹默、沈兼士等。胡适还专门解释了整理过程中的五项最基本的工作:校勘、必不可少的注释、标点、分段、考证或评判性的引论。以后这种整理愈益形成规模,分类和分工也越加明晰,而无一不在考证和校勘的基础上进行。由“结账式整理”再发展出专史式研究,如鲁迅的小说史研究,冯沅君的中国戏剧史研究,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等,都可说是这种整理的延续。
上述线索,是在阅读徐雁平先生的专着《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时清理出来的。作者在这一课题中爬梳多年,累积了大量资料,弄清了很多今人甚为陌生或熟视无睹的问题。我读后最受启发的,是现代出版业对于古籍整理的推动,这在过去虽然“知道”,却并不“懂得”,是本书的作者打开了我的思路。
这里的关键词,应是“亚东图书馆”——它本是绩溪人汪孟邹于一九一三年在上海创办的一家小出版社,出书寥寥,生意惨淡,多亏有陈独秀、胡适这两位安徽同乡常将自己的书交他们印,这才有了点名气。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曾与胡适相处,胡适让他读过《水浒传》和《红楼梦》,从而受到了一些影响。大约在一九二〇年,汪原放尝试对《水浒传》作新式标点并分段,同时删去金圣叹的眉批夹注,打算排印后看看市场反映,如成功,便接着标点《红楼梦》、《儒林外史》、《西游记》等。此举得到陈独秀的支持,陈于一九二〇年的七月七日写了《〈水浒〉新序》;胡适也应约于七月二十七日完成了三万余字的《〈水浒传〉考证》,他在文中说:“这是用新标点来翻印古书的第一次。我可预料汪君的这部书将来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当然,标点只是其特质之一。后来唐德刚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中,在回忆这部“有系统的整理出来的本子”时,胡适强调的是三点:“一、本文中一定要用标点符号;二、正文一定要分节分段;三、[正文之前]一定要有一篇对该书历史的导言。”这以后,亚东的生意一发而不可收,短短几年间,除原先想到的那几种小说外,还整理出版了《三国志演义》、《镜花缘》、《水浒续集》、《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等十余种书。胡适投入了相当的精力,除写了一系列考证性的序文(其中包括极具学术价值的《红楼梦考证》、《西游记考证》等),他对版本的选择、校读、分段标点等都热心关注,他成了这一事业的核心人物。正如当初日记中所说:“若自己不能成之,当数人为之。”他把钱玄同、顾颉刚、俞平伯、刘半农、孙楷第等都拉进来一起干,甚至徐志摩也被拉来做了那篇九千字的《醒世姻缘传序》。这以后,不仅过去被视为“闲书”的章回小说渐渐登上了“经典”的宝座,而且标点古书成为一时风气,各地书商纷纷仿效,连施蛰存、钱杏邨、刘大杰等青年文人也被发动起来。吴组缃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他最初读到亚东版章回小说的情景:
我在高小的时候,看过一些小说书,都是借来的,土纸土版本……密密麻麻的字迹,看得头昏眼花。可是,我一进中学,就买到了胡适主持整理的亚东版新出的《红楼梦》,跟我以往看的那些小说从里到外都是不同的崭新的样式,白报纸本,每回分出段落,加了标点符号,行款舒朗,字体清楚。拿在手里看看,真是赏心悦目。我得到一个鲜明的印象:这就是不同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
这番感受,在那个时代是很有代表性的。徐雁平认为,对古书的这种整理出版之所以能成为普遍的风气,与胡适等倡导的那套整理方法大有关系:“这套方法简言之就是标点、分段、搜集必要的版本对勘、拟定校读说明等等,可操作性比较强,后来也就成了亚东的一种模式。”毋宁说,它也成了二三十年代古籍整理的基本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五十年代初,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开始了最初的古典文学整理出版工作,由冯雪峰、聂绀弩负责,当时集中了张友鸾、顾学颉、文怀沙、汪静之、舒芜、王利器、周绍良、周汝昌等一大批学界精英,稿子则直送胡乔木审定。有趣的是,当时整理出版的第一部书,与亚东版一样,竟也是《水浒》。而整理工作,主要也还是标点、分段、校勘、作注,以及撰写出版前言。
时隔三十年后,进入了“新时期”,古籍整理被又一次作为大事提出,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这一整理工作至今仍在延续。而这次整理,其基本方法,仍离不开当年“亚东模式”的那几个方面。
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感谢八十多年前胡适的开山之功。当然,我们也得感谢本书作者对这一开山之功的发掘、清理和他那一丝不苟的分析。
(写于二〇〇三年末)
7、学学杨绛和朱正
在《文汇报》的“笔会”上曾刊载金圣华女士的文章《四访三里河》(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其中有一处令我过目不忘,并感慨了好些日子。那是杨绛先生在电话里听金女士说起她的近作《走到人生边上》,马上问:“你手里的书是第几版?”并认真解释说,书中错的很多,“要第八版才改正过来。”
杨绛这本书出版后,我曾从报上读到过指出书中引文等错误的文章,写得很不客气。当时有点担心年过九十的杨先生看了会不愉快。现在看来,杨先生对此相当重视,她一版一版地改,直到出了第八版,这才大致满意。杨先生的这种态度,令人对其越发敬重了。
本来,闻过则喜,是中国读书人和着书人的通例,但这些年风气大变,闻过则喜者少,闻过则怒者多。一般的怒而反击的方式,大概有二:一是,“这点错算什么?斤斤计较于此者,必是小人无疑!”二是,“看看你自己的书吧,哪里哪里不也有错?别自以为是了,我比你高明多了!”每看到这类反击,心中总不是滋味。指出你的错,与指正者的道德何干?别人有错,与你书中的错何干?虽然送书予人时大多爱写“请某某指正”,真有人“指正”了,居然就视为仇敌了。有时自己不出面,就请一个朋友,代为反击,而反击的路数,无非还是上述二者。这样的着书者,是很难有长进的。
日前,在《文汇读书周报》上读到朱正先生的文章《〈一个人的呐喊〉一书有错》(二〇〇八年十月十日),使我又记起了上回读金圣华文章时的感慨。朱正历数自己着作中出现的几个错误,并说:“我请求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朋友给我指出书中的错处,直接写信赐教或者写成批评文字在报刊上发表,我都同样感谢。假如此书还有第二次印刷的机会,好据以改正。”这态度是很感人的。虽然对于一个正直的着书人来说,有这样的态度本应是题中之义。但现在的世道变得实在太快了。
我想,杨绛和朱正的态度,值得“闻过则怒”者好好对照,并认真作一反思。
(写于二〇〇八年深秋)
8、施蛰存的自嘲
施蛰存先生逝世后,热心的记者请我和沈建中、陈飞雪一起,作了一次谈话,很快便以《施蛰存的“趣味”》为题,刊登于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南方周末》。其中有一件事牵涉到《新民晚报》,但与实情稍有出入,使我不得不作一补述。
那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事,有出版社请施先生将自己的短篇小说编一本选集。施先生觉得自己的小说数量不多,有心出一本“小说全集”,但出版社不允。他好不容易才想明白,此中原委,是老作家们都被分成了不同等第:像鲁迅,可出全集;茅盾和巴金,可出文集;而他这样的,只能出选集。于是他在“夜光杯”上以“北山”的笔名,写了一篇自嘲文章。那年我登门索稿(可能就是去取后来刊于《文汇月刊》的散文稿《论老年》),见面就问:“北山的文章是不是你写的?”他脱口道:“北山就是我呀。”接着就笑了,表情犹如孩童,“现在上海,有资格说这种话的,能有几个?你一猜就猜得出的。”
但在这篇谈话中,施先生的话错成为:“现在有资格出全集的人还有谁?”这就变得很狂傲了,怎么看也不像他的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