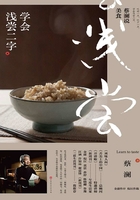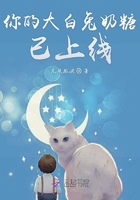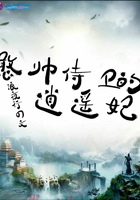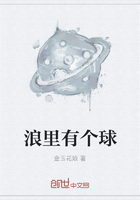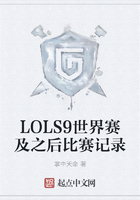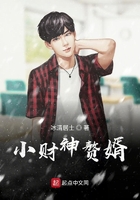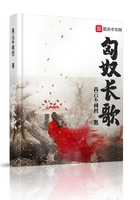中古印度诗学是指从婆罗多的《舞论》一直到世主的《味海》漫长的历史时期的印度诗学。从时间而言,大约从公元1世纪前后起到19世纪西方殖民者入侵,近2000年的岁月。这一时期印度诗学的最大特点是形成了独立的诗学理论体系。诗学理论著作从上古时期的文化经典中分离出来,把文学艺术作为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独特的诗学范畴如味、庄严、风格、韵等被陆续提出,形成了印度诗学在世界诗学史上的民族特色,而且理论前后承传,脉络分明。当然这个诗学体系以梵语作为主要语言,研究对象主要也是梵语作品,所以又被称为梵语诗学。这也是印度诗学民族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黄宝生先生说:“就梵语诗学达到的最终成就而言,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可以说是以味和韵为核心,以庄严、风格、诗德、曲语和合适为外围。”这种诗学体系的内在结构也是独具民族特色的。
第一节 中古印度诗学的文化背景
中古时期印度文化的发展进入了多元化时期。各种文化思想在相互的交流碰撞中互相促进,形成了共同发展的格局。各种不同的流派思想体系化、系统化的特点也十分突出。
这个时期影响文化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有两个:一是公元1世纪以后贵霜王朝和安达罗王朝(Andhna)的对峙以及公元3—4世纪笈多王朝的统一,这个时期印度的社会经济有较大发展,文化生活也极活跃。印度北部的贵霜王朝大力提倡佛教具有重要意义,南方的安达罗王朝支持婆罗门教,为婆罗门教地位的巩固起到了关键作用。随后的笈多王朝虽然崇奉婆罗门教,但也容许其他宗教的发展,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正统派和非正统派在这个时期都有了长足发展。正统派中就形成了正理派、胜论、数论、瑜伽、弥曼差、吠檀多等六大派别,非正统派中也有佛教、耆那教、顺世论、生活派等派别。这些不同派别内部各思想家之间也存在着思想分歧,论争不断,推动了思想的严密化、体系化。另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公元12世纪以后信奉******教的阿拉伯人(阿富汗廓尔王朝)大举入侵,这对于原有的印度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其中最严重的后果是13世纪时直接导致了佛教在印度的消失。其他宗教哲学派别的思想虽然保留下来,但正统派别与印度教融合,神学色彩越来越浓。******教的思想也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当然,阿拉伯人进入印度以后也带来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同思想派别之间的融合,对于印度文化的发展仍有积极意义。
各种思想的繁荣发展对于中古印度诗学具有重要意义。思想的发展不仅为诗学提供了必要的观念和方法上的准备,而且不少思想家还亲自研究文学艺术问题,写出了诗学著作。比如11—12世纪耆那教学者雪月(Hemacandra)就著有《诗教》,另一位12世纪耆那教学者伐格薄吒(Vāgbhaata)也著有《伐格薄吒庄严论》。正理哲学家扎格迪舍、弥曼差哲学家迦摩拉迦罗、毗湿奴教作家伯罗提婆等则为11世纪的曼摩吒(Mammat·a)的《诗光》作过注。这种现象说明诗学已成为各派思想家的研究领域。诗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形态已经发展起来了。
诗学观念的形成是文学艺术自觉的重要标志,文学艺术的自觉,也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并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在印度中古时期,文学的发展为诗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经验。
戏剧方面,《舞论》产生的年代也正是印度戏剧成熟的时代。黄宝生先生指出:“《舞论》大体上可以说是在公元前后1~2世纪,至晚在公元3—4世纪。即使《舞论》的成书年代不能确定,至少现存马鸣的三部戏剧残卷表明,古典梵语戏剧是在一二世纪已经达到成熟阶段。”所谓达到成熟阶段,当然首先是指作品本身已经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征。马鸣(Asvaghos·a)是佛教诗人,现在史料已可证明他写过《舍利弗》、《护国》等三部戏剧作品,这些作品有丑角,有上场、下场等舞台提示,剧中角色在语言上有明确区别,妇女和丑角说俗语,地位高的角色说梵语。戏剧语言韵散相杂。三个戏剧作品讲三个不同的故事也证明了马鸣的戏剧是独立的艺术作品,而不是宗教仪式上的程序化活动。戏剧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其成熟当然不仅仅只靠马鸣一人,马鸣同时代稍晚的还有其他戏剧家。其中著名的有跋娑和首陀罗迦。跋娑约生活在公元2—3世纪,现存的作品有13部之多,称为“跋娑约十三剧”,这些作品取材广泛,包括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还有其他一些文学故事和民间传说。《惊梦记》是他的代表作,描写优填王与王后仙赐在国家危难之际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故事情节曲折紧凑,矛盾冲突紧张、集中,人物性格鲜明突出,心理描写细腻真实,场景生动有致,语言简洁明快,诗歌采用广为传颂的输洛迦体,很适合舞台演出。一般认为跋娑的作品奠定了古典梵语戏剧的基础,成为后世的楷模。生活在公元4—5世纪的迦梨陀娑称跋娑是负有盛名的戏剧前辈,而生活在3世纪的首陀罗迦的名剧《小泥车》更是在跋娑的《善施》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小泥车》共有十幕,前四幕与《善施》大致相同。描写的是乐善好施的婆罗门商人善施与渴望从良的妓女春军的爱情。作品歌颂了他们的正当爱情,同时也批判了社会的黑暗,达官显贵的卑鄙无耻与可笑,表现出了鲜明的民间立场。作者大量运用喜剧手法,营造了紧张有趣的戏剧效果,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对话机智诙谐,大量使用俗语。人们一般认为《小泥车》的戏剧手法比《善施》更成熟,与《舞论》中的论述基本一致。在那个时代的戏剧作品中具有代表性。如果不能说《舞论》与这些作品有直接联系,至少可以说这些戏剧作品所积累的经验是《舞论》的现实基础。
自公元4—5世纪开始,梵语戏剧出现了宫廷化特点,这也是印度戏剧艺术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在此之前以马鸣、跋娑、首陀罗迦为代表的是大众戏剧,深受一般大众的喜爱,题材广泛多样,精神立场与民间观念一致,但是到了以迦梨陀娑和戒日王等为代表的宫廷戏剧时期,戏剧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戏剧本身明显地贵族化、高雅化了。但宫廷戏剧仍然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创作出了成功的作品,代表性作品就是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作品讲述的是民间少女沙恭达罗与外出打猎的国王豆扇陀相恋,遭仙人诅咒后因遗失了信物而不被国王相认,遭遇各种坎坷后国王终于找到了信物,两人终于团聚的故事。作为一部宫廷戏剧的代表作,这部作品除了情节的紧张曲折,矛盾冲突紧凑集中,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等优点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语言的清丽优美,诗歌语言与戏剧达到了高度统一,以至于印度流行的梵语诗歌中有这样的赞美:“一切语言艺术中,戏剧最美;一切戏剧中,《沙恭达罗》最美。”迦梨陀娑的戏剧也被认为代表了古典梵语戏剧的最高成就。
印度戏剧在中古时期成熟以后不断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印度戏剧至《沙恭达罗》时代达到了鼎盛,公元8世纪以后开始走向衰落,作家们虽不断写出作品,但已无法超越前人,概念化、模式化的问题十分突出。
印度戏剧一直都与史诗和传说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取材于其他历史材料。同时,戏剧与宗教和哲学思想也直接相关,从马鸣开始戏剧就成为宗教宣传的重要手段。11世纪的克里希那弥湿那的《觉月升起》竟然直接以哲学概念为人物,以宫廷斗争为剧情,宣传毗湿奴教不二论观点。“原人”和妻子“幻觉”生下“心”,“心”的两个妻子是“有为”和“无为”,又分别生下了“痴迷”和“明辨”两个儿子。这样的戏剧虽然可以表现出印度戏剧与思想文化的密切关系,但对于戏剧艺术的发展并无益处。在文学方面,尽管现在的文学理论著作是公元7世纪婆摩诃的《诗庄严论》。但独立的文学作品却早在公元1世纪前后就已成形。在婆摩诃那里“诗”也并不仅指诗歌,而是指广义的文学,包括叙事诗、戏剧、传说故事和短诗,这也是印度中古诗学中“诗”这个概念的含义。因此,诗学其实是文学理论,由于戏剧已有《舞论》那样的戏剧学著作作专门研究,后来兴起的诗学主要以诗歌、散文、小说等语言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所以印度诗学其实有两个含义,广义的诗学可以包括戏剧学和文学理论,狭义的诗学仅指文学理论,尤其是以诗歌为主要对象的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狭义的诗学)当然是在文学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创作的繁荣是文学理论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不同类型的作品聚集了各种手法和技巧、主题和情节以及审美风格,都为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的形成打下了基础。除此之外,还有两个方面对文学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一是语法学,古代印度语言状况很复杂,既有占主导地位的梵语,也有各地方的俗语。而且不同语言都在文学作品中存在着。两大史诗之中的梵语存在着不少不规则的语法现象,经过语法学家波约尼、迦旃那和波颠阇利的努力之后,在公元1世纪左右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古典梵语”,这也正是古代印度文学从上古经典中分化独立的时期。中古印度诗学中的文学理论正是以这些古典梵语文学为主要对象的。诗学著作以讨论语言问题为主的《诗庄严论》开始,也可以说有其内在原因。另一个对文学理论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是戏剧学理论。由于《舞论》早在公元1世纪前后即已成形,语言问题也是其中重要的部分,这对于后来的文学理论起到奠基作用;另一方面,《舞论》中对于情味的论述也对文学理论中“韵论”、“味论”的思想有启发意义,文学理论在讨论语言问题的庄严论这条线索之外形成了韵味论这另一条线索。
相比之下,中古印度诗学中现存的文学理论虽然比戏剧学晚出几个世纪,但文学理论仍比戏剧学思想更丰富。究其原因,大致仍与文学创作的繁荣与成熟有直接关系。
在诗歌方面,中古印度文学中的诗歌分为大诗和小诗两大类型。大诗是叙事诗,在题材和形式上主要继承了两大史诗的传统,主要取材于两大史诗和历史传说及神话。爱情、战斗、政治和风景成为构成大诗的几个原型要素。在风格上也以华丽雕琢、讲究修辞和文采为特征。现存最早的大诗作品是马鸣的《佛所行赞》和《美难陀传》,而代表着大诗最高成就的是迦梨陀娑的《鸠摩罗出世》和《罗怙世系》。《鸠摩罗出世》共17章,取材于大神湿婆与雪山神女波哩婆提的神话传说,主要描写湿婆因失去爱妻萨蒂而弃绝俗世入雪山修行,山神愿将女儿波哩婆提嫁给湿婆,湿婆不为其美色所动,结果波哩婆提决定以苦行来打动湿婆,终于获得了爱情。他们的儿子就是鸠摩罗。《罗怙世系》共19章,取材于历史传说,罗怙是《罗摩衍那》中罗摩的曾祖,因此该诗又与史诗有关。其特点在于以帝王谱系的形式结构全诗,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但是诗人高超的语言技巧和剪裁手段使全诗可以通过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来刻画人物,语言优美,文采飞扬,诗意盎然,成为印度古典叙事诗的典范。小诗是抒情诗,主要继承的是吠陀诗歌的传统和史诗中的抒情成分。一般有赞颂诗、风景诗、爱情诗和格言诗四类。
印度现存最早的小诗集是公元2世纪的哈拉编选的《七百咏》,这是俗语诗集,语言质朴,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的出现说明在中古时代印度文学已十分繁荣,在高雅的梵语文学之外,文学已深入到民间。文学不是统治阶层的专权,普通民众也可以用文学表达心声。俗语文学成为梵语文学保持生命活力的重要源泉。抒情诗(小诗)的代表性作品是迦梨陀娑的抒情长诗《云使》和抒情诗集《时令之环》(或译《六季杂咏》)。《云使》被认为是代表古典梵语抒情诗最高成就的作品。其成就首先在于构思的巧妙,作品分“前云”和“后云”两部分,共有125节,基本构架是被贬到罗摩山森林的名叫药叉的小神仙,希望借远去的雨云传达对远方妻子的思念。前云是药叉对雨云描绘找到妻子的路线,后云是药叉想象雨云见到他的妻子时的情景。全诗的中心意象是雨云,作者将它由现实中的自然之物巧妙地转化成了爱的使者。其次诗中对自然风光的描绘、对爱情的渴望与对爱人的思念等抒情部分也都十分精彩,辞句华丽,风格幽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出现了众多的摹仿之作,如《风使》、《月儿使》、《杜鹃使》、《孔雀使》、《天鹅使》等等,形成了独特的“信使体”诗歌类型。《时令之环》则按印度的六个季节夏、雨、秋、霜、寒、春为序,分六章描绘了不同季节里的自然景象与爱情的不同表现。构思也极巧妙,爱情描写与自然气候变化和不同景色描绘融为一体,对印度的艳情诗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古印度文学中的诗歌成就当然不是靠一两位诗人的天才取得的,这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也是自由宽松的文化气氛等多种原因导致的结果。因此,我们在印度的文学史上也不是只看到一两部作品,而是有一大批作品构成了一个厚实的基础。这些作品背景形成了一个传统,在不同的方向上进行着探索积累,最终才催生出伟大的作品。这个积累的过程也同时为诗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经验。比如印度文学中广为传颂的大诗就有五部,除了迦梨陀娑的两部外,还有公元5—6世纪的婆罗维的《野人和阿周那》、公元7世纪摩伽的《童护伏诛记》和12世纪室利诃奢的《尼奢陀王传》。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诗人的作品在流传。小诗方面,除了《时令之环》和《云使》之外,7世纪伐致呵利(Bhartr·hari)的《三百咏》也广为传颂,12世纪胜天(Jayadeva)的《牧童歌》问世后也出现了许多仿作,形成“歌诗”的诗歌类型。
在散文体叙事文学方面,印度文学中也有很长的历史传统,主要有两大类型流传于民间。一类是宗教的通俗寓言或传说,比如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各种“往世书”,佛教的“佛本生故事”等。另一类是世俗的民间寓言故事,如《故事海》中所收的各种民间故事。这些散文体叙事文学的世俗精神十分明显,即使是宗教类的故事也都是通俗性的。随着印度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也发展起来,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直接激起了市民对世俗生活的积极追求,作为市民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小说也发展起来。现存最早的一批作品是公元6—7世纪苏般度的《仙赐传》,波那的《迦丹波利》以及檀丁的《十公子传》。前两部描写浪漫爱情,后者则描写浪荡公子的艳遇,都是世俗题材,表现世俗精神。这些作品在手法上吸收了史诗、大诗和民间故事的结构技巧,情节曲折离奇,带有传奇色彩,反映出市民的趣味。但在语言上却明显受到古典梵语叙事诗(大诗)的影响,注重修辞技巧的使用,风格也雕琢藻饰,与民间故事的纯朴自然不同。这或许是因为古典梵语文学影响深广,广大市民耳熟能详,成为接受习惯。由此看出,古典梵语中将所有文学体裁都称为诗的确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各种体裁在语言形式方面都有诗歌的影响。
总之,中古时代的印度诗学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发展的。宽容多元的文化氛围不仅直接导致了文化的繁荣发展,也为诗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各种不同的思想在争论中不断深化,为诗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直接推动了诗学理论的前进。相反,在文化冲突加剧、思想矛盾激化、宗教统治严酷的时代,文化走向衰落、思想枯萎也是必然的,诗学也难以有所创新。
第二节 中古印度诗学体系
中古印度诗学已经具有了独立的形态。从广义上说包括戏剧学和文学理论(即狭义诗学)。戏剧和各种语言文学都属于梵语“诗”的范围。但是戏剧学和文学理论又是两个独立发展的知识系统,它们之间有区别又有联系。这种情况与西方诗学理论有些相似。西方诗学理论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奠基之作,《诗学》是讨论戏剧为主的理论著作。印度诗学也是以戏剧学著作《舞论》为基础的。《舞论》中关于语言的论述以及戏剧艺术效果“情味”的论述对后来的文学理论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先从以《舞论》为代表的戏剧学理论中的诗学思想入手,总结其在中古印度诗学中的贡献,然后再讨论文学理论在中古印度诗学体系中的地位。
一、戏剧学中的诗学思想
戏剧学在中古印度诗学中是一个独立的支系。从公元1世纪左右婆罗多的《舞论》到15—16世纪鲁波·高斯瓦明的《剧月》,中间还有10世纪胜财(Dhananjaya)的《十色》,12—13世纪沙罗达多那耶的《情光》等著作,形成了中古印度诗学中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个传统中的后世著作大都是对《舞论》的继承,基本观点没有越过《舞论》所达到的水准。在这个戏剧学传统中,主要特色是围绕戏剧艺术的特点展开研究,特别强调对戏剧创作和舞台演出的实际经验的总结概括,具有较强的实践性。黄宝生先生说:“这正是印度古代戏剧学的特色,注重戏剧艺术的具体体验和演出工作的实用需要。因此,《舞论》也可以说是一部印度古代的戏剧工作者实用手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这些戏剧学著作主要是从戏剧艺术本体的角度进行研究的,突出戏剧艺术自身的独特性。比如戏剧的分类、风格,剧本的结构,舞台的设计,化妆,表演的姿态,动作程式,语言的表达等。这些论述,只有一部分内容与诗学理论有关。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情味论对文学艺术本质观的启示。味是婆罗多《舞论》的核心范畴,也是中古印度戏剧学传统的核心范畴。从“味”的角度理解戏剧是印度戏剧学的重要特色,这种戏剧理论也在文学理论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了文学理论中“味论”传统的产生。所谓味,就是指戏剧艺术所产生的效果,也就是观众所体验到的审美感受。《舞论》认为味是由情产生的,味产生于情由、情态和不定情的结合。情是人们所感受到的艺术作品的意义,而作品之所以产生意义是因为作品中包含有情由和情态。情由是指产生情感的原由,而情态是情感的外在表现。情又分为常情、不定情和真情。常情是人的基本感情。不定情是随时可能变化的不稳定的感情。真情是指逼真地反映出内心真实状况的感情(其实只是情态,是某种内心情感的外在表现)。这些不同的情之中,以常情为主,婆罗多说:“情由、情态和不定情依附常情。由于这种依附关系,常情为主人。其他的情成为常情的附属。”味就是由常情产生的,这其中的关系是,情和情态和不定情共同引起常情,而常情则产生味。这是情味理论的基本原理。
《舞论》还对情味的类型进行了具体划分。常情共有8种,真情也是8种,不定情是33种。8种常情是爱、笑、怒、悲、勇、惊、惧、厌。8种真情是瘫软、出汗、汗毛竖起、变声、颤抖、变色、流泪和昏厥。33种不定情是忧郁、虚弱、疑虑、妒忌、醉意、疲倦、懒散、沮丧、忧虑、慌乱、回忆、满意、羞愧、暴躁、喜悦、激动、痴呆、傲慢、绝望、焦灼、入眠、癫狂、做梦、觉醒、愤慨、佯装、凶猛、自信、生病、疯狂、死亡、惧怕、思索。与常情相对应的味也是8种。情味对应关系是:
艳情味(srn·gara)滑稽味(hasya);
(爱)(rati)(笑)(hasa);
暴戾味(raudra)悲悯味(karun·a);
(怒)(krodha)(悲)(soka);
英勇味(vira)奇异味(adbhuta);
(勇)(utsaha)(惊)(vismaya);
恐怖味(bhayanaka)厌恶味(bibhatsa);
(惧)(bhaya)(厌)(jugupsa)。
艳情味、暴戾味、英勇味、恐怖味是根本味,分别产生出滑稽味、悲悯味、奇异味、厌恶味四种衍生味。由常情到味的产生过程是怎样的?婆罗多对每种味的产生都有具体的描述。比如滑稽味产生于常情“笑”。婆罗多说:“它通过不合适的服装或妆饰、冒失、贪婪、争吵、言不及义、显示肢体缺陷和指出缺点等等情由产生。它应该用咬嘴唇、翕动鼻孔和两腮、瞪眼、挤眼、出汗、脸色和叉腰等情态表演。它的不定情是懒散、佯装、失眠、入眠、做梦、觉醒和妒忌等等。”这样的分析可谓细致入微,也可以看出这种理论的实践性,的确是对舞台表演经验的总结。
但是,这种由具体的艺术实践而来的理论却又具有普遍性,它对文学理论也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除了不同的门类之间具有相通性这个表层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在于印度文化思想中对于人类共同心理的认识,构成了印度诗学中认识文学艺术本质的共同基础。印度哲学思想中很早就区分出人类情感中的固定情感和变化情感,并把固定情感看成是普遍的超越具体经验世界的本体。数论中就把原初物质看成是由喜(sattva)、忧组成的,称为三德。德就是性质、属性。这为理解事物的本质提供了一个途径,即从具体的现象去把握其背后的心理特征。至少是肯定了人的心理有某些共同的情感存在。在数论三德的基础上,后来又有人作出进一步的描述,也就更接近共同心理的概念。比如喜的性质是轻快的、照明的,忧的性质是兴奋的、动荡的,的性质是沉重的、闭塞的。甚至有人直接把三德与心理状态相对应:喜是廉洁、柔软、正直、清洁、谦让、智慧、忍耐、怜悯等,忧是憎恶、危害、怨恨、非难、顽迷、不安等,是无智、暗愚、恐怖、悲惨、怠惰、不忠实、弛缓、睡眠等。这些分类就与婆罗多对于常情、不定情的分类相近了。在诗学理论中,即使不把常情理解为世界的原初本质,也可以看成是人心中普遍的情感、共同的情感,当艺术活动能使人感受到这些情感时,人的内心就产生了共鸣,产生审美感受。印度哲学中的众生有情观念,也可以理解为众生有共同的心理。艺术活动就是要通过各种具体方式和手段去激起这种共同心理的共鸣。“美的东西只有在刺激主体经验到其中的审美快感时才是美的。这意味着,美是以隐蔽的形式存在于欣赏者或创作者的大脑之中,并通过美的东西表现出来。”美的东西既可以是戏剧中的动作、语言和表演,也可以是文学作品中的词句和形象,而隐藏在人心里的美则是共同的。因此,戏剧学中的情味论,也可以启发文学理论对诗歌或其他文学作品的认识。
其次,戏剧学中的语言研究对于文学理论的意义。语言是戏剧的重要构成要素。在独立的文学理论尚未形成之时,戏剧学中的语言研究就成为文学语言研究的雏形。尽管戏剧中的语言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有所不同,但由于印度戏剧语言是韵散相杂的,其中不少诗作可以看成独立的文学作品。戏剧学中对于诗的语言特征的论述也直接启发了后来的文学理论。
《舞论》中除了论述诗的音律之外,还重点论述了诗相(laks·an·a)、庄严、诗病(dos·a)和诗德(gun·a)四个方面,其中庄严、诗病、诗德的概念都被后来的文学理论继承了下来,诗相中的不少具体分析,也被归入庄严范畴中。
婆罗多把语言与形体、真情和妆饰看成是戏剧的基本构成要素。演员最直接使用的工具就是这四个要素,通过这些要素才能表演出情由、情态和不定情,激起常情,产生味。他首先肯定了语言的重要性,认为“语言是戏剧的身体。形体、妆饰和真情都展示语句的意义。在这世上,语言构成经典,确立经典。因此,没有比语言更高的存在,它是一切的根由。”也许正是由于对语言如此看重,婆罗多才详细规定了戏剧中语言使用的各种规范,从语音语调、韵律节奏到人物角色,该用哪一类语言都有严格要求。虽则这些规定都与演员表演直接相关,但对语言重要性的认识,为后世文学理论中的庄严论对文学语言作专门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舞论》中对庄严的论述是后世文学理论中庄严论的先驱。婆罗多分析了四种庄严,即明喻、隐喻、明灯、叠声。明喻是“依据性质或形态相似,与某物相比”;隐喻是“观察形象,依据可比的性质,与各种事物相连”;明灯是把词语“合在一句中,处于各种关系的词语共同明亮”,比如“在这里,水池、树木、莲花和园林/从不缺少天鹅、花朵、狂蜂和人群”,“从不缺少”就把水池与天鹅、树木与花朵、莲花与狂蜂、园林与人群联系起来构成一个整体;叠声(yamaka)是“音步头部等等位置的音组重复。”婆罗多只举出了这四种庄严,与后世诗论中所总结的100多种相比虽然过于简单,但他为庄严论开创的研究范式却具有重大价值。庄严作为一个诗学概念,其基本含义和分析方法都是由婆罗多提出的,后世诗论家只是将其系统化而已。
《舞论》的诗论部分中诗病与诗德是相对应的概念,也主要是讨论语言运用问题。诗病是语言使用不当或缺点,诗德则是语言使用的优点。他列举出的诗病诗德各十种。十种诗病是:意义晦涩、意义累赘、缺乏意义、意义受损、意义重复、意义臃肿、违反正理、诗律失调、缺乏连声、用词不当。十种诗德是:紧密、清晰、同一、三昧、甜蜜、壮丽、柔和、易解、高尚、美好。这些分析为后世诗论家所继承并细化,成为印度诗学理论中的重要范式。
由此可见,婆罗多关于语言的理论主要是从形式着眼的,语言只是产生情味的手段和物质媒介。他对语言的研究也像对其他戏剧要素的研究一样重实际经验,重具体分析,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理论思辨,这也正是印度诗学的一大特点。
《舞论》作为中古印度诗学的奠基之作,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情味和语言理论之外,情节和风格也直接与后来的文学理论有关,但分析方法却与情味和语言研究相似,在此不再重复。
二、文学理论与诗学体系
中古印度诗学中,文学理论是主要部分。从理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来说,文学理论都比戏剧学更甚一畴。尽管文学理论的出现较晚,而且也受到戏剧学的影响。黄宝生先生在论及梵语诗学发展状况时说:“在六世纪以前,梵语诗学主要依附梵语戏剧学和语法学。而从7世纪开始,梵语诗学独立发展。七至十世纪是梵语诗学的创造期,产生了分别以庄严、风格、味和韵为核心的四大梵语诗学体系。”当然,这四大体系也不是同时形成的,而是有一个前后顺序的。这个顺序就是从庄严论、风格论发展到味论和韵论。这里的梵语诗学,主要是指中古印度文学理论。由此可见,中古印度文学理论在诗学体系中与戏剧学并列,文学理论又有四个主要系统,共同构成了中古印度诗学体系的主体部分。
(一)庄严论
庄严范畴早在婆罗多的《舞论》中就已提出,并有简单的分类,已如前所述。文学理论中的庄严论是由公元7世纪的婆摩诃的《诗庄严论》建立起来的。属于这个理论系统的还有优婆吒(udbhata)的《摄庄严论》和楼陀罗吒(Rudrata)的《诗庄严论》等。庄严论在诗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在于对文学语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形式主义文论。所谓的庄严本义是装饰或修饰,在诗学理论中有两种含义,狭义是指修辞方式,广义是指文学魅力形成的因素。由于庄严本义是装饰,所以这里所说的形成文学魅力的因素也主要指语言形式因素,而不是主要指思想或艺术形象等内涵方面的因素。印度诗学中的庄严论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因为受到戏剧学的影响,比如在《舞论》中讨论语言问题就主要集中在形式方面,因为语言在戏剧中本来就是一种材料。另一方面,庄严论也受到语言学的影响。梵语语言学认为语言就是音和义的结合,诗当然也是音与义的结合,诗学以文学创作经验为基础的实践性特点使得诗学研究重视实例的归类概括,带有明显的经验主义色彩。
庄严论从文学语言入手来解释文学的本质,应该是诗学理论的一条基本途径。这条途径把文学当成语言现象,把握住了文学是语言艺术这个基本事实。这条途径在西方直到20世纪才被重视起来,形成了形式主义文论思潮。尽管这种西方现代文论与印度中古诗学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文学语言入手回答文学本质问题,并对文学语言进行细致分析,思路的相近也是不可否认的。
那么,庄严论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庄严论建立起诗学体系的基础是对语言形式的研究,其核心问题就是对各种不同“庄严”的研究。这种研究的基本前提是把诗看成是一种语言现象。婆摩诃为诗下的定义是“诗是音和义的结合”。他所说的当然是经过了修辞技巧加工过的音与义的结合。在这个基础上,他展开了对庄严的分类和举例分析。首先将庄严分为音庄严和义庄严。音庄严是语言方面的修饰,主要包括谐音和叠声两种;义庄严则是语义方面的修饰和各种修辞格,包括37种。两者相加共有39种。
除了庄严之外,诗病也是庄严论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也是从《舞论》开始就被专门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由于庄严论以语言形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诗病也主要是语言方面的缺点,包括语音和语义两个主要方面。不过婆摩诃并没有如此明确地区分,而是将诗病分成了两个10组共20种。这20种诗病中只有最后“违反地点、时间、技艺、人世经验、正理和经典”才涉及内容方面,主要是指出了违反人世经验和正理给文学作品带来的缺点。
当然,就像风格论、味论和韵论也会论及语言形式问题一样,庄严论也有关于文学功能、性质等方面问题的论述。婆摩诃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使人精通法、利欲、解脱等,也使人获得快乐和名声。“法是指社会法则,利是物质财富,欲是感官享受,解脱是摆脱生死轮回。这四个方面是印度文化传统中所确立的人生目的。”可见,庄严论认为文学可以实现人生理想。这个论述给予文学以崇高的地位,而且这个定位也被后来的文论家所认同。这使得印度诗学在繁琐的分类举例之外,多了一些理论色彩。这多少弥补了过多关注语言修辞所带来的不足,使庄严论对于文学的认识也更加全面。
(二)风格论
风格论是在庄严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诗学理论,其奠基者是比婆摩诃稍晚的檀丁(Da·ndin)。在《诗镜》这部重要著作中,檀丁继承了婆摩诃的研究领域,继续讨论庄严问题和诗病问题。他认为诗是由形体和庄严组成,形体是传达意义的特殊的语词组合,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文体,他把形体分为韵文体、散文体和韵散混合体三种就是证明。而他的庄严观念与婆摩诃没有本质区别,也是分成音庄严和义庄严,只是具体种类稍有调整。檀丁对诗病的看法与分类与婆摩诃相近,所以人们往往把檀丁看成是属于庄严论者。而风格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8世纪的伐摩那在《诗庄严经》中建立的风格理论也是在庄严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认为:“诗可以通过庄严把握。庄严是美,来自无诗病,有诗德和有庄严。”他把庄严概念由修辞的含义扩展为美的含义,说明了其理论渊源是庄严论。由此可见,风格论与庄严论的共同前提都是以语言形式为主要对象来讨论文学本质问题,都是属于形式主义文论范畴。
但是,风格论毕竟不同于庄严论。它的理论贡献在哪里?首先是对诗德的研究。诗德是在《舞论》中就已提出的概念,并作了初步研究。但在婆摩诃的《诗庄严论》中没有专门讨论。是檀丁的《诗镜》接着《舞论》的传统将这个概念引入到文学理论系统中,并系统地研究了十种诗德:紧密、清晰、同一、甜蜜、柔和、易解、高尚、壮丽、美好和三昧。其后伐摩那在《诗庄严经》中进一步重视诗德,把诗德的地位提高到与庄严等同,认为“诗是经过诗德和庄严修饰的音和义”,并进而将诗德分成十种音德和十种义德,对檀丁的十种诗德分别从音和义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使诗德研究更全面,也更系统。风格论对诗德的研究也是从语言形式方面入手的。对于完善这种形式主义文论又是一大贡献,而且,对诗德的研究为风格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因为风格的概念就是在诗德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诗德是风格中最重要的要素,可以说是风格的灵魂。
其次是对风格的研究。在檀丁和伐摩那的风格论中,风格都是指的地方特色或地域风格。檀丁主要区分出了维达巴(Vidarbha)和高德(Gaud·a)两种风格。维达巴是印度南方的地名,高德是印度东部的地名。伐摩那在这两种风格之外,又加上了第三种即般遮罗风格,般遮罗是印度北方的地名。这些不同的风格虽然以地域命名,但在风格论中,它们的风格特征却是用诗德来描述的。檀丁认为维达巴风格具有他所列举的十种诗德,而高德风格则表现出了与这十种诗德相反的特征。黄宝生先生认为:“大体上说,维达巴风格是一种清晰、柔和、优美的语言风格,高德风格是一种繁缛、热烈、富丽的风格。”伐摩那也认为:“维达巴风格具有所有诗德,高德风格具有壮丽和美好两种诗德,般遮罗风格具有甜蜜、柔和两种诗德。”可见,风格的确是在诗德的基础上提出的概念,它是对诗德的综合与概括,不同的诗德组合在一起会形成不同的风格。由于诗德是对文学作品语言特点的分析,所以风格论所研究的风格也仍然是语言风格,地域只是进行概括与综合的一个角度,风格论并没有强调地域因素在风格形成中的重要意义。另外,由于诗德的含义是文学语言的优点或审美特点,所以风格的概念也含有审美的意义,换言之,并不是所有的语言特点都可以成为风格的构成要素,而只有那些具有审美价值的因素组合起来才能构成风格。因此,风格也是文学作品的语言达到特定的审美标准时的一种表现。风格不仅是形式概念,而且是形式美的概念,一个美学概念。
因此,通过对诗德和风格的研究,风格论在庄严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印度诗学中的审美的因素。虽然风格论仍然属于形式主义诗学范畴,但它对审美价值的重视一方面使形式主义诗学更加完善,另一方面也为印度诗学走出形式主义诗学,走向审美研究开辟了道路。
(三)味论
味论在印度诗学中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味在《舞论》中就是核心观念。但由于《舞论》是戏剧学著作,婆罗多在论述“味”时也主要以戏剧为依据,所以如何将这种观念引入文学研究领域仍然是一个问题,引入文学理论之后,味论又将如何发展又是一个大问题。因此,尽管味论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文学理论中的味论对于中古印度诗学体系而言仍然是一个新的分支,对于中古印度诗学具有重要意义。
在现存最早的文学理论著作《诗庄严论》中,作者婆摩诃已经开始注意到“味”的问题,他所提出的39种庄严中就有“有味”。但他的认识还是十分朦胧的。檀丁在《诗镜》中对“味”的讨论是有意识的探索,因为他已按照《舞论》中所列举的八种味来详细讨论“有味”这种庄严了。但由于庄严论和风格论都侧重从语言方面来研究文学,而“味”则主要是一种审美感受,所以在形式主义诗学理论中只能作为次要问题而存在。直到9世纪楼陀罗吒(Rudrata)的《诗庄严论》和10世纪的楼陀罗跋吒(Rudrabha·t·a)的《艳情吉祥痣》才实现了从形式主义诗论向味论的转变。前者在传统的八种味之外又加了平静味和亲爱味,将味的种类扩大到十种,而后者则将《舞论》中的味论用于诗歌研究,认为味才是诗的本质,确定了味在文学领域中的本体地位。10—11世纪新护(Abhinavagupta)的《舞论注》,对《舞论》中的味论进行新的解释,文学领域中的味论体系才完全建立起来。
那么,新护的味论与传统的味论有什么不同?它对于诗学体系又有什么贡献?
首先,新护明确了“味”的存在方式,他认为味是一种心理现象,不存在于演员的表演,也不存在于对常情的摹仿。“味”是观众和读者的心理感受。其次,新护解释了“味”产生的原理。在新护看来,味的前提是由于人的心理存在着由无数次轮回留下的潜印象,这些潜印象是普遍的,对每个人来说都相似,所以在阅读文学作品或观看戏剧演出时,这些潜印象就被唤醒,与作品中的描绘产生心理感应,这就产生了“味”。第三,新护解释了味产生的过程。他认为味的产生是一个超越各种障碍的直觉心理过程。超越的障碍共有七种,即不适合感知、陷入自己或他人的时空特殊性、陷入自己的快乐等等、缺乏感知手段、缺乏直观性、缺乏主要成分、产生怀疑。超越这些障碍一方面使对象直接作用于读者和观众的心理感知,另一方面也使对象超越现实的具体性而获得普遍性,从而唤起心理潜印象的感应。第四,新护论述了“味”的性质,他认为“味的唯一性质是可品尝性。它不是超越品尝的独立存在。也就是说,一旦品尝过程结束,它也结束”。因此,味是一种心理过程。它不同于常情,常情是稳定的情感,而味是常情被唤起时的心理体验。第五,新护论述了味的特征,认为味是以超越世俗的惊喜为特征的。超越世俗就使对象不受现实功利和现实条件如时空物理环境等方面的限制,而惊喜是沉浸在心理体验中的特殊感受,用现代美学的术语来说应该相当于审美愉悦,是一种沉醉在审美感受中的心灵震颤。
通过对新护的味论的简要概括,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味论在中古印度诗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首先,它在传统的形式主义诗论之外开辟了心理主义和审美主义的领域,从而对文学艺术的本质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从“味”的角度来研究文学艺术,有助于揭示出文学艺术更为复杂的本质特征。其次,味论对味的讨论,对于审美心理研究是一个独特的贡献,这在世界诗学史上是一项重大理论成果,在那个时代的诗学中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关于味是一种心理体验过程的论述,在20世纪的西方审美心理美学和现象学美学中仍然是一个基本理论观念,而关于味是潜印象的心理感应的观点,也与20世纪西方的原型批评有相似之处。可见其理论价值之久远。
(四)韵论
印度诗学中的韵论是在梵语法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在公元前2世纪,梵语语法学家波颠阇利就对词的音与义进行了区分。认为词是原本就存在的、不可分割的、不变的意义。这种意义就是词本身,称为“常声”(sphot·a),而这个常声又是通过几个音素组合到一起的发音呈现出来的。这些能展示出“常声”(词的原本存在)的发音被称为“韵”(dhvani)。
关于语言有音和义这两个层次,在中古印度诗学中已有讨论。庄严论中就有音庄严和义庄严的论述。但音与义长期被分开来讨论,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没有明确的认识。词的意义一直都被认为是确定的,直陈式的,没有顾及词的表面意义之外的其他意义。语法学中关于“韵”的论述在诗学中长期没有得到回应。直到9世纪欢增(nandavardhana)的《韵光》才在语法学理论的启发下,提出“诗的灵魂是韵”的观点,建立起了印度诗学中的韵论派。
那么,韵论派的主要诗学贡献是什么?首先,韵论派通过对韵的论述,为文学艺术的本质的讨论开辟了新的道路。庄严论和风格论是形式主义诗论,主要从语言形式以及修辞方式和特征角度论述文学艺术的本质。味论主要从审美心理的角度论述文学艺术的本质,而韵论则是从语言表达效果或功能的角度论述文学艺术的本质。这从韵论派对于韵的界定可以看出来。欢增在《韵光》中说:“若诗中的词义或词音将自己的意义作为附属而暗示那种暗含义,智者称这一类诗为韵。”在语法学和哲学中,词的基本功能是表示和转示,词的意义也有两种,即表示义和转示义。表示义是字面义或常用义,而转示义是引用义或转换义。在韵论派诗学中,词又被发现具有另一个功能即暗示,因此词也就具有了第三种意义即暗示义或暗含义。诗的本质正是这种暗示义。而这种暗示性就是诗的“韵”。从词的功能角度来规定文学艺术的本质,不仅在印度诗学中是一种全新的探索,而且直到20世纪西方的符号学美学中仍然讨论相似的问题。由此可见其重要价值和对诗学理论的贡献。
其次,韵论吸收了庄严论、风格论和味论的思想,成为一种综合性的诗学体系,成为印度诗学体系中最为完善的理论。欢增的《韵光》出现在9世纪,在此之前已有《舞论》中的味论,与欢增同在9世纪的楼陀罗吒在《诗庄严论》中已经将味论引入文学理论中,而在此之前,7世纪婆摩诃的《诗庄严论》中已形成系统的庄严论,也是在7世纪,檀丁的《诗镜》中建立起了风格论,这些理论在欢增的韵论中都得到了体现。“欢增创立的韵论可以简单地归纳为韵是诗的灵魂,味是韵的精髓。庄严属于诗的外在美,而韵和味属于诗的内在美。韵和味代表了文学语言和非文学语言之间最本质的区别。韵论以韵和味为内核,以庄严、诗德和风格为辅助成分,构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梵语诗学体系。”味论在韵论中演化成了“味韵”,是韵的一种。不仅如此,欢增还对“味”进行了新的解释,使之内涵上与韵论的基本思想保持一致。他认为味也是暗示性的,味不是由一个名称直接得到的,而是通过情由、情态、不定情的暗示而领会到的。这样,“味”就与“韵”相融合,完全变成了韵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庄严问题上,欢增首先明确了庄严在韵论中的地位,认为庄严只是辅助味和韵产生的手段和工具,不能因为追求庄严而损害味和韵。另一方面,欢增认为有一些庄严本身也含有暗示性,但是如果暗示义不占主要地位,而表示义占主要地位,则这些庄严仍不能算韵,和韵有严格的区分。所以庄严和味与韵之间的主次关系是十分明确的,味和韵是中心。在风格问题上,欢增也是将诗德看成是对韵和味的表现。诗德是味的属性。比如甜蜜的诗德属于艳情味。诗德成为味的一种特定表现形态,风格论也就被有机地吸收到了韵论体系中。通过这样的体系建构,韵论比庄严论、风格论和味论更加全面,而且也更多理论色彩。不妨说韵论代表了中古印度诗学的最高成就,在世界诗学史上独具特色。
总之,中古印度诗学完成了作为世界三大诗学体系之一的印度诗学体系的建构。除了我们在此介绍的戏剧学中的味论和文学理论中的四个分支之外,还有王顶在《诗探》中集中讨论的诗人学,恭多迦(Kuntaka)《曲语生命论》中的曲语论,摩希摩跋吒(Mahimabhat·t·a)《韵辨》中批判韵论后建立的推理论,安主(Kt·emendra)《合适论》中全面阐述的合适论,世主《味海》中提出的可爱论等也都在印度诗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印度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