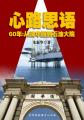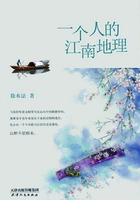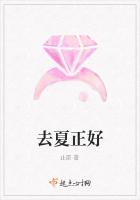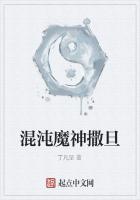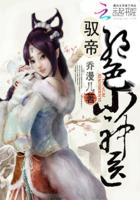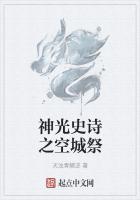1.后鸟羽上皇的歌论
后鸟羽天皇(1180—1239)1184年至1198年在位,退位后改称后鸟羽上皇。为夺回被镰仓幕府抢去的政治大权,1221年他发动了“承久之乱”,失败后出家,随后被流放到隐岐岛,后客死在那里,被追谥为后鸟羽院。后鸟羽上皇在让位后对和歌创作显出极大的热情,1200年命群臣进献《正治二年初度百首》,他自己也咏歌一首,借此机会得以接触到藤原定家的新歌风,受其影响,迅速成为了一名优秀歌人。他频繁举办歌会活动,不仅自己咏歌,还担任评判。作为一名帝王诗人,后鸟羽上皇非常看重诗歌的政教功用,他相信和歌可以“和神明,成治国之基”,于是经常献和歌于伊势神宫(皇家太庙),以求祖先保佑,因此其歌风格调高雅。
《后鸟羽院卸口传》是后鸟羽上皇的一部歌论书(文艺批评),他认为和歌的诗境有绮丽格调者,也有优美华艳者。对于初学者,作者列举了七条“至要”,结合自己创作活动的心得体会,论述了作为歌人应具备的艺术修养及创作技巧。本书的重点放在了对《新古今》时代歌人的评价上,如著名的歌人源经信、同俊赖、俊惠、藤原清辅等人,尤其是对藤原俊成和西行法师的歌风大加称赞,“优艳诣深、柔婉清怨”,同时还对同一时代的式子内亲王、藤原良经、慈元等歌人的作品进行了评价,他对藤原定家的和歌的评论是该书的主要内容,反映出了作者与众不同的审美观念。他对定家的作品多持批评态度,于是产生了他与藤原定家关系不和的传说,其实并非如此。后鸟羽院在书中道:“总的来说,他(定家)的和歌风格无人能及,然而并非人们应仿效的。他不致力于表现该有的思想内容,徒有艳丽典雅的辞藻风格。……定家是一个天生的作诗天才,(歌作)虽不具有深刻意蕴,然而词采优美流丽,无人可及。”后鸟羽院的这种观点与其后的顺德院(1197—1242年)在《八云御抄》中的观点是一致的:“总之,(和歌创作)应该以情志表现为主,闻之优美艳丽,追求诗情诗趣,而且直抒胸臆”,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如果强调词采艳丽,则必然导致情志表现不足。而直抒胸臆也可能会显得过于直白”,因此最理想的还是“心词”的统一。
产生这样结果的原因在于后鸟羽院的特殊身份,他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战乱不断,经历了源氏与平氏两大武士集团的权力争斗,政治上成为了镰仓幕府的傀儡,不仅如此,他在位不长时间便让位给了土御门天皇。1221年为夺回大权他发动“承久之乱”,失败后被流放到隐岐岛,他始终不忘夺回大权,传说他死后化成怨灵(鬼)作祟。虽然他热衷和歌创作,但是他更注重和歌的政教功用性,在他看来和歌只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御口传》是他流放后写成的。
2.花园天皇的歌论
花园天皇(1297—1348),1308年至1318年在位,1335年出家,死后谥号称花园院。花园天皇生活在****的南北朝时期,极少过问政事,潜心钻研佛法与歌道,具有内省性格,“诗品出自人品”,他的性格较多反映在他的文学活动中。他的诗学理论反映在《花园天皇宸记》及《风雅和歌集序》中,他继承了京极派歌人藤原为兼的学说并有所发展,强调表现的内容性,主张复古及注重文学的政教功用性,反对只重内容而忽略形式,但由于妖艳浓丽的诗风容易流于懦弱浮华,应避免过分雕章琢句。花园院将儒释两教与和歌理论相融合,赋予了歌道以宗教般深刻的哲理性,在他的述怀歌(言志)中,以理入诗的倾向非常明显,且具有禅趣。
花园天皇将他的歌学思想贯穿于《风雅和歌集》(1349)的编纂工作中,该诗集具有和汉两种序文。为这部歌集增添了权威性,在选歌时,除了选取前人的优秀作品外,更注重当代歌人作品的选取,尤其是京极派的诗歌。从入选的作品来看,诗人们对自然界中的曙晓、黄昏、明月、斜阳、雾雨等意象有着特殊的喜好,在对自然景物观照时,注重的是感觉上对其把握,对光影等自然的变换敏感纤细,描写手法细腻自然,而且排除任何主观情绪与抒情,少有雕琢之感。此外,从咏题上看,描写向往自然、深山隐居的作品非常多,追求的是一种枯淡衰颓之美。这与当时的社会政治不无关系。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社会动荡,贵族文人们向往世外桃源的隐居生活是符合情理的,他们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向宗教寻求精神的解脱,审美的注意也转向内心世界的挖掘上,成为后世流行的“闲寂”文学的胚胎。
(四)幽玄说
“幽玄”,是一种用语言难以描述清楚的深奥精微之义,最早是指老庄哲学或佛理的深奥,在我国古代,将“幽玄”用于文学评论的用例很少;日本最早用于文学方面的用例则见于《古今集》的汉文序,即“或事关神异,或兴入幽玄”。藤原宗忠在《作文大体》中说的“余情幽玄体”只是一种创作技巧而已。壬生忠岑在《和歌体十种》提出了“幽玄”与“余情”这两个美学范畴,但没有对其内涵作出阐释。从他举的例诗来看,“义入幽玄”是对诗的作者寄情山水、超凡脱俗的品行的一种称赞。至院政时期(指白河、鸟羽、后白河三代上皇实行院政的时期),“幽玄”脱离了原意,演变成朦胧、脱俗、高雅、有情趣等含义,成为当时的日常用语。而首先将它用于歌会评语的是藤原基俊(1060—1142),如他说的“言隔凡流入幽玄”,以及“词虽拟古质之体,义似通幽玄之境”等用语。藤原俊成继承了前人的学说,将“幽玄”变成了真正意义的文学范畴,后又经藤原定家、鸭长明、假托的鹈鹭系歌论四书的作者、正彻等人之手,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与完善。
1.藤原俊成的“幽玄说”
藤原俊成(1114—1204年)欣赏《万叶集》的“直寻”风格,他在评价《万叶集》时说,古人在创作和歌时,没有刻意去“饰姿磨词”,意为不追求华丽的词藻,由于人心质朴,吟咏性情时能做到感情的自然流露,毫无矫情作态,使人感到格调高雅。但他认为《古今集》的和歌才是和歌文体的范本。因为他认为:“和歌之本体,唯古今集可仰信也”。《万叶集》的和歌虽然“心深姿高”、格调高雅,但在作品优劣的选定上还做得不够,良莠混杂;而《古今集》才称得上是第一部精选的敕选和歌集,何况“《万叶集》年代久远,其姿(风格)、词皆难习得”。
对于和歌的本质,藤原俊成认为和歌应该朗朗上口,富有韵律美,他说:“凡歌者,颂于口咏于言也,故应有艳丽而幽古之声”。藤原俊成在《古来风体抄》中提出了评价和歌优劣的审美标准——“余情幽玄”,不过他未能对“幽玄”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如同“风骨”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内容与文辞一样,“幽玄”是一种风格,是题材、内容、文辞三者达到高度统一时营造出来的幽深清远的意境,它是日本社会由士族门阀制度向武士阶层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转变时期的产物,与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的产生有着近似的历史环境。
藤原俊成在《慈镇和尚自歌合》十禅师跋解释“幽玄”概念时所列举的和歌多为“婉丽妖艳”的男女情歌,而“妖艳”是“幽玄”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妖艳”本义是指美女诱人的姿态,以及给人带来的神魂颠倒、虚幻迷离的感官刺激与心理感受。在日本古代有许多例子,如日本人作的汉诗中就有“妖艳佳人望已断,为因圣主水亭”和“妾年妖艳二八时,灼灼容华桃李姿”的诗句。而将“妖艳”变成审美范畴,最早见于藤原基俊写于1134年的《中宫亮显辅家歌合》的“判词”。“妖艳”中的“艳”字则用得要早,藤原俊成非常喜欢使用“艳”字来评判和歌的优劣,在他的歌论及判词中出现多达90多例,但“妖艳”的用例仅有3例。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诗歌整体意境中表现出来浓丽妖艳的风格来把握“幽玄”的内涵。而这种妖艳的风格,藤原俊成用“姿”来表现,当内容与形式完美的结合产生出美的意境,带给人一种摇曳生姿的视觉美,具有浓烈的感染力,这便是和歌的“姿”,也可以说是一种风格。在心与姿的关系中,哪个更重要,藤原俊成与藤原公任各有侧重。藤原公任注重“心”(思想性)的表现;而藤原俊成则认为“姿”比“心”更重要,读者接触和歌时首先是受注重审美效果的“姿”的吸引,然后才是思想内容。藤原俊成倡导的“幽玄”已与壬生忠岑等人有所不同,他努力使和歌的传统美进一步内潜深化,旨在寻求一种深邃静寂的氛围和意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韵味清幽余味绵长的复合性情调美。
2.藤原定家的“幽玄有心体”
藤原定家(1162—1241)出生在一个和歌世家,其父俊成是当时宫廷歌坛的权威。藤原定家从十四五岁时便开始接触像《俊赖脑髓》这样的歌学理论,显示出非凡的文学天赋。他赠给西行法师的和歌“秋日眺江浦,红枫叶凋零。唯见渔家屋,孤立暮色里”,极具寂寥之色,意境幽远,弥漫着一种悲凉的气息。
藤原定家强调对古人创作经验的继承,他说:“和歌无师匠,只以旧歌为师”。藤原定家非常推崇纪贯之的歌风,他认为从源经信到藤原俊成,每一次对歌风的创新都未能脱离纪贯之的歌风。“新古今歌风”的确立标志着六歌仙歌风的复兴,强调了它具有的正统性。作者感叹正统歌风复兴不久却又走向衰落的现实,为打破这种僵化的局面,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在《咏歌大概》中提出“情以新为先,词以旧可用,风体可效仿先达之秀歌”,“词采慕古调,内容宜求新。欲达难及之诗境,可仿宽平以往歌者,其事自然成矣”。“慕古调”者,具体地说就是“本歌取”,也就是援用前人和歌的一部分歌语进行再创作,借用原和歌的意境来扩充自己作品的想象审美的空间。
藤原定家继承了其父藤原俊成的“幽玄论”中的“艳”的思想,他在《近代秀歌》一书中提出“余情妖艳”的命题。将“艳”与“余情”明确地联系起来,定家所提出的“余情美”是一种“不见文字但睹性情”的境界,其理论体系是以“艳美”为中心,确立了细婉妖艳、含蓄内敛、唯美浪漫的艺术风格,这也可以理解成一种意境论。
为此,他提出了“幽玄有心体”,即“构思奇巧、格调奇高、词采绮丽,意境优美之歌体”与“余情妖艳之体”(言外之旨、浓丽梦幻)。他认为“存和歌之本意者,莫过于有心体也”,意思是说“有心体”这种文体最能表现和歌的本质意义。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将天地之文采分为形与声两类,而人则为一下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他接着说道:“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岂无文欤?”按他的说法,人是“有心之器”,也即是人具有感情,可以“雕琢情性,组织辞令”。藤原定家说的“有心”也许与刘勰的“有心之器”有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标举“情文”,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所以说,“有心”即是“有情”或称“余情”。
藤原定家诗学思想集中反映在《每月抄》中,又名《定家卿消息》、《和歌庭训》等。藤原定家指出和歌有“十体”,即十种不同的和歌风格或体裁,作者最为推崇“有心体”,为了学好“有心体”,藤原定家认为要“静心凝神进入此一境”。只有诗人内心静虚,忘却功利,才能极大限度地遨游于审美的世界。从这一点来看,“有心体”不单是一种风格,也是一种创作方法,“有心体”虽是“十体”中的一体,但同时又是对“十体”的概括。作者表面上在谈论和歌的风格,实际上认为和歌的意义并非在于词采的华美,以及对景物的摹写,而在于借歌咏的对象来表现自我,“夺他人酒杯浇心中垒块”。这样一来,原本是风格论的“有心体”就变成了表现论和方法论。
所谓“有心”,是与“无心”相对的文学概念,无论人事抑或自然,诗人对咏题都有深刻的理解,这样创作出来的诗歌便会神思奇巧、意蕴深远,并富有情趣。有人将“有心”与“妖艳”两概念混为一谈,这是不准确的。妖艳是有心体和歌表现出来的一种浓丽风格,“有心”的和歌可以“妖艳”,而反之则未必然。“有心”被用于歌会的评判语,最初注重的是和歌的表现技巧,后来转为注重诗境的营造,也就是经历了由形式到内容的转变过程。从有心的内容上看,分成注重道德教化或宗教因素和注重抒情两方面。不过,禅僧诗人心敬的“有心”论则与此不同,他认为“有心”的最高境界应为“无心”,类似于王国维所说的“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但心敬将“无我之境”仍称为“有心”。另外,晚于和歌出现的另一种诗歌即连歌,分“有心连歌”和“无心连歌”两类。“有心连歌”注重思想内容的表现,而“无心连歌”则更多具有文字游戏的成分。
日本诗学很早就出现了“心词论”,“心”(内容)的概念先于“词”(表现形式或文采)出现,具体的每一个词语本身没有优劣之分,然依靠词语的搭配巧妙与否则关乎遣词造句的技巧高下。与心词论相近还有“风姿论”及“花实论”,“花”是指词采;“实”指不是由“生硬的”而是由“华丽雅正”的词语所带来的艺术效果,进而可以说“有实”也即是“有心”。最理想的状态是“心”、“词”二者如同鸟的双翅,即所谓的“花实兼备”。谈到“姿”论时,藤原定家提出了“秀逸体”,将其与前面提到的十体结合起来而成,不同于十体中的任何一体,然“皆挟其姿也”,用“心词论”来说就是“心深格高巧,词尽意有余,风姿雅正”。钟嵘说过“赋比兴三法酌而用之”,则诗有诗味,这就是说诗歌的技巧运用巧妙可以产生好的艺术效果。《每月抄》作为藤原定家的代表歌论著作备受后人的重视。
3.鸭长明的“幽玄体”
鸭长明(1155—1216)在歌学方面亦有很高的造诣。所著《无名抄》成书的年代不详,内容繁杂,体裁类似我国古代的诗话形式,作者论述了《古今集》与《新古今》所分别代表的歌风得失,即所谓的中古风与新风,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藤原定家的近代秀歌中论述的“达摩歌”、“幽玄体”的阐释。他认为“幽玄体”的和歌应有“言辞无法尽意的余情(象外之旨),用姿(意象)难以表现出来的景气(意境)”,就如同水中花、镜中像一般,迷离缥缈,可望而不可置于睫前。“景气”作为审美范畴首先由藤原俊成提出,作为幽玄的补充概念而使用,它不是指诗句中的词语描写的景象,而是由读者的联想带来的一种虚忽缥缈亦真亦幻的审美体验。对这种抽象的审美意象,鸭长明也采取种种比喻试图加以说明。
“景气“作为诗学范畴出现在中世文学,最早提出“景气说”的是俊惠(鸭长明的老师)还是藤原俊成,尚无定论。藤原俊成的最早用例见于建久四年的《六百番歌合》的判词。藤原俊成在《慈镇和尚自歌合》十禅师十五番跋中写道:“大凡和歌者,未必声律奇巧、理趣精彻。原本咏歌之事,读者吟之咏之,应觉其清丽优艳、意境幽深(余情)等莫名之感。若为良歌佳作,其词采之外定有景气添附。例如,春花丛畔一抹霞,皓月当空鹿清呦。岭前秋雨飞红叶,篱垣春风送梅香。”而俊惠没有直接的论著传下来,只是在其弟子鸭长明的论著《无名抄》中略有记载。俊惠说:“世间常人所作之和歌犹如坚文法编织的平纹布一般,而优美艳丽之和歌则像浮文法织就的提花锦缎一样。景气浮于空也。”
鸭长明的歌论在许多方面都吸收了藤原俊成父子的歌学理论,又与他们有不同之处,如藤原俊成非常注重和歌的声律音韵,而他则不以为然。况且藤原父子俩在幽玄论上本身就存在着差别,鸭长明试图作出调和,但矛盾依然存在。此外,鸭长明总结了日本歌论中关于心与词的关系的发展轨迹,他认为《万叶集》的和歌虽注重陈述心志,但还是强调心与词的调和;《古今和歌集》、《后选和歌集》则打破了这种调和,以写心为重;《拾遗和歌集》起又重新回到了心与词的调和上来。就这样,日本文学通过对心与词的认识的不断深化,最终从中国诗言志的功利思想中摆脱出来,走向审美诗学的发展之路。
4.鹈鹭系歌论四书论“有心体”、“幽玄体”
鹈鹭系歌论四书指《愚见抄》、《愚秘抄》、《桐火桶》以及《三五记》,除太田水穗在《日本和歌史论》中世篇一书中主张是藤原定家之作外,绝大多数日本学者认为是有人假托之作。但历史上正彻、心敬及世阿弥等人都在自己的书中引用这四本书,并认为是定家所著,这足以说明该书在日本中世歌论的流传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
《愚见抄》等书被放在两个木匣内,分别写着“鹈”字与“鹭”字,故被称为鹈鹭系歌论书。虽然它们并非定家所著,但主要内容与定家的《每月抄》有着密切的联系。“定家十体”中“有心体”最为重要,“幽玄体”只是和歌基本四体之一。《愚见抄》除了十体外,又增加了八体,也是以“有心体”为最主要,将“幽玄体”细分为“行云”与“回雪体”,大概受到了《高唐赋》的启发,“幽玄体”的地位被提高,仅次于“有心体”。至于《三五记》更是增加了二十体。这四本著作都注重“有心体”,那何为“有心体”?因为“体”的概念比较混乱,有的是指风格,有的是指诗格即形式体裁,而“有心体”则指一种思维形式或创作态度,“有心”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指和歌的思想内容,而是作者才性、情志的综合体,是从其父藤原俊成提倡的“本意”发展而来。刘勰在《原道》中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此言用于和歌也同样是有道理的,和歌的创作是诗人有表达“本意”的需求,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和情感的抒发,而理想的状态则是“有心”,正所谓“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和歌创作如果“有心”,则自然诗境天成,意境幽远,具备“妖艳”的美感。
5.藤原为家的“幽玄论”及其他
1241年藤原定家去世后,他的儿子藤原为家(1198—1275)成为了歌坛的中心人物,同年他作为“御子左家”的传人当上了“权大纳言”(官名),从藤原俊成到藤原定家,再到藤原为家,形成了连续三代御子左家独霸歌坛的局面。藤原为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歌人,代表作有《咏歌一体》等。他认为和歌的词语应平易清新,风格上应具有清逸怡静之美。这对二条派及后世的和歌创作影响较大,但没有脱离藤原俊成、藤原定家等前人理论的窠臼,少有创新。藤原为家于1243年举行了“河合社歌会”,并任评判,显示了他的权威及诗学主张,在评判和歌时将“心”(意蕴)、“词”(词采)、“姿”(风格)作为评判的标准,并没有偏重其一,而且注重和歌的审美功用,将“幽玄”解释为“优”(优美)、“艳”(浓丽)的风格,认为和歌以优美典雅为上品。在其判词(评语)中可见“景气幽”、“远白”(雄浑)、“有力”等词语。
藤原为家在他的歌学著作《咏歌一体》中还系统地论述了诗学理论。他首先提出了“稽古”思想,“稽古”即练习,大意是说学习和歌,应摹仿前人的优秀作品,多多练习才能尽快掌握写作的技巧,这在《后鸟羽院御口传》、《徒然草》以及后来心敬的学说中都有所反映,只是藤原为家的歌道思想更多地注重写作技巧,而忽视了诗人情感思想的表达,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次他提倡平淡之美,这与其父定家主张的妖艳(浓丽)之美明显不同,所谓平淡,不是简朴单调,而是外枯内膏,是对审美规律认识的深化。而且这种平淡之美要求创作时不能使用“刺耳”之词,即避免使用感觉浓烈刺激的词藻,这一点构成了后来二条派歌学的理论基础。第三点是强调用少量词语表达意蕴深厚的内容,尤其注重情感的渲染,这与前人主张的“余情”(余韵)有着一脉相传的关系。此外,藤原为家主张“制之词”,或称“禁之词”,对和歌的用语进行规范,将古人的著名诗句中的秀章丽句列为有主之词,禁止后人借用甚至抄袭。这种观点为古代日本人学习和歌提供了易于掌握的规范,其意义深远。只是后来的继承者们因循守旧,使和歌创作陷入保守僵化,这也是藤原为家歌论常受人诟病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