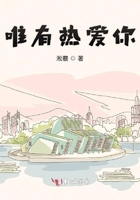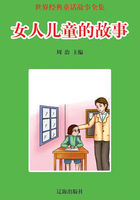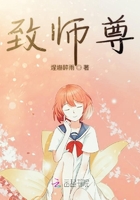二、茅盾的自然主义诗学观
如上所述,在20年代初期,茅盾曾花大力气介绍过自然主义。茅盾提倡自然主义,是从批判鸳鸯蝴蝶派,发展新文学创作这一积极意图出发的,茅盾将自然主义当作文学发展中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明确指出“现代文艺都不免受过自然主义的洗礼,那么,就文学进化的通则而言,中国新文学的将来亦是免不得要经过这一步的”。茅盾是用进化的文学发展观来审视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自然主义在西方文学演进的历史上尽管已成为过去,但对于中国新文学来说,其文化进化的链条上还缺少这一环节。在《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中,他进一步阐述了作为文学进化过程中的自然主义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意义:
以文学为游戏为消遣,这是国人历来对于文学的观念;但凭想当然,不求实地考察,这是国人历来相传的描写方法;这两者实是中国文学不能进步的主要原因。而要校正这两个毛病,自然主义文学的输进似乎是对症药。这不但对于读者方面可以改变他们的见解、他们的口味,便是作者方面,得了自然主义的洗炼,也有多少的助益。不论自然主义的文学有多少缺点,但就校正国人的两大病而言,实在是利多害少。
他认为今后中国新文学要走新浪漫主义道路,而“走路先得预备,我们该预备了”。在茅盾看来,当时中国的新文学显然尚未达到搞新浪漫主义的阶段,必须先让自然主义出来,而吸收自然主义的技术,也可以进一步为建设新浪漫主义文学创造条件。他还提到“新浪漫主义在理论上或许是现在最圆满的,但是给未经自然主义洗礼,也叨不到浪漫主义余光的中国现代文坛,简直是等于向瞽者夸彩色之美”。
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对茅盾影响最大的一点,是在科学旗帜下对作品真实的极端追求。以法国现实主义与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相结合形成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把这种真实推向了极端:与现实主义相比,“写实主义是以写现实为目的,……而自然主义却只是写真,真的一语是自然主义的生命,是自然主义底标语”……茅盾认为,自然主义的“真”有两层含义,“一方要表现全体人生的真的普遍性,一方也要表现各个人生的真的特殊性”,只有把普遍的真与特殊的真结合起来,文学才会“美”,才算“善”。从“真的普遍性”出发,茅盾要求文学反映的现实社会人生具有普遍真实性。因此,他极为重视文学反映时代的广阔性,体现出时代精神。
从“表现各个人生的真的特殊性”出发,茅盾要求文学作品的细节的真实,人物个性的鲜明。因为“从客观方面说,天下本无绝对相同的两件事,从主观方面说,天下亦决无两人观察一件事而所见完全相同的”。据此,他在文学批评中要求新文学作品在描写上要“件件合情合理”,给人以真实感。自然主义这种真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使早年的茅盾尽管未能明确提出“典型”的概念,但却使他较早地触及到典型理论的核心。早在1920年1月,他就认识到“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不过描写全社会的病根而欲以文学小说或剧本的形式出之,便不得不请出几个人来作代表。他们描写的虽只是一二个人、一二家,而他们在描写之前所研究的一定是全社会、全民族”。
茅盾对一切文学理论的介绍、提倡、批评,都是以怎样使文学更好地“为人生”之目的为准绳的。他对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观念提出了社会化、理性化的批评。他认为,把自然主义理论引入文学创作领域自有其可取之处,而倘若推及人生观的范畴,那就大谬不然了。他提醒人们,不能让自然主义那种“由生理方面观察人生”的原则对社会理性造成干扰,“因为人生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而且科学的实验的方法,未见能直接适用于人生”,“何况人生是不能放在试管里化验的呢!”他强调道:“我们要自然主义来,并不一定就是处处照它,从自然派所含的人生观而言,诚然不宜于中国青年人,但我们现在所注意的,并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我们所要采取的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为了严格区分人生观和创作方法之间的界限,茅盾对自然主义“技术上的长处”下了明确的定义,即“科学的描写法”,“见什么写什么,不想在丑恶的东西上面加套子”。
茅盾从自然主义理论及其作品中,接受了科学的真实概念,但从为人生出发,他所强调和追求的艺术真实与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所要求的真实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左拉那里,创作中的科学精神是指作家要像自然科学家做试验一样,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与方法,对人进行一种真正的实验;茅盾摒弃了左拉的这种试验方法,而把科学精神用来要求作家具有严肃认真而非游戏消遣的创作态度。在左拉那里,关注自然的人比关注社会的人更重要;而茅盾则要求作家学习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社会问题、男女问题、进化论等,以避免作品内容的单薄与用意浅显两个毛病。左拉要求的“真”是指作家要从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身上挖掘出“兽性”,“全神贯注地分析人体的肌理”;茅盾要求的“真”,是真实地表现社会人生。茅盾汲取的是左拉的“真实”概念与认真的态度,摒弃的是其“作品内所含的思想”。因此可以说,茅盾对典型问题的认识,受到自然主义真实论的启发,但又远远超越了自然主义。
第四节 象征主义诗学的理论旅行
象征主义源于爱伦坡的诗学理论与创作实践,后成为19世纪末法国文学艺术的主潮,进而辐射欧美乃至全球。象征主义注重意蕴传达的朦胧性、暗示性,强调借助意向、象征和“客观对应物”等手法来间接表达作者意旨,它为20世纪的世界诗学开辟了一条使文学审美内涵进一步向丰富化和复杂化迈进的道路。
中国新诗在外来流派的诸多影响中,受象征主义的影响尤为明显。罗家伦曾说过:“《新青年》上有些新诗就是采用西洋Symbolism(象征)的方法写成的。”随着象征主义新诗创作的发展,作为对创作现象归纳总结的相应的诗学理论也大量出现。总体上来说,现代中国语境中的象征主义诗学话语是横向移植的产物,其理论形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构成:一是对国外象征主义理论和作家、流派等的译介、评述;二是中国作家植根于本国本民族文学的历史、现状与艺术期待,在吸取融会基础上所建构的中国化的象征主义诗学理论;三是中国作家以自己所理解、掌握的现代象征主义理论对新文学创作中的象征主义所进行的批评。
一、1913—1926年:象征主义诗学的****
中国较早一篇从思潮角度介绍象征主义的文章是赵若英的《现代新浪漫派之戏曲》,该文将象征主义译为表象主义。作者把象征主义思潮视为对自然主义的反拨,认为这些作品“对于一种超自然者,或神秘者,或一种不可抗的命运,或一种异常的情绪,无不含有不安以及阐明之色彩”……这是从内容方面对象征主义的把握。
茅盾从文学应该为人生、救时弊的功利主义出发,认为写实主义的文学虽然能暴露社会的丑恶,但是因为社会人心迷溺,不是一味药可以医治好的,应该同时走几条路,象征主义也值得提倡。他说:
写实文学的缺点,使人心灰,使人失望,而且太刺激人的感情,精神上太无调剂,我们提倡表象,便是想得到调剂的缘故。况且新浪漫派的声势日盛,他们的确有可以指人到正路,使人不失望的能力。我们定然要走着路的。……表象主义是承接写实之后,到新浪漫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得不先提倡。
谢六逸将借表象的手段、取暗示的方法,视为象征主义的主要特点。认为:表现主义的文艺,有偏于神秘的情调的倾向,是主观的艺术,有寓意、暗喻、讽刺、暗示种种。这派的手段,是要使著者自身的神经震动,直接传之读者。使阅者起共鸣(resonance)的作用;并要使阅者生联想的情感,将从前经验过的事物,重新表现出来。
可以看出,早期涉及象征主义的文章均停留在泛泛介绍的层面,而介绍人的动机也各不相同,有的基于文学救世立场,期望引进象征主义以医治“社会人心的迷溺”;有的持文学进化观,主张文学演进,循序渐进,不可跨越,西洋如此,中国更不能例外。直到1925年李金发出版诗集《微雨》,对诗集的评论相继而来,现代中国的象征主义诗歌批评才开始出现。
钟敬文在1926年12月5日出版的《一般》杂志上发表了《李金发底诗》一文,文章写道:在“诗坛的空气消沉极了”的时候,读了李金发的诗“突然有一种新异的感觉,潮上了心头”;虽然“起初就已是那样觉得它的不大好懂了”,但“像这样新奇怪丽的歌声,在冷漠到了零度的文艺界,怎不叫人顿起很深的注意呢?”一个月之后即1927年1月,赵景深也撰写了《李金发的〈微雨〉》。他先指出李诗“是很难索解的”,接着列举了一些也是作品难懂的中国古代诗人后发出感喟:“我真不懂他们为什么做人家看不懂的东西。文学不是要取得读者同情的么?”很明显,两篇文章对李金发的诗不论肯定或否定,还都只是感受层面上的表达,还没有达到理论分析的高度。
周作人不是象征主义诗人,也没有系统研究过象征主义诗论,但他的文艺观与象征主义却是有相合之处的:“诗的效用本来不在说明,而在暗示,所以最重含蓄”,“诗思的深广全凭暗示的力量。”周作人:《论小诗》,载《民国日报·觉醒》,1922年6月29日。1926年周作人在为刘半农《扬鞭集》所作的序言中对新诗直白化、散文化和哲理化的倾向提出非议:“新诗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欢唠叨的叙事,不必说唠叨的说理”。周作人在《扬鞭集·序》里,首次将古典诗学中的“兴”与西方诗学的“象征”对应起来,主张诗应给人带来一种“余味和回香”,即能造成一种朦胧含蓄的美,而这样的诗学效果可以通过传统的“兴”来取得,“用新名词来讲或可以说是象征”;认为“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写法,但也是最旧,在中国也‘古已有之’”。他一语中的地点破了对于李金发来说尚在朦胧含糊状态的“根本处”,一锤定音,准确地把握到“兴”与象征的共同之处是将物与心境沟通,旨在营造诗歌蕴藏含蓄的意境,表现诗歌的“正意”、“精意”,是克服新诗直白的叙事说理弊端的有效艺术手段。周作人虽未对象征与“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理论思考,但他的“象征即‘兴’说”指出了西方象征主义诗学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和中国古典诗艺在审美本质上的相通处,并敏锐地意识到中西诗艺的“融合”将会开拓出中国新诗无限广阔的发展道路:“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会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这番表述在当时很具有代表性,它清晰地展示出,救助新诗直白化的一个必然路径便是对象征和象征主义的倡导。
郁达夫在《文学概说》一书中介绍过象征主义,他认为艺术的表现中,我们要想表现自己,必须用一种媒介物或材料即象征。象征有两种,一种是粗杂的象征,一种是纯粹的象征。纯粹的象征是一种象征选择的苦闷,“何以有一派要选择纯粹的象征呢?因为象征是表现的材料,不纯粹便不能得到纯粹的表现。这一种象征选择的苦闷,就是艺术家的苦闷。我们平常听说的艺术家的特征性,大约也不外乎此了。”“所以艺术家是对于选择表现象征最精细的人,就是最能纯粹表现自己的人。”在该书第二章的艺术分类图表中,他把象征主义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并列。在《怎样叫做世纪末文学思潮》一文中,郁达夫称象征主义运动是世纪末文学思潮的一种末流。在《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中,又把波德莱尔称为颓废派,认为自然主义“没有进取的态度,不能令人痛快的发扬个性,于是一群新进的青年,取消极的反抗态度的,就成了所谓颓废派和象征派的运动”。
1928年1月,黄参岛在《美育》第2期上发表《〈微雨〉及其作者》,文章不仅谈到《微雨》“在我们的心坎里,种下一种对于生命欲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丽”,而且指出作品受波德莱尔《恶之花》和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的影响,对“此时唯丑的人生”“同情地歌咏起来”。所以,如果从理论分析的高度看问题,这篇文章才开始涉及象征主义诗学批评。
在早期介绍“象征主义”的普及文章中,周无曾提到“‘象征主义’专爱描写心理上的人神交感主义或是类如宗教的渺茫荒诞的迹象”,来满足“神秘要求者的信仰心”,助他们逃脱科学达不到的“僻境”或“奥秘之处”……周无站在无神论的立场,关注“象征主义”的宗教追求,以及由此带给读者的信仰满足。谢六逸在《文学上的表象主义是什么》中,探究象征的起源,“全系根基于神秘的倾向”,以为“人目所见的世界与人目未见世界、物质界与灵界、有限世界之间,是相通相应的”,因此,非用“表象的手段”、“暗示的方法”不可。周无与谢六逸或多或少地接近了象征主义的核心内涵,注意到“象征主义”源于一种超越现实的宗教渴望。1926年以后,“象征主义”的超验内容在文字中消失,代之以对“纯诗”的命名和定性。象征手法被抽离出来,成为锻造“纯诗”的不二法宝。
二、1927—1937年:象征主义诗学的鼎盛
20年代中后期,以李金发为首的初期象征派不遗余力地引进象征观念、现代技法,以别具一格的创作实践和真切的象征体验,大大加深了人们对象征主义的理解,也推进了对象征主义的研究。无论日后评论界肯定李诗“如拆碎的七宝楼台,散落的明珠,朦胧恍惚,富于幻觉,带有感伤颓废和异国情调”也好,还是直言李诗“半文半白,似通非通”,“对于母语(白话和文言)都缺少修养”也好,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李金发凭借诗人独有的敏感,竭力搜寻“中西诗之间”的“同一思想、气息、眼光、取材”,“试图沟通、调和中国古诗和西方诗歌之间的根本处”,这种努力使他成为现代诗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
作为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始作俑者,李金发既是“第一个”将波德莱尔介绍到中国诗界的诗人,也在象征主义诗学领域有所拓展。1919—1925年,李金发留学法国。在这期间,他读到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并非常崇拜魏尔伦。他曾回忆道:“雕刻工作之余,花了很多时间去看法文诗,不知什么心理,特别喜欢颓废派Charles Baudelaire(波特莱尔)的《恶之花》及Paul Verlaine(魏尔伦)的象征派诗,将他的全集买来,愈看愈入神,他的书简全集,我亦从头细看,无形中羡慕他的性格及生活。”他把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等人誉为自己的“名誉老师”,说他“最初是因为受了波德莱尔和魏尔伦的影响而作诗的”……他从波特莱尔等象征主义先驱那里首先获得了“艺术至上”的理论滋养,曾颇带学舌意味地声称:“艺术是不顾道德,也与社会不是共同的世界。艺术上唯一的目的,就是创造美,艺术家唯一的工作,就是忠实表现自己的世界。”李金发:《烈火》,载《美育》,1918年1月创刊号。这番洋溢着唯美主义色调的阐述突出了“美”的地位,而他所说的“美”在内涵上也染上了浓重的象征主义色彩。
李金发这样论述自己所理解的“美”:“夜间的无尽之美,是在万物都变了原形,即最平坦之曲径,亦充满着诗意,所有看不清的万物之轮廓,恰造成一种柔弱的美,因为暗影是万物的装服。月亮的光辉,好像特用来把万物摇荡于透明的轻云中,这个轻云,就是诗人眼中所常有,他并从云去观察大自然,解散之你便使其好梦逃遁,任之,则完成其神怪之梦及美也。”以拖沓生涩的腔调表达关于美的朦胧特性和变形本性,这正是象征主义诗学所求索的结果。李金发出于对象征主义诗学的理解,将美视为主观心性的体现,甚至以此排斥客观之美的可能。他鼓吹“现实中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美,美是蕴藏在想像中,象征中,抽象的推敲中”的极端之论,从而为他大力倡导象征主义诗学张目:既然美蕴藏于想像与象征之中,那么理所当然地,“诗之需要Image(形象、象征)犹人身之需要血液”,象征主义诗法也就成了必然强调的对象。
穆木天的象征主义诗论受马拉美的“暗示说”的影响最深。和马拉美一样,穆木天主张诗歌的宏旨是揭示心灵世界的奥秘。穆木天的诗论以反对胡适倡导的“明白清楚”的美学规范为起点,以探求蕴藏含蓄的新诗的创作途径为指归。他倾向于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原则取代传统现实主义的再现原则,在审美价值上更偏重诗的内涵的朦胧、神秘和多义性。穆木天的诗论对西方象征主义的借鉴成分重,创见不多,但是他强化了象征主义的“暗示”、“表现”的创作原则,强调把“含蓄”、“深邃”作为诗歌的审美价值尺度,重视诗歌的审美特性。
穆木天“纯诗”理论是通过《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集中提出的,该信最初发表于《创造月刊》的创刊号上,后收入作者《旅心》集中。所谓“纯诗”,就是“纯粹的诗歌”,其代表观点乃是瓦雷里表述的:“纯诗的思想,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典范的思想,是诗人的趋向、势力和希望的绝对境界的思想。”说得较明白一点,纯粹的诗歌就是要保持诗歌纯粹的艺术性,从诗歌中“完全排除非诗情的成分”。穆木天也认为“纯粹诗歌”是“纯粹的诗的Inspiration”的表现,“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是“人的内生命的深秘”的象征。穆木天显然受到了瓦雷里的启发并直接沿用了他的概念,但他并没有带着强调的语气重申后者的观点,甚至没有在文中接上后者的话茬,因为他虽然仍从诗歌艺术表现和艺术形式着眼,可并未打算重炒艺术至上主义的冷饭。于是,穆木天的“纯诗”理论既与波德莱尔的唯美主义传统拉开了距离,也与瓦雷里的共名概念存有区别。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些理论完全是出自他自己诗性思考的“杂碎的感想”,也完全体现着他的理论贡献。
穆木天所提出的“纯诗”理论,大约包含三方面的内容:“诗之物理学的总观”,诗的“暗示能”及“诗的思维术”。所谓“诗之物理学的总观”其实就是关于诗歌形式的总体思路。象征主义有着深厚的形式主义传统,穆木天对于形式的追求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一传统。他的“纯诗”观首先强调的便是形式的纯粹性,包括诗与散文的区别之绝对性的阐述:“我们的要求是诗与散文的纯粹的分界。”他认为这就是营造“诗的世界”之必需的前提。在这样的观念基础上,他甚至对波德莱尔式的散文诗都有所保留:他并不一般性地反对散文诗,只要它表现了“诗的旋律”;可波德莱尔常常是“在先作成散文诗,然后再译成有律的韵文”,“先当散文去思想,然后译成韵文,我以为是诗道之大忌。”波德莱尔是象征主义代表,可在诗歌形式上对他的如此责难并不意味着中国诗论家乖违了象征主义。
穆木天并没有从单纯的形式意义上阐述自己的“诗之物理学的总观”,他知道“内容与形式是不可分开”,要保持形式的“纯”,必须从支撑形式的内容要素上寻找根本依据。于是,他别出心裁地提出了“诗的统一性”和“诗的持续性”两重命题。所谓“诗的统一性”,即主张诗歌在一定形式中表现内容的单纯性,“一首诗是表一个思想”,这样才能保证诗的“秩序井然”,保证诗的形式像在“先验的世界”里一样清纯。他指出,“一个有统一性的诗,是一个统一性的心情的反映,是内生活的真实的象征。”
一般认为王独清发表在同期《创造月刊》上的《再谭诗》是对穆木天《谭诗》一文的补充和呼应,王独清的诗学观念同穆木天的“纯诗”理论趋于一致,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早期象征主义诗学的基础。王独清是呼应着穆木天《谭诗》的“纯诗”理论才写了《再谭诗》的通信,在《再谭诗》中王氏也确实对穆木天的象征主义诗学提出了若干补充意见。王独清初看到穆木天“谭诗”的那封信,便惊叹“何以你对于诗的观念竟这样和我相似”,可见这些诗学思想在他也是早已有之的;他对于穆木天“纯诗”理论即使算是补充,也还是充满了学术建树,有些观点实际上还对穆氏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修正。
王独清在阐述自己诗学思想的时候始终坚持自己的诗人角色,同穆木天相似地,尽量将自己的诗性感受糅进理论表述之中。他的感受浸润着欧洲现代文明的末世风情,与象征主义情调更趋于一致。他看出穆木天的诗法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古尔蒙的影响,又自述他“也很想学法国象征派诗人”。在法国诗人中,他最爱的四位诗人便是拉马丁、魏尔伦、兰波和拉法格——都是象征主义诗国的坚守者。比较起来,他对象征主义诗学的理解更接近法国象征诗人们的主张,并从诗歌外在结构与内在构成这两方面作了更明确也更个人化的发挥。王独清的诗歌外在结构观类似于穆木天的“诗之物理学的总观”,在这方面,他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完美之诗的“公式”与应取的“诗形”二说。他“理想中最完美的‘诗’便可以用一种公式表出:(情+力)+(音+色)=诗”,在这个公式中,最重要的因素是“音”与“色”,特别是这两者的结合:“‘色’‘音’感觉的交错”,即有“色的听觉”或者所谓“音画”之魅。他十分准确地总结出法国象征诗人“把‘色’(Couleur)与‘音’(Musique)放在文字中,使语言完全受我们底操纵”的诗学原则,在这种原则下,诗人的直觉感应将得到完全的呈现,读者也将直接由神经刺激的经验层次涉入诗性的解读。这确实是象征主义出奇的一招,也是备受古典主义者甚至传统浪漫主义者指责的一点。
以较为系统的理论评析现代中国的象征主义诗人、作品和流派,是30年代以后的事。1933年7月,苏雪林在《现代》第3期发表《论李金发的诗》,这是可见到的第一篇使用了“中国象征派”这个术语和以现代象征主义理论观念批评李金发作品的文章。
1935年5月的《清华周刊》第43卷第1期刊载了孙作云的《论“现代派”诗》,谈到现代派在创作上反拨了新月派的“文字之美,而求诗的意象之美”。他认为现代派深受欧美象征主义诗歌运动和美国意象派影响。他把戴望舒的诗论同意象派提出的“六个规律”作了比较,认为前者对后者有“许多因袭之点”。孙作云的论述虽不乏正确,但总体上说失之平浅,对创作艺术特征的分析尤其显得不够。
朱自清写于1935年8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也有对象征派诗人的论述,他将十年来的诗坛分为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和象征诗派等三派。一年多以后,在《新诗的进步》一文中他仍然坚持“三派”分法,并从流派的角度分析说:“象征诗派要表现的是些微妙的情境,比喻是他们的生命;但是‘远取譬’而不是‘近取譬’。所谓远近不指比喻的材料而指比喻的方法;他们能在普通人以为不同的事物中间看出同来。他们发见事物间的新关系,并且用最经济的方法将这关系组织成诗;所谓‘最经济’就是将一些联络的字句省掉,让读者运用自己的想像力搭起桥来。没有看惯的只觉得一盘散沙,但实在不是沙,是有机体。要看出有机体,得有相当的修养与训练,看懂了才能说作得好坏。”他的这段分析深入浅出,相当精辟地揭示出象征诗派在艺术思维方式和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方式上的特征,至今是我们解读象征主义创作的一个指南和评论象征主义创作的理论依据之一。
李健吾把象征主义文学批评的笔触主要集中在了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创作赏析上,象征主义文学批评在他那里被引向新的范围与层面。在《〈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这篇文章里他极力肯定了现代派形成的必然性,认为他们的作品中“言语在这里的功效,初看是陈述,再看是暗示,暗示而且象征”。卞之琳见到这些评论后声言与自己的创作初衷多有不符。于是李健吾再写了《答〈鱼目集〉作者》,他写道:“如今诗人自白了,我也答复了,这首诗(指《圆宝盒》——引者注)就没有其他‘小径通幽’吗?我的解释如若不和诗人的解释吻合,我的经验就算白了吗?诗人的解释可以撵掉我的或者任何其他的解释吗?不!一千个不!……诗人挡不住读者。这正是这首诗美丽的地方,也正是象征主义高妙的地方。”好一个“诗人挡不住读者”!李健吾的回答触及了接受美学最基本的内容,虽然在当时的认识条件下他未能对此作出具体的理论分析。
30年代梁宗岱得益于开阔的中西文化视野,在理性的支撑下,以感悟为先导,对“象征主义”进行了最富诗意的阐释和左右逢源的论证。“象征主义”似乎不再是西方诗学的专利品,而是有史以来中西方诗学共有的财富,是不同时空的诗人的共同追求。可以说,梁宗岱对象征主义诗学理论的介绍是最集中的,也是最成规模的,他是第一个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的语境中系统阐释象征主义诗学观念的理论家。他继周作人之后再次提出“象征”与“兴”的相似之处,进一步用象征主义的诗学观念去解读中国古典诗词,从而使象征主义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进入了对话与互读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象征主义的诗学观念得到了更加系统的中国化的阐释。
具体而言,深谙中西诗学精髓的梁宗岱并没有展开宏观的全面的比较,而是敏锐地发现某个概念上二者的相似性,并以此向彼此的纵深处推进。“象征”便是这样一****相。30年代,梁宗岱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象征主义》、《诗论》、《瓦雷里与歌德》、《韩波》等,尤其可贵的是,梁宗岱始终坚持在创作理念上讨论象征。梁宗岱丰富和深化了周作人提出的“象征即‘兴’说”,把象征的解说从单一的艺术手法引向更深的理论层面。在《象征主义》一文中,梁氏首次郑重其事论证了“兴”与“象征”的关系,“我以为它和《诗经》里的‘兴’颇近似”,并依据《文心雕龙》“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义”,提出自己的主张:“所谓‘微’便是两物之间微妙的关系。表面看来,两者似乎不相联属,实则是一而二,二而一。象征底微妙,‘依微拟义’这几个字颇能道出。”他指出象征与“兴”的奥妙之处都在于能表现出物与物、人与物内在的共感。一方面,梁宗岱在杜甫、陶渊明的作品以及严羽的《沧浪诗话》中寻找“象征”的佐证,进一步得出结论:“所谓象征,只是情景的配合”,而其两个主要特性为“融洽或无间”、“含蓄或无限”;另一方面,他又援引英国批评家卡莱尔的观点和歌德、莎士比亚等西方大师的经典之作,印证象征主义“藉有形寓无形,有限表无限”的真正品质。这种从西方到东方再由东方到西方的双向论述使“象征”和“兴”不仅作为两个相似性的概念被探讨,而且在其相似性上中西诗学呈现出一种互动的局面。
另一位对象征主义诗学在中国传播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曹葆华。从1933年至1935年,他翻译了大量关于象征主义诗学理论的著述和文章。这些文章大都首先发表于《北平晨报》,后来结集为《现代评论》。《现代评论》是30年代介绍西方诗学理论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其中涉及“纯诗”与象征的论述,它与穆木天、梁宗岱等人的“纯诗”理论遥相呼应,共同推动了象征主义诗学中国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