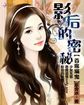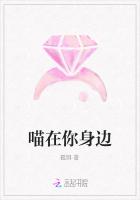诗者,天地之心。
——《诗纬·含神雾》
唯当亲密的东西,即世界与物,完全分离并且保持分离之际,才有亲密性起作用。在两者之“中间”,就是在“区分”中成其本质。这里海德格尔说的“区分”,我们可以理解为“差异性”,只有差异和区分,才能彰显我们在这个世界存在的独特维度。只有差异和区分,才能使世界和物归隐于它们的亲密的纯一性之中。只有远离故乡,才能更深切地体验到故乡的本质。故乡的本质对于一直居于其中的未离乡者来说,反倒是陌生的,却被远离而漂泊异乡的游子所体验,从而让其本质得以呈现。这正如特拉克尔的那句诗歌所吟唱的:
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
同样,对于中国诗歌、诗人和诗学来说,如果没有一种远离和逃逸,华夏族的诗性本质便难以得到显露和揭示。幸运的是,当汉王朝的大一统帝国瓦解后,一种新的悲剧性命运,让华夏族诗人深刻地体验到一种远离故乡之痛。以个人情志的抒发,以天下使命的担当,为中国诗人传统吟唱的核心要素的东西,在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完全被消解了。“诗言志”,“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诗缘情而绮靡”,这样一种传统两极文化结构体制下形成的诗学精神主流,也即皇权文化道德主义尺度与平民文化物欲主义追求所共相认可的东西,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完全失效。
在“忠”、“义”、“诚”、“信”等传统伦理失坠的时代,作为这种传统伦理土地上成长的传统诗学之花也无所皈依。或许,华夏族源初诗学中有一种要素曾经被遮蔽,而终究在远离异乡的游子那里被唤醒。这种诗学精神就是道家诗学精神,就是在五夷乱华和佛教诗学介入中,就是在作为故乡形态存在的儒家主流诗学被冲击的过程中,被那些在乱世中寻找出路的诗人和游子寻获。当然,这种在新时代中经过了冲击和变异的诗学已不再是本原的道家诗学,而是形成了新的魏晋时代特有的玄言诗学。魏晋玄言诗学是在新兴的魏晋世族文化土壤中酝酿生成的,它既有着对传统诗学精神的通变,也有着对异域佛教诗学精神的融合,并由此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诗学精神气质,从而在诗学史上具有伟大的变革性意义。
魏晋玄言诗与《诗经》、《楚辞》以来的传统诗歌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檀道鸾认为玄言诗盛,而“诗骚之体尽”,似乎说明了“诗骚体”与“玄言诗体”的不相容性。当代不少学者也认为,玄言诗不过是在诗的外壳中放入玄学的内容,玄言诗在本质上是“非诗”的。然而,魏晋时代,玄言诗的确盛极一时,深得诗人喜爱,并曾经将传统以“诗骚体”为主流的抒情诗放逐到了诗国的边缘。仔细考察,我们会发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背后隐藏的是两种诗学精神的变迁。魏晋玄言诗的繁荣,虽然也继承了传统诗学的某些精神气质,但更开辟出独特的玄言诗学新向度。
一、传统诗学的双层结构
中国传统诗学是集“情感—表现”的本位精神与“道德—讽谏”的功能主义于一体的双层结构。“发乎情,止乎礼义”说,“兴观群怨”说,是这种诗学的双层结构的典型表达。下面就对中国传统诗学双层结构略作论述。
“情感—表现”诗学是颇能体现中国艺术神韵的原创性诗学,是抒情诗长期繁荣背景下民族精神的集体无意识积淀。从源头上说,它具有一种自发性特征。中国诗学萌芽于何时,现在已难确考。根据《尚书·舜典》的记载,似乎起于极其久远的尧舜时代:
帝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帝,指舜。夔,相传是尧舜时掌管音乐的人。舜命令夔以音乐教育子弟们。而这种音乐并非单纯的乐器鸣奏,而是诗、乐、舞的合一。“诗言志”的开山纲领也在这里被提了出来。这段记载当然带有极其强烈的神话传说与历史想象成分。略去神话与想象成分,我们认为这其中有关诗与乐舞一体并具有和合娱悦天地神人的说法应当是可信的。
“诗言志”作为较成熟的诗学观,构建了中国两千年诗学的本位精神。它很可能是抒情诗写作已有漫长的历史并成为民族艺术的普遍样式后才被提出来的。《尚书·舜典》因为其附会年代的久远,故很难指陈其中的“诗”是何种类型的抒情诗。但《论语》“诗可以兴”、《庄子·天下》“诗以道志”、《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中的“诗”,却是较为明确的“诗三百篇”,或后人说的《诗经》了。“诗三百”并非全为纯粹的抒情诗,但情感志意的表现却是其主要旨归所在。
《尚书·舜典》除了从发生学的角度,说明中国抒情诗学具有“情感—表现”的本位精神外,又从社会学角度,说明中国抒情诗学还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主义。这是中国传统诗学双层结构的最初胚胎。当然,以“道德—教化”为目的的功能主义诗学观不太可能在尧舜时代已经成熟,而极可能是西周礼乐文化变革背景下的思想艺术结晶。“教胄子”,指明诗乐的功用是教化贵族子弟。“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是诗乐教化所希望培育成的“中和”、“中庸”的“仁人”或“君子”品格。这无疑打上了西周礼乐文化甚至是春秋儒家文化的烙印。
《尚书·舜典》所代表的诗学双层结构在后世成为中国传统诗学的主流,并出现了分化,即关于究竟是“情感本位”还是“道德本位”的争执。屈原“发愤以抒情”、司马迁“发愤著书”、陆机“诗缘情”、钟嵘“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可视为情感本位的诗学观。孔子“有德者必有言”、《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可视为道德本位的诗学观。《毛诗序》、《文心雕龙》则是仍旧保持了“情感”为体、“道德”为用的传统诗学的双层结构。这种传统诗学的双层结构如一条醒目的红线贯穿着中国两千年的诗学史。
从词源学上看,“诗言志”的“志”最初就内蕴着“情”,孔颖达云“情、志一也”,杨树达《释诗》中说“志之从心”。显然,情、志本无太大区别,但随着道德理性主义对自然情感主义精神的提升,“志”逐渐有了道德伦理化的倾向。“诗言志”的“志”逐渐渡入更多的政治、道德内容,并成为“心情、心意、道德、政治志向”的综合体,蕴涵着被后人各取所需的多重含义。同时又因其缺乏“个体之志”的规定,就必然被包括孔子在内的后人作“兴于诗,立于礼”的群体化解释,最终演变为“文以载道”及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类型化、公式化。孔子将《诗经》作了“思无邪”的儒家之“志”的阐发,所以真正的“个体之志”是不被“诗言志”的阐发者所认同的,而可能仅仅在少数不理睬“诗言志”的作家创作实践中存在。可以说,传统诗学“情感—表现”的本位精神与“道德—讽谏”的功能主义是合二为一的。前者是体,后者是用,即体即用,体不离用,用不离体。
这种稳态的诗学结构绵延数千年,对华夏民族的文化精神与艺术精神既有着基础的建构作用,但又从根本上固化了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理与艺术模式,阻碍了本土诗学对他种诗学精神的借鉴。
二、玄言诗寓含的诗学新向度
魏晋玄言诗繁荣,从而导致“诗骚之体”衰落,是因为它寓含着“玄道—感悟”的诗学新向度。玄言诗常常被古今学者视为“非诗”,亦是因为这种重“玄道—感悟”的诗学精神与传统诗学重“情感—表现”与“道德—讽谏”的双层结构相违逆。魏晋玄言诗人挑战了传统诗学的双层结构,将老庄本真的诗学精神向具有某种艺术形式的诗歌世界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转渡。我们下面的重点便在于发掘这种诗学精神为何及其在玄言诗中有何表现。
诗是民族的心灵之歌。诗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传统诗学的双层结构表征着华夏民族丰富的情感世界与道德理想,映射着宗法血缘的小农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世俗化、情感化、伦理化、群体化,是这种生存状态的丰富意蕴。但因为这种生存状态日益被文明的尺度所计算,从而失落了它本质的“诗意”。“诗意”正是诗人所要寻获的。人的现实栖居所以能够是非诗意的,只是由于栖居本质上是诗意的。诗意来源于神圣真理的澄明与启蔽。庄子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现存文明社会中的人因为自我中心主义与功名利禄追求而遮蔽了“道”或“真理”的神圣之光。至人、神人、圣人,就是发掘生命诗意栖居本质的真正诗人。体道返真,在大地的栖居中寻获诗意的神圣尺度,就是老子与庄子揭蔽儒家道德化世界掩盖下的生命诗性,启迪着魏晋玄言诗人的真理之路。
魏晋时代,儒家的道德化世界已然动摇,然而被经学威权主义与皇权专制主义层层遮蔽了近四百年的民族生命仍旧是在黑夜中摸索。被奴役的民族并不曾意识到自己本有的诗意神圣之光。老子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老子》三十八章)礼义是文明的产物,是人远离道德源泉的生命蜕化。魏晋世族与皇权分庭抗礼中,礼制秩序已完全沦为权力的伪饰与护身符,而失去了其标示正义的本质。在黑夜无保护性的深渊中,作为黑夜的冒险者,魏晋玄言诗人在走向神圣之踪迹的途中体悟着玄虚妙道的神圣向度。
作为黑夜中追寻神圣踪迹的诗人,何晏无疑是其中的先行者:
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
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
鸿鹄,是追寻此在生命根基的诗意化身,《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是其先声,鹏飞九天,仍有所待,故难得自由,但自此而后,有关飞翔的鸿、雁等形象,遂成为追求生命自由的化身。诗人秉承庄子追求生命不受束缚的本真自由精神及逃脱世俗的此在诗意根基,敏锐地觉察现实的功利之网对生命自由诗性的戕害,在极尽逍遥的本真之游中,不禁发出内心深处的惊惧与惶恐。但遍布这个贫困时代的是道路的艰险,陆机《君子行》诗云:
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难。休咎相乘蹑,翻覆若波澜。
去疾苦不远,疑似实生患。近火固宜热,履冰岂恶寒。
掇蜂灭天道,拾尘惑孔颜。逐臣尚何有,弃友焉足叹。
诗人追寻着平坦简易而神圣的天道,却不得不在艰险而困难的世俗人生道路上颠沛流离。祸患接踵而至,人生翻覆若大海的波澜。不能远离祸患,又难免被人猜疑。诗人临深履薄,战战兢兢。源于生命根基处的大道与诗性被遮蔽,通往神圣的道路也掩蔽在重重迷雾中。人成为被抛弃在异乡的孤客,只有诗人在人的异乡状态中奋力前行,不惮于道路的艰险与黑夜的贫困。
天损未易辞,人益犹可欢。……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人被抛入黑夜的贫困,是此在历史难以抗拒的命运,“天损”即谓此在的历史命运,“未易辞”则意指诗人并不为终有一死者被抛入异乡的沉沦状态而怨天尤人。诗人的使命只是在尽其最大的天职,“人益犹可欢”,在领受天命而又不屈的前行中,感受到作为先行者的喜悦。天职攸归,乃是诗人“自信”的基础,在自信中,诗人走向拯救人之未来命运的历史之路。
魏晋诗人正是在对时代贫困的追问中,“思入那由存在之澄明所决定的处所”。顾秘《答陆机诗》:
恢恢太素,万物初基。在昔哲人,观众济时。
“太素”、“初基”,清楚地标明超越现实,穿透历史,思入那存在敞开自身之处。老子云:“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四章)又云:“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老子》五十二章)太素,也就是“象帝之先”、“天下之母”的大道或存在开端之处,万物在此建基,也由此绽开,历史由此开始,世界由此形成。但万物开端处的最根本建基者,乃是终有一死者,是能觉悟自身存在的此在。存在开启自身又遮蔽自身的历史中,常人已失去其觉悟性,而唯有“哲人”能思入那存在澄明之所,在世界贫困时代的纷纷扰扰中,彻悟存在的秘密。
这里诗人似乎是在召唤大道,但实际乃是响应道的应答。在召唤与响应中,“存在者”得以命名,并被唤入“存在”的圆寰之域的光照中,从而得到保护。这些被命名并得到保护的物,也即被召唤的物,把天、地、人、神四方聚集于自身。这四方是相互让渡、相互映射的原始统一。物让四方的四重整体栖留于自身。这种聚集着的让栖留乃是物之物化。在物之物化中栖留的天、地、人、神的统一的四重整体,我们便称之为世界。物化之际,物展开世界;物在世界中逗留,因而一向是逗留着的物。物由于物化而实现世界。物化之际,物才是物。物化之际,物才实现世界。物物化,世界世界化,诗人透过黑夜的浓重夜色,直接被唤入存在的澄明光照中:
利交甘绝,仰违玄指。君子淡亲,湛若澄水。
余与吾生,相忘隐机。泰不期显,在悴通否。
功利与道德绘成的世界图像已然远离诗人的本真世界,在淡然若澄水的心之明澈中,诗人与诗人的对话,达到了“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的忘我、忘你、忘他的境界,祸福荣辱、忧患得失再难以搅动诗人平静而回归存在的原始道心。
三、玄言诗对传统诗学的挑战
在对传统诗学精神的反叛及对老、庄诗学精神的传承中,玄言诗实现了中国古典诗学精神的一次转渡,并促成了其新的发展方向。玄言诗既以玄道冲济淡化着传统诗学情感自然与道德讽谏的向度,而这种转变又是围绕着语言来实现的。在传统诗学的双层结构影响下,语言被视为工具与手段。“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辞达而已矣”,是其经典表述。这样,文采与修辞便成为传统诗学的重要内容。在玄言诗开辟的诗学新向度下,语言与道具有某种同一性。道是至虚冲淡的,不可言说,语言的华丽或修辞的讲究与否,便不再重要。平淡寡味的语言反而被认为是最接近道的。在玄言诗人那里,语言是最危险的,有遮蔽道的可能。但语言又是道路,开启着道的神圣意蕴。
真正的玄言诗人就是语言的冒险者,在语言的历险中切入存在,故玄言诗人实际又是存在的冒险者。普通的诗人只会感觉到语言作为传递信息、抒发情感的工具性困难,而较少体验到语言超越工具性的源发、原始意义及语言保证人而非人、保证语言的语言之本质。因为语言开始处,才建构着人的世界,这和诗是人的建基性相同,所以语言的本质就是诗。诗之语言引向存在,而非诗的语言却威胁着遮蔽着存在。诗人愈依靠语言,语言便愈益进入非诗的器化中;诗人完全舍弃语言,存在的本真之路又难以得到指引。因而,诗人不是现实生活的冒险者,却是语言与存在的冒险者。
玄言诗人与老子、庄子的相通处就在于他们体验到诗人冒语言之险、冒存在之险的天命与本质。语言,在魏晋以前传统的“诗”中还未成为问题。尽管在更广阔的“思”的领域,语言已深深地触动着哲人们的心弦。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隐无名”,“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是认为,普通的形名言语言不足以指称言说“恒道”。日常语言遮蔽着道,在无名无言处,道自动涵藏彰显。庄子亦云:“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至言去言,至为去为”,“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庄子继续对“恒道”与“语言”的关系问题作了进一步发挥,指出本真语言与恒道同在,但现实的日常语言却遮蔽道的非本真异化特性。“道不可言”,“道不当名”,直接针对人们司空见惯的语言提出了最尖锐的问题。《周易·系辞》对此作了调和: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这既是对老子、庄子有关语言问题的回答,同时也是对《庄子·天道》中关于“书—语(言)—意”问题的解决。《易传》作者认为,书虽难以尽言,言虽难以尽意,但圣人可以通过立象以尽意,这就是在“言”与“意”之间介入了“象”。然而,虽然在思想的领域,“语言”的相关讨论已触及了存在(大道)的高度,但因为这时的诗歌多从自然的情感抒发及道德伦理的责任言说方面出发,相关诗学问题也就仅仅触及情感化、道德化的“情志”问题,而难以深思语言的存在本质。这其中只有少数篇章或个别诗人触摸到了存在的踪迹:
道可受兮,不可传;
其小无内兮,其大无垠;
毋滑而魂兮,彼将自然;
一气孔神兮,于中夜存;
虚以待之兮,无为之先;
庶类以成兮,此德之门。
这是《楚辞·远游》中的一个片断,这里作者是否为屈原并不重要。需要注意的是,语言在这首诗中已成为问题。诗人敏锐地觉察,道只能在诗人先行的现身本质中赢获,而不可以在语言的工具性言说中传达。这既可能是受到老、庄思想影响的结果,也可能是诗人自行悟得了语言的本质。但无论如何,这个有关语言之思的传统未能在传统诗人及诗学的世界得到广泛响应。在诗文中,人们熟练地运用语言,间或遇到表达的困难,却从未意识到语言还隐藏着更深刻的危机。
只有到了魏晋之际,诗歌中的语言问题才真正摆置到诗人们面前。这一方面虽缘于魏晋玄学中有关“语言”的探讨,但另一方面,却不能不归功于诗人们的“语言自觉”。玄言诗人或玄学名士敏锐地察觉到,诗歌中的语言问题并不仅仅是修辞表达的细枝末节问题,而是缘于更深层的语言之危险。汤用彤将魏晋的“言意之辨”视为“治学之眼光之方法”,这某种程度上已忽视了造成“语言”在魏晋成为重大的“思”与“诗”之问题的更深层原因。如果仅仅把“忘言忘象”、“寄言出意”、“微言出意”、“假言”视为魏晋玄学的方法论,那么我们便难以看到魏晋哲人与诗人缘于存在高度的“语言自觉”,从而忽视中国诗学中一直存在而在魏晋时期凸显的语言哲学。
海德格尔指出,语言是存在之圣殿(templum),是存在之家(Haus des Seins),“从存在之圣殿方面来思考,我们能够猜断,那些有时冒险更甚于存在者之存在的冒险者所冒何险。他们冒存在之区域的险。他们冒语言之险”。魏晋玄言诗人从“道”的存在之圣殿走来,他们更甚于日常生活中常人所冒之险,而直接冒存在之险,冒语言之险。我们这里先看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其一: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这首诗的重要性倒不在于它如何高妙地表现了与亲人的依依惜别之情。相反,这种惜别之情在诗中几乎是看不见的。这首诗的重要性在于它探入了秦汉诗人们未曾触及的一个维度——“寂静之音”。秦汉诗人常常将他们现实生活的欢欣与痛苦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以此感动读者。但在这里,诗人却将这种日常的喜乐轻轻收藏,他的视线从身边拉向苍穹,站在大地上的诗人看见了天空中的“归鸿”,鸿是大地和天空的居间者,它在飞向故巢。这似乎是在召唤,召唤着诗人。诗人轻轻地弹奏起他心爱的五弦琴,美妙的琴声悠悠,将诗人从大地唤向苍穹的近旁,苍穹乃是神的居所,诗人是否在想象着羽化的仙人?诗人是否已幻化为一只归鸿,亦在飞回自己的故巢?我们只能怀疑,而难以猜断。我们只能跟踪诗人“思”的足迹: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诗人的确是在想念自己的故巢,但这故巢并不是诗人现实中的山阳故居,温暖的人世居所。当然,现实的家或许也让诗人思念,但此时的诗人却是在追寻更本质的家。“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这两句诗将诗人的心曲暴露无遗。俯者,屈身向下,叩击大地;仰者,抬头向上,追问苍天;自得,得其本己本真的乐趣。诗人何以能在天地间安然而居,并自得其乐?因为诗人觉悟到其当下的安居乃是源于更本质的居所,是赋予人安居的本质的居,是令天、地、神、人聚合为一的原始存在,诗人的心灵已为这本质的居所而牵缠,为这原始的存在而颤动。这一先于天、地、神、人的原始的在与本质的居就是“太玄”,太玄只是一强名、假名,而非恒名,因为它就如同老子、庄子说的“道”那样,不可为名。它乃是“寂静之音”。老子云:“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不可听的寂静之音,只能归本于静默。诗人是语言的冒险者,诗人在语言之说中开启着存在,令本质的居“太玄”到来。但当诗人发觉本质的居无可言说,而更多的说,只能冒僭越的危险,令本质之居被遮蔽在更漆黑的深渊时,诗人不禁遥想起庄子的箴言:“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作为器具的鱼筌,其目的在于抓鱼;作为道路的语言,其终极在于指引存在之光。
当诗人在语言中历险时,突然发现最深的危险来自语言,语言开启存在,又遮蔽存在。本质的居在语言的喧哗中,有远离人的危险。诗人不得不深入语言更深的本质: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寂静之音”是更深层的语言之本质,是语言对自身的留白。人能说,首先是因为人能听。人在听语言寂静之音的召唤。在听中,诗人归本于静默。静默乃是寂静之音的本质。“作为寂静之静默(das Stillen der Stille),宁静(die Ruhe)总是比一切运动更动荡,比任何活动更活跃。”因而,“寂静之音”并非空无所有,它是最丰富的丰富者,是诗的本源,是现实语言的根据,是一切存在者的源发地,是诗人安居的本质居所,是天、地、神、人的圆舞之场。《庄子·知北游》的一则寓言最能体现这最深层、最丰富的“无”,即“寂静之音”:
光曜问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
光曜不得问而孰视其状貌:窅然空然。终日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搏之而不得也。
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为无有矣,何从至此哉!”
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假名:“光曜”与“无有”。“光曜”是天地万物无遮蔽的敞显,就像太阳普照,没有任何阴影,这实际是作为终有一死的人对自身知识、理性的盲目自信,认为只要凭借自身的能力“视”、“听”、“触”、“知”,便可以洞察世界的一切奥秘。“无有”,暗喻超越存在者的非存在,或曰本质的存在,它根本不是人的理性、知识所能认识的,是人的能力不能到达的世界。故而当“光曜”面对着“无有”时,不免显得手足无措。它以其囿于存在者的习惯思维方式追问:是“有”抑或是“无”?但这最深的本质存在却不可通过智识者的探问而寻获。“光曜”不得不放弃这日常的问,而转向更深层的“视”、“听”、“感”。但“无有”却又不可视而见,不可听而闻,不可触而得,似无而有,似有而无。光曜在这超越存在者的本质存在中,终于放弃了一切现成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损之又损的减法式陌生化的思中,人却触摸到了存在的边缘,而以非现成化的澄明心境靠近了大道的敞开之域。最后,光曜在感叹中,揭蔽了人作为现成者的局限,以及人虽不能入于存在却愿依存在之源而居的向往。
如海德格尔所言,诗人是半人半神,是由存在者嵌入存在的媒人,诗人召唤存在者—物,入于存在—世界之栖留中,又召唤存在—世界,居于存在者—物之敞开中。这种世界和物的聚集、存在和存在者的分离就是裂隙,是痛苦,诗人为此而冒险,而痛苦,却不惮前驱。诗人听从作为存在与存在者区分的裂隙之召唤,这种召唤就是语言作为寂静之音而说。“语言即寂静之音乃由于区分之自行居有而存在。语言乃作为世界和物的自行居有着的区分而成其本质。”“人之说是命名着的召唤,亦即那种从区分之纯一性而来令物和世界到来。人之说的纯粹被令者乃是诗歌之所说。本真的诗从来不只是日常语言的一个高级样式(即melos)。毋宁说,日常言谈倒是一种被遗忘了的、因而被用滥了的诗歌,从那里几乎不再发出某种召唤。”语言之说是更本质的说,人之说只是响应语言之说。诗是人之说响应语言之说的纯粹的令说。魏晋玄言诗的诗学精神就在于它力求超越现实的人之说,尽量避免将诗歌视为日常语言的高级样式,而使其成为语言之说,实现“道说”(sage)。这样,传统诗学的“情志本体论”及“艺术本体论”在玄言诗中都不再重要。因为情志本体论不过是对人作为现实存在者的情感、道德指向或喜怒哀乐的书写,而这都是与玄言诗呼应庄子式的以存在为旨归的诗学精神距离甚远的。“艺术本体论”则不过是将诗歌视为日常语言的一种高级形式,或将诗歌视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而这与玄言诗将诗歌之说视为道说或语言之说的响应,又显然有较大差别。这些都是玄言诗与传统诗学精神相背,而又发展了传统诗学精神的原因所在。
但是,当响应存在成为魏晋整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成为由“个体诗学”向“群体诗学”复归的内在动力时,源初“存在”却有了堕入现成“存在者”的危险。因为存在本身不可说,真正的诗人只能在“人说”响应“语言之说”的留白中最近地居于存在之近旁。这样,存在就有被“人说”僭越的危险。在启蔽“存在”的本源冲动中,玄言诗人以“人说”直接说“存在”:
大道夷敞,蹊径争先。玄黄尘垢,红紫光鲜。嗟我孔父,圣意通玄。非义之荣,忽若尘烟。虽无灵德,愿潜于渊。
即使像阮籍这样伟大的诗人,也难免以人说直接僭越存在,从而更深层地遮蔽存在。当然,诗人这里的人说,还未完全堕入日常智识语言的迷障,他并未对大道进行断然的界定,而只是描述大道与人道的差异性所在。诗人说,大道是广阔平坦的,可以容纳芸芸众生乃至世间的一切存在者前行,但存在者特别是人却遗忘了大道的存在,而任其被自行遮蔽;人道是狭窄危险的,但人们却都争先恐后地往这条危险的道路上奔竞。在人道的路上,功名利禄的现成需要已遮蔽了大道的光芒。只有真正的圣人才能超越现实存在者的物质之需,深深地潜入大道的灵渊。诗人在思索存在,但又急切地以人之说的方式,更深地遮蔽了存在。
魏晋时代的开始,道在向诗人敞显自身的同时,又不断地被深层地遮蔽了。因为在崛起的自由诗人群体面前,在挣脱皇权奴役的世族名士心中,情感、道德的世俗之物既然应当被抛弃,那么大道显然就只能是唯一的被言说之物。先行于这个时代的伟大诗人尚能避免道的世俗化与器化之危险,但在随之而来的“道”成为中心话语之后,“道”便随时在日常之说中被谈论,被摆置,被歌吟。“道”遂成为一对象化之物,成为知识、理性、认识讨论的对象。佛家的寺庙是优越的“道”场,世族的园林是无可置疑的论“道”之地,山川名胜更成为悟“道”之所。清言问“道”,诗歌吟“道”,道一步步被泛化,似乎成为人人皆知的东西。人们都以为道是“无名”的、“素朴”的、“本质”的、“整全”的,如云:
道贵无名,德尚寡欲。俗牧其华,我执其朴。人取其荣,余守其辱。
森森群像,妙归玄同。原始无滞,孰云质通。悟之斯朗,执焉则封。
这似乎是深悟道的真谛,“无名”、“寡欲”、“朴”、“守辱”、“玄同”、“原始”,都是道的禀性或得道圣人的品格。但在无名、朴、玄同、原始的表象下,道更丰富、更本质的东西却被遮蔽了,得道圣人寡欲守辱操行下的更宏大精神内涵被遗忘了。诗成为干瘪的说教,毫无存在呼唤的深沉宏大之音。大道作为寂静之音而呼唤的力量已悄然远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