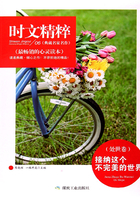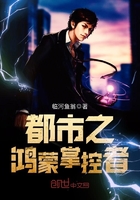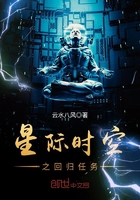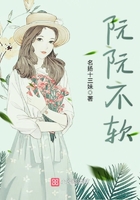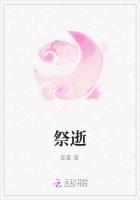闽派诗人众多,然开宗立派则非陈衍、郑孝胥二人莫属,由于陈衍的诗论和郑孝胥的诗歌成就影响甚大,同光体的后学往往以其为师法对象。陈、郑二人可谓各有所长,陈衍以说诗见长,郑孝胥则以创作胜出。从《石遗室诗话》中论及郑孝胥之处看,二人的诗学观点基本一致。当然各人在具体的宋诗观不可能尽同,下面以郑孝胥、陈宝琛、沈瑜庆三人作为闽派主要代表讨论其宋诗观。另外,林旭二十四岁因变法殉国,其诗学观与其他闽派成员不同,所作诗风格生涩峭健,不同于闽派大多数成员“唐神宋貌”之特征,录之于后。
一、郑孝胥
郑孝胥(1860-1938),字苏堪,号太夷,福建闽县人。光绪八年(1882)举人。后入李鸿章幕府。光绪十五年(1889)考取内阁中书。改官同知,分发江南。官至湖南布政使,入民国后以遗老居上海。九一八事变后,从溥仪任伪满洲国总理,声誉大减。郑孝胥工诗善书。著有《海藏楼诗集》。
郑孝胥在清末民初诗坛影响甚大,被誉之为诗坛“射雕手”。当时后辈学诗者往往直接以郑孝胥为模仿对象,陈衍说“后来之秀,效海藏者,直效海藏,未必效海藏所自出也”。又说:“近来诗派,海藏以伉爽,散原以奥衍,学诗者不此则彼矣。”钱仲联先生亦说:“近代为海藏一派诗者最多,号称闽派”。郑孝胥不是以诗歌理论而是以实际创作带动宗宋的诗学风尚。
郑孝胥一生诗风多变,《石遗室诗话》中说他“三十以前,专攻五古,规模大谢,浸淫柳州,又洗炼于东野……三十以后乃肆力于七言,自谓为吴融、韩偓、唐彦谦、梅圣俞、王荆公,而多与荆公相近”,因此,其宋诗观从汉魏古诗入手发展而来,取唐韦应物、柳宗元之体格兴趣,于宋人独钟情王安石。在郑孝胥的诗学观念中,唐诗性情是根本,宋诗的体貌中亦要暗含唐诗韵味,方为得法。
光绪八年(1882)乡试中举是郑孝胥诗学观念转变的一个分水岭。早期郑孝胥对宋诗颇为不齿,他毫不隐讳地表示了宋诗无可取之处。光绪壬午年(1882)他与叔祖郑世恭论诗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叔祖忽曰:“昨闲中拟喻有唐诸大家诗。谓少陵如日;太白如月;摩诘如云,随地涌出;孟浩然如雪;高、岑如风;孟郊如霜,着人严冷,其气肃杀;昌黎如雷;长吉如电;飞卿诗远胜义山,在天虹也;卢仝、刘叉等雹也;自初唐至盛唐,如四杰诸公,五行二十八宿也。”余曰:“未也。韦苏州之雅淡,在天为露;柳子厚之冲远,在天为银河;元、白雾也,能令世界迷漫。自宋以下,则不足拟以天象矣。”相与捧腹大笑。
四时之天象乃万古长存之物,其具体呈现方式虽有不同,但姿态万千,各具其美。在此时的郑孝胥眼中,唐诗的典范意义要远远超越于宋诗之上,只有唐代的大诗人可与自然天象比拟,宋代诗人不可与之同日而语。至于宋代江西派领袖黄庭坚,郑孝胥对其尚能作较客观的评价:
余复谓:“黄涪翁诗,功深才富,亦是绝精之作,特门面小耳。此譬如富翁十万家私,只做三五万生意,自然气力有余,此正是山谷乖处。”
虽然对黄庭坚不乏赞语,“功深才富,亦是绝精之作”,但是“特门面小耳”则将江西派的风格予以了否定。郑孝胥认为江西诗派虽强调博学多识,内里丰厚,但出手却是沉迷于技法、字面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而没有汉魏、盛唐诗之宏大气象。
光绪八年(1882)乡试中举之初,郑孝胥诗学尚以尊崇汉魏古诗为主。他评近人所作古诗道:
近代罕解古诗者。五古尚有佳者,长短句直无其人。往时窃谓长短句高于五古,五古至汉始有,古所传者俱是长短句。……下至晚唐、宋、元、明诸老所作,则直是近体气力音节,只袭其貌尔。
在批评近人那种“貌古实律”的诗歌同时,也表达了他重古诗轻律诗的诗学观。乡试后他曾问同年林纾“为诗祈向所在”,当林纾答以《钱注杜诗》和《施注苏诗》时,郑孝胥毫不客气地反问道:“何不取法乎上?”可见,此时他的诗学观念还只有汉魏古诗,唐以后的近体在他心目中还没有什么地位。
陈衍论郑孝胥的诗学历程曾说:“苏戡诗少学大谢,浸淫柳州,益以东野,泛滥于唐彦谦、吴融以及南北宋诸大家,而最喜荆公”。陈衍所述郑孝胥之变化,当是郑孝胥与其交流时的“夫子自道”,此后提及郑孝胥诗,诸家所论于此往往大同小异。如李肖聃《星庐笔记》称郑孝胥:“有海藏楼诗数卷,自谓取境吴融、韩偓、唐彦谦、梅尧臣,而最喜王安石。”邵镜人《同光风云录》:“太夷幼工五古,规抚灵运,三十以后,稍肆力七言,而服膺荆公”。《郑孝胥日记》中亦不时可见“阅荆公诗,甚可爱”;“阅临川诗,极可喜”;“阅唐文粹,王荆公诗”;“钞王介甫诗毕”。郑孝胥日记论及其他宋人之诗,多是不带感情色彩的阅书或抄录,偶尔也有“甚佳”“极妙”之评,但往往一带而过,唯独对王安石反复提及,且始终赞不绝口,绝无微词,以至于“阅宛陵诗,古淡精简,旷世少匹”,也会联想到风格相似的王安石,于是“复取王介甫诗看之”。
郑孝胥对王安石的推重颇引人注目。一则自宋诗形成自身特色以来,后世学宋者大多以苏轼、黄庭坚及江西诗派为宗,对王安石如此仰慕者似较少见;二则郑孝胥晚年失节,与王安石“洁白之操,寒于冰霜”的人品大相径庭。但事实又确如叶参所称道:“(郑孝胥)对王安石尤持满腔感服与敬意,是以终生奉之不懈,故其作品在可能范围内,要由形神两肖方面而使之幽峭奇响”。
王安石的诗歌以熙宁十年(1078)罢相退居江宁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意气风发,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有强烈的参政意识。以韩孟诗派为尚,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承欧阳修、梅尧臣以来的朴质直露,不重词采修饰。强调为诗文“务为有补于世”,反对浮华巧饰。后期则在广泛学习唐人诗歌的基础上,逐渐改变早期质朴直露的风格,讲究新奇工巧,诗风含蓄不露,深婉不迫。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评王安石:“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事实上,恰恰是“与唐人尚隔一关”成为王安石诗歌的最大特色。王安石诗在宋代有“荆公体”之称,莫砺锋先生指出“荆公体”的特色是:“既体现了宋诗风貌的部分特征,又体现了向唐诗复归的倾向。王安石在建立宋诗独特风貌的过程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最能代表宋诗特色的诗人却不是他而是苏黄。”由此可见,郑孝胥所好之宋诗并非纯粹的、完全成熟的宋诗,而是唐宋兼具甚至偏重唐音的诗歌风格。
1889年,郑孝胥二十九岁时,日记中始有将《宋诗钞》置于案头研读的记载。在诵读的过程中,日记中的读后感却比比皆是对《宋诗钞》观念的继承,如:
吴之振孟举与吕晚村、吴自牧同选宋诗,孟举序之,略约:嘉隆以还,尊唐黜宋,实未见宋诗,并不知唐诗也。宋之去唐近,用力于唐尤精,今逐父而祢其祖,亦唐之所吐而不飨矣。曹学佺谓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不事剿袭前人。然万历间李蓘选宋诗,取其远于宋而近于唐者;曹学佺亦云,选自莱公,以其近唐调。以此义选宋诗,唐终不可近而宋诗已亡矣。兹选尽宋人之长,使各极其致,故门户甚博,不以一说蔽古人云。
《诗钞》称:乖厓诗,雄健古淡,有气骨。有《游蜀中赵氏西园》诗曰:“翻空雅乐催欢处,入格新诗上板初。方信承平无一事,淮阳闲杀老尚书。”亦不乏风趣也。
诸如此类连篇累牍大段摘抄自《宋诗钞》的文字随处可见,可见其重宋诗之“唐神宋貌”不仅有闽地诗风的原因,还有《宋诗钞》的影响。然而,在新的时代环境下,郑孝胥的宋诗观渐渐发生了变化,逐渐有了自己的见解。
(一)重诗之性情与以“意”相贯的气势。
唐诗尚情,宋诗尚意。郑孝胥《书韦诗后》阐述了模仿与性情之间,他说:
性情之不似,虽貌合,神犹离也。夫性情受之于天,胡可强为似者。苟能自得其性情,则吾貌吾神,未尝不可以不似,则为己之学也。
说明了不能得其性情,勉强为之,只能是貌合神离;如果性情合,即便是不似也有似处。同时他也能渐能接受苏黄诗歌一气直贯的气势。“苏黄有如大江,浩漫天壤,所经处皆成名胜,而人隐其利,亦可据以设险。韩昌黎若黄河,然天地内自有此一股劲派,非他力量所及。”认为苏黄诗内涵丰富,内有后世取之不尽的资源,即“所经处皆成名胜,而人隐其利”,而韩愈诗歌的雄奇奔放,有如大河自上而下,饱含阳刚之劲美。
(二)肯定宋诗之法,重学问但要深入浅出。
1893年12月24日的《日记》载:
李东阳曰: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其高者失之捕风捉影,而卑者坐于黏皮带骨,至于江西诗派极矣。
李东阳简单地将宋诗之法归为“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予以否定。郑孝胥认为李东阳批判宋诗,否定宋人诗法正好证明了明代诗歌成就不高的原因:“明人心眼中多有此种见地,故令一代梦魇”。所以他指导人学诗途径时说:
君诚喜此,非用力数年不可。今宜取唐人诗二家,宋人诗三两家,国朝人一家,置案头常看之,久又易之;俟极斐然欲作时,便试下笔,务求瘦劲,避去俗氛为主;仍随时收罗诗料,如是久之,渐有把握,自成艺业矣。
“唐人诗二家,宋人诗三两家”,可见其胸中已无唐宋芥蒂,“瘦劲”“去俗氛”“收罗诗料”都可略见江西家法。而对学问不足的诗歌,他则明确表示这的确是一种缺陷:
览戴石屏诗。杨升庵讥其无百字成诵,石屏亦自憾读书不多,细看诚有此病,其落想下笔处皆欠包孕故也。
因此,他主张为诗者自身不能浅薄,浅人不能为深,而深者则宜出之以浅,反对艰深文字,苦语为诗。“深人何妨作浅语,浅人好深终非深。观人以此得八九,能辨深浅真知音。”“浅语莫非深,天壤在毫末。何须填难字,苦作酸生活。”正因如此,金天羽认为郑孝胥的诗歌是“读破万卷而不为书累,外疏简而中含精实。”
郑孝胥一生诗风多变,反映了其不断求新的诗学追求,甚至对胡适以宋儒“语录之体,推行于诗文”他都认为是“但使措辞妙绝,读者感动,与古何异”。郑孝胥诗歌之所以成为光宣诗坛最有成就的作者之一,与他诗学观念之通达圆融密不可分。
二、陈宝琛
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橘隐,晚号听水老人、沧趣老人。福建闽县人,出生于一个累代簪缨的名门望族。少年颖悟,十三岁为秀才,十八岁中举人,同治七年(1868)二十一岁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擢翰林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历任江西学政、内阁学士、钦差会办南洋大臣等职。入阁后,以直言敢谏而闻名。光绪十年(1884)因上书言事被黜,赋闲居里二十五年。晚年曾担任末代皇帝溥仪的“帝师”。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有《沧趣楼文存》二卷、《沧趣楼诗》十卷存世。
在晚清民初,陈宝琛是一个有着广泛影响的政坛人物。他是晚清“清流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与张之洞、张佩纶、宝廷、邓承修、黄体芳、李端棻、张楷等人或为讲臣,或为台谏,相互砥砺,评论朝政。在陈宝琛身上,我们能看到他承继中兴以来理学名臣的传统,不媚时俗,不畏权贵,敢于直谏,同时也不顽固守旧,注重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改革内政。早年忙于政务,无心为诗。陈三立在《沧趣楼诗集序》中说他:“早岁官禁近,已慷慨以身许国,勇于言事,章疏凡数十上,动关匡拂朝廷、培养元气大计,直声风节倾天下”,因而“未遑狃章句求工于诗也”。在罢官归里的二十五年,“戢影林壑,系心君国,盖抱伟略,郁而不舒,袖手结舌,无可告语。闲放之岁月,遂假吟咏自遣”。所以,在现存的沧趣楼诗中,前五卷为1887至1908年闲居在家时作品,后五卷为1909年召复后至1935年去世时所作,不同阶段的作品有着不同的特色。
至于陈宝琛的诗学宗尚,陈衍认为他“肆力于昌黎、荆公,出入于眉山、双井”。又说:“弢庵意在学韩,实似荆公,于韩专学清隽一路”。林庚白说他“诗以昌黎、荆公、眉山、双井为依归,落笔不苟,而少排奡之气,不甚似荆公,于其他三家,皆有所得”。而黄秋岳却说他自认“得力实在陆务观”。实际上陈宝琛的诗作可能确如诸家所强调的沉浸于韩愈、黄庭坚等众唐宋大家中,各有取舍,但读其诗却深感晚唐李商隐和宋代王安石对其影响更深。
陈宝琛幼承庭训,其父陈承裘常“诲以古今忠孝故事”,“为述祖德、庭训及道咸间所闻士夫贤不肖行事与生平所接名士硕儒之言论风采,勖以名节”,使他很早就树立了以家国天下为重的思想。在学术思想上,他深受明末清初遗民顾炎武、黄宗羲“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认为“若得宗羲、炎武二人,树之风声,动其观感,使天下咸晓然于学问经济自有本源,理非空谈,功无速化,行己有耻为质,读书以有用为程,则功名不贻气节之羞,而风俗可得师儒之益”。
陈宝琛由于少年早达,在同治朝有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中兴气象,中兴精神在他心中引发的感触极深,在他一生的诗歌创作中,“同光”与“中兴”等字眼屡屡出现,如:
吾年似汝登高日,四海兵戈望中兴。
手定中兴四纪周,女中尧舜古无俦。
盲僧能说同光盛,歌者何戡恐亦无。
日辉风畅鸟雀喜,想望中兴验春气。
儒效难为前辈继,朝班曾及中兴辰。……
在中兴的理学名臣身上,诗只是政务学问之余的事情,作诗只是偶尔的娱情遗兴,他们更看重的是有经世之用的实学。受此观念影响,早年为宦期间的陈宝琛极少作诗,退居林下后虽潜心于诗,诗歌创作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他很少去做细致的诗歌鉴赏。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在他眼中显然没有地位。即使在为他人的诗文集作序时,他更关注的是作者的事功,而不是诗歌本身的教化功能。如他在《味雪堂遗集序》开始就说:“访西姻丈于学无所不窥,而志在用世,以绳武自期”。篇幅不小的序言,仅在结尾处提了一句“君赡于文藻而不以鸣于世”。对郑孝胥的诗学成就他也是了了几句:“今海之内外,皆知有海藏楼,即予之夙心,亦岂望君老于诗人?然君诗,年谱也,语录也,亦史料也,可以鼓人才、厚人道、正人纪。盖必如是始可为诗人”。在陈宝琛看来,诗歌具有“鼓人才,厚人道,正人纪”之用,能为此诗之人,才称得上是诗人。这种看上去充满了实用功利色彩的诗学观点,与他一贯的论诗似存在矛盾,事实上这种矛盾来源于儒家的诗教观与他本身诗学观的差异。他不可能在理论上反对儒家的正统的诗学观,但显然不认为诗歌真有那么大的功用,倒是他自己的创作透露了他的诗学选择。
陈宝琛大量作诗始于罢居乡里之时,在与陈衍兄弟交往中,由于客游的陈衍“归则录予诗以去”才以诗名世。汪辟疆说他“及受谴家居,筑沧趣楼、听水二斋,与陈书(木庵)酬唱往来,无间晨夕,而诗日益工。体虽出于临川,实则兼有杜、韩、苏、黄之胜”。陈宝琛回顾自己的学诗经历说:
初学诗于郑仲濂丈,谢丈枚如导之学高、岑,吴丈圭庵引之学杜。而君兄弟则称其类荆公,木庵且欲进之以山谷。
郑仲濂为郑孝胥之父,《石遗室诗话》载其《夕阳》绝句一首:“水碧沙明惨淡间,问君西游几时还。乐游原上驱车过,愁绝诗人李义山。”可以看出其中唐诗风味。至于陈宝琛自身无论是学高、岑还是学杜,主要还是在唐诗的圈子里。后来在与陈衍兄弟交往的过程中,陈宝琛渐渐吸取了宋诗的某些技巧、方法和诗学理念,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以文为诗”和“诗史”说的结合。
“以文为诗”和“诗史”是宋人分别从韩愈和杜甫那里继承并发扬光大了的两个诗学概念。“以文为诗”发散为“以文字为诗,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三个方面;而“诗史”说则被赋予了“善陈时事”“寓意褒贬”及“春秋笔法”等史学意识,同时亦有“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的道德评判在里面。“以文为诗”在陈宝琛那里,主要继承的是韩愈对文章的要求。韩诗虽然也有轻快明亮之作,但总体上还是以险怪著称,而韩愈对文章的要求却是语言流畅、简洁,要求“文从字顺”。陈宝琛将“诗史”融合于“以文为诗”中,他认为“诗”具有“年谱也,语录也,亦史料也”的功能。唐宋两代相比较而言,唐代明显诗重于文,而宋代及其后,文重于诗,故以文为诗并非对诗的轻视,反而是赋予了诗及诗人更多的责任。陈宝琛对“以文为诗”的认识也有这种道德责任在其中。他在《题伯严诗卷》云:
老于文者必能诗,此道只今亦少衰。生世相怜骚雅近,赋才独得杜韩遗。江湖浩荡身行老,肝肺槎枒俗固疑。牢落年来欢会叹,始知高论未需卑。
这里虽然是论陈三立的诗歌风格,在感慨“此道只今亦少衰”时,也可看出他对“以文为诗”的赞成态度。而随后的“生世相怜骚雅近,赋才独得杜韩遗”则是对“以文为诗”的进一步说明,诗歌要承骚雅精神,刺世讽时,同时有杜韩诗作的铺叙排比,能够用诗来实现文的作用。在《匏庵诗存序》中,他极力称赞作者胜过元好问,“君若录所闻见以为史料,翔实岂遗山所及?”揄扬沈瑜庆亦说“所为诗,出入杜苏,可为光宣间史料,盖必传之作。”不过这样要求诗歌未免有“过犹不及”之嫌,而且他自己的诗作也未见有什么“年谱、语录、史料”。
(二)对王安石创作多有借鉴。
陈宝琛在《谢琴南寄文为寿》中写道:
不才社栎敢论年,刻画无盐正可怜。万事桑榆虚逐日,半生草莽苦忧天。身名于我何曾与,心迹微君孰与传。独愧老来诗不进,嗜痂犹说近临川。
借答谢林纾之机,表达了对王安石诗歌成就的向往之情。林纾在《沧趣先生六十寿序》中也指出了陈宝琛诗近王安石的特点:“所为诗,体近临川,而清靖沈远,挹之无穷,临川未能过也。”陈衍指出陈宝琛与郑孝胥作诗习惯的差别:“苏堪为诗,一成则不改。在天津时与余书所谓‘骨头有生所具,任其支离突兀也’。陈弢庵宝琛则必改而后成,过后遂不能改,谓结构心思已打断矣”。陈、郑均学王安石,郑孝胥效王安石诗意,以气贯之,并不学王安石晚年对诗歌精雕细琢的精深功夫,所以诗作气势凌厉,风骨挺拔。陈宝琛则取王安石精工雅健、深婉不迫的风格,融以晚唐李商隐、韩偓的缜密、工丽,虽有宋诗之笔法,但神理间却尽是唐意,甚至能达到让人误为唐诗的程度。《今传是楼诗话》载:
(静安)殁之前为人书扇,中有“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之句,死志之决,即此可知。都下报纸多以为录李义山作,人以诗工,亦不暇考,实则乃摘录陈弢庵先生诗也。
王揖唐对此感慨曰:“即以诗论,何减西昆”。
(三)“诗教”转向与宋诗“自持与自适”心理功能的结合。
陈宝琛《疑庵诗序》中较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诗学观:
圣人以“思无邪”称诗,旨盖深矣。凡人之心有所偏倚,求其好恶之不失常,不可得也。好恶失常而又冒为贞人正士之言,欲其无为伪焉,亦不可得。孟子著诐词以下之失,至谓之生心害政,则所关非鲜小矣。思至无邪,斯哀乐之情通于性命。好贤求诸寤寐,恶恶欲畀之豺虎,悉发于天倪而不能自己,又何门庭派别之分哉……然且娑娑光景,体状物理,云态风绪,花坼树萌,莫不有独喻之微、弗宣之趣。弗宣人同,而人亦罕同之。其心孤,故其气静,好恶受之以正,而天地民物之变数相与感发于无穷。由是心而推之,将可寄之以道,岂但言诗而已!夫以末艺视诗,与欲因之以为名,皆中不足而张于外者。然则劳逸休拙,为作德作伪之征,在于诗亦有然矣。
理学思想始终对陈宝琛有着直接的影响,“内省”的方法使他将诗歌的“思无邪”作为心灵净化的寄托之具,因为只有“思至无邪”,方能“哀乐之情通于性命”。作为个人的修养,则要能在“娑娑光景,体状物理,云态风绪,花坼树萌”中体会到“独喻之微、弗宣之趣”,并且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由诗心与“天地民物之变数相与感发于无穷”而得到“诗道合一”的合理结论。此序作于1925年,陈宝琛已七十八岁,自身的诗学观已定型,他以一种超然达观的态度对待诗,认识到功利化地将诗歌视为“末艺”或者“因之以为名”都是违反“思无邪”诗学宗旨,虽用诗教术语,但实质已有所转,更偏重于诗歌“自持、自适”功能。
陈宝琛诗歌创作态度严谨,“必改而后成”,钱仲联先生以为其诗歌成就当于陈衍、郑孝胥等列,而由于其在诗歌理论较少创见,故不在同光体派的领袖之列。但无论怎样,其取径宋诗,推源唐诗,熔铸古今,终自成一家面目,对宋诗学的贡献的确是实践意义大于理论意义。
三、沈瑜庆
沈瑜庆(1858-1919),字志雨,号爱苍,别号涛园。福建侯官人,沈葆桢第四子,林则徐之外孙。光绪十一年(1885)中举,次年会试不第,以父荫赏主事,寻改官道员,先后委办、总办江南水师学堂、宜昌盐釐局等。曾入张之洞幕,主文案兼筹防局营务处。光绪二十七年(1901)补淮海道,授顺天府尹,出为山西布政使,移广东,旋调江南。因事罢归,后复起为贵州布政使,升贵州巡抚。民国后卒于上海。
沈瑜庆十一岁时,母亲林氏“口授《资治通鉴》”。沈瑜庆读书好《左传》等史书,喜诵庾信、杜甫、苏轼的诗、词、赋,常翻阅曾国藩、胡林翼等的奏议、书牍,谙熟当代掌故。能够对国事政事有较深的了解,为以后具有干练的经济之才奠定了基础。十三四岁时就表现出惊人的天赋,下笔千言立就。同治十三年(1874),年仅十六岁的沈瑜庆在与其父沈葆贞的通信中,就谈到中兴诸臣多不知外国情况,不懂处理对外事务,只有兵部侍郎郭嵩焘、江苏巡抚丁日昌等较通达,但他们却被朝廷清议所排挤,不得重用。对他的这些观点沈葆贞都深以为是。对于沈瑜庆的干练之才,他的恩师翁同龢赞不绝口:“门人沈蔼苍(瑜庆)(注:当为‘爱苍’),江南道员。此人识略极好,且有断制,不愧为沈文肃之子”。沈瑜庆也颇有中兴时重视人才的思想,他在寄给洪汝奎(琴西)的硃卷中阐述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性道:“有大臣乃有人才,有人才乃有国祚。”
沈瑜庆与陈宝琛同为同光体派中官居显要者,且父祖辈亦身居要职,因此甚重经世致用之学。陈衍在《涛园诗集正阳篇诗序》中说:“涛园少为诗,未成,喜治经济家言,足以推倒一时豪杰”。沈瑜庆与陈宝琛相同的是,早年勤于政务,少问津于诗歌之途,诗集存诗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陆续创作了《淮雨集》(已失传)《春申集》《正阳集》,而辛亥后作寓公数年,往来诗友酬唱渐多,又成《南州集》《黔中集》《义熙集》。在他去世两年后,由其外甥李宣龚整理出版,定名《涛园集》,郑孝胥为之题签,沈曾植、陈衍等人作序。全集收录诗歌四百五十七首,词五首。
沈瑜庆的诗歌创作以苏轼为宗,且好用《左传》典故。钱仲联先生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指出:“爱苍虽闽人,而所作与闽派诗风迥异”。其实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都可能出现理论与实践不符的情形。所以,虽然沈瑜庆创作与闽派的诗风有异,但其诗学观念和创作倾向与闽派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沈瑜庆的宋诗观与陈衍相近而不尽同,最突出的有两点:
其一,对宋诗学中“诗史”的继承发扬。杜甫之诗以大量反映安史之乱及时事而被称为“诗史”,五代孟棨首倡诗史概念,至宋人“诗史”观念进一步加强,试图将诗与史两种不同的学科融合在一起。这一方面是宋代特殊的国情决定,国力的衰弱和周边民族矛盾的突出,使杜诗的忧民爱国情怀得到极大的理解。另一方面,与宋代发达的史学和宋人强烈的史学意识密切相关,他们更倾向于写实的文学创作,更注重比兴传统与史学理论结合的诗歌。沈瑜庆生于晚清末季,国事日非,他一生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对国家民族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而沈瑜庆本身对史学有着强烈爱好,使得他很容易从史学的角度出发,从宋人推崇的杜甫“诗史”精神找到共鸣点。
沈瑜庆认为,“诗史”不仅是在记录史实、反映现实,而且是一种忧国忧民情怀。他在《题崦楼遗稿》中道:
人之有诗,犹国之有史。国虽板荡,不可无史。人虽流离,不可无诗。
可见其始终将诗与人、诗与史视做一体,特别是国家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诗人不能忘记自己有着“以诗记史”的责任。
沈瑜庆宦海沉浮多年,政务缠身,但所到之处,官吏之弊、生民哀痛,常援之以笔,以诗记之。如《淮北行》是对当地盐政积弊的批评。诗中写道:“江淮自昔拥盐利,乱后公私叹重困。建瓴蜀船势莫御,齐豫捆输亦殊健。繄我追维陵替由,商而改票票改贩。……承平官吏病因陋,比量淮南更滋蔓。载盐即以船守轮,盐难周转船久顿。劳则思善逸则淫,盗卖夤缘毋乃混。积重忍隐成铤走,剜肉补疮亏巨万。典鬻俱尽且兔脱,始知水懦为民恨。”叙事长篇带有明显的史家笔法和史学观念,鲜明地表达了对官商勾结为害盐民的痛恨和盐匪横生、百姓苦不堪言的境遇的同情。陈衍在《涛园诗集正阳篇诗序》道:“甲午中日战争既殷,南皮张尚书权督两江,涛园总筹防局,接应北军饷械,兼午夜草奏治军书,既益更事,而目击感愤,间形诸诗。一时初未卒业,今年榷盐淮北,乃记忆补缀。六月至沪,手一巨编相示,则长篇大序,皆《诸将》、《八哀》之遗也。”陈衍将沈瑜庆的诗作与杜甫的《诸将》等相提并论,有过誉之嫌,但甲午海战中国败于敌手,割地赔银。沈瑜庆以实录精神痛心疾首地写下了《哀余皇并引》等诗,将讽刺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清政府,指责政府挪用军费致使作战失利,批评当朝的军政大臣渔利失职、祸国殃民的丑恶行径。诗中写道:“行人之利致连樯,将作大匠成虚位。子弟河山尽国殇,帅也不才以师弃,即今淮楚尚冰炭,公卿有党终儿戏。”希望朝廷能看到积弊所在,弃旧而图新。同时他还直承杜甫诗歌的写实精神,敢于讽刺朝野大臣、名士。如《咏史寄虚山师》讽刺帝师也是自己的座师翁同龢,骑墙于慈禧与光绪之间。《杂感》刺翁同龢、康有为等人,书生干政,天真轻信。《贾谊》讽刺康有为谋事不周,祸及国家。《晁错》为戊戌死难者而作,《罪言》写庚子事变,这些诗部涉及当时的重大事件,议论感慨,感伤时世。《今传是楼诗话》认为沈瑜庆诗反映的现实可当做历史来看:“谓君于同光以来朝政时局、人物掌故多所纪述,可作史观”。
其二,诗文相济,以文为诗。沈瑜庆论诗主张以杜、韩为宗,间取苏轼之高旷清疏,要求将叙事与抒情有机地结合为一体,以达到情感真挚、生动感人的创作目的。沈瑜庆与同光体派大多数官僚士大夫诗人们不同之处在于,他虽然也强调学苏轼,但是并没有把“恶俗恶熟”作为诗歌的要点,反对务为奇巧之作,不强求诗中表现学问或者一味吟咏理趣。只是由于个人的偏好,他喜欢在诗中使用苏轼诗歌或《左传》中的典故。沈曾植就说“世咸知君为诗好用苏轼、《左传》语”,陈衍也说他“有左癖,作诗文未有不挦扯及之者”,李宣龚《涛园集跋》道:“生平熟读《左氏传》,往往运用若己出”。《左传》与苏轼诗虽不算僻典,但与闽派诸人不强求用典的主张相比,沈瑜庆已显得与众不同。陈衍指出沈瑜庆的诗学源渊道:“生平肆力,深于少陵、昌黎,不如其深于眉山”。说明沈瑜庆最欣赏的是宋代诗人苏轼而非唐代的杜甫或韩愈。
陈衍指《正阳集》是“诗皆学杜,叙皆学韩,绝少苏家习派”。“诗皆学杜”指以杜甫的实录精神记述时事,“叙皆学韩”是以韩愈的古文笔法作叙。事实上客观地来看,《正阳集》非但不乏“苏家习派”,恰恰是学习苏轼“以文为诗”的实践,只是沈瑜庆将苏轼的“以文为诗”以“诗”加“序”的方法进行了改造,从而使诗歌使事用典以增博奥,序文则采用韩愈“文从字顺”的古文笔法,二者结合既扩大了诗歌的内涵,又阐明了诗旨。沈曾植《涛园诗集序》即强调沈瑜庆的诗歌要与文字配合起来才能明白作者的旨意:“涛园之诗,要当合其无韵之文字,平生议论简牍杂文,参伍错综,互相证,交相发,而后意匠所经营,所谓居要而警策,所谓词高而意远者,乃视而可识。”这里“无韵之文字”包括其“平生议论简牍杂文”,那“诗”与“序”更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
四、闽派别调——林旭
林旭(1875-1898),字暾谷,号晚翠。福建侯官人,光绪十九年(1893)年举乡试第一。甲午战争爆发后,参与公车上书,入赀为内阁中书。在京师参与兴办强学会、闽学会,与一时名士黄绍箕、沈曾植、康有为、梁启超均有交往。以王锡蕃荐得光绪帝召,与杨锐、谭嗣同、刘光第等同授四品衔充军机章京,参与维新变法。政变起数日遇害,年仅二十四岁。生前曾自刻《晚翠轩诗》一卷,卒后李宣龚辑其作刊刻《晚翠轩诗集》二卷行世。
林旭为近代文学史上少有的早熟文学天才,《今传是楼诗话》载:“有史以来,年少能诗,卓然可传者,唐惟李贺,宋惟王逢原……近贤如侯官林暾谷旭,卒年仅二十四岁,以诗格论,亦庶几卓然成家者”。然而,就在短短的一生中,林旭的诗歌成就得到当时文坛诸大家的推许,狄葆贤誉之为“深造有得,真解个中之三味,殊不似少年人作也”;梁启超赞曰:“波澜老成,环奥深秾,流行京师,名动一时”;在汪国垣的《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居马军五虎将之首,为“天雄星豹子头林冲”。
林旭在京应试期间结识沈曾植、陈衍、郑孝胥等人,这个时候宋诗已渐成风气。闽派的宋诗观在同乡之间已成共识,但林旭对于时代的宗宋诗风有自己的看法,并不紧随他人。在创作实践上,径师宋人,而又能自出机杼。钱仲联先生将林旭列做闽派的领袖之一,当是着眼于他在闽派中与众不同的诗学观:“近代闽派诗,暾谷为其开山之一,但他家大都学半山、简斋、诚斋,真能学后山者,暾谷而已”。林旭论诗之语并不多见,但从其诗中,可见其对宋诗的态度和看法。
林旭论诗,并不专提唐宋,而以己意所向,手摹心追,不求形神俱似,专注于有所超越。他认为:
读古人诗,望能自得好路走之,往日所共讲求,殊不尽然也。过犹不及,足下过取狂言,便觉眼中皆草,未思鄙诗入他人口中,皆刺藤也。刺藤有何可贵?欲自挫削不能,故用相告。
林旭指出,学诗应从读古人诗入手,但读古人诗,并非要紧随其后,在古人的道路上亦步亦趋。所谓“过犹不及”,当指效法古人,画地为牢者。“自得好路走之”,强调的是有自己的创见。林旭并不反对唐诗,但比较而言,他对某些浮滑无根的唐音确有不满。在《露筋祠》一诗中道:
篝火深宵叩庙门,拜瞻環佩自然尊。诗成不得夸神韵,只好从人笑钝根(注:渔洋斥后山为钝根)。
林旭仰承后山之诗,并不特别张扬,尽量避免一味拟其形迹,而失自得之意态。
基于戊戌变法的积极意义,后人对林旭在内的戊戌六君子在道德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诗歌观念上,林旭崇宋,重在以诗为诗,少见以理学或道德观念作为诗歌的更高要求。参与国事之际,心有所感所发,自然带有爱国热忱和追求,如《狱中绝句(示复生)》:“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但这种强烈的情感表达方式并非他有意追求的。在具体的宋诗接受上,陈衍指出:“暾谷力学山谷、后山,宁艰辛,勿流易;宁可憎,勿可鄙。”宋代诗人中,林旭主要师法黄庭坚、陈师道的同时还能兼及杨万里等人,取己所需,融合锻炼以成自家面目。
刘克庄评论后山道:“文师南丰,诗法豫章,二师皆极天下本色,故后山诗文高妙一世。”陈师道在以文为诗方面,则显然是出自南丰古文,以古文笔法造生新句子,以文章的章法结构和创作方法入诗,使句子峭拔瘦硬。林旭学后山,也多着眼于诗歌的句法结构,以古文的曲折跳宕之法,寓沉郁顿挫之气于其中,“听之使人不欢”。对于黄庭坚诗歌所表现出的瘦硬奇峭,林旭同样企图靠句法的改变来实现,以开阖动荡的结构、涩苦诗风和僻典拗句造成陌生化的效果。如《写经居士赠诗盛道闽派而病予为涩体谓学芜湖袁使君,因答及之》:
夫子论诗笑口开,叨逢目色却低回。涪翁不忘弦歌旨,杜老谁区排比才。底用为藩防楚舍,更羞酌水溯嵹台。似闻辛苦腻颜帢,要傍东家司寇来。
作为对自己为涩体的辩护的诗歌,依然因为典故和句法结构的欹侧多变而难测其意。《冯庵先生日成数诗,辄呼予视之》:
闭户空参曹洞禅,从人嗔劝乐吾便。诗题满眼浑无字,那对先生万斛泉。
顷刻催成纸面花,吚唔唤起笔间霞。撚须自向灯前读,想见潘郎果满车。
随舟芍药伴诗翁,更盗酴醿阳虎东。冷淡生涯人四个,谁家翠幕覆重重。
林旭自注“三诗均有本事”,显见是担心为人误解。陈衍对林旭的这种诗法颇不赞同,在《重刻晚翠轩诗序》中道:“后山学杜,其精者突过山谷,然粗涩者往往不类诗语,暾谷学后山,每学此类。”如果到了“粗涩者往往不类诗语”的地步,那显然与诗歌的艺术特质是不符合的。
林旭对杨万里亦有一定的认识和效仿。他的《舟中读诚斋诗》曰:“装中一卷荆溪集,拂拭船窗得暂披。不道霞光侵漆几,忽看赤鲤出清池。”虽集中此风格之作并不多,但亦不是一时之兴致。他在《冯庵移居穿虹滨以诗贺之,是日四月八也》中赞赏陈书的“无穷诗句出清新”,在《叩冯庵门就睡矣诵一律使予书之和作》中道:“说似诚斋吾亦允,心头约略识清妍。”不排除林旭对陈书作为前辈诗人的尊重,在长期的诗学交流中,陈书等人的诗歌观念还是会对林旭产生一定的影响。他和陈书同游淮北之后,陈衍再观其诗,就发现诗风与以前有所不同:“游淮北年余,所作数十首,则渊雅有味,迥非往日苦涩之境”。
林旭论诗是主张转益多师,李审言《药裹慵谈》指出林旭对当代诗人也有所学习:“诗大都宗节庵、苏堪,饶有生造之趣。”林旭自己也表明学诗不可专主一家,自设疆界,他在《酬黴宇江亭谈诗见赠》说道:
论诗如文较多派,能驿众家即无害。孤生为道颇自封,比来稍欲观其外。几人南郭空连墙,谁士郯途忽倾盖。细思离合似有缘,妄生分别旋自戒。迢遥上奉一诗王,四国交侵无经界。龂龂执律欲正谁,空使达人笑多怪。感觉广我用意多,惟是褊心将永赖。夜窗病渴玉泉干,三复佳章舌根沛。日夕西山在眼中,此乃吾家真晚翠。
林旭认为诗歌要兼取众长,要“能驿众家”,反对“孤生为道”,应该放开眼界,不要画地为牢。
郑孝胥《题晚翠轩诗》对林旭的诗学做了全面的总结:“称诗有高学,云以涩为贵。子岂真可人,所诣遽尔邃。诗怀文字前,未得殆难会。即论句法秘,大事匪狡狯。初如咀橄榄,枯中说滋味。终乃啖枇杷,甘平宜渴肺。子诗真早就,流宕可毋畏。试回刻意功,一极才与思。向来谬见推,浅语不予赘。仍当摹千文,为君题晚翠。”指出林旭诗学以“涩”为贵,讲求句法,极思力于诗,意味隽永而耐咀嚼。同光体闽派论诗宗宋但并不特别推崇山谷、后山,诗歌往往较平易而少槎枒,林旭的宋诗观及生涩诗风在闽派中确属别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