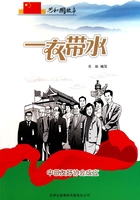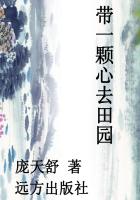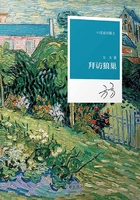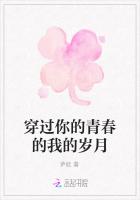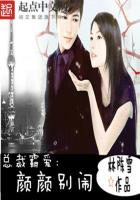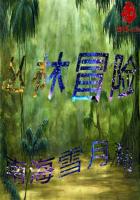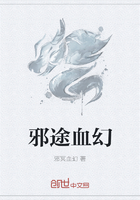第一章我们分析过,玄学思维方式上第一个重要特点,是尚简约。汉代经学是繁琐的,注经繁琐,它们构筑的庞大的宇宙图式论也是繁琐实证的,这也就有了汉代繁复铺陈辞藻和名物的文风,其代表就是汉大赋。玄学出来,一扫汉代人繁琐风气,直指简明深刻的本体。这既为崇本息末的本体论所决定,也为玄学所要解决的现实矛盾所决定。现实矛盾决定它不能就事论事,而应该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不应该着眼于繁复的细枝末节的表面现象,而必须一下子抓住根本,把繁复的矛盾统摄起来。在玄学看来,执一之宗主就可驾驭万物,这个宗主,在玄学家那里,就是无形无名。它们是要以简驭繁,以一统众。简和繁,一和众,是本和末的关系,以简驭繁,因此便崇本息末。
玄学以简驭繁,思想风气便为之一变。当时清谈就明显感受到这种变化。魏晋士人常常以最简约的言辞表述他们的玄理。
《晋书·王承传》载王承“清虚寡欲,无所修尚,言理辩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饰文辞,有识者服其约而能通。”“约而能通”是说他能用简约的言辞把复杂的道理解释通畅,不是归于繁复,而是归于简约,明其指要。这反映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变化。王承当时只是一普通之士人,但因其言理约而能通,得到时为太尉的名士王衍的雅赏。
至于那些名士,其风尚更是如此。乐广是一个尚简约的典型。乐广这一点常为当时名士所称道。清谈名士王衍曾说:“我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见于《世说新语·赏誉》二十五,而同条注引《晋阳秋》,则说王衍、裴楷并说:“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晋阳秋》说:“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世说新语·文学》十六说到乐广一个故事,说:“客问乐公‘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日:‘至不?’客日:‘至!’乐因又举麈尾日:‘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从这则故事看,乐广大体是直截人里地抓住问题要点,以简约的言辞给以点悟。他把繁琐的论证分析过程全部省去了。《世说新语·文学》
十八载“三语掾”的故事也是一个典型。这说的是阮惰和卫玢的故事。王衍问之:“老庄与圣教同异。”这本来涉及许多问题,需要多方阐述才能说清,但阮惰只回答三个字:“将无同。”这三个字稍有费解,是说并不相同呢?还是相同呢?如果“将无”二字是虚语,则是说老庄与圣教本无不同。从当时社会的思想倾向看,后一解释更为可信。但这么复杂的问题,阮惰只用了三个字,他是抓住最要点的东西,而舍弃了一切细节。阮惰因此被王衍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应该说,三语之说已非常简明了,但卫蚧说,只一字即可,阮惰又进一步说,可“无言”而辟。问题总是要分析,要分析就要有言,所谓“无言”而辟,只是以为“无”可以包容一切的“有”,一切的答案尽在其中。“无言”,当然简约到了极点。类似的例子,《晋书·阮惰传》说惰“言寡而旨畅”,《阮瞻传》说瞻“读书不甚研求,而默识其要,遇理而辩,辞不足而旨有余”。
玄学这一思维方式,与《易传》的影响有关。《易》本来就是三玄之一。《易·系辞传》论述《易》卦爻辞的特点,说:“其称名日小,其取类日大。”以简单细小之名物以类比重大繁多之事理,就是以小总大。玄学以少总多与此是一致的。玄学思维方式上的这一特点,便直接影响到文学,影响到一些文学理论的体系建构,影响到观察一些具体文学的角度方法。
一些文学理论,表现出以简驭繁、以一统众的体系建构。
典型的当然是刘勰《文心雕龙》。《文心雕龙》体大思精,虑周言密,在它严谨的体系架构中,有玄学思维方式的影响。
《文心雕龙》的体系架构,其《序志》篇有完整的表述: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割情析采,笼圈条贯:摘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四十九篇之外是哪一篇?一说是《原道》篇,一说是《序志》篇。
从刘勰的论述来看,后说为是。他明确说:“长怀《序志》,以驭群篇”,“群篇”,就是《序志》之外的四十九篇,《序志》篇和“群篇”的关系,就是一和四十九的关系。他并没有说,文本于道,以驭群篇。从“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云云,到“耿介于《程器》”,也就是从《原道》篇到《程器》篇,恰恰是四十九篇。《原道》篇在四十九篇之内,而不是之外。在这之外的,是《序志》篇。
刘勰为什么以《序志》篇,而不是以《原道》统驭“群篇”?这是因为他直接要说明的是《文心雕龙》这部“书”的架构,而不是其他。作为“书”的架构,他需要用《序志》篇说明取名《文心雕龙》的考虑和根据,以及写作这部书的缘由,需要对前代论文者作一评价总结,也需要简明地描述一下全书的理论体系,需要表明它“弥纶群言”的宗旨,和“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研究方法。《序志》篇没有讨论具体的文学问题,但有这一篇,读者对书中的具体论述,对全书的理论价值、基本体系等等,才有一个更为全面完整的了解。从体系架构来说,这是外在的。刘勰用这一篇驾驭“群篇”,是要由外而内,逐步引入它的内在理论体系。
这种外在的架构,“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以一统摄四十九,是从《易》学中来的,也是从玄学中来的,是王弼释大衍义以一总多思想的体现。
当然,《文心雕龙》有它内在的理论体系,上面这段完整的论述,既表述了全书的外在架构,同时也表述了《文心雕龙》的内在理论体系,它所体现的,还是玄学思想方法。
这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文本乎道。《文心雕龙》以《原道》为首篇,《序志》篇又明确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刘勰是以“道”为文之本原,而所谓“道”,笔者认为,即是自然,每一事物的自然本然。刘勰认为,天地万物之文,从天地之分,日月运行,山川万物,均本于自然,而人参效天文,因而有人文,因而人文也本于自然。刘勰是以这样一种“道”为文之本原,用以统摄《文心雕龙》所有的问题。首先是统摄“文之枢纽”数篇。为什么要“征圣”、“宗经”?因为它们是“道”的具体体现。因为“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因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为什么要有《正纬》、《辨骚》两篇?因为它们可以补经书的不足,而这补不足,恰恰是文学自身发展所需要的,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说,需要从纬书中吸收“事丰奇伟”的特点以益文学想像,需要从《骚》中吸取其情和奇,作为创作奇情壮采的借鉴。其次,更重要的是通过“文之枢纽”,统摄《文心雕龙》的所有问题。
比如,诗之写作,乃“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比如,创作构思,须“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 (《神思》
篇),须“率志委和”,“从容率情,优柔适会”(《养气》篇),从容不迫直接抒写,也就是一种随顺自然的写作态度。他论体性,也就认为“吐纳英华,莫非情性”,“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体性》篇),认为文章风格本于作家的自然情性。他论定势,也就认为,作为一种风格走向的客观态势,“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定势》篇)。他论丽辞,也就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丽辞》篇)。他因此解释了声律、章句、对偶、比兴、夸张、用典、练字这些人为创造的写作技巧存在的合理性,因为这是文章写作自身所需要。在刘勰看来,自然之道是“本”,《文心雕龙》论述的其他问题都是以此思想展开的,相对于文之本原来说,其他问题是“末”。而这个“本”,也就是“一”,众多具体问题,则是“多”,以自然之道统摄所有具体问题,体现的是以一总多的思维方式。《原道》篇虽不是《序志》篇所说的四十九篇之外的一篇,但实际上,它处于一种以一总多的地位,它所表现的,是内在体系上以简驭繁的思想特点。
再一个层面,是“文之枢纽”。“文之枢纽”,即《序志》篇所说的“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原道》
以下四篇,《征圣》、《宗经》、《正纬》、《辨骚》,同样在文本自然之道的前提下,对《文心雕龙》论述的众多具体问题起着统摄作用。刘勰认为,后代一切文体,都源自《五经》。他说:“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
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宗经》
篇)所谓“终人环内”,是说一切文体,均统摄于《五经》之下。
他指出,《五经》特点各不一样:《易》是“旨远辞文,言中事隐”;《书》是“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诗》
是“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礼》是“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春秋》是“辨理一字见义”,“婉章志晦”。《尚书》是“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是“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因此后世各种文体写作时就应当本于这些特点。他提出文章写作的基本原则。他提出“衔华佩实”(《征圣》篇),提出宗经“六义”说:“一则情深则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宗经》篇)他又提出要吸收纬书事丰奇伟和奇情壮采的特点。他主张抒情,又主张教化;主张文采华丽,又希望归于雅正。这些,都贯穿于《文心雕龙》以下论述的从文体论、创作论到文学史论、作家论、鉴赏论的各个具体问题。刘勰的思路很清楚,他是在“文本于道”的前提下,提出“文之枢纽”,进一步把众多繁杂具体的问题统摄起来,归到他理想的文学风格之下。他的思路,仍是以简驭繁、以一统众。
要之,《文心雕龙》这部体大思精集大成的著作,是由本及末,以本统末,以简驭繁,由此建构起全书的理论体系。
在一些具体文学问题上,也表现出以简驭繁、以少总多的思维特点。
这首先还是《文心雕龙》。它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宏大体。《通变》篇论通变说:“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他这里提出“规略文统,宜宏大体”,或者说“总纲纪”的问题。他说要“先博览以精阅”,纲纪是以“博览”为基础的,博览是博览前人之传统之作,是讲“通”的一方面。他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变是无方之数,通是有常之体。刘勰是重视创新的,但他认为,创新要以“通”即继承前人优秀传统为大体,以此为大体,“规略文统”。之所以要“通”,因为不同文体有不同的写作规范,这是需要遵从的,所谓“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当然,所谓“通”可能还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当有征圣、宗经的思想在,因为征圣、宗经事实上也是“通”。
一切文学的变化创新,都统摄在圣人经典的纲纪之内。《定势》
篇说:“执正以驭奇”,《辨骚》篇说:“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他的文体论,“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序志》篇),所谓“原始以表末”、“敷理以举统”,是讲统即“通”的一方面;“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是讲“变”的一方面。二十篇文体论,事实上讲各种文体的发展史。涂光社先生《文心十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说得好,《文心雕龙》是以史为纲,以论为目交织而成。因为以史为纲,所以《序志》篇说:“上篇以上,纲领明矣。”上篇以上,包括文体论。文体论何以是纲领,就因为《文心雕龙》是以史为纲。因为以论为目,所以《序志》又说:
“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下篇,就是具体之“论”。这与论“通变”的思想是一致的。他是以“通”为正,为大体,为纲纪,执此之正,驾驭无方之数。《通变》篇说:“望今制奇,参古定法。”万变之奇是需要的,但必须参古定法,古之定法是统摄驾驭变化之奇的。
、
《熔裁》篇说:“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斫削矣。”又讲到“本体”,讲到“纲领”。“熔”解决规范本体,使纲领昭畅的问题。所谓“熔”,就是内容的提炼。他提出“三准”说。因为“思绪初发,辞采苦杂”,而辞采繁杂归根结底是思想内容繁杂,因此“草创鸿笔,先标三准”。所谓“三准”,是“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先确立思想主题和文章体式,然后选择适宜表达主题的具体生活题材,使作品题材和主题体式相一致,最后是选择适当的言辞突出主题之要点。在此基础上,再“舒华布实,献替节文”,再“剪截浮词”,所谓“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熔和裁的关系,就是规范本体和具体的言辞剪裁的关系。
文体论论各体文章写作,也每每强调要立大体。《诠赋》篇论赋的写作,说:“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祝盟》篇论祝盟文的写作,说:“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哀吊》
篇论哀辞的写作,说:“原夫哀辞之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杂文》篇论杂文的写作,说:“原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体之大要也。”《论说》篇论论说文的写作,说:“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议对》篇论议对体文的写作,说:“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然后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蔌为美,不以深隐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
与宏大体,规范本体相联系的,是强调贯一。《神思》篇论神思便说,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而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有的“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有的“情饶歧路,鉴在疑后,研虑方定”,因此“临篇辍虑,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为“博见”和“贯一”。他说:
“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刘勰的意思,是找到一根贯穿全文的线索,把繁多杂乱的材料统摄起来。统摄繁杂所谓“拯乱”的线索不能多,只能是“一”,这就是“博而能一”。
“贯一”是文章写作中寻求统贯全体,统贯各种繁杂因素。
宏大体的目的,也就为贯一。《附会》篇附辞会义,说:“凡大体文章,类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是以附辞会义,务总纲领。驱万途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务总纲领”,就是前面所讲的宏大体。总纲领的目的,是使枝派繁多的思路言辞归于一致,用总一的纲领把群言百虑统摄起来,总纲领是为“贯一”。
宏大体以“贯一”也就是以一总万。《总术》篇有更明确有论述。“术”在《文心雕龙》中指方法技巧,也指原理。方法技巧在刘勰看来,也就是文章写作的原理。他说“文体多术”,就是说,各种文体都有其写作之术,文体论二十篇就分析了各体文章写作之要术。这要术,《序志》篇称之为“敷理以举统”。因此《总术》篇一开始,要先论文、笔之分,其意是说,不论有韵之文,还是无韵之笔,各种文体写作都有“术”可寻可循。他又认为,为文过程的一切方面,都有“术”。《神思》篇说,创作前学识的积累,事理的分析,丰富的生活阅历等等,“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而神思本身亦有“术”,有术所以要养,所谓“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他论通变、定势、情采、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附会等等,都提出一些写作原理性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创作论就是文术论。因此他把《总术》既放在文体论之后,也放在创作论之后,他要总论各种文体及为文过程一切方面文术之作用意义,强调作文须总持文术。他批评说:“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总术》篇)他又说:“才之能通,必资晓术。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哉?”(《总术》篇)
要对各种写作原理方法分辨得一清二楚,得心应手,方能熟练的驾驭文思,写出好文章。他用“执术驭篇”来说明“术”和文章写作的关系,“执术”,也就是总术,总持文术。文体各种各样,文章写作过程千变万化,都要用术来驾驭。这“术”就是大体,就是“一”,《总术》篇最后就说:“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思无定契,理有恒存。”《总术》篇“执术驭篇”,体现的是以一驭万的思想,而这也是整个文体论和创作论的基本思想。
宏大体旨在“贯一”,宏大体和贯一体现的都是以简驭繁的思维方法。
刘勰讨论文术问题,总是体现这一思路。《事类》讨论用典。
用事用典对于文章写作何以是必要的?刘勰作了分析,说:“故事得其要,虽小成绩,譬寸辖制轮,尺枢运关也。”他用车辖控制车轮、户枢转动门扇作比喻,车辖、户枢之小而能控制车轮、门户之大,说明用事用典对文章写作之所以必要,乃因为它能以简要的事典统摄、包容繁多的内容。他的看法包含了以少总多的玄学方法论的思考。
《文心雕龙》还常常直接说,他的思路就是以一总万。前面引述的《总术》篇就是这样。《附会》篇也说得比较明显。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章句》篇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知一而万毕”出《庄子·天地》“通于一而万事毕”。《庄子》此句成玄英疏:“一,道也,夫事从理生,理必包事,本能摄末,故知一,万事毕。”刘勰前说“振本而末从”,后说“知一而万毕”,知刘勰所谓“一”,亦指本,指道,具体则指分章造句之理。掌握基本原理,则一切事状均可尽知。《物色》篇也说,《诗经》经常用一些简练生动的状语描摹物色之貌,如“‘灼灼’
状桃花之鲜, ‘依依’尽杨柳之貌”,或者“一言穷理”,或者“两字穷形”,他说这是“以少总多,情貌无遗”。
《隐秀》篇论“秀”,更体现了这一点。所谓“秀”,是“篇中之独拔者”,是“以卓绝为巧”。具体说,“秀”就是指篇中卓绝独拔的秀句。《隐秀》篇屡屡提到“秀句”,他说“篇章秀句,裁可百二”,说“秀句所以照文苑,盖以此也”,现存《隐秀》篇论“秀”,引作例证的,为“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也是摘句。虽只存一句,但可以想知,《隐秀》佚文中当引有大量摘句。
现存佚文便是如此。这样看,“秀”所反映的,就是魏晋六朝以来追求摘句之美的倾向。魏晋士人诗文品评便带有这一倾向。诗文品评伴随人物品评之风而兴起,从一开始就常常不是品赏诗文作品之全篇,而只是摘句评赏。当时可能已有专门摘句品评诗文的著作,如《南齐书·文学传论》就提到“张际摘句褒贬”。这类著作今日已不可见。现在可见较早的这类著作,是元兢的《古今诗人秀句》。但魏晋时期却有不少摘句品评诗文的例子,可以佐证这种风气之存在。品诗如《世说新语·文学》:“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日:‘讦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古物,焉得不速老。”’
不是说哪一篇最佳,而是说哪一句最佳,人们的欣赏眼光在句而不在篇。品诗如此,品文品赋也如此。《世说新语·文学》:“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做金石声。’范日:‘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
‘应是我辈语。”’刘孝标注:“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而界道,此赋之佳处。”钟嵘《诗品》也常摘句批评,他评谢胱便说:
“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一二佳句较之赋作之全篇似更能引起人的美感。崇尚摘句之美,精心创造出一两个秀卓绝之句,用这样的艺术手法,造成作品的可以句摘的美,以这样的秀句辉映全篇,在诗文品赏中欣赏这样一种秀句的美,这就是隐秀之“秀”的主要内涵。
隐秀之“秀”的提出,和魏晋时以“秀”品人的风气可能有密切关系,也和玄学崇尚自然的思想有联系,因此在刘勰看来,所谓“秀”,只能是自然会妙的结果。刘勰区分美和秀说:“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朱绿染缯,深而繁鲜,英华耀树,浅而炜烨。
秀句所以照文苑,盖以此也。”秀在艺术上高于美,就因为它是自然会妙。
这里所要讨论的是它所体现的思想方法。从思想方法看,秀句的语言总是简少的,但它却蕴含着比篇中其他句子更为丰厚的内涵,一些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精华,往往通过一两个秀句集中体现出来。刘勰这样概括“秀”特点:“言之秀矣,万虑一交”。
就是说,所谓“秀”,是把极为繁复的内容(所谓“万虑”),通过一点(所谓“一交”)着力透露出来,表现出来。它所体现的,是玄学以少总多的思想原则。
强调以简驭繁,因此尚简约。刘勰认为,圣人经典就是这样。《征圣》篇说圣人经典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简文以达旨”。
《明经》篇说《五经》各有特点,而其基本之处,在于“辞约而旨丰”,它提出明经之“六义”,其中之一是“体约而不芜”。它论历代各类文体之特点,都体现这一要求。《铭箴》篇说铭箴是“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搞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说“义典则弘,文约为美”。《诔碑》篇称赞蔡邕的碑文“其叙事也该而要”。《杂文》篇说连珠的写作当“义明而词净”。《诸子》说,《尹文》的特点就是“辞约而精”。《论说》篇批评一些汉代人注经过于繁琐,而毛公训《诗》,孔安国给《尚书》作传注,郑玄注释《三礼》,王弼注《易》,则是“要约明畅,可为式矣”。
《檄移》称赞陆机的《移百官文》“言约而事显”,说这是“武移之要者也”。《章表》篇说章表的写作,当“要而非略,明而不浅”。《议对》篇说议对文的纲领大要,在“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在“总要以约文,事切而理举”。尚简约,体现的是审美意识,而这种审美意识的背后,是以简驭繁的思维方式。
三
以简驭繁的思维特点,在《文心雕龙》之外的其他文论著作中也有体现。
如陆机《文赋》。刘勰曾批评陆机《文赋》 “巧而碎乱”(《文心雕龙·序志》篇),所谓“巧而碎乱”,重要的一点,就是未能像《文心雕龙》那样不论在整个体系上还是在具体文学问题上,有一个贯一统众的东西。就《文赋》总的架构来看,可能是这样,但在文章具体写作要求上,《文赋》其实也有和《文心雕龙》类似的思想。比如它论四种创作技巧,其中之一:“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极无两致,尽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立片言旨在突出中心,在文繁理富之时以片言将众辞统摄起来,使之繁而不乱,多而不散。这片言和后来说的警句不完全一样,和刘勰说的秀句不完全一样,警句、秀句都未必统摄全篇,而陆机说的“片言”,是统摄“一篇”,使“众辞”有条之“警策”。片言是“一”,立片言使众辞有条,也就是以一统众。
如刘知几《史通·叙事》。他说,史书叙事的写作,当求简要,就像饵鱼捕鸟一样,“盖饵巨鱼者,垂其千钓,而得之在于一筌。捕高鸟者,张其万置,而获之由于一目。”史书叙事也一样,“夫叙事者,或虚益散辞,广加闲说,必取其所要,不过一言一句耳。荀能同夫猎者渔者,既执而置钓,必收其所留者,惟一筌一目而已。”因此史书叙事的繁文缛句,都当删去。但是,删浮辞去骈枝,是为了用简要的语句表达更丰富的含义。刘知几论章句,说:“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他的倾向,以为省字约文的晦之文优于显之文。刘知几说:“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史通·叙事》)就是说,省文约句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用更为简省的语言巨细无遗的容括众多的内容。
如刘禹锡的《董氏武陵集纪》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工于诗者能之。”后一句说的是想像力的丰富,陆机《文赋》所谓“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刘勰所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者是。前一句则说的是以简明的语言表达丰富内涵的问题。
再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其十一论“含蓄”一品,用了空尘和海沤作比喻,说:“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郭昭虞《集解》:“尘与沤之浅深,形形色色,博之虽有万途,约之只是一理。”所谓“万取一收”,就是“以一驭万,约观博取,不必罗陈,自觉敦厚”。含蓄是审美风格,而这一风格集中体现了以一总万的思维方式,司空图的解释,正是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还有欧阳修的《论尹师鲁墓志》,该文对尹师鲁之文评价极高。他说“简而有法”, 《六经》之中只有《春秋》可以当之,其他经非孑L子自作文章,都虽有法,而不简。而欧阳修则用这句评价尹师鲁之文。历史上,韩愈与孟郊联句,则仿孟郊诗风,与樊宗师作墓志,则似樊宗师文风,因此他为尹师鲁作墓志,也“用意特深而语简,盖为师鲁文简而意深”。这实际反映欧阳修自己的审美标准。这审美标准,从思维方式来说,显然是以简驭繁。
四
以简驭繁的思维方式,也广泛体现于文学创作。
典故的广泛运用值得注意。典故是中国古代文学特殊的一种意象,而尤以诗歌使用更普遍。这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度所特有的文化现象。诗歌中运用典故,有一些并无太多深意,但不少诗歌确因典故的使用而使其意蕴大大延伸,由单层面变为多层面。典故亦称事类。据《文心雕龙·事类》篇,早在《易》
经,就已开始运用事类。但普遍的用事用典,是魏晋南北朝发展起来的。典故,即事类,从思维方式来说,如前引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篇所分析的,体现的是以少总多的原则,以简要的表象性语汇,包含内容繁复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背后,又有丰富指绘画之法,其思想基础,是老子学说的“道”。“一画”所谓“一”,就来自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一”。《一画章》开宗明义就说:“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太朴”是混沌的状态,也就是“道”,太朴一散,则法立,也就是所谓“道生一”。
“道”产生万物,又统摄万物,石涛所谓“一画”也是统摄万有的根本。 “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见用于神,藏用于人”。它在绘画中起着神妙的作用,因此说“见用于神”。人们绘画时,绘画之法,即所谓“一画”自然而然就起作用,绘画之法也只有通过人们绘画才能体现其作用,因此又说“藏用于人”。
石涛又说: “立一画之法者,盖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也。”“道”是无,“一”是有,“一”从“道”中产生,有法从无法中产生,因此说“无法生有法”,而“一画”之法统摄所有具体之法,统摄各种具体的艺术技巧,因此又说“有法贯众法也”。“一画”之法贯穿于绘画始终,在绘画的所有方面起着作用,石涛说:“此一画收尽鸿漾之外,即亿万万笔墨,未有不始于此而终于此。”所有的绘画,绘画的每一处笔墨,都从“一画”之法开始,而又终于“一画”之法。掌握了“一画”之法,绘画就“能方能圆,能直能曲,能上能下,左右均齐”,就能“用无不神而法无不贯,理无不入而态无不尽。信手一挥,山川人物,鸟兽草木,池榭楼台,取形用势,写生揣意,运情摹景,显露隐含,人不见其画之成,画不违其心之用”,运笔自如,信手一挥,一切东西都能得心应手地表现出来。“一画”是统摄具体的万物的东西,因此,“一有不明则万物障,一无不明则万物齐。画之理,笔之法,不过天地之质与饰(本质和现象)。”“天有是权,能发山川之精灵,地有是衡,能运山川之气脉。我有是一画,能贯山川之形神。”“以一画测之,即可参天地之化育” (《山川章》)。就是说,掌握了“一画”,则万物均能表现,没有掌握“一画”,则一切都不能表现。“一画”是贯穿山川之形神,贯穿万物根本的东西。绘画规律蕴含于客观万物之中,因此石涛说“夫一画含万物之中”(《尊受章第四》)。石涛认为这个客观规律“世人不知”,“所以一画之法,乃自我立”(《一画章》),是他发现了这一规律。如果不掌握这种规律技巧,则笔与墨会,只能是细缇不分,混沌一片。掌握了这种规律技巧,则不会细绲不分,笔墨不会混沌一片,笔墨相会就能成为画,不论画什么,都生动有灵气,所谓“笔与墨会,是为纲绲,细绵不分,是为混沌。辟混沌者,舍一画而谁邪。画于山则灵之,画于水则动之,画于林则生之,画于人则逸之。”(《纲组章》)绘画就像世间其它纷纭复杂的事物一样,发展变化都循着特定的规律,掌握了这种规律技巧,就可以一通百通,以简驭繁。“自一以分万,自万以治一,化一而成细组”(《纲组章》)。这所谓“一画”,所谓绘画表现的规律技巧,是通过绘画整体体现出来的,因此, “一画”所谓“一”,具体到绘画,可以理解为绘画作为整体的“一”。但是,它又体现于每一笔画中,绘画的每一笔画,都体现绘画的规律技巧。因此绘画只要一落笔,画家所掌握的绘画的根本规律技巧就自然体现出来,一切具体的画法都随之而得到表现。因此石涛说:“一画落纸,众画随之,一理才具,众理付之。”这里,绘画的规律技巧就表现在每一画之中,表现在绘画一开始的那一画之中。“一画”,本来就指绘画造型的一根根线条,在石涛看来,“一画”虽然平凡,但它却是绘画技法研究最基本的对象和条件。
所以,在他的画论里,“一画”统辖着所有的绘画技法,绘画一切的变化,都根源于“一画”的变化,极源于“一画”之法。石涛认为,对绘画规律的真正把握,真正理解,应该是一个以天合天、物我为一、心手两忘、物我两忘的境界。绘画规律是无形的,人们所能见到的,只是具体的画,从具体的画中,体现出“一画”,从这个意义上,“一画”又非人所有,人所有的只是具体的画。因此石涛说:“画乃人所有,一画人所未有。夫画贵乎思,思其一,则心有所着而快。”(《远尘章第十五》)。“一画”和具体的绘画的关系,就是本和末的关系, “画”是具体的“有”,“一画”是内在于“有”,无形中从根本上起作用的东西。
“一画”的表现就是具体的“画”。所以石涛说:“一画者,字画先有之根本也。字画者,一画后天之经权也。”(《兼字章》)
文人画之尚简率,石涛的“一画”说,就其体现的思想内涵来说,就这种内涵的思想渊源来说,是多方面的。宋元离玄学时代已远,未必可以直接和玄学相接,但从思维方式来说,确似表现出以简驭繁的特点。说它和玄学思维方式暗合,或者说多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离事实不会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