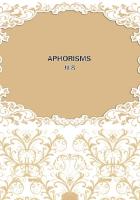我于六月份回国之际在南京给三民主义青年团员做过一次演讲。当时盛况空前,一个非常宽广的会场居然没能容下与会的听众。一些听众站在会场外面通过扩音喇叭听了我的演讲。
朋友来到我这儿,对我说,“这么多听众都是冲着您来的。”我说,“不是这样的。因为大家对日本感兴趣,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聚集而来。”在北平演讲的时候也是如此,会场里的白色的椅子差不多都要被踩坏了的样子。就这样,我的几次演讲都用了扩音喇叭。在我演讲后的座谈会上,青年们一点儿都没问及有关战犯问题以及赔偿问题。而是问了许多有关日本的文化、战后的思想动向、妇女的解放、男女共学以及将来日中关系所应保持的关系等问题。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中国青年绝没有拘泥于过去,而是一心一意地勇往直前。
接着向大家传达一个坏消息。“珍珠港事件”以后,我在燕京大学的朋友们都被日军逮捕了。其中一位赵承信先生写了一本名为《狱中杂记》的书。他是燕京大学的法学系的系主任,也是一位社会学家。另外,还有强东孙先生的狱中日记,他是中国有名的哲学家。再有一本便是燕京大学总务长蔡一谔先生用英文写的《日本狱中的五个半月》。我于不久前的六月十八日回国,这一天正是他们出狱两周年的纪念日,于是我被邀请和他们一起用了餐。被监禁的有十七位教授,其中两位在狱中去世。在那次纪念会上,大家都坐在榻榻米上,用监狱中的编号互相称呼对方。教授们的书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即,死不应该是最可怕的,思想不应该被压制,并且人类的爱与耶稣的爱绝不是能用剑或刀压制得住的。所以我在这儿要以今天这个题目来谈谈知识分子应该怎样为中日关系而努力。我来日本以前对有关日本国民是怎样被日本军阀欺骗的一无所知。这是我旅居日本以后才明白的。那就是七千万的日本人中的六千几百万人被极少数人引上了一条走向毁灭的道路。
我的几本著作被翻译成了日语。但我来日本才发现其中一本叫《寄小读者》的书中的部分内容被省略未翻。为什么这本书中的一小段被省略了呢?我猜想这种现象恐怕是由于军阀的压制而造成的。被省略未翻的是我在一九二三年去美国途中逗留东京参观“游就馆”时的一段。那儿陈列着甲午战争时期的战利品以及有关战争的图片。我把目睹这些展品时的感想以《寄小读者》为题写了下来,那时我觉得非常遗憾也觉得非常可怕。我直率地述说了我的这些感想。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段——我十分歉疚,因为我对你们述说这一件事。我心中虽丰富地带着军人之血,而我常是喜爱日本人,我从来不存着什么屈辱与仇视。只是为着“正义”,我对于以人类欺压人类的事,我似乎不能忍受!我自然爱我的弟弟,我们原是同气连枝的。
假使我有吃不了的一块糖饼,他和我索要时,我一定含笑地递给他。但他若逞强,不由分说地和我争夺,为着“正义”,为着要引导他走“公理”的道路,我就要奋然的,怀着满腔的热爱来抵御,并碎此饼而不惜!请你们饶恕我,对你们说这些神经兴奋的话!让这话在你们旋转一周罢。说与别人我担着惊怕,说与你们,我却千放心万放心,因为你们自有最天真最圣洁的断定。这是我二十多年前写的。如果这段文章在二十年前在日本被介绍的话,难道不会对日中两国的合作起到一定作用并且在两国的理解方面带来一些希望吗?像我这样热爱和平的人写的作品尚且未被完整地翻译、出版,那么思想激进的作家的著作想必就更没有被介绍的可能了。
传人日本人民耳际的只是一些中国强烈抗日的谣言。中国的抗日运动是从“卢沟桥事件”开始并一天天高涨的,这些运动都是为了自卫而发起的。这是一个噩梦。我现在很想忘却这一切。我待在日军占领下的北平的那一年正赶上日军从华北向南方进军,那也是中国所有的主要城市基本沦陷的时期。我们呼喊着“庆祝徐州沦陷”、“庆祝上海沦陷”。这和举起一杯酒在他人面前说“祝你不健康”是一回事。大家想像一下东京大学和其它大学的学生能做到汇集在一起,举起旗帜在东京巡游并欢呼“庆祝东京沦陷”吗?这是不可能的,他们绝对做不到的一件事。但是我们的学生却做了,因为背后有冰冷的机关枪对着他们。这种被强制的事不断发生,所以知识分子在北平再也待不下去了。我也不得不逃离北平。但是我特别喜欢日本人。几天前,我看了一篇名为《目前才是知识分子力量最强大的时期》的德国人写的文章。对处于与当时的中国同样状况的日本来说,目前正是两国应当携手的时刻。如果日本现在不走正确的道路,那便会永远地失去机会。我们努力的方向正在于扭转直到今天为止的错误。我们必须知道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我国的孙文先生曾经说过:“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对待我们的民族,共同奋斗。”和没有平等思想的人是实现不了合作以及共存共荣的。战争刚刚爆发时,中国有一首非常流行的义勇军进行曲,其中一句歌词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日本军阀通过工业、矿山、农业、商业、军事等方面的统计了解了中国。他们用数据式的理解方法来了解中国。但是也有从数据中推断不出的东西。这就是中国的国民性。中国的国民性通过军人是绝对无法理解的。我曾经这样想过,不通过知识分子中国的国民性是理解不了的。如果将那么多的将军、上校全部改为教授会怎么样呢?如果那么多的士兵都成为学生的话,又会怎么样呢?那时才能实现真正的共存共荣,才能建立真正的大东亚共荣圈。我觉得为了将来的日中文化交流,应该采取以下三点措施:
第一,签订“和平条约”以后,两国互相派遣教授与学生,而且要多派一些人。从各个大学挑选优秀的青年,让他们研究他们所感兴趣的问题。并且在两国的大学开设日中两国的政治讲座与文化讲座。
第二,两国的文化团体进行互访。
第三,两国的报刊记者在报纸上尽量鼓励双方的协力合作。
以上这些是为了使人与人之间拥有爱心。其结果将使最优秀的日本学生在中国最正确地理解中国,从而使个人之间也能在各个方面保持最紧密的合作。
《大公报》的总编辑王艺生先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主要从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描述了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
其内容让人悲恸不已。但是现在我想把这些历史都抛在脑后,我想去除这六十年来的悲惨历史。日本和中国之间具有二千年的交流历史,我认为今后我们必须创造更新的历史,这就是最光辉的文化教育。耶稣教诲我们“不能把拿着犁(农耕工具)向后看的人当作自己的同行者”。两国青年在今后的中日文化史上应该紧紧地握着“犁”勇往直前。在此我为大家指出一条路。这是一条民主之路、自由之路,也是一条通向东亚和平的道路。
(1947年10月21日在日中文化协会的演讲)
(虞萍 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