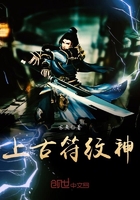草桥沟在那个冬天便全线竣工。邓吉昌带着近二百名劳力返回蛤蟆湾子时,已近腊月。外地民工队伍也纷纷撤离,他们推着来时的铺盖卷儿,过度的疲劳已将昔日冲天的豪气扫落一空,与混熟的村人有气无力地打着招呼。他们用自己的血汗和生命为荒原留下了一条百余公里的大沟。邓家已在十几间房边又盖起五间,这个家庭除自己现住的老少十一口人外,另住着兆喜媳妇秋兰的弟弟妹妹、红霞,以及郑好学的两个遗孤和浪女人送来的孩子,成为村里唯一的一个杂姓之家。
民工撤去后的第二年和第三年春种前,邓吉昌拖着一双病腿沿着大沟两侧的大坝走了两个来回。面对一边的黄河水和另一边汹涌的大海,这位最早闯入荒原的六旬老人感慨万千。他的心情比双腿更加沉重。大沟两侧的大坝宽达数十米,他的足迹清晰地印在新翻的坝土上。大坝经过两年雨水的侵蚀,上面泛着白花花的盐碱,寸草不生,几乎每处的坝面上都残留着荆条疙瘩和海生动物残骸,一如多年前鲍文化带人挖出的东西一样。这些更加证明了他对这片土地来历的推测。在他六十岁的生命里,已记不清颠沛流离过多少地方,没有一块土地能像这片河父海母之地一样,使他感觉如此亲切。当他携儿带女走到那片自己圈占下的红土地时,便曾有过飘叶归地之感。此时,这种感觉变得更真切、更实在。“兆喜的坟墓里,应该是我啊。”他一遍遍地对刘氏说。他常常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梦中自己平静地躺在一具棺木里,耳边激荡着河海相拥的巨响。又有一天,他对刘氏说:“这里,就是咱们的葬身之地了。”从邓吉昌的话里,刘氏看到了邓吉昌几乎一夜间衰老了的身体和心。邓吉昌的短发已经花白,一双病腿更加剧了他的衰老。刘氏一时被男人的话所感染,用手捋着自己同样的一头花白头发。经过两次各到尽头的沿坝而行,邓吉昌全部的心思已从探明脚下土地的来由转向了别处,他的思维有时连他自己也感到吃惊。他已昏花的二目从肥沃的荒原表层看到地下。“地下是海滩啊。”他这样提醒自己,然后,又真切地看到地下海水在往上渗透,他知道这并非幻觉,地下有比海水更苦咸的潜流已从鲍文化带人打出的那口井里得到了证实。这盐碱肯定在往地表渗透,只是被一场场大雨压下了,可多年后盐碱肯定会渗上来。就像他推测黄河摆尾和此地为河海所生一样,邓吉昌对这一预感深信不疑。但他同时为这一推测而惊恐异常,仿佛看到了村人耕种的沃土已经白花花泛着盐碱。今年早春从外探查回来,他的心一直被自己的推测扯得生疼,连日默声不响地吸着旱烟,只是马队从这里经过时,才暂时从自己的冥思苦想中走出来。
此时的蛤蟆湾子基本停止了外来迁居,人口的增长仅依靠村人自己的繁衍。即便这样,在马队从此经过时,大队会计的户口本上在加上雨的第三个孩子时,已有五百六十三口人。村里人知道,本该比这个数大得多的,除各种原因死亡的外,女人们有两年因饥饿闭经没有生育。郑好学死后,公社党委书记曲建成到村里几番考察,最后决定让鲍文化担任大队支部书记。为调动村里人劳动的积极性,蛤蟆湾子大队两个生产队已分得干净利落。各队的收入归本队社员。在大队长邓吉昌支持下,两队调整了归队农户。两个生产队分别由石头和雨担任生产队长。邓吉昌家在一队,书记鲍文化分在二队。每户劳力都怀揣一个记工本,一天活干下来,纷纷持着自己的小本本去各自生产队记工。工分就是命根儿,年底分粮分钱,各家工分的比例占了百分之九十,另有的机动部分照顾老弱病残和孩子多的社员。王来顺比邓吉昌衰老得更快,五十岁的人头发已全白,腰弯成了满弓。他对村人的仇视也换来了全体社员对他的轻视,脾气变得越来越坏,使赵氏变得小心翼翼。这年春耕结束后,赵氏大起胆子向他建议入社,使王来顺的激愤全部发泄了出来。他上前一把抓住赵氏的头发,把她从炕上拖到地上,两眼血红地狠狠地殴打:“我让你入社,我让你入社!”直到两个闺女听到赵氏的哭叫声赶来,将他拉开。王来顺还不解气,抓起顶门杠在屋里乱抡,把家什一件件打得粉碎。可第二天,他再也没能下炕,不间断地咳着,最后吐出一口稠血。赵氏大惊失色,慌慌地亲自去找村里的医生秦建军。秦建军是最后进蛤蟆湾子的移民,因他祖辈干过兽医,三年前被公社指定为村医。秦建军极不愿登王家大门,他说自己是给社员看病的,不管单干户。赵氏听完一下便跪在了地上。这才使秦建军软下心来,背起药箱来看王来顺,在他伸手给王来顺号脉时,却被连声咳嗽的小气鬼一把推开:
“我没病,我没病,你给我滚!”
他的怒吼引来了更厉害的咳嗽,他歹毒的双目让秦建军不得不退出他家房门。当天夜里,小气鬼永远停止了咳声,却传出了赵氏和三个孩子的号哭声。村里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没人过来,只有邓吉昌和刘氏踏进了他家屋门。赵氏对邓吉昌夫妇的到来感激流涕,她拉着刘氏的手让她看地上的脸盆,里面满是黏稠的黑血。
村人对王来顺的突然死去反应冷漠。他们第二天一早仍如往常一样有说有笑跟着生产队长下地干活,似乎此事和他们毫无关系,甚至有种解脱的感觉。因为那双歹毒的目光从此永远在他们眼前消失了。料理王来顺后事的外人只有三个:邓吉昌、刘氏和瞎嫂。邓吉昌亲手为王来顺打造棺木,刘氏和瞎嫂为死者赶制寿衣。瞎嫂微微蹙着眉头飞针走线,神态专注而平静。瘸哥死后,她是大队照顾的村户之一,村里人已很少见到她的身影,也很少有人进入她的家门。在给王来顺换寿衣时,刘氏惊奇地发现这个平日里背弯如弓的小个子男人腰身平直,骨瘦如柴,身体轻如七八岁的孩童。
王来顺出殡的傍晚,社员们都已放工,却仍无人过来帮忙。邓吉昌再也忍不住了,他挨户叫着众人:“帮着抬抬棺材吧,王来顺是咱村的人啊!”碍于大队长的面子,十多名劳力才极不情愿地来到王家。这是蛤蟆湾子有史以来也是此后最简单的一次葬礼,甚至连多年前那个寡妇死时都不如。但当十多名劳力草草为死者搭起一座新坟返回时,墓地四周却忽然聚集了难以计数的飞禽走兽。它们井然有序地聚在一起,发出各种鸣叫声,如同人的呜咽,凄厉动人。此时,众人忽地记起十年前那个百兽袭击村子的可怕之夜。村人对此惊奇不已。自饥荒后,荒原生灵已在人的疯狂捕捉下难见踪迹,但这个傍晚却一下子冒出如此之多,挤满了村外的整个坟地,密密麻麻。邓吉昌昏花的双眼准确地从百兽之中看到了一只白尾红狐。而此之前,对王来顺的白尾红狐之说他压根儿没信过,一直以为是王来顺的幻觉。整个晚上,蛤蟆湾子所有大人孩子都听到了彻夜的兽禽呜咽声。第二天夜里,有人说看到坟地里荧火通明,王来顺就坐在地上吧嗒吧嗒地吸烟,一群飞禽走兽伺立在他的身边,在王来顺的对面坐着一只长着一条长长白尾的红狐。此事很快传遍了全村,众人惊恐异常,各自回忆起与王来顺的种种摩擦。自此,晚上没人再敢靠近那片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