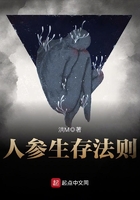黄昏时分,索宁选派的十名武士陆陆续续地来到沈府外的各个角落,不着痕迹地地隐藏起来,他们隐藏的办法与子敬派来的人不同,他们是扮作路人,有意无意地盯着沈府的各个角落,勘察着是否有可疑的人。可能是这两拨人的敏感度的原因,他们在天黑之前互相察觉到了对方的存在,于是很快有手脚伶俐的分别去回报给了各自的主人。
最先发现异常的是子敬的人,他们感觉到沈府周围来了一帮武士,他们的装束没有破绽,平常人很难看出来,只以为他们是屠户或者农夫;他们的容貌粗犷,看起来不象中原人士,且他们的双手的虎口有厚重的老茧,便知他们不是平民,而是长期使用刀剑的武士。这些情况汇报给子敬之后,子敬迅速跑到了沈府对面的楼上,由于夜色朦胧,看不真切,他揣测不出来这拨人的真实意图,于是问那个送信的人,“你看这些人善恶如何?”
那送信人说,“不瞒公子说,就这一时看不出来什么,不过我们会认真盯着这些人,防止他们趁虚而入,叨扰沈府。”
何子敬手托下巴问道,“你看能不能抓个舌头过来盘问一下?”
送信人说,“那我去试一下,不过看他们警觉性很高,唯恐不能得逞。”
子敬说,“莫急,你去找买宵夜的人,然后…”子敬在那人耳边低语了几句,那人连连点头,然后就下楼出去了。
且说颜宗也同样收到消息,他也找了一个较高的暗处观察子敬的人,他也看不出什么端倪,只是叮嘱送信人小心地方去,加强戒备,然后就回山水画廊去了。
且说接了子敬口令的那个人,快步走到沈府门口约五十步的一个夜宵摊位,那时候已经掌灯了。他坐在摊位前点了一碗馄饨,自顾吃了起来,而那“摊主”则吆喝着说“不花一文钱,酬谢新老街坊”的话,以此来吸引过往的路人。摊位前徘徊的那位武士闻着醉人的香气,难免吞咽了几下,那“摊主”马上把这武士拉到了长椅上坐了下来,随后就上了一碗馄饨给那武士。那武士吞完一碗之后,便趴在了桌子上,“摊主”示意几名游侠把他抬到了子敬面前。
一瓢冷水泼下去之后,那人清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这位公子,小民哪里得罪了您?还请您格外开恩,小民上有高堂下有妻房,您就放了小民吧。”
子敬笑嘻嘻地问那人,“在小爷面前就不要撒谎了,说实话吧,谁派你们来的,目的何在?”
那武士依旧辩驳,“这位公子,您真的误会了,小民乃一介屠夫,哪有什么人派我来?我此刻正要回家,看见馄饨酬客,贪吃才会被下药,让你们抓了来;试问倘若真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小民一定会十分警惕的。”
何子敬朝旁边的人挨了一个眼色,旁边的人便端上来一碗羊奶和一只小羊,有一个人脱掉那武士的鞋袜,在脚底抹上羊奶,然后让那小羊去舔。开始那武士还承受得住,但是那挠心的痒让他忍不住地笑,过了约莫半个时辰,他实在受不了了,只好招认他是奉了主人的命令来保护沈府的。
子敬问道他们来自何处,受何人的命令,那人缄口不言,任凭小羊如何****,那人始终不吐露半个字,即便已经笑得岔气,始终不再说话。子敬也实在无法,只好说,“既然人畜无害,那就暂且放你出去吧,你只需要记住,我既能放你,也能再度擒你。”
那人问道,“工子既然如此气魄,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在下也好跟我家主人有个交代。”
何子敬几乎想都没想,“小爷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云水居何子敬是也,回去告诉你家主人,如果我们目的一致,就精诚团结;胆敢生事,休怪我辣手无情。”说这话的时候,子敬的眼睛里发出了凶狠的光芒,一向温驯如羔羊,和气如流水般的何少爷今日如此紧张,也不知究竟为了哪般。
那人被解了绳索之后,报了个拳便下楼去了,然后很快就有人把这个事情告知了颜宗,他很是诧异道,“这位何少爷为何如此疾言厉色?久闻这位少爷脾气最和顺,言语也是清流如溪,从来没红过脸的,怎的今日改了性子?”
那送信之人说道,“大皇子,属下听闻中原有句话,叫做'关心则乱'…”
这句话提醒了颜宗,他自言自语道,“这似乎不大可能,他们才见面两三次,莫非是看着明轩的情面?他向来是不愿得罪权贵的,更不愿意插手这些不关己的是是非非。”
那送信之人看着颜宗的自说自话,“想那沈府要保护的是何等人物?竟然让爷这般惶恐不安?”
颜宗并未回答他的问话,只说,“你暂且回去吧,密切关注出入沈府的人,发现可疑立即来报。”
那人领命便回到自己位置去了。
而此刻在沈园中的玥儿却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她跟初桃两个人在一起一边下棋,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她此刻并不担心自己会被强娶,她选择了相信何子敬的本事;她担心的是父兄的安危,也不知道此时兄长是否已经到了上京。她忽然又想到救了自己的那位少侠,虽不是十分俊美,却也是“双目朗日月,二眉聚风云。”那人说要教授玥儿武艺,可是她连人家的来历都不甚清楚,就贸然答应了,也太轻浮了些。玥儿还想到了颜宗,也不知道他说能帮忙搭救父亲是否只是客套言语。
她就这样东想西想,走错了好几步棋,当他看到初桃的棋子包围了自己的棋子之后,她推了一把那棋盘上的棋子,“不下了,心中烦闷,再怎么下棋也还是输。”
初桃知道玥儿的诸多心事,想要宽解她,“小姐放心好了,若实在苦闷可以去找姚姑娘呀,只是今日太晚了,明日初桃陪你一起如何?”
玥儿抿着嘴,一言不发,初桃又说,“小姐,听说大相国寺的菩萨很灵验,不如我们明日去拜一拜,祈求菩萨保佑老爷和少爷平安归来。”
玥儿听到初桃如此说,看着她还是不说话,初桃便继续说道,“都说救苦救难观世音,慈航普渡有缘人,小姐何不去试一试呢,心诚则灵。”
玥儿终于肯开口,“那好吧,只怕菩萨要管的事情太多,无暇照拂到每一个善男信女呀。”
初桃说道,“小姐不去试一试怎知不灵验呢?”
玥儿答应之后便回屋休息了。
第二日卯时,玥儿就起床了,她拿了宝剑在沈园的那片空地上练了起来,初桃贪睡到辰时才出来,看到练剑的玥儿,说道,“小姐怎的今日如此发奋?用完餐点就该去大相国寺了,您看今日天气晴好,莫要辜负了。”
玥儿收了宝剑,“好,倘若早日发奋也不至于受辱,唉。”她回房梳洗后,简单吃了一点,便和初桃换了男装出门了。
她此行并未骑马,也没有坐车,而是携了家丁,乘了一乘轿子,初桃跟在旁边,她之所以如此是想让自己安心些,人多势众她也不必太担心。他不能为父兄分忧,保护好自己也是对父兄最好的慰藉吧。
她们主仆出门后,那些暗中保护的人也有几个跟着一起去了大相国寺,其中既有颜宗的武士,也有子敬的江湖。到了相国寺之后,玥儿跪在佛前虔诚祈祷,祈求菩萨保佑父亲无恙,保佑兄长顺利抵达,更保佑二人无虞归来。
且说这一日来大相国寺参拜的,有一个人不得不说,那就是“赵公子”。他与玥儿几乎是同时到的观音殿,参拜完上香的时候,二人才发现了彼此,都有点惊异。那赵公子今日穿了一身紫色衣袍,头上依旧是攒金珠的束发冠,黄色垂绦,脚踩粉色厚底朝靴,腰间换了苏绣的香囊和浴火凤凰的玉佩。
还是赵公子先开口了,“我当是谁,原来是沈家公子?可是做了亏心事,求菩萨保佑不让鬼敲门么?”
玥儿冷笑一声,“赵公子莫不是也有同样的顾虑?”
赵公子并未回答,上完香便走出了观音殿,玥儿也一道走了出来,她想起上次在樊楼,虽然有些不愉快,可也没有不欢而散,今日相见,她也想跟人化解尴尬,尤其那赵公子的声势,更是常人所得罪不起的。不一定多一个朋友,少一个对头总是好的,于是便作揖道,“上次跟赵公子有些误会,因为某些不得已的原因,没有与赵公子多谈,今日既然同来佛家参拜,也算是有缘;且今日日丽风清,若不乘兴同游,当真是少了趣味。”
那赵公子见玥儿如此说,马上变得和颜悦色,“沈公子既如此说,那本公子就与相公找个清静少人的地方,好好叙一叙。”
那赵公子依旧是带了一帮跟班,她乘的是一顶黄缎软轿,银顶黄盖红帏,每个角上各有黄色流苏穿着珍珠垂坠下来,抬轿子的人也有十几个,周围各有骑马武士护卫,好大的声势。玥儿的轿子在那顶豪华的轿子面前,显得卑微极了,不过这并不影响玥儿的心情,毕竟人与人还是有差别的。
赵公子一行人在前,玥儿和初桃几个人在后面,他们从大相国寺的前门一直绕行到后门,那里有一片松林,一条僻静的青石板小路一直通向松林深处。那赵公子下了轿,只带了四位武士一起,其他的仆从都在原地待命。他去喊了玥儿和初桃一起,一行人沿着小路朝着松林深处走去。
阳光透过松树的间隙,斑驳地投射到小径上,大家都不说话,只是感受着那份静谧,石板路上有些干枯的松针,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偶尔几声鸟啼,拐过几道弯之后,只见一泓清泉直泻而下,一潭碧水深邃幽静,玥儿不禁吟诵道,“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原来真有如此禅意的所在。”
赵公子道,“更有禅意的还在前方。”
那碧水小潭的边缘,一条长长的索道桥,走在上面仄仄的,听着流水潺潺,瀑布声声,深呼吸一口深林中略带潮湿的空气,那清爽的感觉,让人心旷神怡,宠辱偕忘,其乐何极。走过那索道桥,前面一座小山,一条石阶路沿着山脊修建,拾级而上,便可看到山顶的一座亭子,走近一看,“一览亭”三个大字刻在一面鎏金匾额上,落款是一个奇怪的符号,那三个字“天骨遒美,逸趣霭然”,有点像黄庭坚,可是又仿佛褚遂良,但是这字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玥儿感叹道,这三个字精妙,笔锋飘忽快捷,笔迹瘦劲,至瘦而不失其肉,如屈铁断金,好字。”
那赵公子微微一笑,“书写这字的可是天下仅此一人,再无第二,沈公子颇懂文墨,这字的精髓竟全让你说中了。”
玥儿拍手叫好,“的确好字,一览,顾名思义,取自杜少陵的《望岳》,不过用在此处似乎不大合适。”
赵公子快步走到那亭子里,“沈公子所言差矣,此处虽不是“一览众山小”,却也可以尽观泗州繁华,东京的街巷尽收眼底,秋日登高,把酒临风,其乐何极?”
玥儿登上那亭子,看着眼底的情景,连连点头,“赵兄所言不虚,不才境界差了许多,这字也是颇有风格,不知出自何人之手?”
赵公子坐在亭子里的石凳上,“天下一人呀,哈哈哈哈。”
玥儿不明白这“天下一人”是何意味,便追问道,“'天下一人'是何人?”
赵公子摇开扇子,“佛曰,不可说,不可说。”
玥儿见他如此说,心里嘀咕着“故弄玄虚”,便不再多问下去。
赵公子遣了那几个家仆留在亭子外的石板路上。玥儿也把初桃留在了那里。
玥儿说,“此地风景甚好,可惜无酒无茶。”
赵公子说拍手三次,便如魔法一般,有几个家仆从亭子的另外一侧端了茶盏过来,玥儿不得不感佩这赵公子的能力,虽然谈不上呼风唤雨,却也是遇水乘船,她不禁开始猜测这赵公子的真实身份。
有一位家仆留下为他们斟茶,其余的就留在其他家奴守候的地方。
玥儿的好奇心驱使她问道,“赵兄如此排场,每出门便前呼后拥,看兄台所乘软轿也是斐然,不知赵兄府上?”
赵公子品了一口茶,并没有回答玥儿的话,而是说,“让沈公子见笑了,每次出门总想随性一些,无奈家兄始终不允,只好带了这一众家奴,不为别的,只为家人安心。”
玥儿很赞同,“不瞒赵兄,愚弟以前出门也是十分随性,可是最近琐事缠身,且那一日在樊楼赵兄也看到了,那张衙内死死咬住我沈家不放。如今我父兄皆不在东京,我出门便多带了几个人,也是为了让家人安心。”
赵公子询问道,“张衙内?可是那一日言语放浪的无耻之徒?”
玥儿点头,“正是,他是当朝太宰大人的三公子。”
赵公子做了明白的姿势,微微颔首,“不知沈公子如何惹得上这样的人呢?”
玥儿说道,“赵兄不必沈公子长短地喊我了,您喊我明玥即可,与那张衙内的恩怨说来话长呀。”玥儿就把汴河斗恶少以及张衙内要强娶沈家小姐的事情说与那赵公子听,当然并未提及自己是那沈家小姐。
赵公子边听边颔首,“原来如此,那沈家小姐莫非就是令妹?想来定是窈窕淑女,否则怎会引得那张衙内垂涎三尺呢?”
玥儿摇摇头,她叹了口气,“兄台莫要取笑,沈家小姐的确是舍妹,姿色平平,庸脂俗粉,就是因为愚弟多事,才惹下如此事端。”
赵公子说道,“明玥,你也不必唤我赵公子了,喊我永福即可,你的苦恼我已然尽知,那张恶少着实可恶,但是明玥家里似乎也不应该畏惧权贵,我看你的装束不输王公子弟呀。”
玥儿自己打量了一下自己,“永福兄说笑了,这只是普通家庭出身的少年郎罢了。”
赵公子摇摇头,笑着说道,“普通人家的少年郎又怎会引得当朝太宰公子的注意?我可是听说城里有位沈万里老员外,富可敌国,可是令尊?”
玥儿没想到父亲的名号竟然蜚声京城,她不知道面前这位赵公子是否有恶意,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要承认自己就是沈家的后辈,她犹豫着不说话。
永福看出了玥儿的顾虑,“既然贤弟不愿回答,为兄也就不多问了,为兄也是有所保留,不怪贤弟多心。”
玥儿赶忙补充道,“不是明玥不愿多说,我的确是那沈翁之子,只是如今父亲在北地深陷险境,生死不明;家兄去营救数日,杳无音讯,明玥实在不愿横生枝节,惹人侧目了。”
永福道,“贤弟放心,为兄不是多事之人,你父亲既在北地,为兄想帮忙亦是鞭长莫及,只是贤弟放心,你在东京城,我保你平安,今日之后,那张衙内定不敢再滋事。”
玥儿感激道,“多谢永福兄关心,何公子看在与家兄的情分上,已经派了人暗中保护着沈府,愚弟觉得安心许多。”
“哦?可是那开封府尹何栗大人之子何子敬?”赵公子很是惊诧。
玥儿点头,永福哈哈大笑道,“看来那沈家小姐一定是倾国倾城,才貌无双,否则这位'去次花丛懒回顾'的京城浪子怎么会如此主动?”
玥儿不明所以,“永福兄所言何意?”
永福又饮了一杯清茶,“何意?贤弟真看不出来么?那何子敬也拜倒在令妹的石榴裙下了。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为兄瞧着贤弟若是女儿身,定是位眉目如画的佳人。”
玥儿听到永福如此说,脸上泛起红晕,“永福兄不要打趣小弟了,我怎么可能是女子呢?我看你口如朱丹面如润玉,英姿飒飒,倒像极了木兰。”
永福听完哈哈大笑,“贤弟真是巧舌如簧呀,今日你我能再次相见,可谓有缘,不如咱们以天地为证,义结金兰如何?”
玥儿欣喜道,“能与永福兄结为兄弟,实乃沈明玥三生有幸,承蒙不弃,小弟十分愿意。”
于是两个人便在这一览亭上,对着天地神灵,结为了生死“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