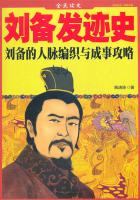因为当偶尔透射进密林的阳光开始大幅倾斜后,所有人都意识到当前的境况正如这位临时头领所言,队伍很有可能无法在当夜回到聚落,而潜藏的敌人也已瞄准这支容易溃散的组织。
一路众人行色匆匆,前列的灰狗与格根冷静而迅速地收纳沿途所有讯息,调整队伍的前进方向,树木、茅草、岩石被他们抛在身后。哪怕零星倒在地上的尸体,无论形体再如何怪异,也只是耽误他们一息时间,便会被诃伦叫喊着鞭策进程。
一走起来,风在耳边刮过,就好似有无数猛兽在后面驱赶吼叫,众人不敢耽搁。无论是滚兽群抑或是其余什么怪物,都能轻而易举剿灭他们,所有的猎人与战士就会沦为猎物,供这个丛林玩乐。
但队伍接下来的行进迅速,众人又都放下心来,只等着孛儿帖的大篝火豁然出现在眼前。
约摸一个时辰的时间里他们都曾满怀希望返回卓力格图与埠人身边,直到暮霭弥漫扩散进林,朦胧中与数天前向着西南面出猎的残部偶遇。
西南面的队伍早已混合,而此时与诃伦一行相遇仍着实吓得兵戎相向。残部的原人在头与胸膛围上编织的草圈,蹲在一处中心被虫蛀空的树洞中,如一块块长满青苔的岩石般一动不动。当诃伦一行经过时,他们拔出武器向这边冲来,却在近处猛然定住,丢去武器,开始激动地呼唤这第三支队伍里熟识的人的名字。
更有一个人,夹杂在人群里向格根呼喊。
前一息尚在安慰众人的扎昆·诃伦一拳将西面队伍中的蒙根打在地上,回身用乌仁图娅刀指着哥哥格根。突然之间的事故,西南面的埠人大惊失色,可显然他们已经失去头领,顿时如同受惊的鸟群散开,盯着场中央陌生却令人敬重的战士。
“莫怪我领导无方,看看这两兄弟,还想怂恿队伍里的埠人讨伐我。”他大吼着咒骂卓力格图,全然忘记了是自己接下了这个担子,也彻底忘记了证明狼群存在的初衷。他对地上的蒙根骂道:“蠢货,跑的可比野马还快,让我们一通好找。当所有人为你的失踪焦头烂额时,你躲到了别人的队伍里打算从容地返回孛儿帖?”
蒙根擦着满脸鲜血,鼻口皆是腥味。他感受到熊皮战士较之首领不遑多让的气力,胸膛里不可遏制的凶性燃烧而起。
寻得弟弟的格根,远没有那样猖狂的凶性,尽管诃伦那柄锋锐的刀直指着自己的头颅,但他仍没有动弹,而是双手远离腰胯,微微颔首对有些脾气的诃伦表达心中存在的过错。“蒙根!”他见自己的兄弟偷偷从地上跃起,手里的斧子正袭向诃伦!
诃伦回头一看,退回格根脖颈前的乌仁图娅刀,转身将它斜挡在手斧上,只听“吭啷”一声,斧子应声分裂为三,摔在地上。一阵短促的直呼,蒙根见袭击失败,向后连忙翻去,还未回身,便被一脚踢倒。
诃伦的刀重指格根,并喊额尔德穆图。年轻猎人穿过统统围拢过来的人群,朝倒地的蒙根飞奔去。地上是一条蜿蜒的血路,一直连结到蒙根,当额尔德穆图俯身检查他的伤势时,终于呕出一大滩鲜血。
“扎昆·格根,按照原人的惯例,我早该将你们格杀,可我没有。”诃伦将尚存理智的哥哥格根唤醒,他收回乌仁图娅刀入鞘,在灰暗的林间一边审视面容疲乏的另两路队伍一边正色道:“你看看这些西南面的残部……”
“怎么样?”那边猎人的关切没有收到回复,被蒙根用力搡开手,这位扎昆像一头受伤的黑熊在暴怒。他活动开全身筋骨,打算重新起来一战。
孛儿帖光荣的战士,绝不应该输给一个部落的叛徒。他怎可能让自己在半个支埠原人的目光下忍受一拳之辱,然后等待漫长的半月,旁观部落的战士前来将诃伦捉拿归案?四周幽暗的天幕已降下,惟一的光源似乎是蒙根眼中燃腾的火光。此刻急躁的情绪消失不见,他逐渐冷静,却不顾额尔德穆图的劝阻,一步一步向对他放松警惕的诃伦走去。
一股如蛛网般的烟雾从诃伦与格根之间的缝隙里渗出,惊得蒙根连忙止步,他看见两人的手里分别紧握自己的武器,却并没有互相厮杀,隐约察觉出一丝非常。
再看诃伦,他嗅着携带腥味的烟雾,显得忧心忡忡:“这烟雾我似曾相识。”
“是孛儿帖南面的鹿木林迷雾。”西南残部里的一个魁梧的老战士突然哀嚎起来,他跑向自己的队伍,像一个得了失心疯的公牛,原人同侪们纷纷拦住了他,可嘴里仍止不住的邪论。“我就说这辈子都走不出去了,大丛林中了邪!”
诃伦闻言撇下格根,暂且不管面前飘来的烟雾,大步向那个须发泛白的老战士走去。
格根疑惑地望着朝他靠近的弟弟,方才的话,在场二十余人都听个分明。既然蒙根一直跟随残部的人,想来也该知道那名老战士疯话的缘由。
“哥哥,我忍不了这扎昆·诃伦。”蒙根接近兄弟才发现,烟雾是从北面向这边弥漫而来。
“忍不了又能如何,你没看到现在二十余人几乎听命于他。何况在这里起争执,回头卓力格图拿我俩是问该怎么办?”
“也对。”蒙根听了哥哥的忠言,只好暂压心头火。
格根见三四名西南残部的孛儿帖人正三言两语向诃伦比划之前所见,接着便问弟弟:“那个老头说林子中了邪是怎么回事?”
“鬼知道这几个蠢货带的什么路。”蒙根凑到兄弟的耳边说道:“我跟着他们向北返回孛儿帖,已经走过一遍鹿木林,如此看来,我们一直在原地打转。”
“应该不怪西南领路的人,我和灰狗带路,扎昆·诃伦殿后,也同样迷失了。”格根道:“而且,以路程和时间算,鹿木林应该还有好一段距离。”他只觉得事情越来越扑朔迷离,仿佛被一层雾霭笼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