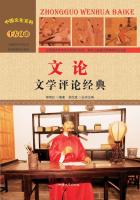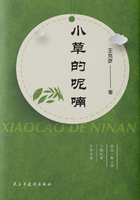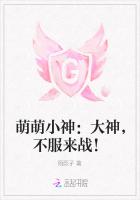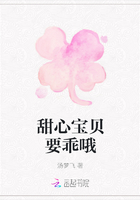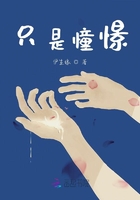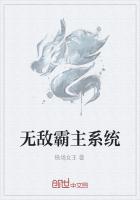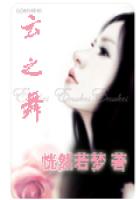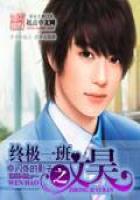一
郑利华先生在《复旦学报》今年第2期上发表的有关中国近世文学开端的讨论,我觉得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深入研究很有意义。由此联想到与之相关的中国中世文学的开端问题,似乎亦有值得讨论的地方。现在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将魏晋作为中世(或中古)文学的开端,而这种做法又似可追溯到刘师培所著的第一部以中世文学为叙述对象的断代文学史《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 年初版)。此说一个最主要的依据在于,无论从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发展来看,魏晋都可以说是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始,从这一时代起,文学逐渐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与伦理的要求,其抒情、审美功能逐渐得到真正的认识。这样一种判断,作为对于中国文学在魏晋以来之发展的评估无疑是深刻而切近其本质的,它经过铃木虎雄、鲁迅等富有识见的学者的阐发,已经成为我们今天文学史研究普遍认同的一般知识。但是,若遂而据此将魏晋作为中国中世文学的开端,却是存在着问题的。
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史有关上古、中世(或中古)、近世(或近古)的历史分期法,是通过明治时代日本的中介影响,借鉴了欧洲历史的分期标准。据汤因比《历史研究》,最早按“古代希腊社会内部无产者的残余看法”,历史只有“古代”和“近代”,大体上同《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的时间,或公元前、公元后的时代。十五世纪中后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首次使用“中世纪”一词(拉丁文Mediumaevum,意为“中间的时代”),用于表述西欧历史上从五世纪后期罗马世界帝国瓦解到人文主义者正在参与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一阶段,于是西方历史开始有了“古代”、“中世纪”、“近代”三个时期的划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历史时期的概念,自其诞生之日起,就蕴涵着介于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与这种古典文化之“再生”(Renaissance)———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这两个黄金时代之间的“黑暗时代”之意义。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它在文化上就被置于与前后两个时代的文明对峙的地位。十八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又再次强化了这样一种意义,差不多在二十世纪以前,这种观点一直是西方学术界的主流看法。
在这样的历史构架下,作为古典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古希腊罗马文学,历来被视作是一种比较自由、开放、富有生命力的文学,无论是史诗、神话、戏剧、抒情诗等,都洋溢着一种对人的尊重的文化精神。如马克思评价希腊艺术和史诗,是人类童年时代“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因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但从中世纪开始,人们的精神世界则普遍地被神学所笼罩,雅各布·布克哈特如下一段说明其时理智蒙昧的描述,常常为其后的研究者所引用:“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这个时期的文学,姑且不论其宗教文学,即便是世俗文学作品,也常常具有一种比较收敛的、以神的名义对人加以种种压抑的特征。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正是以将人性从中世纪神性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为使命———从薄伽丘的《十日谈》可以看到,他是以个人的自然情欲、现世幸福,人自身的自由、价值与尊严,来对抗宗教的禁欲主义与神权,从而宣告了近代社会的诞生。
我们再来看魏晋文学。魏晋文学所具新的思想与文学价值,在中国是五四以来才被发现的,当时的学者在欧洲人文主义思想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强烈的影响下,建立了新的文学标尺,这也正是鲁迅所说的“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刘大杰在二十年代后期撰成的《魏晋思想论》,集中体现了这样一种新的发现。他指出:“魏晋时代,无论在学术的研究上,文艺的创作上,人生的伦理道德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便是解放与自由。这种特征,与其说是自然主义,不如说是浪漫主义。”(第二章)“在中国的政治史上,魏晋时代无疑是黑暗的;但在思想史上,却有它特殊的意义和价值。魏晋人无不充满着热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他们在那种荡动不安的社会政治环境里,从过去那种伦理道德和传统思想里解放出来,无论对于宇宙、政治、人生或艺术,都持有大胆的独立的见解。”(前言)他将之称为“人性觉醒的思潮”,并认为魏晋人的人生观,正是在汉代通行几百年的儒家修身主义思潮的反动(第五章)。五十余年后,李泽厚又重新提出这一概念,指出魏晋文学中突出存在的“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并认为“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
如果我们将五四以来学者按西方的“文学眼光”所发现、并为今天普遍认同的魏晋文学上述特征与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基本特征相对照,就会发现两者的情形恰好截然相反;既然我们是以西方历史的分期标准为参照,则拿这样一种“解放与自由”的文学作为应该以压抑、衰退为主导的中世文学的开端,我个人认为是不甚妥当的。倒是上述两位学者都提到的汉代,显然有着与欧洲中世纪相对应的文化特征。
诚然,论者会说,现代西方历史学研究早已突破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学者对于中世纪黑暗的描述,中世纪文化的积极意义正在被日益发掘出来,既如此,以魏晋为中世文学的开端又何尝不妥。但问题在于,随近代西方历史主义兴起逐渐展开的对于中世纪的重新认识,是基于强调历史发展之连续性的历史观念,他们所关注的焦点是中世纪社会如何持续发生变化,从而孕育发展出以理性与科学为主要特征的欧洲近代文明。这种相对更为辨证的历史考察,并非是要一笔抹去中世纪宗教文化的传统及神学对文化禁锢、压抑的一面,而是要从其自身的变化中寻找它与近代文化精神的内在联系。在我看来,这不正是魏晋文学处于中世文学之中,经六朝、盛唐而变化、拓展,向着近世文学曲折地演进的理由与意义吗?
二
在明治时代的日本所诞生的最早一批中国文学史著述,已经比较普遍地采用了上古、中世、近世这样三分或上古、中古、近古、今世这样四分的历史分期法。如儿岛献吉郎发表于1891—1892年的《支那文学史》,虽仅由夏商迄于周末,但此为第一编,标为“上古史”。其“总论”述时代区分,第一期从太古至秦,第二期从秦汉以来至唐,第三期从宋至清,第四期为清。其约发表于1894年的《文学小史》,时代区分基本同上,分别为上古(文学创立至秦焚坑),中古(至唐初),近古(至明灭亡),今世(清世祖即位至今)。此种见解在其以后刊行的《支那文学史纲》、早稻田大学讲义《支那文学史》中亦基本不变,惟明确将秦文学归入上古文学,唐文学归入近古文学。藤田丰八早大讲义《支那文学史》
撰于1895—1897年,第一期“古代文学”自三代至秦,第二期“中世文学”未完,仅迄东汉。在其刊行于1897年的《先秦文学》“序说”中,专设“时代的区划”一节,拟将整个中国文学史分为古代文学(上古至秦),中世文学(汉、魏晋六朝、唐、宋),今世文学(元、明、清)。他如高濑武次郎《支那文学史》作如下划分:上古期,唐虞三代以下至春秋战国时代;中世期,秦汉以下至唐宋;近世期,宋以下至现今。久保天随1904年由早大发行的《支那文学史》分为上古文学(三代、周末包括秦),中古文学(两汉、魏晋、六朝),中世文学(唐、宋),近世文学(金元、明、清)。明治末期早大出版的松平康国讲义《支那文学史谈》则作———上世(唐虞三代、春秋、战国),中世(秦、汉、魏晋六朝、唐、宋),近世因篇幅而搁笔。
综观这些文学史的分期,无论三分、四分,其所划定的中世文学之开端,非秦即汉,近世文学开端则在唐、宋、金元三者之间。
直接受其影响,中国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只要是采用这类分期法的,大都不出上述界域。如曾毅1915 年初版的《中国文学史》,实为儿岛献吉郎《支那文学史纲》的编译、改写,分期全然相同。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分期为:上古文学史,邃古至秦;中古文学史,自汉迄隋;近古文学史,自唐迄明;近世文学史,前清以来。周群玉1928 年出版的《白话文学史大纲》共分上古文学(黄帝以前至秦)、中古文学(两汉至五代)、近古文学(宋至清)、中华民国文学四编。欧阳溥存193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亦分为上古(唐虞至秦)、中古(两汉至隋)、近古(唐至明)、近世(清)四编。故郑振铎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言”中,曾对近二三十年来,“他书大抵抄袭日人的旧著,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及近代的四期,又每期皆以易代换姓的表面上的政变为划界”,表示不满。
所以这样或那样划分的依据与构想,大部分著作皆语焉不详,宫崎繁吉说历来史家是“唯从其便宜以为标准”,郑振铎也宫崎繁吉《支那近世文学史》“例言七則”,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年不详。
指出中国早期这种分法的文学史“没有什么详细地说明这样分法的道理”,多少显示出西方的历史分期法东渐移植的初始状况。而且,最早一批中国文学史著述在文学观上确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由学术、辞章之传统概念向与Literature相对应的“文学”概念的转化,难免会使历史时期的划分标准显得驳杂不纯。
然而,这样一种界限不甚清晰的文学观念所致之标准未尝没有合理的因素,更何况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学者力图从比较纯粹的文学观出发,来考察中国文学历史的发展过程及时代性特征,如久保天随针对此前文学史著作“不问思想,只是诠索外形”、“详其发达、变迁之迹,不是使之为生命有机体,不过是一个个作品的各个胪列”的根本缺陷,强调根据“艺术以形式与内容之调协为最上乘”这一根本性原则,“新编出一部真正的中国文学史”;儿岛献吉郎则在其《支那文学史纲》中已试图辨明“学术界之时代观与文学界之时代观不必一致”,并勾勒出文学与学术两套有所区别而又可相互参照的历史分期。这表明他们在文学史观上已经有了比较自觉的思考。
真正在中国历史分期上构成成熟的体系性阐释,是中国史研究领域为人所熟知的内藤湖南之“中国史三区分说”,学术界因之称为“内藤假说”。简括说来,他是“从中国文化发展的波动来观察大势,从内外两方面进行考虑”,以殷盘庚前后至东汉中期为上古时期,东汉后期至西晋为上古向中古的过渡阶段,东晋至唐末为中古时期,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为中古向近世的过渡阶段,宋元明清为近世时期(参见《支那論》、《概括的唐宋时代観》、《支那上古史》、《支那近世史》、《支那中古の文化》诸篇,分别见收于《内藤湖南全集》第5、8、10卷)。这一学说对于包括中国文学研究在内的整个日本中国学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吉川幸次郎在一篇题为《三区分说杂感———内藤博士的中国史观》的文章中,就说自己对这一分期说推服不已,称之为“不磨之说”,并在1948—1950年于京都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时予以借鉴,其专门探讨中国文学史时代划分的一个章节,将周到前汉末的文学称为古代文学,后汉至北宋中叶的文学为中世文学,宋到民国六年的文学革命为近代文学。
基于“京都学派”创立者的中国学研究区别于传统汉学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要从中国的价值基准而非日本气质出发来加以考察,吉川幸次郎认为自己与内藤湖南见解相一致的地方在于,这样的分期依据了中国宋以后哲学史上的常识与文体变迁的常识。从哲学史上来说,据“道统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经孔子集其大成、孟子予以正确地祖述,为古代的光荣;以后千数百年失传,陷没于中世的黑暗;至北宋周敦颐、程颢兄弟,迎来文艺复兴,为复活古代的近世。从文学史上来说,先秦至前汉,是“古文”即非对句文体的时代,为古代;后汉经六朝至唐,是“骈文”即对句文体的时代,为中世;唐中叶韩、柳为先驱、北宋欧阳修、苏轼完成的非对句“古文”文体的复活,发展为近世。
不过,与此同时,吉川氏在以汉武帝、司马迁、司马相如等为个案,开展对汉代文学之深入研究的过程中,于中国历史分期的认识已有所修正。撰成于1948 年的《论司马相如》一文提出:
“汉武帝以前的时期,即公元100 年以前的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古代;武帝以后,至唐宋之交,即至公元900年前后,是中国历史的中世;宋以后,至本世纪初叶的民国革命,是中国历史的近世。”1949年为“岩波新书”所撰《汉武帝》(同上)一书,又重申了这样一种分期。其理由首先在于,他认为“最能显示汉武帝时代是一个历史转变期的,是在这个天子的时代,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并且,这“成了此后二千年中国精神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最明显的外廓”。其次,“与整个历史的转变相应的,是文学的历史,也在这个时代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那就是发展起了高度修辞性的辞赋文学及散文的美文文体。他进而指出,在武帝时代,儒学的确立与文学的确立是同时产生的,“但两者间并不仅仅是并行的关系”。应该说,“儒学的确立是文学确立的重要条件”,他以司马相如的文学创作为例,说明其“在当时的意识里,是作为儒学实践的一部分来进行的”。由此,他一方面从“儒家把修辞性语言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加以承认乃至支持的态度”,肯定“儒学的确立对于文学的确立是自觉的原动力”;在另一方面,也明确揭示出,“武帝时代儒学的确立,把后来的中国人的思想纳入了儒学的轨道,阻碍了文学精神的自由发展,在这一点上,是中国文学史的祸害”。
有关吉川幸次郎在深入研究汉代文学及历史的基础上,将汉武帝时代作为由第一期(古代)向第二期(中世)转移之切点的思想历程,在其1967年为《全集》第6卷所作的《汉篇自跋》中有总结性的说明,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时代划分问题上朝着更接近文学自身实态方向的进一步探索。
至1966年,吉川幸次郎为新潮社《世界文学小辞典》撰写《中国文学》,又一次将中世文学的开端向前作了推移。他将中国文学分作四期,第一期,秦以前,所谓的“先秦”时期;第二期秦汉至唐中叶(8世纪前半);第三期唐中叶(8 世纪后半)至清;第四期,本世纪初“辛亥革命”及与之相应的“文学革命”开始的现代。这一所谓“一千年分期”法又见于他的《中国文学史序说》,此稿估计是1947 年左右的讲义,稿中即将第二期称作“文学史上的中世”。这位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大师级学者,晚年在文学史分期问题上重又采用以前的看法,这件事本身是很值得玩味的。在《中国文学》一文中,作者从社会政治背景、文化特性、文学的表现功能及艺术形式等诸多方面,整合性地描述出中国文学历史的阶段性变化。虽然,限于篇幅与体例,未展开何以将秦汉作为中世文学开始的解说,但从其叙述中可以看到,这种划分是在上述以汉武帝时代为分界线的同一框架、同一理路上进行的,只不过他在这里已经充分注意到了作为古典时代的先秦与秦始皇大帝国以后的时代那种特别的差异,以此作为划分古代与中世文学的界限或许更为精确。作为与之相关的依据,吉川氏在发表于1961年的《〈诗经〉与〈楚辞〉》一文之第二小节“作为文学史史前时代的先秦时代”中,从五个方面对秦始皇以前与以后的时代差异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该文收入《中国诗史》,可以参看。
回顾中国文学史这一学术体系自明治时代受19 世纪欧洲国别文学史的影响而建立以来,有关时代划分认识在日本的发展,我觉得,吉川幸次郎基于对中国文学历史本身的实证性研究所形成的自成体系的阐释是富有借鉴意义的。就中世文学的开端而言,从其举述的种种理由出发,无论是以汉武帝时代抑或秦汉作为分界线,比起前述从魏晋开始划分的分期来,都是一个更为合理的看法。
三
依我个人的想法,我认为以秦汉作为中世文学的开端,应该更切合整个中国文学演变的实际状况。其理由如下:
先秦文学与西方的古代文学相比,虽然更强调政治与伦理的内涵,更重群体而克制个人的欲望,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却还是一种相对比较自由的文学。我们看《诗经》的所谓“变风”、“变雅”之作,无论是《魏风·伐檀》及《硕鼠》讥刺统治集团中人的不劳而获与贪婪成性,《秦风· 黄鸟》揭露统治者以贤臣殉葬的暴行,还是《小雅·何草不黄》怨恨西周政府将“下国”百姓如野兽一般驱使,都表现出了对时政比较激烈的批判。至于《楚辞》中的作品,不但如屈原的《离骚》、《九章》诸篇呈露出对现实政治、对“党人”较强的批判性,或“对特异环境的反抗”,其炽热、沉痛之感情的抒发亦是那么强烈;即如宋玉的《九辩》,也有对“时俗”及个人遭际相当大胆的不满,所谓“贫士失职而志不平”。
而到了秦始皇的时代,随着中央集权的专制独裁政体的建立与极端文化统制政策的推行,我国历史上最为酷厉的思想黑暗时期出现了。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大都注意到了自这一时代开始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这种裂变,如古城贞吉在总括出“中国文学最著者,为儒教主义之发展”的特点的同时,指出秦汉之际“为学术古今之关键。”高濑武次郎《支那文学史》也说:“至秦造成了中国文运的一大顿挫。”曾毅《中国文学史》在《秦之文学》这一章中,对儿岛献吉郎原著作了较大程度的改写,他揭示说:“夫始皇之统一学术,与汉武之表彰儒术、罢黜百家,其用意何尝不同?”复又申论道:“学而至于秦,战国思想活动之一大结束也;亦学而至于秦,汉以后思想略开一新生面也。”然而他们在具体讨论秦代文学时,却要么略而不论,要么仍取旧的价值标准,以“辞藻瑰丽”来评价李斯的《谏逐客书》,以“苍劲峭质”来评价诸石刻(参见曾毅《中国文学史》该章,与儿岛氏《支那文学史纲》略同)。其实,秦代文学同样鲜明地表现出与先秦那种相对比较自由的文学的离异。就拿多出李斯之手的刻石铭文来说,充斥的只是歌功颂德这一种声音。试举二例:
皇帝临立,作制明法,臣下修饬。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黎,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祇颂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著明,陲于后嗣,顺承勿革。皇帝躬听,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泰山刻石》)
维廿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菑害绝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之罘东观刻石》)我们看到,铭文中竭力宣扬秦始皇并一海内的文治武功以及如何圣聪勤政,所要表述的无非是从臣的效忠之心,这种一味取悦君王、唯统治者意志是从的作品,何尝有一丁点儿的自由可言!
在汉代文学中,除了像司马迁这一种已被打入另类的人的作品外,我们也已看不到《诗经》中“变风”、“变雅”那种虽出自于群体利益、而敢于批判时政的精神,看不到《楚辞》中那种强烈的感情与反抗现实的精神。汉初社会虽说比起秦来,在文化上的统制要稍显宽松一些,如惠帝时即废除了“挟书之禁”,又汉兴以来60余年间采用黄老思想治国,然秦作为一个大一统帝国的政治形态基本上被延续了下来。从当时士大夫在思想上表现出来的收敛、退守倾向来看,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实质上并无多大松动。汉文帝时的贾谊,向来被认为与屈原有相类似的政治遭遇,并且在司马迁看来,也是至他的时代唯一与屈原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的作家,故在《史记》中将贾谊与屈原同列一传,以示同类。但是,我们从贾谊的辞赋作品,无论是哀悼屈原的《吊屈原赋》,还是自我感伤的《鵩鸟赋》,都已看不到屈原那样一种自我决绝的激烈情绪与抗争意识。《吊屈原赋》中虽然在一开始就感愤屈原“遭世罔极,乃殒厥身”的不幸遭遇,并以种种比喻描写一个价值颠倒、善恶不分的世界,但他对屈原投水而死的选择却并不认同,认为应该“远浊世而自藏”或“历九州而相其君”,此为“所贵圣人之神德”,这宣示的是他自己一种明哲保身的进退观。在《鵩鸟赋》中,贾谊则是用祸福相倚的道家思想来解释自己可能面临的凶险,看似达观,实际流露的却是“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这样一种命运无常而不可把握的无可奈何的悲哀情绪。
至于从汉武帝时代开始,伴随着专制独裁政体的重建,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一家独尊的主体地位,文学中自由的精神进一步丧失。在一时骤兴的颂赞盛世、润色鸿业的主调文学之外,恐怕只有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李陵的《答苏武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奏出了与时代的不和谐音,他们确实继承、发扬了《诗经》“变风”、“变雅”的批判精神与屈原“发愤以抒情”的传统,各自在文中倾吐个人在当时专制政权重压下的愤懑与悲痛,表现出对统治者、对这个社会毫不屈服的反抗。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会受到来自封建专制统治阶级最严厉的制裁。
李陵因为远在异域,汉帝国的法绳尚奈何他不得;而司马迁就未必有那么幸运了,尽管现在已无法证实东汉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所说的武帝怒削司马迁所作《景帝本纪》,以及司马迁受腐刑以后“有怨言,下狱死”是否有确实的依据,但有两个事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司马迁在作《报任安书》之后,其事迹便无可考了,不管是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定此书作于太始四年(前93),还是赵翼《廿二史札记》认为征和二年(前91)间所作;二是所撰《史记》在司马迁生前并未流行,这在《汉书· 司马迁传》中有记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而且据《文选》卷四十八班固《典引》,汉明帝曾于永平十七年诏曰,司马迁著书,“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后代的统治者于《史记》尚且作如是观,当朝的皇帝又会有如何的反应呢?则司马迁及其用生命铸就的伟大著作在当时所可能遭遇的命运,实在令人有不寒而栗之想。他的外孙杨恽,就是因为《报孙会宗书》成为“大逆无道”的罪证,而被远不如武帝忌刻的宣帝处以腰斩。如此看来,此时的汉代统治者与秦帝国统治者在扼灭文学精神的自由发展上,实是如出一辙,吉川幸次郎曾经提出的以汉武帝时代为中世文学的开始亦确有依据。在二十世纪初,黄人在其《中国文学史》中就已清醒地认识到:“至秦汉二主出,而文学始全入于专制范围内,历劫而不能自拔。”应该说,处于这种政治文化格局下的文学,在与上古文学划出一道鸿沟的同时,对后世文学的精神面貌及演进路线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近年来新出版的几部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当中,我们看到,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不仅重新采用了“上古”、“中世”、“近世”这样的历史分期法,而且在中世文学的划分上,正是以秦汉作为其开端的。在该著《导论》及《上古文学· 概说》、《中世文学· 概说》
诸篇中,作者对何以这样划分的依据及构想已经作了相当清晰的论述,我赞同他们的意见。
(原载《复旦学报》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