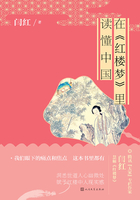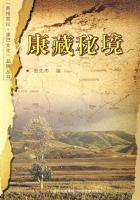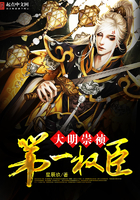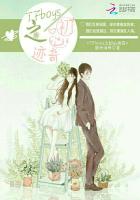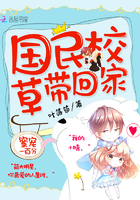一、一个简单的历史对比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女性的诗文创作可以说代不乏人。作为其中突出的个体,她们似乎也能适时地获得男性士大夫阶层的表彰。不过,女性诗文总集的编纂在明以前却并不繁盛。专录女性诗文作品的总集最早当出现于南北朝时期,这也是对女性及其文学表现相对来说比较关注的一个时期。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 经籍志》、《新唐书· 艺文志》等书志著录,南朝宋殷淳编有《妇人集》三十卷,宋颜竣编有《妇人诗集》二卷,又有不著撰人编《妇人集》二十卷、《妇人集》十一卷(《梁书·徐勉传》则载徐勉“为《妇人集》十卷”)、《妇人集钞》二卷等。另外,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据《古今图书集成· 经籍典》,录北朝后魏崔光表上《妇人文章录》一帙。之后,女性诗文总集的编纂便如凤毛麟角,据胡文楷著录,唐宋六百多年间,仅有蔡省风编集的《瑶池新集》一卷,录唐世能诗妇人李秀兰至程长文二十三人,诗什一百十五首;陈彭年集《妇人文章》十五卷;汪元量编《宋旧宫人诗词》一卷(知不足斋刊本)。另外,或还可算上后蜀韦縠《才调集》中《闺秀》一卷。这与这样的时代所呈现的文学之盛极不协调。
我们也知道,其实问题的关键主要并不在女性创作主体本身,而恰恰在于这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及习尚。后来如田艺蘅在所编《诗女史》自序中追究历来男女以文著者“曾何显晦之顿殊”,谓“良自采观之既阙也”,应该说还是触及了问题的实质,在儒家社会伦理体系逐渐完善并居主导地位的中世社会(魏晋南北朝时期之所以是一个例外,恰恰因为它是以儒家思想的衰微为前提的),相对于居中心地位的男性群体来说,作为边缘的女性群体,毕竟尚未在整体上独立地进入人们关注的视野。而像文学这样的精神活动,历来被视作男性士人的特权,虽然不时有才女涌现而加盟,从男性的视角来看,即便是那些以欣赏、表彰的动机采录者,亦不过带有某种传奇性质,明人俞宪一针见血地指出:“前辈论诗,多以缁黄、女妇为异流。”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至于其对文学女性的表彰,若加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则不外乎蔡省风《瑶池新集序》所说的以证“今文明之盛”,表明文明教化的力量已深入到女性,仅此而已。事实上,这些总集所录,基本上为闺秀、宫闱之作,从社会阶层上说,她们属于可能接受教育的少数精英妇女,更为重要的,是她们所体现的与男性之间的关系,显然是在儒家政教诗学阐释的两性关系范围内,尽管其中会有种种个人独特的感情诉求。因此,从明以前这些女性诗文总集的数量相当有限这样一个表象事实出发,我们可以观察到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而推究其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女性意识未获得突破性进展所造成的局限。
这种情形,一直要到明代才出现了很大的改观。同样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所录明人编刊的女性诗文总集总计已达二十八种,首先在数量上就大大超越了前代编纂女性诗文总集的总和,它们分别为:田艺蘅《诗女史》十四卷,张之象《彤管新编》八卷,郦琥《彤管遗编》三十八卷(按:《澹生堂藏书目》、《万卷楼书目》、《天一阁书目》等皆著录为二十卷),不著编辑者名氏《吟堂博笑集》五卷,俞宪《淑秀总集》一卷,郑文昂《名媛汇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下下“总集类”《瑶池新集》条所引。
诗》二十卷,题名锺惺《名媛诗归》三十六卷,新安蘧觉生《女骚》
九卷,江元禧《玉台文苑》八卷,江元祚《续玉台文苑》四卷,赵世杰《古今女史》二十卷,梅鼎祚《青泥莲花记》十三卷、《女士集》
二十卷,题邗上徐石麒又陵父评阅《影鸾集》四卷,张梦徵《青楼韵语》四卷,池上客《名媛玑囊》,卓人月《女才子四部集》,江盈科《闺秀诗评》,苏毓眉《胭脂玑》,许定泰《予怀集》,不详撰人《名媛新诗》,不详撰人《闺秀逸诗》,徐士俊《内家吟》,王豸来《娄江名媛诗集钞》,周履靖《古今宫闺诗》十六卷,方维仪《宫闺文史》、《宫闺诗史》,沈宜修《伊人思》一卷。这还不包括其作为合刻收录的冒愈昌《秦淮四姬诗》四卷、周履靖《香奁诗十种》
十二卷、叶绍袁集妻及三女闺阁之作《午梦堂全集》十二种等;周之标《女中七才子兰咳集》五卷有明末刻本,则亦应作明人编刊计入。另外,总集部分未及收录的至少尚有如胡文焕《新刻彤管摘奇》、周公辅《古今青楼集选》、马嘉松《花镜隽声》十六卷、郭炜《古今女诗选》六卷、张嘉和《名姝文璨》十卷、张梦徵《闲情女肆》四卷等数种。这当中,编刊时间最早的,一是华亭张之象所编《彤管新编》(嘉靖三十三年魏留耘刻本),以世所传《彤管集》篇帙未备,更为辑补,采录自周迄元,凡诗歌铭颂辞赋赞六百五十四首,《璇玑图》一篇,序诫书记奏疏表三十三首,厘为八卷;一为嘉靖三十六年(1557)钱塘田艺蘅编刊的《诗女史》,应该可以算是明代最早的女性诗歌总集,该集依时代先后辑录了上古迄明代的女性诗作,凡三百一十八家,厘为十四卷,拾遗一卷。
稍后,锡山俞宪编《盛明百家诗》前、后两编,共三百二十四卷,其前编专列《淑秀总集》,收有明一代十七家女诗人共七十二首;后编末有《杨状元妻集》、《马氏芷居集》、《孙夫人集》、《潘氏集》为女性诗,除潘氏属再辑,合计二十家。为最早的明代断代之作。
又有会稽郦琥于隆庆元年(1567)编刊《姑苏新刻彤管遗编》,实际分为前集四卷、后集十卷、续集三卷、附集一卷、别集二卷,收录自春秋迄明历代女性诗歌作品。万历以降,直至明末,有关女性诗歌总集的编纂、刊行,达到了空前繁荣,上列其他诸集,除数种刊刻年代不详外,绝大多数为万历至崇祯间人编刊,表明晚明士人乃至女性作者自身对编刊女性诗文总集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且此风之盛,一直延续到了清初。为此,如果借用西方社会学家在讨论古代文明发展史上出现重大转折所运用的“哲学的突破”(philosophicbreakthrough)这样一种说法,我们是否也可以将这个时代称作是一个“女性文学的突破”的时代。
二、商业出版背景与大众阅读趣味
在中晚明这样的时代骤然出现女性诗文总集的编刊热,当然不是偶然的。尽管学术界对近世社会、近世文学的起始阶段有种种不同的划分,然对明嘉靖以来社会与文学所呈现的巨大变化及其近世性特征的认识,却是相当一致的。十六世纪以来,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出现的商品化经济增长,从社会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一直到文学生产、传播机制等都发生了不同以往的深刻变化。人们首先会想到,出版产业特别是私人刻书业的迅猛发展,是中晚明女性诗文总集得以大量编刊的一个重要原因。确实,就中国印刷、出版史而言,嘉靖以来恰是出版业出现巨大转折的一个重要时期,商业化运作使得出版业无论在印刷总量、出版物品种以及流通区域、速度,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并且,这种繁荣在改变阅读受众以及阅读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阅读趣味。我们看这些适时出现的女性诗文总集,确实带有明显的书肆特征与浓重的商业化意味,如题名锺惺编的《名媛诗归》,王士祯在《居易录》中已辨为坊贾伪托;同样,田艺蘅编《诗女史》,亦令四库馆臣疑为书肆所托名。又如张梦徵辑、李万化重订之《闲情女肆》四卷,为崇祯六年刻本,实即《青楼韵语》一书,刊者仅将书名改换,原文并无变动,这也是书肆惯用的伎俩。
至于如《彤管遗编》所收明诗,其中大部分已见于《诗女史》,《名媛诗归》所选明诗乃至作者小传,亦多有因袭《名媛汇诗》处,这种因袭,实亦体现了坊刻的某种特点。这说明,女性文学具有巨大的市场价值。
然而,这似乎仍然不能说明,为什么女性文学会在这一时期成为商业化出版关注的热点?或者说,为什么女性文学会成为大众阅读趣味之所趋?我们知道,城市经济越来越细密的劳动分工,导致了一种“社会闲暇”的产生,而对于这种“社会闲暇”消费的需求,又促使了文学功能发生巨大的转变,市民社会娱乐性的要求在推动文学朝着俗世化、个性化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形下,大众对公领域以政教为职能的人文传统开始表现出某种疏离,而往往将热情转而投注到私领域以娱情为主的精神生活中去。因此,与这一时期的小说、戏曲呈现同一倾向,人们对像家庭生活、个人情感这样属于私领域的题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女性文学恰恰以表现这样的题材见长。对于男性读者来说,这样一种娱情的需求,既包含着对女性色艺的品赏,也包含着更高层次的与尚情相关联的个性主义文化价值观的自我投射,这在下面将会作进一步的分析;而对女性读者来说,这种娱情或许表现为对她们的同类内心情感生活的体验与仿习,时常也会混杂着女教这样的道德方面的要求,如题名为池上客编辑的《名媛玑囊》,一本作《镌历朝列女诗选名媛玑囊四卷》,与《女论语一卷》
合刻(万历二十三年书林郑云竹刻本),高彦颐以为显示了女性文字的商品化,已将训诫和诗歌合而为一,具有消遣的功用。这种大众读者文化的需求,才是这一时期女性诗歌总集编刊热的根本动因。
应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推助这一时期女性文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仍然来自男性的关注与认同,来自他们那具有某种突破性进展的女性意识。研究者可以费很多笔墨探讨明代社会环境的松动,女性得以比较自由地接受教育、与社会交往,甚至讨论女性的主体性,藉以解说这个时代女性文学创作的繁盛;尽管说,大约在万历十八年(1590)之后,女性创作开始大量涌现,而在明末也出现了女性诗歌总集的女性编刊者,但事实上,这个社会仍是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正是他们以一种自我投射的方式塑造才女文化,甚至肯定其具有拯救当下文学的作用,才助长了女性文学的繁荣。也正是他们的这一份对女性积极的品格的发掘与肯定,使得女性诗人与编者也开始意识到自身的意义与价值,并又进一步影响女性受众。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恐怕还不能毫无鉴别地套用西方性别理论的“差异”(difference)概念来加以解说,认为女性主体性的建立已足以可与男性社会相抗衡,从而将男女两性置于完全对立的位置,而还是应该将之放在男女性别互动的框架中加以考察。
三、史家职志与诗人诉求:男性编刊者的
历史担当与自我投射
从以男性为主体的编刊者的角度来说,除了迎合大众阅读趣味的驱动,他们的编辑、出版女性诗歌总集,表彰才女文化,实还有更深层次的意图与动机,而这才是体现女性意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获得某种突破性发展之所在。
我们注意到,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女性诗歌总集在叙述其编刊宗旨时,都冠之以一种严肃的史官使命。田艺蘅《诗女史叙》在慨叹“然圣史如司马子长,尚寂无所录,其后间纪一二,概已疏矣”的同时,以观风采诗者自命,所谓“乃探赜索隐,剔粹搜奇。人有善而必彰,言无征而不齿”,其以《诗女史》为题,即体现了这样的意旨。赵时用在为新安蘧觉生辑《女骚》九卷所作序中,亦将其“搜索世代”、“摘采情词”之功提到了很高的高度,谓“兹刻也,庶几与典谟训诰,并垂不朽”。他如张正岳为郑文昂《名媛汇诗》所作序,则表彰其“乃搜自昔,以迄于今”,是“仿述作于仲尼,效纂编之萧统”;赵世杰《古今女史》自序在阐发其“遍加搜辑、以备古今之阙逸”的意义时则曰:“异日有修彤史者,不至揣摩人于寤寐中,而取之缣缃,以振骚雅之遗音。则涵洪并纤,而无所不具足,故亦名之曰史。”诚然,诸如此类的自我标榜,未尝没有广告策略的成分,但是,联想到谢肇淛辈曾建议将“才智”、“文章”之女列入正史的《列女传》中,并且这样的意愿在当时江南地区的一些地方志中已开始部分地获得实现,我们不能不认真地看待他们的这样一种陈述。
在他们所述编刊宗旨中,这样一种标榜是与其在这个时代对于男女性别及两性关系的重新思考、重新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诗女史》编者序如下一段论述常为人所引用:
夫天地奠居,则玄黄宣色;阴阳相匹,则律吕谐声。故文章昭于俯仰之观,音调和于清浊之配,讵由强作,实出自然。造物如斯,人事可测矣。远稽太古,近阅明时,乾坤异成,男女适敌。虽内外各正,职有攸司,而言德交修,材无偏废。男子之以文著者,固力行之绪华;女子之以文鸣者,诚在中之间秀。成周而降,代不乏人,曾何显晦之顿殊,良自高彦颐曾特别关注到十六世纪以来,在江南地区一些地方志中,已有女性单单因文学才能突出而被载入史册的事例。参见其《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第131—133页。
采观之既阙也。夫宫词闺咏,皆得列于葩经;俚语淫风,犹不删于麟笔。盖美恶自辨,则劝惩攸存;非惟可考皇猷,抑亦用裨阴教。
首先,序者由自然、社会秩序出发,承认男女有别,各有职司,然这并不意味着材质有偏废,能力有短长,而恰恰认为“乾坤异成,男女适敌”,即将女性视作与男性相独立、在才能上相对等的一个群体而与男性相辅相成。这种观念,与俞宪所质问的“前辈论诗,多以缁黄、女妇为异流。乃其生质之美、问学之功,多出于凡民俊秀之上者,是岂可以异流目之”其实是相通的。如果说,前代文人士夫一直是在儒家伦理体系的范畴内将女性视作男性的附从,对于她们以“三从四德”为范的道德以外的才能从未予以正视,那么从他们开始,就要调整这样一种认识,给予女性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与她们的才性学养及其表现以重新定位和评价。后来如《古今名媛汇诗》余文龙序谓“天地生才,不专于七尺丈夫”,张正岳序谓“虽男妇之质变,或刚柔之道殊,然五蕴未空,七情欲动,率成文于叶韵,悉依永于比音。而况四时三经,奚难演绎;七声六义,固易追求。则学而可能,何独疑于女子;而力之所至,亦岂让于丈夫”,所表述的都是这样一种认知;人们所常常举述的李贽所辩驳的“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
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其实也是这个时代正视女性及其道德、智力潜能的产物。
这是这些女性诗歌总集编刊者立志弥补历来于女性文学作品“采观之既阙”的思想基础。
其次,序者认为,男女间“虽内外各正,职有攸司”,但她们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与男性创作的文学作品一样,具有“美刺”、“风教”的社会功能,所谓“盖美恶自辨,则劝惩攸存;非惟可考皇猷,抑亦用裨阴教”,这意味着原本被认为属于私领域的女性在公领域或人文传统中与男性一样也可以有所作为,因而可传。所说虽不免有些陈腐,但这是以一种与男性趋同的标准来阐扬才女文化的合法性,等于为自己专门汇辑、传播女性文学作品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俞宪《淑秀总集》自识曰:“古人自王宫以及里巷,皆有妇人女子之诗,盖风化政俗之所关也。”《名媛汇诗》朱之蕃序曰:“大则有关于理乱兴衰之数,小亦曲阐其深沉要眇之思;正则固足表其苍筠劲柏之操,衺亦能写其风云月露之致。奏之房中帐底,欢醼不隔千秋;纵同濮上桑间,鉴戒可垂百代。”所传达的其实也是这样的意思,所谓言在彼而意在此也。
正是鉴于这样的原因或理由,他们通过竭力搜辑考索,力图比较全备地将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编纂起来,或以时代为纲目,或因人系诗,或以体裁分类,有的所列编纂条例还颇严去取,以示采录之足可征信。说起来,这种种编纂方式或原则,当然体现的是文献学的编纂要求,然其背后未尝没有要像已有各种为男性文学创作所编纂的传世文献一样,开始全面地为华夏历来女性文学创作建立一种历史谱系的意图,意在通过这样一种历史谱系,为女性文学在原本由男性占领的文学传统中争得一席之地,亦令其传芳百世;同时也算是他们在正视女性的前提下,重新发现女性智慧才能的一种见证。
这是一种情况,或者更确切地说,往往是编刊者用以自我标榜的一种显性层面的编刊意图与动机。还有一种情况,是一部分士人浸淫于晚明新的哲学与文学思潮,通过采辑女性文学作品,意在以一种鉴赏的心态,张扬女性特质,强调其才性在审美、尚情的领域优于男性的方面,将对于“才女”的认知与塑造与一种对于本真性的表达联系起来,以此作为一种与正统意识形态抗衡的积极的品格;或者这样来说,是欲通过对女性才情的认同,向传统儒家对男性的正统性生活理想提出挑战,从而为自己才情至上的个体文化价值观寻找合法性。这是以一种与男性趋异的标准来表彰才女文化,但却是男性新的生活理念的一种投射,可能更多的是属于隐性层面的动机,而其有意表彰的“才女”
特质,则被赋予了政治或文化救赎的功能。
有关将这种非政治的女性气质理想化为“情”的潜在、纯净的化身,用以对抗正统的道德权威与生活理想,是包括男性主人公以及作者与读者在内的情感投射,原是近二十年来美国中国文学研究界在研究明清小说及戏曲等通俗叙事文类中已有的发现,我想,这种情形其实在诗文创作与鉴赏领域也同样存在。
就中晚明女性诗歌总集的男性编刊者来说,绝大多数已由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下移到了低级功名获得者,或者直接就是那些失意文人,他们身上具有鲜明的市民文化阶层的烙印,因为已基本上游离于金字塔式的儒家官僚政治体制构架之外,而以从事某些与社会文化工作相关的职业为生,因而很自然会凭藉自存自利的人格发展要求,通过找寻某种文化载体,提出他们在文化价值取向及人生态度上的诉求,女性的文学才性及其诗文创作,正是他们寻找到的这样一种表现自我诉求的载体。因为这种诉求的表现具有强烈的感性成分,我们姑且称之为诗人诉求。
在这方面,托名锺惺所编《名媛诗归》的作者自序大概可视作代表。序曰:
诗也者,自然之声也,非假法律模仿而工者也……故夫今人今士之诗,胸中先有曹刘温李,而后拟为之者也。若夫古今名媛,则发乎情,根乎性,未尝拟作,亦不知派,无南皮、 可参阅艾梅兰《竞争的话语———明清小说中的正统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义》
第二章相关论述及该章注释第101与102,罗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9—73页、第281页。
西昆,而自流其悲雅者也……
夫诗之道亦多端矣,而吾必取于清。向尝序友夏《简远堂集》曰:“诗清物也,其体好逸,劳则否;其地喜净,秽则否;其境取幽,杂则否。”然之数者,未有克胜女子者也。盖女子不习轴仆舆马之务,缛苔芳树,养絙薰香,与为恬雅。男子犹籍四方之游,亲知四方…… 而妇人不尔也,衾枕间有乡县,梦魂间有关塞,惟清故也。清则慧…… 嗟乎,男子之巧,洵不及妇人矣,其于诗赋又岂数数也哉!
……今人工于格套,丐人残膏,清丽一道,頍弁失之,缬衣反得之。呜呼,梅岑水月妆,肯学邯郸步,盖病近日学诗者,不肯质近自然,而取妍反拙。故青莲乃一发于素足之女,为其天然绝去雕饰,则夫名媛之集,不有裨哉。作者在这里将女性与男性、“古今名媛”之作与“今人今士之诗”
完全对置而论,以前者发于自然、本乎性情,后者从学入,“假法律模拟而工”;前者远离尘俗、虚静心灵,故“清”而“慧”,后者劳其心体而奔走四方,求获闻见知识,结果适得其反,“取妍反拙”;结论为女性更接近诗的本质,更能体现文学的审美特性、抒情职能,其“真”之性、“清”之趣、“自然”之质,恰可对救治当今文学有所助益。由此我们看到,作者其实是在女性或女性气质上赋予了“性灵”说的全部内涵,其意义当然首先体现在文学的方面,但又不仅限于此,可以说正是这种被赋予了特殊意义的女性气质,成为颠覆儒家正统文化价值观念与生活理想的有力武器,这当中文人所投射的才情至上的个体文化价值观,实关涉到对于人性的认识进程,确实可延展至所谓政治或文化救赎的层面。
高彦颐亦曾对此序作过一个堪称细致而深刻的解读,认为“其论点的根据是这样的一种对立,即一方面是妇女、性情和私领域,另一方则是男性、人文传统和公领域。在他的观点中,不仅真正的诗作源于前者,而且它还特别体现了女性的纯真和敏感”,“女性被排斥于男性的公领域和政治奋斗之外,实属一件潜在的幸事”,“这种认识促使他去出版女性的诗歌,以作为走入歧途的男性的榜样”。两性间这种差异与对立的被强调,明显是新旧两种生活理念冲突的反映,女性气质因而成为人们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拓展新的生活空间的一种导向,这是这个时代女性诗歌总集编刊者将女性意识与尚情的个性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新见解。
四、从德行到色艺:选录及分类
标准体现的新女性观
尽管中晚明编刊的诸种女性诗歌总集各有不同的选录与分类原则,但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总体倾向,是围绕着才女文化的塑造,突显以才艺为中心的标准。说来好像有点同义反复,既然是编刊女性文学作品,表彰女性文学才能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以这样一种标准操持选政的意义并不限于文学本身,而是要通过这样的工作,对原来儒家传统伦理关系中于女性所谓“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之“四行”的规范要求作比较彻底的转换,并利用自身的传播机制,使之深入到当时广泛的各个社会阶层。
郦琥编纂的《彤管遗编》,算是比较早刊行的一种女性诗歌总集。较之之前《诗女史》、《彤管新编》以时代为序的编纂体例,《女骚》卷首赵时用序曰:“论及闺闱淑媛,则惟德容言貌是肃己尔,幽闲贞静是修己尔,翰墨笔砚,宜不必亲。纵酣醉艺场,如曹大家之踵成《汉史》,亦不慨见,他何足喙。故虽列女有《传》,唐文德有《女则》百卷,洵可为宪往昔、范来今之助,卒未以诗词特闻者。间有之,亦散佚未汇,然而不谓阙遗也。”应该已算是意识到这项工作潜在的意义。
它采用了一种比较特别的选录与分类标准。据其《凡例》:
学行具优者,载诸首简……
德行未甚显著而仅优于文者,纪于后集……
行劣学优,以年次续焉。即后妃、公主,亦不得与民间妇人有德者同一类也。
孽妾、文妓别为一集,然中有贤行者,升附于前、后集之末,以为后世修行者劝。
看上去这是一种因人分类的编纂方式,然所依据主要又非女性作者的社会身份,而是标举德行与才学的双重标准,这应该已可看作是对“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的一种公然挑战。虽然,在其自述中仍强调德行优先,似乎表现出与传统观念的妥协,但其实际的效果,却是在德行的金字招牌下,弱化了女性的社会身份标识,若德鄙行秽,“即后妃、公主,亦不得与民间妇人有德者同一类也”;同理,若有贤行,即“孽妾”、“文妓”亦堂堂正正地得与后妃、公主及闺秀共坐一堂。因此,如果说,这之前如《诗女史》,如《盛明百家诗》的《淑秀总集》,其选录范围尚主要以“闺中”、“良人”为限,那么,该集则在德行与才学的双重标准下,以一种有限的平等观念,将“孽妾”、“文妓”的文学创作亦予收录,这是其较之前人有所突破的地方。当然,这种选录范围的拓展,实际上是这个时代女性文学担当者社会阶层扩大或者说下移的一种即时反映。在另一方面,编刊者虽然标举的是德行与才学的双重标准,但在实际收录女性诗歌作品时,却显然又是以才艺为隐性的优先标准,显露出重文的实际好尚,正如有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它又实际上更青睐‘优于文’者,后者在五集中占十卷,篇幅最多,便是明证”。 这种种看似矛盾之处,主要不在于编刊者价值观念的紊乱,我们倒是可以从中看到塑造一种才女文化在激荡包括官方意识形态在内的风俗时一种左冲右突的艰难。
万历以降,情形有了比较显著的变化。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倾向,可举郑文昂编选的《古今名媛汇诗》二十卷为例。该集《凡例》称:
集以“汇”称者,谓汇集其诗也,但凭文辞之佳丽,不论德行之贞淫。稽之往古,迄于昭代,凡宫闺闾巷鬼怪神仙女冠倡妓婢妾之属,皆为平等,不定品格,不立高低,但以五七言古今体分为门类,因时代之后先为姓氏之次第。由其陈述可见,编者已不再半遮半掩地打德行之旗号,而是明确以“文辞之佳丽”作为女性诗歌作品的选录原则,才艺成为唯一的评判标准。在此标准之下,女性间一切身份的界限被全然消解,品格优劣也不再重要,可以说是各色女性在艺术面前人人平等,相比较徐熥万历间编选的《晋安风雅》在《凡例》中的陈腐之见:“妇人之诗,《品汇》总曰‘闺秀’,兹编另立‘名妓’一目,特严薰犹之别。”这实在算是一种不同凡响的胆识。当然,徐熥在高棅《唐诗品汇》所立“闺秀”目外,另立“名妓”一目,本身也已经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因此,郑文昂所采取的分类法,是干脆以体裁与时代为经纬,这与其以才艺为选录标准也是相符合的,它将人们对女性文学创作关注的焦点由人引向了诗作本身,也就意味着引向真正的才艺鉴赏。
另外一种倾向,则表现为称赏女性文学才能的标准又向色艺一边偏转,这其实与当时一种特别强调女性特质的女性意识是密切相关的。谢肇淛曾对他所处的时代一味标举女子之才而忽视其女性的美色特征表示过不满,他说道:“荀奉倩云:‘妇人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此是千古名通。女之色犹士之才也,今反舍色而论才……岂理也哉?”当然,他这么说的真实意思并不是要否定女性的才具(高彦颐将之解释为这不过是他对模糊了的社会性别界限的一种焦虑),而恰恰是要求以一种色艺的标准来衡量女性的特有魅力,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妇人以色举者也,而慧次之”(同上)。联系到上举郑文昂《名媛汇诗》,看上去唯一强调的是男性可同样具备的文辞标准,似乎也有模糊性别特征之嫌,但我们从该集张正岳序所阐发的编纂宗旨,所谓“加以柔情弱骨,婉衷媚肠,即睹言笑动止之容,已具月露风云之态。粉白黛翠,摛藻缋于新妆;犀齿蛾眉,写烟花于巧倩。体裁不异,自觉轻盈;制服虽同,更加妩媚”,还是能够看到其对女性特有的审美表现的关注,可以说仍然隐含了某种色艺的标准。
天启间马嘉松所编《花镜隽声》十六卷,主要收录自汉迄明的历代女性诗作,所涉诗人身份从宫人、闺秀到女郎、平康,各阶层都有,其《凡例》自述选录原则曰:
诗之幽绝韵绝者,喜录之;娇绝丽绝者,亦录之。得无太艳乎?曰:不然。夫子删《诗》而不废郑卫之音,可以著眼。
显然,这可以说是比较明确地标榜侧重女性特征审美表现的诗歌选录标准,其标出的“艳”也好,未标出的“淫”也好,虽然都是指文学作品本身所呈现的色韵、情调之极致,然其于女性特质的指向性是确定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个时代在这种色艺的标准之下对妓女文学的特别关注,如万历间冒愈昌编《秦淮四姬诗》,张梦徵辑《青楼韵语》四卷,稍后周公辅选《古今青楼集选》等,都属专录词妓之作,正如《青楼韵语》在杭子序所感叹的,“嗟夫,尤物易于移人,妓且词,其机韵故足倾动一时”,这种属于家庭外的两性关系而又身处男性公众交际网中的词妓,大概最能满足当时士人所一直苦苦寻求的情感和艺术上的共鸣。而这样的标准,无疑表现的是男性文人一侧伸张个性、欲望的诉求。有意思的是,如清完颜恽珠编《国朝闺秀正始集》,作为一个女性编刊者,却全然以“名媛”为范,其定集名曰“正始”,旨在标榜性情之正,所谓“庶无惭女史之箴,有合风人之旨尔”;故其“例言”自申其选诗标准曰:“青楼失行妇人,每多风云月露之作,前人诸选,津津乐道,兹集不录。”即便如柳是、卫融香、湘云、蔡闰诸人,最终以晚节而破例入选,亦不过是“遵国家准旌之例,选入附录,以示节取”。曼素恩曾就此分析她们的动机说:“盛清时的‘闺秀’———闺阁中培养起来的女性———自觉地将她们的学识和艺妓的学识区别开来。”表明她们宁愿取一种与男性在公领域的使命趋同的标准来重新论定才女文化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从而体现出欲摆脱男性文人于女性仅止于色艺鉴赏的视阈,那当然意味着精英女性对于其主体性的某种自觉,但亦显示了时代风气的变易。
五、结 语
透过中晚明女性诗歌总集编刊所呈现的女性意识,我们已可清晰地观测到这个时代从社会结构到人的思想情感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动及其相关轨迹。围绕着对女性文学才能的关注与鉴赏,自然会引发人们对女性的能力、与男性的差异、女性在社会中担当的角色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与重新定位,上述种种解读的内容,可看作是这个过程中的一种见证;更为重要的,与这个时代的精神主潮相关,是在那些男性编刊者所在的新知识阶层的带动下,男女之间的社会性别关系,正不断逾越传统伦理的界域,在审美的个人才情上达到某种共鸣。尽管这种对女性文学才能的关注与鉴赏,可能复合有多种价值观,甚至仍有陈腐的道德评判,有媚俗的市民趣味,但当它通过赋予女性积极的品格,将之与尚情的个性主义相联系,从而对儒家构建的恒定社会秩序与生活理想提出挑战时,其意义也就突显了出来———而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阐扬的。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