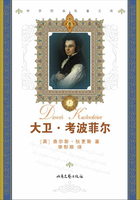苏小雨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下楼的时候,苏小棋还在屋里磨蹭。
小雨说,快点啊你,再不走就迟到了。
苏小棋对着镜子中的自己,发出一声叹息。紧接着,她听到楼下卷铁门的响动,她的心狂跳起来。紧接着听到小雨细软的声音:罗医生好早!罗医生也许冲小雨笑了一下,也许没笑,小棋又听到他充满磁性的声音,小雨,上课去了?
苏小棋连滚带爬地扑下楼,惊慌失措地看着罗朝江。她也想学小雨一样跟罗医生问早安,话在嘴里憋了半天,就是吐不出来。正在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罗朝江对姐俩笑了笑,转身进了屋。
苏小雨推着自行车说,小棋,你到底走不走。
苏小棋冲小雨盯了一眼,一屁股坐上自行车的后座。小雨交给她煮熟的玉米棒,练功很累人,得吃点东西。
十八岁的苏小雨骑着一辆二十四寸自行车带上十六岁的苏小棋穿过京果街,苏小棋坐在车后座,看着小雨晃动在她眼前的纤细的腰身,狠狠地咬了一口玉米。
京果街的小巷在苏家姐妹的成长中也一步一步地迈向衰老,记得她们刚学走路的时候,路面还滑得怎么站都站不稳,鞋底像装了轮子。而今她们的屁股真的坐在了轮子上,这条小巷已变得磕磕碰碰了。苏小棋啃完玉米,把那根印满唾液和牙齿印的棒子向上一抛,正好落在人家晾在头顶的胸罩里。苏小棋吃饱了的肚子里发出胜利的咕咕声。苏小雨握着车把的手颤抖了一下,车轮子撞在路边的石墩上,她尖叫一声,苏小棋像那根玉米棒子一样被扔了下去。
苏小棋的身体在地上摔了个狗扒屎。她活动了一下四肢,没觉得什么地方不妥,便在地上坐了起来。苏小雨望着她“哇”的哭了。苏小棋诧异地抹了把脸,她的手背留下一抹血迹。她咬了咬嘴唇,尝到一股腥咸的味道。苏小雨还在哭,一边哭一边手忙脚乱地翻书包,终于翻出一条小手帕。苏小棋拍着屁股站起来,狗屁大的事,哭什么。
苏小棋想,今天这一跤摔得真他妈的冤。好不容易放个暑假,苏影兰竟异想天开地把她和苏小雨一起送进文化宫学芭蕾舞。出门前还特地找了条苏小雨穿过的裙子套在她身上,还企图将她的头发像苏小雨一样盘个结,可惜她的头发太短,只是能插几棵小秧苗。
文化宫那位舞蹈老师姓姚,皮肤白皙,手脚很长,听人说话时喜欢直着脖子,像只吃饱了撑的长颈鹿。老实说她长得并不美,又或者说,她本来也是美的,只是跟苏小雨站在一起,才美得有点勉强罢了。
姚老师逼着苏小棋穿上练功服和舞蹈鞋,同班那些漂亮的小女生都和苏小雨一样,六岁就开始学舞了。而苏小棋已经十六岁,她无法将双腿从侧面抬起一百八十度,也无法用脚尖走路,她甚至连站都不会站,她们站的时候老喜欢双腿并拢,脚尖向左右两侧站成个“一”字。而无论苏小棋怎么努力,都只能站成个“八”。当那些美丽的小天鹅随着音乐的节拍翩翩起舞时,苏小棋则像只丑小鸭一样扑腾着笨重的翅膀。
苏小棋望着镜子,她被自己的样子逗乐了。正想换个法儿让自己站得好看点,姚老师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站好!她大喝一声,只听见“啪啪”两下,苏小棋的双腿被踢了两脚,她的身体晃了晃,应声倒下。
这个早上苏小棋摔了两跤,当她的双脚被姚老师这样一踢,身体落下地板的姿势竟和从苏小雨的自行车上摔下来时一模一样。她的门牙又一次受到撞击,鲜血发了疯似的从嘴里淌将出来。她又尝到那股腥咸腥咸的味儿,她趴在地板上愣了好一会,刚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姚老师居高临下地说,起来,别装死。
他妈的我苏小棋是装死的人吗?她在心里喊道,从地板上一跃而起。这时候,包括苏小雨在内的漂亮女生都围过来了,她们被她满嘴的鲜血吓得花容失色。姚老师显然也被吓着了,但她当老师这么多年,不知道踢了多少脚,从没失过手。她盯着苏小棋的脸看了好一会,伸出手去沾了一点那鲜红鲜红的液体,放到鼻子边去嗅了嗅,走吧,到我办公室上点药。
苏小棋咧了咧嘴,露出那只豁得更加彻底的门牙。她看了她们一眼——姚老师,和那群美丽的小天鹅,她们看着她的目光是那样好奇,那样忍俊不禁,那样不可思议,好像全世界的女孩子都应该像她们那样活着。苏影兰真是吃饱了撑的!
她没有跟姚老师去办公室,而是把吊在胸前的铜钥匙摘下来握在手里,迈开大步走出练功房。苏小雨走上前去,试图拉住她,最后还是把想说的话吞回去了。
文化宫门外栽着两棵高大的石栗树,树下整齐地停着一溜儿自行车。苏小棋一眼就认出苏小雨的车子,那辆车有着翠绿色的外壳和像苏小雨一样玲珑的身段。她走过去,尝试着把它推动起来。她没骑过自行车,也不会骑,但苏小雨以为她会,她自己也以为自己会。
现在她特想把这自行车怎么样一下,这玩意儿怎么看怎么让她不舒服。车子上了锁,要推动它是不可能的事情。苏小棋伤心极了,她原先只以为面对苏小雨才会有那种自卑感,没想到她的车子也一样不把她放在眼里。她的心里升起一种强烈的报复欲,她像姚老师对付她一样朝车轮子踢了两脚,自行车应声倒下。倒了还不行,她的门牙摔破了,血也流了,自行车看上去依然完好无损。她握紧了手里的钥匙,像苏影兰杀鱼一样,在车胎与钢轮之间的柔软地带巧妙地扎了一下。她感到一股鲜活东西从指间汹涌而出,她嗅到一股鲜活的血的气味。
苏小棋在回家路上,耳边不停地响起轮胎爆破的“嗤嗤”声,血的气息不断从嘴里散发出来,她全身打了个颤。罗朝江的牙科诊所内静悄悄的,那套他赖以谋生的金属工具躺在一只铝饭盒里,闪着冷惨惨的光。
苏小棋的心又狂跳起来,她忘了牙痛,忘了少年宫那班小天鹅和苏小雨的自行车对她的羞辱,她的全副身心和灵魂都被那些金属工具,以及它们的主人吸引住了。她坐在离诊所门口大概五米远的台阶上,静静地看着屋里的景象。晚霞的余辉照在罗朝江的身上,给他的身体镀上一层灿烂的光。从苏小棋坐的角度看过去,正好看到他的侧影,他的嘴唇厚而大,鼻梁高挺,额头向前微突,瘦削的脸颊蕴含着冷静、沉着,而心事重重的意味。他那双正在擦拭工具的手修长而温柔,苏小棋幻想着,这双手应该用来弹钢琴,或者拿画笔,而不是舞弄这些冷家伙。
就在苏小棋静静地坐在台阶上胡思乱想的时候,苏影红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她操着在菜市场卖鱼一样的大嗓门喊道,你姐呢?
苏小棋看着母亲愣了半天才回过神,嘴里发出一声哦、哦的声响。
苏影兰又说,你姐呢?
苏小棋迷茫地摇了摇头,她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尘,向家里走去。临上楼梯那一瞬,她又忍不住回过头去看了一眼罗朝江,这回看到的,却是背影。
苏小雨没回家吃午饭,苏影兰咀嚼的速度也慢了半拍。苏小棋坐在饭桌边,饿得肚子直造反,门牙却痛得她话都懒得说,更不用说吃饭了。苏影兰说,你们不是一起去上课的吗,你姐呢。苏小棋摇了摇头。说话呀你哑巴啦我问你姐哪去了。李广财说,兴许是和男孩子逛街去了吧,女大不中留。苏小棋赞许地看着她的父亲,不住地点头,心里想,这老东西竟变聪明了。
少说两句,没问你呢凑什么热闹!李广财缩了缩脖子,不响了。
苏小雨抿着双唇,尽量不让那块棉花团露出来。苏影兰瞪了她两眼,又看了看李广财,扔了筷子说,饭桶!
苏小棋笑了起来,样子像想哭,有点幸灾乐祸地望着李广财。说你呢,笑什么笑,李广财用筷子敲打着苏小棋的饭碗,不吃就拿去喂狗。
上完舞蹈课以后苏小雨和同学们走出文化宫,才发现自行车全被划破了胎。她没有像别的小女生一样推着破车就回家去,第一反应还是哭,一边哭一边思考这一突发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她的思考浪漫而虔诚,绝不会想到是哪个坏分子搞的破坏,一味认定了是上天对她的惩罚,因为苏小雨的门牙摔破了。她没想到的是,上天对她的惩罚会殃及池鱼。她看着姚老师和她的同学推着车子艰难地行走的背影,就内疚得想死。于是,美丽的苏小雨哭完以后,就坐在那两棵高大的石栗树下,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自责或者忏悔。
暮色苍茫的时候,苏小雨推着她那辆气数已尽的自行车走进京果街,她蓬头垢面,眼睛周围红肿得像熟烂了的茄子,那身洁白的连衣裙沾满了油污,她的双手因为过分用力长了泡泡,膝盖上还无中生有的紫了一块。京果街的人们神色暧昧地夹道相迎,他们对于苏小雨的新形象感到兴奋而又不可思议,迫于无奈人们只好多费了些脑汁去想象在她身上可能发生的一切。
苏小棋坐在二楼的露台上安静地看着她的姐姐,她被她的样子逗乐了,正欲告诉屋里的苏影兰,耳边却突然响起自行车倒地的声响,紧接着,小雨晕倒在地。她呆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正不知该作如何反应,想喊人,刚张嘴,就痛得不行,她赶紧把嘴捂上。这时候,罗朝江突然出现在她的视野里,他扑将上去,把小雨扶起来搂在怀里大喊,苏阿姨!小雨晕倒了!
正在洗碗的苏影兰扔下活计扑下楼,罗朝江已经抱着苏小雨走进门,小雨静静地躺在他怀里,像一只委屈的小猫。罗朝江抱着小雨的手舍不得放下,苏影兰着急地上前抢过小雨,把她放在沙发上,吩咐李广财,快,拿保心安油!
李广财和苏影兰手忙脚乱地掐着小雨的人中、太阳穴,苏小棋呆站在屋里的一角,眼看着罗朝江却紧握着小雨的手,轻轻地抚摸,她的身体晃了晃,以为自己也快晕倒了。她的意志和身体经过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终究没有倒下。
苏小雨终于睁开她那美丽的双眼,看到罗朝江那忧郁而关切的眼神,她长舒一口气,喊了声,妈——眼泪又流了下来。
我说,罗医生,楼下有人找你。
苏影兰才回过神,几乎是使劲地掰罗朝江握着小雨的手说,罗医生,谢谢你,小雨醒了,你快忙去吧。
罗朝江恋恋不舍地走向门口,苏小棋伸出脚使劲一踢,砰的一声,门重重地关上了。
苏小棋站在露台上,看着罗朝江的诊所透出来的灯光。阁楼上传来小雨嗡嗡嗡的抽泣声,和苏影兰的安慰声。后来,声音渐渐变小变弱,最后变成呜咽。苏小棋看着京果街的灯火亮起来了,蓬江河畔的灯火也亮起来了。她又听到苏影兰与李广财的争吵,以及罗朝江拉下卷闸的声音。
苏小棋躺回床上,看着墙上挂着的画像,脑海里闪过罗朝江抱着小雨的情景,握紧了拳头。
苏小雨像往常一样迈着细碎而优雅的步伐走出家门,罗朝江早早地开了门,故作忙碌地坐在工作台前,一边擦拭他的工具,一边向着他心中的女神行注目礼。他看着小雨的身影消失在自己的视野,才叹了口气,站起来,走到厨房准备早饭。
苏小棋从诊所门外一晃而过,走到街口的灯柱前站住了。她咬了咬牙,下决心地把头撞向灯柱,那只断了的门牙,终于掉了下地。她顿时感觉头脑一阵晕眩,眼看就晕倒在地,遗憾的是,她却没有晕,竟还能清醒地捡起那半截牙齿,来到罗朝江面前。
罗朝江被罗小棋的样子吓着了,他惊呼,小棋,你怎么了?苏小棋什么话也没说,把那只断牙举到罗朝江眼前。
苏小棋躺在小床上,清晰地听到罗朝江的呼吸。罗朝江的手在她的嘴里手忙脚乱地折腾,一边关切地问,痛吗?苏小棋正痴迷地看着罗朝江胡思乱想,这时候,她发现了他身上的白大褂的领子附近有一块微黄的污垢,那块小污垢随着他喉结的上下滚动快乐地颤抖。
罗朝江终于长舒一口气,好了,过几天我帮你把牙补上。
苏小棋依然痴痴地看着他。
罗朝江感叹,奇怪,真是奇怪,牙齿摔成这样应该很痛才对,你为什么一滴眼泪都没有。接着他又仔细地看了看苏小棋的耳垂和额头,脸上浮现诡秘的神色,风水佬骗你十年八年,但我的话你是要信的,不瞒你说,你的命硬得很哪,男人治不了你。
苏小棋愣了愣,刚才把牙齿撞向灯柱的悲壮,因为罗朝江这几句俗不可耐的话变得索然无味。她皱了皱眉,站起来说,我回家吃饭了。罗朝江说,我话还没说完呢你走什么,你听我说完……苏小棋早没影了,像鬼吃了一样。罗朝江望着那道楼梯的入口,心里升起一丝不安,他晃动着盛满智慧的脑袋自言自语,为什么就没人肯听我说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