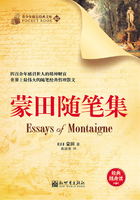曾经有个女人找到我,给我留言说:你赢了。我没回复她。后来她又找到我,留类似的话。我至今没有回复,也不会回复。从她出现到她离开,她从没有走出过输赢的权衡,所以时时计较、时时揣测、时时失态……所有这些,都是女人处在那种情境中的正常反应,我也不能幸免。但在另外一些时候,我付出,我得到,我享受,我承受,没有输赢,没有亏欠。
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是一种涵养,也是一种无奈。每次吵完架,我们坐下来,半调侃半认真地分析为什么吵架,看起来是为了共同进步和美好的明天,事实却是说着说着都不好意思起来。因为吵架要么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破事,要么就是因为我们都改变不了的积习,所以真是毫无意义。
与其他女人比起来,我既不漂亮也不性感甚至不够专心致志,那么我的优势大概是浑不吝的幽默感、仗义和不以为意——不以为意,这非常重要。在操蛋的生活中,用美景、美食、美酒、美男和工作阅读之类去分解作为一个女人的注意力,又用化妆买衣服之类的女人活计消解作为一个人不定期的对人生涌起的怀疑。
我还有个优点,是言出必行,尤其是撂狠话,总结起来就是,我比较狠。当我说“你再让我看见这个我就给你撕了”,大多数男人会觉得是一时气话,但我真的就在夏天的黄昏,拿着美工刀慢悠悠地把一件没拆封的新衬衫撕成拖把似的布条丢在地上。因为我不是在示威,而是在践诺,事先打过招呼了,很礼貌,很平静。这个场景说起来当然有点儿歇斯底里,不过我知道这件事在我和他的底线之内,它符合我一直以来的浑不吝,也符合他对我的印象。在衬衫变成拖布之后的两个小时,我们又可以把这件事当作一件尘封的笑话讲起来,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武志红的书里否认了“对的人”的说法,他认为人应该先搞定自己,我非常同意。可惜如果你恰好遇上一个搞不定自己的、不断作死的人,并且爱上了他/她,那就不大好办了。不作死就不会死,可不作死还叫人生吗?其实我很想回复那个女人这样几句话:第一,没有人输也没有人赢,这压根儿不是一场战争,我也从没有以你或任何人为敌。第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脱身要趁早,我祝福你。第三,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当这是一场战争了,你或任何一个她,都不是我的对手。
十几年前,我们都是初恋受挫的小女生,坐在一起肿着眼泡互相问一些“你还相信爱情吗”之类的傻问题。有一个女孩给我分析我的分手,说:“你跟他分手就是因为你不能忍他了,这说明你不够爱他,因为一个人有多爱一个人,就有多能忍一个人。”她满脸都是17岁的像煞有介事,于是我也分外肃穆地注视着她,可心里想的是:不是啊,我很爱他啊,可我就是不能忍。忍和爱,是两码事吧?
我不是情感专家,因为太多事算不明白,比如上面那段话,我想了13年还没想明白答案。可是想明白了又怎样?条分缕析的人生该有多无趣啊,像整天穿着白大褂儿在一尘不染的档案室上班,四周的纯白木柜里整整齐齐地摞着冷冰冰的钢制文件夹。
其实我见过那个女人,只是我从她身边走过时,我知道她,她却不知道我。如果她发现了这件事,大概会备感羞辱,因为她当这是一场必须一决高下的较量。其实有什么呢,傻女啊,不知是福。
灯乍亮,必有人端坐于千万人之中,她以为会是我。其实我早已趁乱遁走,不知所踪。
人生的真相应该自己去寻找
因为最近工作上遭遇的一些挫败,虽然嘴上说着不在乎,心里是痛的。前天晚上一整夜睡不着,昨晚早早爬上床,还是梦见面孔模糊的人跟我说:“你就是不行啊,就是不行啊。”这种痛苦跟男人被说在床上不行,孰轻孰重,我分不清。
醒来之后,我回想自己,其实从没有走过什么捷径,也没有大人物眷顾,自己拼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使的都是牛劲。无论考试、工作、感情,还是交朋友、赚钱,基本是实打实戳在那儿的,所以对命运公或不公、运势顺或逆,历来没有太大的感想。在第一万次给自己做了心理建设之后,我一早起床打起精神,用心推敲和修改专栏的题目和信息,反复修改小说已经完成的部分——有时候我想,人活一辈子,须如树一样扎根大地,伸展枝丫。未必一定成为最繁茂的,但至少成长为自己希望的姿态。
以树(当然也有其他美好植物)自比,是很清高的传统,无论是为了那种高大、挺拔、正直、长远、沉默,还是潜意识里的生殖崇拜。传说胡杨三百年生而不死,三百年死而不倒,三百年倒而不朽——我在福建读书的几年,看到许多大榕树,几个人围抱不来的树干上钉着牌子,写着五百年八百年的字样,又感动,又心疼。世间百态,见多了,看久了,漫长的时间里独自缓慢而坚实地成长,怀揣的,大概一半苍凉、一半悲悯吧。
2013年初,我帮杂志整理周信芳之女周采茨的访谈。她在上海做元媛舞会。记者问她,你这样推贵族、名媛概念,不觉得是在给人分类,是不公平的吗?周采茨反问,你觉得世界是公平的吗?你瘦,我胖,已经不公平啦。记者又问那些妙龄名媛:你们都爱上过穷小子吗?你们的父母会同意吗?周采茨说,我从来不跟有钱人搭界的!你没听过吗,“宁弃白头庸,不嫌少年穷”。少年穷不可能一生穷的,他有才华就可以啦。你们也应该这么想。
最后,我引用了黄佟佟的一段话作为这篇访谈的引子——
白氏家族的后人白先勇说:“月余间,生离死别,一时尝尽,人生忧患,自此开始。”宋美龄的侄媳宋曹琍璇说:“成就对我们来说好像过眼烟云。”而周信芳的女儿则教育她的儿子:“人生的真相应该自己去寻找。”
“人生的真相应该自己去寻找。”这就是我的那棵树。
命运的鼓点
年前有一天情绪差到心像被刀狠狠剜了一块,很冷的晚上走出来去浴池洗澡,洗完到楼上拔罐。
拔罐的大姐问我拔竹罐还是玻璃罐,我说随便吧。她说竹罐贵一些,但效果也更好。我还是说随便吧,趴在床上。她身手利落,我听见身后呼呼的点火声,感觉到燃起又熄灭的热度。好像过了很久,她才停下来,问我:“疼吗?”
我很认真地感受了两秒钟,回答:“有点儿,还好。”
她把小腿上的两个罐子卸掉了,像在怪我,又像在自责:“娃儿哦,疼也不说一声。”
后来她屈起一条腿坐在对面的空床上跟我聊天:“我哦,跟我男人都是四川的,种地的,后来听说东北有好多工厂,工作机会好多的,我们就来啦,没想到呼啦啦工厂就都倒闭啦,只好找别的工作。有什么工作好找哦,又没有文化,你说是吧?四川也回不去了,房子啊地啊都卖啦……我们卖过麻辣烫,根本不赚啊。娃儿啊你不懂的,麻辣烫要开在学校附近才有生意哦,烦。现在他也没干什么,打点儿散工,我在浴池也10年啦。我儿子大学毕业啦,倒是有工作,不过也就那样啦,还不是给人打工?他有女朋友啦,说要房子,哎呀,我们哪里有钱买房子啊,早知道房子会这么贵,我们就早买啦,现在哪里买得起哦,儿子还要怪我们没有早为他打算……”
我歪过头望着她,时不时嗯嗯哦哦一下。她看看时间差不多了,站起来准备把我身上的罐子都卸掉。“反正哦,我这辈子,就是步步不赶点儿,步步都选错。”
洗完澡回家的路上更冷。风打过来,头发针一样戳着棉衣的前襟,发出沙沙的响声。
昨晚在电影院看《西游降魔篇》,看到镜花水月,看到众生皆苦,就想到微博上看到过两个段子。一个说在超市逛,听到身边的人在打电话,说“出来打个分手炮啊”,正暗想此等牛人一定要结识一下,一回头却发现打电话的人虽语气嬉笑实则满脸都是泪。另一个,好像是庄雅婷写的,出租车的广播里播放着一首苦情歌,红灯处,司机停下车,默默掉眼泪。
初中时读孔庆东,那时候他还没有这么张扬,甚至并不知名。他有一篇写顾城的小文,题目叫《生命失败的微妙》,文中提及这个题目让他想了很久,是生命失败的微妙,还是失败生命的微妙,还是微妙的生命失败。文字与文字之间有一种节奏,是美感也是喜好,是每个写作者时时都在斟酌的。
昨儿跟群里的几个女人提到一些天性必须用绝望来印证存在的人,都有点儿感慨。小时候喜欢大侠萧峰,喜欢没把球踢进门的巴乔,一是因为男子气,二是因为有能耐,但大半还是因为够悲情。在许多文艺不死的人心中,悲情简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审美追求。
然而年纪渐长,就有诸多忌惮,不能想象自己有一天会对一个素昧平生的人闲聊既往人生,做结的时候说一句“步步不赶点儿”和“步步都选错”。
梅艳芳生前在演唱会上翻唱周华健的《明天我要嫁给你啦》,结尾处说了一句:“祝你们都嫁个啊,你们最爱的男人。”台下一片尖叫。芳华绝代的梅姑早已不在,当年那些尖叫的女孩而今也都不再年轻,她们有没有选错?有没有赶上命运的鼓点?
许多问题的难,在于无处发问,且没有答案。
最后一次让你心疼
下班了好容易折腾到家,牛奶箱子几乎是丢在地上,长舒一口气。父母又去新房,我突然不想面对空房子,把包里的书稿掏出来扔在柜子上,转身去超市。
一路用手机听着歌,走灯火阑珊的地方。大广告牌后面突然传来哭声,我还疑心是耳机的杂音,一转弯,就见一对男女相视对峙着。非礼勿视,我心无旁骛地走。女孩转身要走,动作很快,差点儿撞到我,男人啪就拽住她的马尾辫,咔地一下扯回来——就是那样的一瞬间,女孩惨叫出来,几乎是被半拖着跪在地上,下不去也起不来,而男人甚至没有松开手。我大大地惊怕了,快步走了过去。
我也留过这么长的头发,直的,黑的,没经过一点儿修饰的长发。我不知道这个身手敏捷的男人,是不是也曾将手指拂过女孩的长发,柔声说情话给她听。他已经这样丧失了理智,她哪儿来的勇气和自信转身离开?她想到他会这么对自己吗?她现在是更疼,还是更难过。心死,心没有死。或者,凌迟一般的后爱情时代,才刚刚开场。
就这么胡思乱想着,一路走过去。
买薯片的时候,一对男女在身后。男人趴在购物车把手上,很悠闲,女孩面对他站着。我没有留意他们,绕过去,专心辨别那琳琅满目的价签和口味。他二人也不避嫌,就幽幽在我身后聊天。
男人说:“生活总是很现实的。”
女孩:“可是……我什么都能忍受。先前你那么说……都已经那样了……我都接受了,我都不觉得有什么……我从来没麻烦你,是吧……你看……可是……”
男人还是很镇定:“是,我是很感激你。”
女孩愣了一下:“不是这么回事儿……不该是感激。我是说……你现在不能……这么长时间了,你不能说没就没有了……我的想法,你是明白的。”
女孩说着说着,就哭了。
男人又接着说:“所以我说生活是很现实的,事儿不会像你想的那样去继续。我很感激你……”
女孩哽咽着:“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我胡乱拿了一罐薯片就跑开了,可身后还是传来那男人的话:“很多事儿不像你想的那样,谁都没办法,你就得承受……”
在超市里一圈一圈地绕,不想回去。天气那么冷,没人帮我提东西,没人给我买烤地瓜,没人心疼我这么晚还加班,没人问候我这一天过得好不好。一圈一圈。没有人在意我。回家也是我一个人。一圈一圈。很多老太太在抢购鸡蛋——我不需要鸡蛋。很多小夫妻在抢购打折的面包——我也不需要面包。一对对男女推着购物车穿梭在我身边——他们是否真的相爱,会爱多久,会怎么分手,会不会分得很难看,像他和她,或他和她?会不会明明不该在一起,却互相折磨,直到对彼此一点儿心疼都没有,只剩下恨意?
就是这样的一句话,我突然明白,就是这样的一句话——我想问问那个狠狠扯住女孩辫子的男人,她最后一次让你心疼,是什么时候?我想问问这个随口说出冠冕堂皇的话语的男人,你面前的这个女孩,因为你的遗弃,哭得像个泪人一样,你果真一点儿都不心疼吗?
我想起闺密赵小姐有一次说起跟男朋友闹别扭的深夜,她一个人在操场上绕,走在那么醒目的球场灯光下,无非是为了让他想找她的时候,马上就能找到她。可他没有来,电话也没一个,短信也没一条。她坐在灯下,渐渐冷了,困了,才不得不回家。房间里,他面对着电脑或一本书,安详地坐着。看见她,什么也不问。赵小姐跟我说:“他一点儿也不担心,即使有时候他会象征性地问一句,但是……我知道,他一点儿也不觉得心疼。”
爱情只有有无之分,没有深浅之别。在生病的日子里,因为炎症而高烧不退的夜晚,妈守在我床头,我疼痛又虚弱得说不出话来。去小诊所打针,一步步挪过去,400米的路途要走上20分钟。手术时的恐惧,不停地跟大夫聊天来掩饰的窘迫。手术后自己走出来,对众人比个“V”字手势。术后几天走路时撕扯的疼痛,换药时切口一次次被扒开的刹那,我紧紧捂住自己的嘴,不叫出声来……
所有这些,我多么努力地去做到,不让谁看出我的难过和无助,不让人心疼我。近乎偏执地守卫身体的隐疾,不告诉任何人感官的刺激有多强烈——无非是因为,我怕我想能心疼我的那个人,并不能做到那样的心疼。我怕这样的一个他,会让我忍不住腹诽。可我不忍心责怪他一分一毫,因为如果他因为我而负累,我一定会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