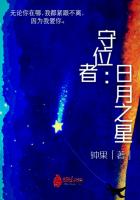玄兔三千杵,捣就白玉丸。一服去百病,二服忘忧烦。彼独是何人,心如石不转?饮月得长生,不顾雪满山。
在那个弦月如刀的夜晚,一曲《寄玄兔》不知是从何人口中开始传唱,念诵声逐渐越来越大,其中混入了叹息与啜泣。
无知的山民们听不懂这曲子在唱什么,只当是赞颂白狼神的歌谣。有人躺在柔软的床铺上,望着木窗外清幽的月光,一边跟着那些声音唱诗,一边想着当时如果手脚再快一点,抢到神母投下来的白玉丸该有多好……
羽卫小雉蹑手蹑脚地紧贴窗边而走,将还温热的鸡汤放在桌上。故意碰到了桌边坐着的人的手臂,可那人仿佛泥塑木偶,一点反应也无。小雉觉得害怕,轻声问道“郡主她真的没事吗?”
“保持这样或许更好。”沈玄度从玉瓶中倒出一把花花绿绿的药丸,看也不看就吞了下去,又将那玉瓶抛给小雉,示意她喂给号枝“景阳在外流落久了,学得狠辣,竟然想得出吞服烈毒,从幻术里活活疼醒的法子。她刚烈至此,我也就只能用琵沙迦纳的药物了。”
正如白狼巫师所言,号枝被蛮平女王以密药控制心神,此时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她就那样半睁着无神的眼睛,任由小雉拿着一堆药丸准备往她嘴里填。沈玄度看着她线条优美的嘴唇被掐的发红,不悦斥责“蠢材,喂不进去你不会碾碎化水了再喂么!景阳是一国郡主,是我的妻子,怎能让你如此横蛮对待!”
沈玄度说得急了,便又咳喘个不停。小雉急忙跪地请罪,收拾了药丸便下去了,留下屋中两人相顾无言。
将她脸上的铁面摘下的时候,指尖触摸到了纤长的睫毛。如果有知觉的话,一定是忍不住要眨眼的。可现在的铁面乌鸦就像一具精美的人偶,除了鼻下尚有一丝细微的呼吸,完全没有任何活气了,自然也不会做出哪怕一丝反应。
号枝的关节无力支撑,沈玄度便让她半趴在桌子上,下巴搁在手臂,仿佛趴在那儿小憩,睡得安稳。他看着便忍不住抚摸着她柔顺的长发流泪“究竟为何会变成这样呢,金乌。”
桌上趴着的人自然不会回答,声音来自门外“巫师,俞国钦差求见。”
谢琅一开始吃了闭门羹,可他在门外大声念起那首“此身愿做金乌火”时,沈玄度到底还是答应见他了。
书生一见到白狼巫师,便感觉到他比在山间梯田初遇时更显得苍白虚弱了。夜深露重,主人本来已经打算就寝,恶客贸然来访,自然没有什么好脸色可看,能抬手给谢琅倒上一杯热茶,便算是沈玄度自持镜炴国皇族身份,周全礼节了。
“掷子去,黑云压覆三千里,罗睺一灭万焰生。洗刀唱,此身愿做金乌火,诛尽百里魑魅魍……”诗词虽为小道,却是体现心境的最佳途径,这首长短句听来悲怆,沈玄度仅念了两句,似乎字字带血。他在“小憩”的号枝身边坐下,将她微微凌乱的发丝拢齐,“钦差可知这首《洗刀唱》,写的是什么?”
“谢琅不知,还请白狼巫师赐教。”书生很客气,行的也是晚辈礼。
沈玄度一愣,招手请他坐下“你不知诗词中意,为何在外面大声吟唱?”
“这就如那些山民也随口吟唱我写的《寄玄兔》,仅仅是念着提气,再加上些自以为是的揣摩,试图体会写诗人的心境而已。”谢琅口里答着,目光却落在趴在桌上小憩的女子脸上。那是一张清秀的脸孔,右眼下有颗鲜艳的红色小痣,想必笑起来应该很是娇艳。
“天已晚,我的爱妻已经睡着了。若要谈论诗词,钦差不妨明日再来。”沈玄度危险地眯起眼睛。
谢琅毫不在意地笑了笑,拿起桌上的热茶就喝。白狼巫师看着他手里颤抖地将滚烫的茶水晃出去好多次,连皮肤都烫红了,却仿佛豪饮烈酒般一口将那热茶吞下去的壮烈样子,哑然失笑“若我没有猜错,现在陆凌霜正疾驰在返回安京的途中。”
谢琅摇头“去的是虎迸卫的人,陆凌霜不肯走。”他又将壶里的茶给自己倒了一杯,继续一口吞下去,烫的龇牙咧嘴“我说与他命中犯煞,两人凑在一起就倒霉,他偏生不听,铁了心要和我一起蹲在这里。”
沈玄度又扯了扯嘴角,那手掌支着下颌,好整以暇地看书生在那里狂饮“一份奏折九重天,他身为言官御史,自然不肯放过这种机会的。”
“你这茶汤有够带劲的。”谢琅觉得浑身的血液都翻涌起来,满脸通红,竟然是显出痴狂态来。他随手解开外衫,连挂在腰际的玉佩都摔落在地,顿时便断成两块。谢琅尤为可惜地捡起来拼凑一番,见实在凑不回去了,无奈地对沈玄度笑“这块玉佩,还是靠巴结上官才得来的赏头。可怜我谢平治满肚子挥斥八极,却屡遭大难,连饱饭都没吃上过几口……”
“呵呵,像你这种意气书生,我见多了。”谢琅苦撑着不肯倒下去,沈玄度便接过手来继续往他杯中续茶,“我曾在蒙州见过一名书生,竟然是靠着在秦楼楚馆的相好接济才能活得下去。俞国这些连自己都养不活的才子,很稀罕么?寻章摘句,白首穷经,往故纸堆里凭巧混食,与卖笑的歌妓有何两样?”
这番话说的尖酸刻薄,惹起谢琅脸上血色更浓,他死死握住茶杯,身体抖得如同筛糠“巫师,你说得对。安京的高管勋贵自然喜欢华府文章,艰险绝伦,怪异奇俊的句子最讨人喜欢。俞国有投行卷的,往往凭着一句妙言平步青云,被奉为座上宾,迎入府中歌舞宴饮日夜不歇……呵呵,这便是俞国的才子!”
他说到最后,已经狂态尽显,扔开杯子,一把抓住茶壶也不顾里面液体滚烫便直接仰头灌了下去,浇得满头满脸都是,衣襟也湿了一大片。沈玄度噙着笑,看着谢琅全身发红滚烫地坐在桌边打摆子,连眼球都遍布血丝,便把那茶壶翻过来,倒扣在桌面上,那里面确实一滴液体也没有了,“钦差,你都喝完了。”
“我都喝完了。”谢琅死死掐住自己的大腿,听着窗外突然炸起的喊杀声。那是陆凌霜带着一百三十名虎迸卫与迦楼罗众拼命,无论怎样也要在这虚假的桃花源内撕开一个通往战场的缺口。
“白狼巫师,你还是低估了俞国文人的风骨!我不是来求饶的!”谢琅踉踉跄跄地站起来,一把将茶壶砸碎,嘶哑地大吼“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你拦不住我!我要去蒙州,我要亲眼去看看那个被婊子养活的才子,我要告、告诉他,‘帝流浆’喝了再多、才子,就是才子!不会变成阴沟里的臭虫!”
沈玄度长叹口气,为痴狂的书生扪掌喝彩,他真的是从心底佩服这颗砸不烂煮不软的铜豌豆。蛮平人大多认为风骨这种东西是天生的,只有神才能拥有,至于凡人和愚民只需要趴在地上看就行了。但俞国人却认为铮铮风骨可以后天培养出来,于是他们拼了命地修养身心,花上几年几十年,从书堆里钻出来的家伙脾气一个比一个臭,骨头一个比一个硬。
可是那又如何?沈玄度招了招手,一身黑衣的羽卫小雉不知是何时站在那里的,她手上那个半透光的玉瓶中有荡漾的液体。
“钦差,你刚喝的是另一种药。号枝的药在那里。”沈玄度怪异地笑起来,他迫不及待想看谢琅目瞪口呆的表情。
可是谢琅也笑了,满面通红的咧着大嘴,笑得丑陋且猖狂“白狼巫师,你真的以为我是为了抢药喝来的?”他张开双手,那块已经断成两截的玉佩躺在书生满是血色的掌心,中间明显有一个夹层。
白狼巫师的脸色在看到那个夹层的同时,瞬间惨白。
有一只冰冷而骨节清劲的手搭在了他的后颈,号枝抬起脸低声笑“舒哥哥……”那声音好似来自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