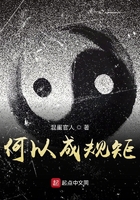就在碧君惆怅的离开景和楼大戏院的时候,晴方也正满戏园子的寻找着碧君。
今天夜场戏开始前,晴方进到后台发现碧君并没有向往常一样等在那里,他起先以为碧君唱完了日场的戏已经先行回去了。可是在晴方对镜上妆的时候,锁头急切的跑了进来,说他听前边戏班子里的人说碧君姐姐在日场唱《玉堂春》的时候好像受了伤,流了不少的血。
锁头的话让晴方十分的震惊,但是具体的细节他也只是听了个大概,晴方连忙放下手中的头面,跑到前头问个究竟。
当听戏园子的人说碧君是被人往缎面垫子里塞进去的瓷片渣子给扎伤了膝盖时,晴方又是心疼又是愤怒,他将那块沾着碧君鲜血的缎面垫子又翻找了出来,仔仔细细的打量了一会,又问了后台管道具的老师傅几句,然后神情凝重的又返回了自己的化妆间。
那天晚上散戏后,晴方带着锁头急匆匆的赶回了家,一进大杂院也顾不得和院里乘凉的邻居打招呼,便快步走进了小月亮门。他见碧君的屋子还亮着灯,便走到门前轻轻的敲了敲门,叫了一声碧君。
晴方敲门的时候,碧君正合衣斜靠在被子上,眼前满是子声的身影。听见晴方在门外叫自己,碧君忙起身答应了一声,本来要去开门,但是碧君看了看自己敷着药的膝盖,又慢慢坐了下来,对外边的晴方说道:“白大哥,我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晴方知道碧君是怕自己担心,他有些心疼又有些关切的说道:“都受了伤还装什么好汉,快把门开开我看看,你不开我可撞门了。”
碧君听晴方如此说,只好挪到门前,将那扇木门慢慢的打开。
晴方进门之后,他忙将碧君扶着坐到椅子上,又不顾碧君的阻拦,蹲下来掀起碧君的裤腿,想要看看她究竟伤的怎么样。”
当看到碧君的膝盖上已经包扎了一层纱布时,晴方有些疑惑的问道:“你自己包扎的?”
碧君笑着看了他一眼,然后有些害羞的将裤腿慢慢放下,对晴方说道:“我哪里有这本事,这是医院里的大夫包的。”
晴方听碧君已经去过了医院,这才放下心来,他也觉得自己方才有些失态,尴尬的笑了笑,然后起身坐到了碧君的身旁,细细的问起日场的事情。
碧君素日是个不喜与人争斗的性子,凡事都宁愿自己吃亏,也绝不愿意把事情闹大弄僵,她知道晴方嫉恶如仇,怕他知道后会替自己出头闹出事来,于是她只是轻描淡写的说许是戏台子没扫干净,自己凑巧跪到上面了,不打紧的。
晴方见碧君到这个时候还在想着息事宁人,愤愤不平的说道:“你别瞒我了,我都把那垫子仔细看过了,那哪里是戏台没扫干净,明明是有人黑了心,故意朝里面塞了瓷片渣子,这是铁了心要让你上不了台啊。”
碧君违心的说道:“我在这园子里也并没有与人结仇,谁又会暗算我,别提这事了,我以后自己多留心就是了。”
晴方皱着眉头对碧君说:“你怎么留心,人家一门心思的要毁你,你却倒好,还再替那人遮掩,孰不知对有些人太过仁慈无异于养虎为患,迟早会为它所伤。”
碧君冲晴方苦笑了一笑后说道:“算了,我也懒得去想那么多了,戏班子这么多人,若一个一个去查问一番,又要生出许多的是非来,不如糊里糊涂的过去罢了,还是好好唱我的戏最要紧。”
晴方气哄哄的说道:“你是真傻还是装傻,这不明摆着的事吗,把那垫子拆开,再一点一点塞东西进去,然后再慢慢的把它缝好,这不是一下两下就能做完的,必定要细细的来做它,后台里人多眼杂,众目睽睽之下做这些定是不可能,那唯有在无人之时动手脚才会神不知鬼不觉,而后台里能够有机会做这些的只有两个人,那就是唐蓉珍和金翠文。想来,那金翠文不大会去下这功夫,她虽然是个爱扯是非之人,但是暗算了你于她也没甚好处。说来说去就只剩下一个唐蓉珍,这是个嘴甜心苦的货色,你救场唱了代战公主,抢了风头不说还上了报,声名也渐渐的大了起来,就凭这一点,她能不妒忌你吗?”
晴方的话说中了碧君的心事,她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去答对,只得面色沉重的盯着地板不再言声。
晴方见天色不早,便叮嘱碧君早些歇着,自己也起身回屋去休息。碧君送走晴方,熄了灯后并没有脱衣睡下,而是一个人坐在黑暗之中,回想着今天发生的一切,就像唱了一出群戏一般,一个一个该来的不该来的,想到的未想到的,一股脑全都涌到了自己的跟前,一时间让她本来平静的心情好一番起伏涨落,弄得人疲惫不堪。
第二天,晴方劝碧君休息几日,可是碧君不想因为自己而打乱了戏园子的戏单,也不想因为这个而看甘经理的冷脸,于是她硬忍着疼痛又准时出现在了茂春大戏院的后台。
碧君慢慢走进后台的时候,蓉珍正和班子里的几个人嘻嘻哈哈说着闲话,见碧君进来,蓉珍忙殷勤的迎了上来,一边将碧君扶住,一边关切的说道:哎呀,好妹妹,姐姐昨个都不知道你受了伤,今儿才听说你的膝盖被扎破了皮儿,要紧不要紧,可把我担心坏了。”
望着蓉珍一脸的关切与心疼,碧君有那么一瞬间都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过于敏感多疑了,但是一想到那条歪歪扭扭的线和晴方昨夜的话,碧君又不得不佩服蓉珍心机的深沉。碧君按捺住心中的鄙视和不悦,似往常一样笑着对蓉珍说道:“不打紧的,只是蹭破了些皮。”
蓉珍听碧君说不打紧,连忙双手合十放到胸前,嘴里振振有词的说道:“菩萨保佑,我碧君妹妹平安无事就好。”
瞧着蓉珍一脸虔诚的模样,碧君意味深长的说道:“姐姐真是菩萨心肠,有姐姐的关照,妹妹定然会平安无事的。”
蓉珍听碧君如此说便又咯咯咯的大笑了起来,那甜腻的笑声响彻在整个后台,可是这笑声在碧君心里再也没有了当初的那份温暖与美好。
当天的夜场压轴戏是晴方和蓉珍合演的《姑嫂英雄》,晴方演嫂子樊梨花,蓉珍演小姑薛金莲,这是一出双旦并重的戏,嫂子威武大气,小姑高傲艳丽。这出戏讲的是樊梨花接到公爹薛仁贵的求救书信,正欲立即发兵前去解救唐王和公爹之时,恰逢小姑薛金莲押着粮草行至她镇守的樊江关,初嫁入薛家的樊梨花听闻薛金莲性子高傲,于是带领兵将阵势浩大的前往关前迎接,想的是与小姑搞好关系。谁料这薛金莲在无意中看了爹爹求救的书信后,误以为嫂子不肯相救,便与嫂子发生口角,无礼的羞辱起嫂子来。樊梨花忍让再三,最终发作,与薛金莲拔出银剑较量起来。姑嫂二人激战正酣之时,母亲柳迎春赶到,训斥了自己的女儿薛金莲一番,金莲从母亲的话语中明白是自己误会了嫂子,连忙向嫂子跪下求情认错,最终姑嫂二人和好如初,一同领兵前去救驾。
晴方在台上演的端庄大气,唱的也是韵味十足,把一个领兵一方的女元帅演的活灵活现。然而,这唐蓉珍却在台上动起了小心思,她在晴方坐在椅子上表演之时,竟然向台下频频的抛起媚眼
晴方唱的正好,忽然被莫名奇妙的喝彩声一阵惊扰,他起初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一边唱一边用眼睛细细的观察台下的动静,他发现叫好的是台下的一帮男人们,他们的眼神完全不在自己这边,而是在身旁的唐蓉珍身上。晴方微微侧过脸一看,终于发现了奥妙所在。晴方在看到蓉珍不知廉耻的在台子上卖弄风骚的时候,心里恨不能一脚将这不守规矩的下作之人踢下台去,但是他毕竟是见过世面又能镇住台的角儿,虽说被蓉珍在旁边抢了戏乱了场子,但是他很快就用一段更加精彩的唱段和潇洒不凡的身段将众人的目光吸引了回来。整个一出戏演下来,晴方要比平日多费了许多的心力,有好几次都险些扰的晴方忘记了唱词,若不是他经的场面多些,否则真的被这妖冶的唐蓉珍给带到了沟里。
一出《姑嫂英雄》就这样勉勉强强应付着演完了,虽说晴方最终还是扳回了局面,但是心里却比吃了苍蝇屎还要恶心。晴方在观众的喝彩声中走回了后台,待台口的帘子一放下来,晴方回身就给了走在自己后面的唐蓉珍一记响亮的耳光。蓉珍本来正满脸得意的回味着方才台上的事,却猝不及防的被晴方狠狠的抽了一耳光,心里猛的吃了一惊不说,脸颊也瞬间火辣辣的疼了起来。
蓉珍捂住左脸,又羞又恼的追到已经快要走远的晴方身边,一把将晴方的胳膊用力拽住,哭骂道:“姓白的,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凭什么打我,凭什么打我?”
本来有些嘈杂的后台,因为这两个人的纷争立马安静了下来,大家都吃惊的看着这两个人。
晴方想要甩掉蓉珍的手,但是这蓉珍索性两只手死死的将晴方的胳膊死死的抱住,像一块橡皮胶一样纠缠住晴方,非要他给个说法,使得晴方一时无法脱身。
晴方冷笑了几声后,大声斥责道:“我凭什么打你,就凭你坏了台上的规矩,我就打得你!”
蓉珍也毫不示弱的说道:“规矩?什么规矩?你无外乎是见我唱的比你的彩头多,因此心生妒忌,白晴方你真真是个下作无耻的东西。”
听了蓉珍不知羞耻的话语,晴方哈哈大笑了起来,边笑边嘲讽道:“我心生妒忌,妒忌你什么,难道妒忌你在台上犯贱发浪不成?真是天大的笑话,我看你明儿也别唱戏了,干脆到八大胡同去当窑姐儿是正主意!”
晴方说出了班子里许多人憋在心里多日想说却不敢说的话,就连那站在一旁瞧热闹的金翠文也忍不住偷笑了几下。
蓉珍被晴方一顿挖苦讽刺,脸上实在有些挂不住,她一边将晴方死死的扯住,一边大哭大闹起来,嚷嚷着非要晴方给自己个公道。晴方素日最厌恶她这等货色,加之她连连暗算碧君,今又在台上不守规矩,晴方自然不肯就此让她再猖狂下去,他用力将蓉珍的手甩开,在她脸上又是一记耳光,然后一把死死捏住蓉珍的脖子,狠狠的对她说道:“收起你的眼泪,我不吃你这套,再若不安分,跳出来暗算人,我就豁出去这戏不唱了,也要让你说出个子卯寅丑来。”
晴方说完,冷冷的将蓉珍一把推开,大步流星的走进了自己的化妆间。
蓉珍方才被晴方捏的险些气都要上不来,整个人都被惊吓的直发懵,一时心里方寸全无,哪里还顾得上再撒泼打滚。待晴方咣的一声关上门,蓉珍才醒过神来,她见班子里的众人都不无嘲讽的看着自己,心里自然是羞愤难当,她哇的一声趴在身旁的桌子上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将桌子上的瓶瓶罐罐连带着头面盒子尽数抛到了地上。
班子里的人除了金翠雯假惺惺的站在蓉珍身旁劝慰她几句,也就她的两个师兄站在一旁满是心疼和同情的看着她,其余的人都暗暗为晴方较好,心里直骂蓉珍这是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
蓉珍哭骂了一会子后,忽的站起身跑到楼上去寻甘经理告状去了,众人心想:想来甘经理也不会为了这个浪蹄子真的会去和白晴方这棵摇钱树撕破脸。
果然,甘经理在听了蓉珍添油加醋的哭诉后,虽然心疼但是也拿白晴方没法子,戏园子自打荫山期满退隐后,就全凭晴方这一个角儿来撑场子,若是真和晴方闹翻了那影响的可是戏园子的生意。
甘经理好言劝慰了一番蓉珍,再三让她忍耐些日子,等往后从长计议。蓉珍见甘经理跟个缩头乌龟一样不肯替自己出头,她猛的站起身,甩开甘经理放在自己大腿上的手,气鼓鼓的说道:“忍,忍,忍,我忍够了,不就是怕他走了没人给你挣大钱了吗?明儿就开锣唱粉戏,姑奶奶让你看看究竟是他假模假式的扮女人好看还是我货真价实的演粉戏招人稀罕,咱们走着瞧!”
甘经理也忙站起身,笑着对她说道:“好,有志气,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一切听你的,咱们明儿就开锣唱粉戏,只要你的名声唱出去,咱就让那姓白的卷铺盖滚蛋,往后这戏园子就全听你的。”说完,甘经理又在蓉珍的背上满是暧昧的拍了几下。
蓉珍从鼻子里冷冷的哼了一声,然后憋着一口恶气摔门出去了,甘经理摸了摸老鼠胡子得意的笑了,唐蓉珍这块白花花的鲜肉终于一步一步的走到自己口边里来了。
蓉珍的粉戏终于开锣了,为保险起见甘经理将蓉珍的这出名为《春宵梦》的粉戏安排在了日场压轴上演,他盘算着要是能够一炮打响,那就日场和夜场都安排上,挣他个盆满钵满。
为了吸引那些狂蜂浪蝶来看戏,甘经理特意制作了两个大大的花牌放置在了剧院的正门两侧,花牌上不光赫然写着“风月皇后唐蓉珍倾情献演《春宵梦》”字样,还在上面画着一个只穿红肚兜的妖冶妇人。
正所谓有烂肉就不愁没有臭苍蝇叮它,粉戏的大花牌一立到那里,便有那些平日就被蓉珍勾引的五迷三道的好色之徒奔走相告,不到半日便将《春宵梦》的戏票一抢而空,那帮浮浪子都等着看蓉珍那雪白的膀子和滑溜溜的大腿。
碧君日场的戏在蓉珍的前边,她进戏院的时候也留意到了那两个大大的花牌,她仔细的看了一看后,才发现这戏自己从未听过,不晓得是不是蓉珍新学的,但是从那风月皇后还有那妖冶的画像上看,隐约觉得这出戏恐怕不是太妥当。这要是放到往日,碧君定然后规劝蓉珍一番,但是自从有了前几日那档子事,碧君也领教了蓉珍的厉害,虽然面子上仍旧与她交好,但是心里却早已嫌恶和惧怕了她,自然不会再去她跟前费口舌。
碧君的腿伤虽然还没有好利索,但是她在台子上却一点都不含糊,一出《金水桥》唱的婉转动人,雍容典雅。但是今日的看客中虽然也有冲着碧君前来的,但是更多的都是为了猎艳而来,他们哪里还有闲心听碧君唱的银屏公主在那里替子请罪,面圣求情,一门心思的等着看后面的蓉珍是怎么个春宵难度。因此上,碧君的一出戏唱下来,叫好声虽有但是不似前几日那般多,而且反响也是平平。
一折戏唱罢,碧君有些沮丧的走到后台,迎面就碰见甘经理送着蓉珍往台口走,碧君微微向两人笑了一笑,然后准备侧身让他们先过去。谁知蓉珍一见碧君,异常热情的拉这她的手,甜腻腻的说道:“妹妹,今天这出戏是姐姐新学来的,你可要留意听听,给姐姐多挑挑毛病,也好让姐姐日后像你一样能干,咱也上上报纸扬扬名。”
碧君听出她这是话里有话,她看着蓉珍一副自信满满的模样,勉强笑了一笑,说:“姐姐,莫要打趣我了,祝姐姐马到功成,旗开得胜!”
甘经理听碧君这话说的吉利,立马凑到碧君跟前笑着说:“还是碧君会说话,蓉珍这出新戏若唱火了,咱们也给你排几出,你们姐妹俩以后就是咱戏院的两朵红艳艳的牡丹花啊。”
甘经理嘴里喷出来的臭味让碧君一阵反胃,她连忙将脸侧到一边,敷衍的笑了一笑,向前走了过去。
蓉珍见甘经理一脸猥亵的盯着碧君的屁股看,心下立时就不痛快起来,她使劲咳嗽了一声,阴阳怪气的说道:“得了,甭看了,人家都走远了还看个什么劲儿呀,您呐就甭打碧君的主意了,人家眼界可高着呢。”
甘经理转过头笑着对蓉珍说道:“怎么,你吃醋了,我的眼里可只有你一人啊,几时让我香甜香甜呐。”
蓉珍杏眼含春的暧昧一笑,然后轻轻的在甘经理耳边说道:“我这天鹅肉还不至于落到您口里,别痴人说梦了。”说完,咯咯咯的笑着走到了台口准备上场开唱。
甘经理等蓉珍过去才反应过来,他鼻子里哼了一声后,心里说道:任凭你再嫩的天鹅肉老子非要尝上一口
蓉珍在幽怨的音乐声中缓缓走出后台,一出场就先伸了个大大的懒腰,那玫红色的小袄本就很短,被她这么向上一抻。台底下的男人们都一边咽了咽口水,一边淫声喝彩起来。
甘经理听着外边的喝彩声,心里一阵高兴,心想这真是个好兆头。
蓉珍一边唱了一句:“鸳鸯戏水池塘边,鸾凤交欢柳林畔,唯有奴家命运苦,红绡帐内少风流”。蓉珍演的李焦氏年少守寡,一片春情无处排解,本欲与花匠偷欢,怎耐婆家规矩森严,一直不能如愿。今夜月圆花好,可叹鸳鸯帐里少一人,蓉珍边唱边脱,没多久就在众人的叫好声和口哨声中,把小袄脱下丢到一旁。
蓉珍本就是放荡之人,跟这喜月红学了这戏后,就更加的风骚浓艳起来,她的一颦一笑,一招一式深的喜月红的真传
后台的碧君一便卸妆一边听这前边的动静,只听得前边是一会子鸦雀无声一会子又是掌声雷动,而那蓉珍的声音也是带着几分迷醉的意味,听着倒也新奇,但是那唱词却十足的不规矩,分明是浓词艳曲的意思,让人一听就不由得面红耳赤。
碧君带着几分好奇走到台口,微微掀开帘子朝外边一看,天呐,那是怎样的淫秽场面,台下的男人们一阵阵的心跳加剧。
碧君慌忙放下帘子,脸色通红的跑下了台阶,心里满是对蓉珍的鄙夷。甘经理见碧君一脸害羞的神情,调笑碧君道:“唉,我说,前边儿的戏好看吧,赶明儿你也学一学,别老在台子上老守着那陈年的老规矩,这唱戏就得像蓉珍一样活泛,越活泛就越有钱挣。”
碧君不等甘经理说完,便带着满脸的厌恶一把推开后台的门冷冷的走了出去。甘经理自讨了个没趣儿,嘴里没好气的骂道:“假正经,有种你别嫁人,别让男人祸害。”
碧君带着对蓉珍的失望与鄙夷走出了后院,她今儿晚上还有一折《桑园寄子》,因此也不能早早回去,只得在街上随意的走走逛逛散散心。
刚走到街角,就看见子声坐着一辆洋车朝着边驶来,碧君心里知道他定然又是来寻自己的,她那天离开景和楼时已经想清楚了,断然不能再和子声有何纠缠,否则该如何去面对晚秋。碧君连忙将身子转到一边,想要背过他去,可谁知子声坐在车上一眼就看见了身穿一身淡青色布旗袍的碧君,他还没到跟前就已经笑容灿烂的朝碧君挥起胳膊来。他见碧君将身子转过去,以为是没有看见自己,便急忙让车夫停了车,匆匆付了钱后,快步走到碧君身后热情的叫了一声:“小福子。”
碧君以为子声已经坐车过去了,没成想他竟然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碧君只得慢慢又转过身子,忍住心中的那份欢喜,淡淡的说了句:“好巧,又碰见了。”
子声没有察觉碧君神色的冷淡,他笑呵呵的说道:“哪里是好巧,我是专程来找的你,还想着你的戏应该没散呢,结果竟然你人已经出来了。”
碧君望着眼前这个一脸灿烂笑容,憨厚质朴的子声,心里莫名有些难过,多好的人啊,可惜已然是错过了。碧君收起心中的那片深情,装出冷淡的样子,轻声说了句:“闫师兄,往后你不要再跑来找我了,你待我的好我都记得,可是今时不比往日了,你我再这样私下往来,倘若被晚秋姐姐知道,她定然会不欢喜的。”
子声满心欢喜的跑来看碧君,谁料想碧君又恢复了冷冰冰的模样,这让子声很是意外,他带着几分伤感说道:“你只想着她会不欢喜,就不想想我欢喜不欢喜?我自从十七岁那年见了你,心里就再也没有装进第二个人去,你知不知道?”
碧君何曾不是看君一眼误终身,方才听了子声这句又莽撞又深情的告白,心里一阵乱跳,脸也烧的厉害,她真想告诉子声,自己也是在六年前的那个夏天就懵懵懂懂的喜欢上了他,随着年岁的增长,就愈加的思念起子声来。就在碧君快要沦陷的时候,她猛地又想起晚秋与子声的婚约,她只能咬牙忍住那即将倾泻的情感,硬着头皮将子声拒之千里之外。
碧君深情的凝望了一眼子声,咬了咬牙之后,平静的说道:“闫师兄,快回去吧,算我求你了,你再过几月就要娶亲了,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于你我于晚秋姐姐都不好,快走吧。”
碧君说完,转身就要离开,子声一把拉住她的胳膊,急切的说道:“小福子,我不管其他人怎么想,我只想着要对你好,求你不要走,你知道我这些年有多想你吗?我有许多话还没有说,你知不知道。”
碧君何尝不是心里有无数的话要同子声倾诉,可是自己来北平就是带着婚姻的枷锁而来,而子声又有婚约在身,两个人若再纠缠在一起,那真真与那些浮浪下作之人有何两样?
碧君的心中泛起阵阵的酸楚,她转过头苦笑了一下之后对子声说道:“你要讲些什么我已然都知道了,你待我的好我都记着,可是还是那句话,今时今日我们都身不由己,听我的话,回去吧。”
碧君说完,也不敢再看子声一眼,她怕自己再呆下去,会控制不住自己而将多年的心事全部说给他听,那样的话可真真就更加难以了断了。想到此,碧君匆匆向前走去,任凭子声在身后喊她,她始终都没有再回头。
子声本是兴冲冲而来,却没想到是这样的局面,他怅然若失的站在盛夏的烈焰之中,却丝毫也感觉不到一点的温度,心中犹如跌入了冰窖一般寒凉彻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