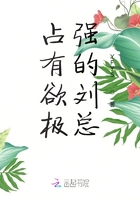出嫁前,三娘曾经给猫儿讲过夫妻之事,说是要脱了衣服,痛了,这才算是夫妻。猫儿不要做别人的妻子,只待喜帕掀开后,一刀劈下新郎官,然后掠了曲陌回山头,占山为王!
花耗要走了,猫儿挤在送行人中,站在“肥臀”背上摆着小手。花耗四下来寻,终是看到猫儿,笑容瞬间灿烂,隔着人潮对猫儿点点头,将大拳头一攥,用行动示意猫儿等着自己,一定凯旋归来!
当花耗的身影完全消失,猫儿跳坐到“肥臀”背上,回了楚府,与楚汐儿一同见了楚大人。
楚汐儿将猫儿是女儿身的事实说出,又说请楚大人认猫儿做干女儿,猫儿愿意代自己嫁人。
楚大人装模作样地询问一番,自然答应了下来,便开始隆重其事地准备认干女儿。一时间,楚府上下张灯结彩,好不热闹。
其实,楚大人之所以当上大官,最初靠的就是这定亲之说。
楚大人原本有一儿二女,都先后天折。算命的说,这是做了天不容的恶事,折了福。楚大人立刻开始做善事,想着弥补过错。
也因为机缘巧合,楚大人帮衬了一位京城大官。那大官感激在心,许诺,若楚大人得了女儿,两家便订下娃娃亲,结成亲家。
不多年,楚大人果然又得一女,可是,任谁也想不到,这最小的女儿也夭折了,此门亲事自然没了着落。就在楚大人的痛心疾首中,他到自家当铺巡视,看见了绣有特殊字样的小棉被,当即眼睛一亮,带人追出,认下了这个孩子。而至于其中缘由,楚大人闭口不谈,只说是对不起楚汐儿母女了。
然而,楚大人的靠山一去世,靠山的儿子越发不争气。楚大人自然不想将自己“唯一的女儿”送到那里,白给了已然无用的人家。
这女儿的妙用,一可以示好,二可以做耳目,自然要放到最利于他升官发财的地方。
若不是楚汐儿自己找来代嫁之人,他也想着寻了模样不错的丫鬟,认做干女儿,代嫁过去。一方面别人不能说自己不顾情意毁坏婚约,另一方面也好将楚汐儿嫁个更利于自己飞黄腾达的地方。
当一切准备妥当,楚大人在等着猫儿跪拜爹爹时,大家却找不到这只灵敏的猫儿了。楚大人气得胡子都竖立起来,楚汐儿从旁安抚着,急得额头隐见汗水,生怕猫儿毁约跑了。
猫儿则是优哉游哉地躺在曲府大树上,跷着二郎腿,啃着果子,望着曲陌作画的身影傻笑着,不消片刻,已经打上了微微的鼻鼾。
曲陌抬起头,望向愈发瞌睡的猫儿,眼中划过一抹忧色。他转过身,唤了护卫,将一笔信笺交到护卫手上,吩咐道:“去找西葫二老,若找到,重礼请回。”略微思索一下,继续交代道,“无论以什么手段,那两人,必须带来。”
护卫领命离开,曲陌抬头望向树上睡得香甜的猫儿,思绪一时间随着猫儿的呼吸起伏着。
猫儿醒来时,已经是天色将晚。她闻到曲陌房间里有香气传来,便一骨碌爬起,由修好的窗口跳进去,弯眼一笑,自然坐到曲陌身旁,心满意足地用美食填着自己的肚子。
猫儿不喜欢清淡的小菜,最喜欢吃鱼,怎么吃都吃不够,但却容易被鱼刺伤,时常对着镜子张大嘴巴往外拔鱼刺。
曲陌却是只喜清淡口味,很少吃荤菜,即使吃,也只因猫儿讨好地往他饭碗里夹上两筷,他才吃下。
一顿饭下来,筷子很少互相磕碰上,却是菜色都见少。
再到吃晚饭时,呈上来的鱼肉都变成了挑完鱼刺的净肉。
吃好后,猫儿抹了抹唇角,就回了楚府。
楚大人虽然气得胸口起起伏伏,但也不好冲着猫儿发脾气,只能狠狠地怒哼一声,甩袖子,转身出了大厅。
这,就算是礼成。
猫儿仍旧一身男装,每天在楚府和曲府之间两头跑,偶尔半夜也溜达到揽月楼,却从来不敢去浮华阁。猫儿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明明银钩对自己很好,但只要一想着靠近那个方向,这双腿就是迈不动,身体某个地方就涩涩地难受。
就这样,猫几天天在曲府和曲陌一起吃饭,晚上又回楚府睡觉,偶尔一高兴,还能灌下一壶好酒。即便曲陌不常和猫儿说话,但护卫们看得明白,自家公子对猫儿绝对是纵容的。即使猫儿喝高了,抱着公子,公子也只是微红着绝美容颜,将猫儿抱到床上,好生安睡。
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外面已经风传楚大人收养的女儿千娇百媚,知书达理,蕙质兰心,当然,这全部归功于楚大人的小道消息。咳……也亏他能夸下这海口。
实际上,猫几天天半夜爬墙,稀里糊涂地睡在曲陌床榻上,还流出了不和谐的口水。偶尔路见不平,举着拳头就上去捶打一番,根本就看不见任何淑女迹象。
时间斗转,原本给楚汐儿定做的凤冠霞帔悉数落在了猫儿身上,又经过丫头们的巧手装扮,猫儿那原本就是块璞玉的材料,在顷刻间俨然成了异常绝色的美人。
丫头婆娘们全部看傻了眼,暗道:当初只知道楚大人认了个干姑娘,今儿让给收拾收拾,不想竟然被三娘领到了猫儿房间,衣衫一换,这才发现,这个半大小子,竟然是个俏生生的姑娘!
柳眉轻画,猫眼细描,朱唇一点,淡晕红腮,眸子莹动间,端的是国色天香中的诱人精灵,丢了世俗的粉黛,却在那露珠璀璨的瞬间,倾城一笑,刹那芳华。
其实,别说是外人,就算是楚家大院里的妻妾们,也没有几个知道猫儿就是代嫁新娘。一方面是没想到,另一方面根本就是不关心。
再说曲陌,即使他的心思极其缜密,也没能将楚府传出的待嫁女子与猫儿联系到一起。更何况猫几天天到曲府报到,俨然一副赖定曲陌的架势。
至于银钩,他一直与猫儿赌气,好几次站在街角看见猫儿由楚府出来,却不是往自己的浮华阁走。心中的气恼自然层层累积,干脆出城外游,省下这份惦念的心思!
这边,三娘看着猫儿越发心酸,不敢摸着良心,怕生生羞愧死自己。夜半垂泪,暗道:若不是小篱跪在自己脚下说此生若不嫁给耗子,那便一头撞死在后院的石井上,她怎能忍心将猫儿代嫁给风流公子?可是她这个做娘的,又怎能眼睁睁看着女儿去死?只能对不起猫儿了。
三娘含泪咽下亏欠苦水,更加细心地帮猫儿多添置了几套新嫁衣,又掏出这几年存的私房钱,留下一半给楚汐儿出嫁时用,另一半全部给了猫儿,添了一只珍稀坊做的珠花。虽然明知道楚大人为了面子也不会短了猫儿的嫁妆,但三娘这样做,不但是为了猫儿爹娘的嘱托,也是为了让自己心里好过一些。
看着眼前身穿嫁衣的猫儿如此灵动美丽,真不晓得猫儿的生母又是怎样的明艳动人?
唉……
虽然猫儿未来的相公有些好色,口碑甚是不好,但任谁看着这样的宝贝,也不会狠心对待吧?
虽然猫儿不是以楚大人的亲生女儿嫁出,但好歹也算得上是义女,排场也够风光,猫儿她爹她娘,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三娘一边为猫儿能嫁个有钱人家而开心,一边却是深深地自责,必须用各种借口来缓解良心上的不安,不然怕是撑不过去的。
猫儿不知道三娘的百转心思,只是在穿喜衣时,偷偷将卷好的“千年青锋镀”大菜刀塞到了用“赤藤”做捆绑的后腰里,心里嘿嘿一笑,只待晚上劈了新郎脑袋,自己就打劫了曲陌回山上去称王!
盖头一盖,喇叭一吹,轿子一抬,猫儿就直接嫁人了。
要说这其中少了什么重要环节?那当然是骑坐在高头大马上的……新郎官!
确实,当猫儿被人塞进轿子时,三娘偷偷将眼泪抹掉,花锄气得攥紧了拳头,楚汐儿心中虽有不忍,更多的却是庆幸今天出嫁的不是自己,只想着这原本就是猫儿的婚事,也算是有始有终。
楚大人干脆眼不见为净,掸了下袍子,冷哼一声,转身走了。
轿子在皇城里转了一圈,晃晃悠悠地抬到了富贵人家。
富贵人家的老管家终于在轿子落地那一刻,汗水湿透地将新郎官拉扯了回来。
那新郎官虽然没穿一身新郎喜服,却着了一件金钩艳粉色的衣袍,风一吹,艳丽得仿佛是一只招摇花哨的蝴蝶。他就那么倚靠着门框,唇角轻挑着一分不屑,如此半眯着风情万种的桃花眼睨着花轿,倒是要看看,那楚家老东西将什么货色塞给了自己。也许,新娘子暴毙是个不错的主意呢,谁让他此刻心情非常不爽,旁人死活,他才不管。
轿子停下,喜娘掀起帘子,轻声唤道:“姑娘,下轿了。”
轿子里面一直没有声音,叫喜娘心生疑惑,伸头一看,新娘还在啊,怎么不应呢?于是,又唤了一声:“姑娘,下轿了。”结果,里面人仍旧毫无声响。
此时,新郎官一抬手,示意喜乐噤声。
接着,喜帕下的鼻鼾声便隐隐传来。嗨,别说,还真是此起彼伏。
众人,傻了……
即便是经历了无数喜事的喜娘,这大辈子,怕是也没见过在花轿里睡觉的新娘,一时间,嘴巴张得老大,忘记了如何才能闭上。
一声轻笑传来,那原本倚靠在门框上的新郎官向轿子迈出一步,却又停住了脚,转而一挑眉峰,问管家:“楚家?”
管家这刚微凉的汗水在顷刻间刷地流下,忙弯腰点头:“是是是……”
新郎官的桃花眼一眯,问:“代嫁过来的……贤良淑德?”
管家的汗水已然如瀑布般哗哗而下,将头垂得仿佛要弯折般用力:“是是是……”
新郎粉色的唇一弯,转身进了府邸,却扔下两个字:“甚好。”
管家彻底傻了,这多年的老寒腿也不痛了,因为已经没有知觉了。暗道:少爷说甚好,这个……什么甚好?少爷的脾气一向阴晴不定,这个甚好,实难猜测,实难猜测。
即使想破脑袋,老管家也不可能将轿子里的新媳妇联想到甚好两字上面。
新郎官进入府邸后,老管家望着花轿,有种想要退货的冲动。他,实在愧对老主子的嘱托啊!瞬间老了十岁的脸上,有着以死明志的意向。老管家深深吸了一口气,使个眼色给喜娘,让喜娘将新娘子弄醒,这脸可是丢尽了!
喜娘早就瞧出了眉眼高低,这少夫人是不讨喜的,如此粗鲁,怎么能匹配上那绝艳无双的新郎官?那新郎官虽然是个男子,却生得如此勾魂,单是看了一眼,险些就要了她的老命。
喜娘觉得今天这事儿也丢了她的脸,新娘竟然在下轿时睡着了,心里生了恨意,弯下身子,抬手就往猫儿的大腿掐去!
只听哎哟一声,一个花红的球状物腾空而起,在惊呼后,重重落地,眼睛虽然没有闭上,人已经昏了过去。
接着,从轿子里踏出一只绣花鞋,一个红色身影闪身跳出轿子,身形一晃,忙用手捂住头上沉重的凤冠,待适应了这个重量后,用眼睛瞄着脚下的路,伸手摸着方向,往大门里走。
一干人等已经忘记了反应,就这么看着新娘子一步步晃到了府邸门口,却因有喜帕挡住了视线而一头撞在了门框上。砰的一声后,新娘子身子突然后仰,却摇晃着膀子挣扎着……
一个努力回弹,猫儿终于阻止住身子后仰,却又是一下撞在了门框上,发出咣的一声!
众人齐齐倒吸气,动作如此统一。
猫儿怒了,一拳头袭出,直接击飞了门框,震掉了一侧大门!然后提起裙摆,气呼呼地大步往里面走去。
猫儿听三娘的话,明白这喜帕是必须要由新郎官来掀开的,不然是不吉利的。猫儿怕麻烦,怕不吉利,怕自己砍不了新郎官,无法抢了曲陌回山上,所以,猫儿忍着!
磕磕碰碰中,也不知道新房怎么走,她忍无可忍,随手抓过一个总在自己旁边晃悠的穿艳粉色衣袍的人,虽然只能看见新郎官的鞋子和衣衫一角,但绝对不影响猫儿震耳欲聋的声势!猫儿暴躁地怒吼道:“新房在哪儿?!”
被扯的新郎官好脾气地没有吭声,单是在猫儿能看见的小小范围里,将修长的手指往旁边一指。
猫儿气呼呼地放开了被自己钳制的人,三步并两步地蹿了过去,心里寻思着,这结婚还真不是一般人干的活,今天多亏来的是她猫爷,若是那弱弱的楚汐儿来,怕是没等进门,就得被这头上的重量压得犯心疾!
想到这里,猫儿开始扬扬自得,一把推开喜门,按照三娘说的,一屁股坐到床沿上,然后就等着新郎官来掀了自己的喜帕子,再然后……嘿嘿……一刀砍下去!
猫儿这边盘算着,渐渐地发觉热得慌。这大热的天,喜服可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大红布,再加上这遮挡面部呼吸的喜帕,还有压在头上的凤冠,只觉得热得无法喘息。
猫儿记得三娘说过,不能自己掀开喜帕,但却没说不能脱了喜衣啊?于是,心动了,行动了。猫儿站起身,胡乱地扯掉喜衣脱在了脚下,仅着一身红色的内衣,一屁股坐到喜床上,烦躁地拉开些衣领,顶着完好无缺的重冠,继续等着。
门外的新郎官看得是目瞪口呆,却在下一刻无声地抚着肚子,颤抖着肩膀,笑得险些背过气去。幸好他示意下人都去了前院,不然,这大好的风光可不就便宜了别人的眼睛?他若是因为嫉妒,挖了别人的眼,还真有些不讨喜啊。如此,甚好。
猫儿在等待中煎熬,却也在轿子里睡够了,此刻精神得无法入睡,单单想着等会儿是横劈还是竖劈?或者斜劈一菜刀?
所以,当新郎官走到猫儿眼前时,猫儿才恍然反应过来,原来,那穿艳粉色衣袍的就是新郎官!忙一手摸向身后的大菜刀,屏住呼吸,等着新郎官掀开自己的喜帕。
然而,新郎官却一动不动地望着自己的……头顶?
忍无可忍,猫儿急着处理这边的事情,于是,朗声催促道:“你倒是掀喜帕啊!”
新郎官不回话,而是坐到了床沿上,伸出纤细干净的手指,非常色情地抚摸猫儿的小腰!
猫儿最怕痒,这一摸下来,已经是笑得体力不支,却仍旧用身体做着掩护,在身侧用手握紧了大菜刀,准备在喜帕掀开的瞬间……突袭!
新郎官的手终于在猫儿险些抽搐中收了手,却又将那手指在猫儿眼下晃了晃,沿着猫儿的颈项一直下滑,直到猫儿心脏的位置,就这么竖立着一根手指,感受着那有力的跳动。
猫儿被新郎官奇怪的举止弄得僵硬,不知道他到底意欲何为。
出嫁前,三娘曾经给猫儿讲过夫妻之事,说是要脱了衣服,痛了,这才算是夫妻。猫儿不要做别人的妻子,只待喜帕掀开后,一刀劈下新郎官,然后掠了曲陌回山头,占山为王!
可……这个新郎官为什么不掀她喜帕,却做什么总是摸她?
在猫儿的疑惑中,新郎官伸手抬起猫儿的小腿,脱了她的鞋子,然后也脱了自己的鞋子,抱着猫儿,就这么躺在了喜床上。
猫儿的胸口起起伏伏,咬牙道:“你!快点掀开喜帕!”
新郎官支起身,手指搭在喜帕上缓缓拉起……
猫儿心里开始紧张,攥在身后刀背上的小手被汗水弄得潮湿发黏。
新郎官却在喜帕掀到猫儿鼻息处时停了下来,轻轻俯下身,微张着淡粉色的唇瓣,轻柔地含住了猫儿那诱人的嫣红唇瓣,在身体一震中,下口就咬!
猫儿一吃痛,抬手就要掀了喜帕。新郎官却用手压住了猫儿的暴躁,继续俯下身,用唇舌细细爱抚着猫儿的小嘴,伸出灵活的软舌,沿着猫儿的唇上细细勾画着,缓缓探入猫儿口腔,想要攫取猫儿的津液甘芳。
猫儿胸口起伏,下口就去咬!
这时,一直遮挡在眼上的喜帕被新郎官瞬间掀开,那双已经有些迷离的桃花眼便生生望进了猫儿眼底!猫儿一吃惊,小嘴微张,新郎官的舌头便乘虚而入,勾起猫儿的丁香小舌,卷在舌尖品味把玩着。
猫儿傻了……
这……这……这新郎官怎么会是……银钩?!
猫儿睁着圆滚滚的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银钩贴近的眉眼,难以置信。
银钩在猫儿唇上轻轻一咬,沙哑道:“闭上眼睛。”
猫儿听话地闭上眼睛,又觉得不对,忙睁开,小手一把推开银钩。
银钩跌落在床的一边,单手支起头颅,撑着半面身子,笑睨着令他惊艳得差点忘记呼吸的猫儿,沙哑着嗓子,问:“你这一直握刀子的手麻没麻?”
猫儿一动,微微皱眉,还真麻了。
银钩笑弯了眼角,抽出猫儿的手臂,在穴位上按摩着,眼睛则是勾魂夺魄地望着猫儿,调侃道:“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见到我,你个没有良心的怕是一点儿都没想,是不是?”
猫儿虽然满肚子的疑问,却忙摇头道:“想了,真想了。”
银钩一挑眉峰:“哦?”
猫儿眼巴巴地凑过去,喃喃地道:“真想了的,就是……没敢去看你。”
银钩心中划过一抹异彩,问:“做什么不敢?”
猫儿挠头:“说不准,就是没敢。”
银钩不再细问,伸手抱住猫儿,将头窝在猫儿的颈间呼吸着猫儿的乳香,很特别的味道,没有胭脂水粉的俗气,却是浑然天成的体香,犹如还没断奶的小猫咪般招人喜爱。
猫儿被银钩的呼吸弄痒了肌肤,咯咯咯地笑开了。
银钩抬起头,一口吻向猫儿那张欢快的小嘴,炽热的唇舌纠缠间,有种想要吸取猫儿一切甘芳的冲动!
以往银钩吻猫儿都是浅尝即止,今儿个却是狂热,猫儿觉得头晕起来,连四肢都变得软绵无力,呼吸更是困难,心口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剧烈乱撞,仿佛要冲破胸腔。猫儿呜咽着闪躲,推开银钩,大口喘息着。
银钩望着猫儿那张嫣红的脸蛋,灵动的大眼弥漫上初尝情欲的迷茫,水润小唇愈发红艳诱人,端的是国色天香,令人难以自持。
银钩缓缓闭上眼睛,努力平复着自己的躁动,却无法抑制地大笑起来。那欢畅淋漓的笑意由胸腔发出,有种遂了心愿的幸福。这个小东西,终究是他的!注定是他的!谁也别想夺走!即使……是他,也不可以!
猫儿见银钩笑得如此欢快,心里也跟着高兴,却嘟囔道:“银钩,你能不能不每次见面都啃我嘴巴?”
银钩眯着勾魂夺魄的桃花眼,满是戏谑地睨着猫儿,慵懒地道:“哦,你不喜欢?”
猫儿吧嗒一下小嘴,脸上一红,朗声道:“不喜欢!嘴唇都被啃破了!”将小舌头在下唇上一舔,伸出,示意银钩看。
银钩只觉得呼吸一紧,一口含下猫儿那绽放了妖艳红花的软舌,轻轻一卷一舔,却不敢多做停留,哑声道:“猫娃,你知道喜欢与不喜欢可是比较着来的,若你嫌嘴唇痛,我可有个方法,让你不再觉得嘴巴痛。”
猫儿好奇地望着银钩,有种跃跃欲试的意思。
银钩虽然急切地想要了猫儿,但却不是个没有自制力的主儿。他与猫儿同床这么久,自然知道猫儿的身子状况,于是轻咳了一声,问:“猫娃,你……来过桃花癸水吗?”
猫儿一脸莫名其妙,反问:“什么是桃花癸水?”
银钩的脸染上红潮,换了个名词,回道:“桃花癸水就是红潮。”
猫儿又问:“什么是红潮?”
银钩错开猫儿清澈如泉的目光,苦笑一声,环绕住猫儿的腰身,揽入自己怀里,缓缓平静着呼吸,心中却给楚大人记上了一笔。他竟然将还没成人的猫儿代嫁出来,这笔账,早晚要算!
猫儿不依,又抬起头,扯了银钩的衣衫,问:“什么是桃花癸水?什么是红潮?”
银钩无法,只得捏着猫儿的小鼻子,卖弄道:“佛曰不可说,且等时机到了,你自然就会明白。”
猫儿瞪眼:“装吧你!”
银钩飞眼:“这也看出来了?”
猫儿扯银钩袖子:“说说,你怎么是这家的少爷?”
银钩装模作样地思索道:“这个嘛,因为我的爹是北斗将军,所以我自然是这家的少爷喽。”
猫儿气呼呼地转过身。银钩就手拔出猫儿身后的“千年青锋镀”大菜刀,用手指轻弹一下,只觉得那声音犹如龙吟般悦耳,轻点下头,赞道:“好菜刀。”续问:“猫娃娘子,你不是打算在我掀开喜帕时给为夫一菜刀吧?”
猫儿一把夺过大菜刀,往枕头下一塞:“幸好你是银钩,不然早就被我砍成两截了。”
银钩笑了,把猫儿抱入怀里,用手指逗弄着猫儿的下颌:“啧啧,还是只难驯的野猫。”
猫儿被银钩弄痒了下巴,闪躲着咯咯笑起来。
银钩将笑软了的猫儿抱入怀里,抚摸着她软软的发丝,道:“爹因曾经受了楚大人帮衬,便订下了这桩娃娃亲。爹去世后,我又是没出息的主儿,不喜朝廷上的功名,终日流连花楼,还开了家浮华阁。楚大人一心攀高枝,对我自然不屑一顾,不想,今日竟为了堵住众口,将你这个小东西代嫁过来,哈哈……哈哈哈哈……”
见银钩笑得开怀,猫儿也眯上了眼睛,乖巧地窝在银钩怀里,只觉得心里舒服起来。
银钩问:“猫娃娘子,你原本打算谋杀亲夫后如何去向?”
猫儿冷不防银钩的问题,张口便答道:“就去找曲陌……”后面的话却万万说不出口了,因为银钩的目光已经如锋利的刺般扎入猫儿的眼,好冷。
猫儿下意识地后躲,银钩却妖冶一笑,抬手抚摸上猫儿的脸蛋,柔声问:“然后呢?”
猫儿受了蛊惑,咽下口水,有些困难地开口道:“然后……然后……回……山……啊!”
断断续续的话被叫声打断,银钩已经压在猫儿身上,困住她的四肢,张口就向猫儿的颈窝咬去!
猫儿失声痛呼,那喉咙本来就响亮清透,这一喊,声音更是直达云霄,震得房梁直颤!
不远处偷听的老管家险些被刺透耳膜,却又笑弯了布满皱纹的老眼,大感英家有后了!少爷终于娶少夫人了,老将军在天有灵,少爷神勇着呢,一准儿给少夫人种上英家种子!虽然少爷改姓了银,但那种子总归是英家的,定然强悍勇猛!一准儿能生两个……不……三个……不,一准儿能生十个男娃!
猫儿从来不是受欺负的性格,在痛呼出声后,就与银钩扭曲到一起,两人一滚,掉到地上,又发出一声极其暧昧的低吟,听得老管家都红了老脸,准备退去。
屋子里,猫儿一个蹿起,膝盖落下,直顶在银钩肚子上。
银钩痛呼一声,忙道:“轻点,轻点,要夹坏了。”老管家脚步一滑,差点摔地上去,敢情,这少夫人还是个……生猛的。
猫儿怪叫一声,就又往银钩身上招呼。银钩一个翻身跃起,回身向猫儿袭去。猫儿一躲,跳到床上,神气活现地道:“来啊!你来啊!快点,来啊!”老管家红了老脸。其他偷听的小厮丫头们都红成了被煮熟的大虾。
两个人你来我往地过起了招,将屋里的木制床板摇曳得嘎吱作响。
银钩一长腿劈下,猫儿一闪,跳上银钩的后背,银钩将猫儿一甩,猫儿转个半圆后用双腿夹住了银钩的脖子。
银钩沙哑道:“放开啊,夹得太紧了,真想要我香消玉殒?”
猫儿喘息道:“就不放,夹死你!”
银钩求饶,大呼道:“再夹,我就过去了。”
猫儿猖狂一笑,亢奋道:“去吧!我掐人中给你弄醒,然后再夹昏你,再弄醒,再夹昏!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老管家和所有偷听的人,全部是喷血爬走的。少夫人,果然……生猛!
两个人在打打闹闹中度过了春宵。第二天一大早,猫儿从银钩怀里抬起头,将带血的手指举到银钩面前,说:“你看,你把我弄伤了。”
银钩一愣,忙抓住猫儿的手指,问:“哪里伤了?”
猫儿转过身,爬起,将小屁股拱向银钩,身体柔韧度绝佳地转过身,指着自己的屁股说:“喏,出血了。”
银钩呼吸一紧,修长的手指隔着猫儿的喜衣,缓缓抚上猫儿的……私处。猫儿一颤,银钩一抖,提起的手指上赫然染了朵怒放的红花。
银钩支起身子,将猫儿抱入怀里,举起手指哈哈大笑起来,兴奋道:“猫娃娘子,这就是桃花癸水,也称为红潮,证明娘子可以为人妻了。”
猫儿盯着银钩那根手指,仰头道:“你说流血就好,装什么有学问?若说这个,我小时候就常常流血,早就可以为人妻了。”
银钩听闻猫儿所言,笑得前仰后合,连带着呼吸都不顺畅了。
猫儿摸着自己的肚子:“肚子有点儿难受。”
银钩伸手为猫儿揉着小肚子,眼底的宠溺溢出,温柔地看着她。
猫儿肚子舒服点儿了,就伸着懒腰站起,往地上蹿去。
银钩拉过猫儿,问:“做什么去?”
猫儿晃了晃胳膊:“洗漱,吃饭啊。”
银钩一挑眉峰:“就……这么洗漱,吃饭?”
猫儿也一挑眉峰:“那你还想怎样?打过再吃?”
银钩扫了一眼猫儿被血污了的衣服,脸上染了分不自然的红晕:“总得处理一下吧。”
猫儿一摆小手,大气磅礴地道:“此等小伤,没事!”
银钩唇角隐约抽筋,转开脸,怕自己忍笑的表情刺伤了猫儿的自尊心,深呼吸后,才一本正经道:“虽然是小伤,但还是得包扎一下,而且……这个伤口虽然不痛,但每个月总是要流些血的。咳……就这么说吧,每个女人都会这样,猫娃娘子需要习惯。”其实,银钩大可以让老妈子来讲解给猫儿听,这样他自己就不用这么尴尬了,不过,他不想猫儿的任何一个成长与他人分享,哪怕是女子也不可以!
猫儿嘴巴张开,圆滚滚的眼睛盯着银钩乱转,最后停留在银钩的下体上,伸手探去,问:“你每个月也流血吗?”
银钩一把抓住猫儿那浑然不知深浅的小手,一脸黑线地抽搐道:“这个……我除了鼻血外,其他地方不流血。”
猫儿满眼的羡慕,感慨道:“唉……这还真是麻烦,幸好每个月我下面流血不疼,你流鼻血也不疼,不然真是遭罪了。”
银钩一口气憋在胸口,将脸涨成了茄子色,想解释自己的鼻血和猫儿的流血不是一回事儿,但见猫儿望向自己的眼睛,所有的解释皆化为一声轻笑。对与错,是与非,不再重要。
两个人研究半天,猫儿终于在银钩的大力指导下完成了第一次用女性物品的历史性任务!
其实,银钩也是一知半解,却极是聪慧,想了想,便知道用布袋装棉花来用,虽然极其奢侈,但不会伤到柔软肌肤,应该很舒服。
猫儿不会针线活,银钩却使得一手好针法,低垂着眼睑,十指飞跃,不消片刻,一个经过两人共同研究的女性用品便成形了。
猫儿高兴得拍手叫好,忙把自己的袜子塞给银钩,只说昨天踢银钩弄坏的,就得他缝补好。
银钩不和猫儿争辩,小媳妇样地坐在床上,盘着腿,有模有样地缝补着。那长长的睫毛微翘,眸子里专注的神情令人痴迷,猫儿看着看着,竟然失神了。
将臭袜子补好,塞给猫儿时,就看见猫儿直勾勾地望着自己,唇边还有隐约的口水。银钩不由得上挑了桃花眼,想摆个更加风情的姿势,却因猫儿的一句话,险些掉床底下去。
猫儿说:“银钩,你别挤眼睛了,都出眼屎了。”
银钩一头倒入被褥中,蒙头哀号道:“呜呼,奴家的……娇颜啊……”
其实,猫儿还是挺向着银钩的,在去换月事袋时还不忘从袋子里揪出一块棉花,塞到银钩手中,说:“这个给你,等你流鼻血时,用上。”
银钩感动得颤巍巍的,竟将那棉花咬在了牙齿间,两口,咽下了。
结果,猫儿傻了。
银钩眯着桃花眼冲猫儿眨了两下,然后从猫儿的嫁妆里取出新衣裙,拿到猫儿面前比量着,为那毫不矫揉做作的容颜所悸动。
猫儿见银钩比量着女装,不由得咂舌道:“银钩,你穿女装一定很美。”
银钩微愣,将那红艳的女装往自己身上比量着,还对着镜子摆了个仙女散花的造型,冲着猫儿飞了一媚眼,嗲声道:“怎样,奴家美吗?”
猫儿狂点头,认真赞美道:“美,比我家院子里的花母鸡还美。”
银钩的动作僵硬在半空,却又是勾唇一笑,问:“比曲陌人美吗?”
猫儿第一次认真思考起来。曲陌和银钩都美,可还是不一样,到底哪里不一样她说不出来,但若说谁最美,猫儿还是觉得曲陌最美。当下回道:“曲陌最美。”
银钩收了姿势,将新衣往地上一扔,转身就出了屋子。
猫儿忙追了出去,扯住银钩的袖口,也不说话,就这么眼巴巴地望着。猫儿这是委屈了,明明是银钩问的话,她说实话,银钩却又生气。
银钩仰望浮云,伸手将猫儿抱在怀里,霸道地说:“这次我不生你气,下次,若有人问起我和曲陌谁美,你一定要说银钩最美,可记得了?”
猫儿点头应了。
银钩勾起唇角,笑得一脸奸诈,他就不信了,曲陌有天会不问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