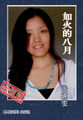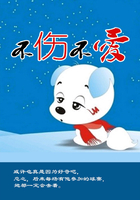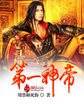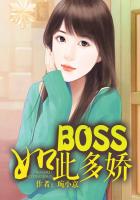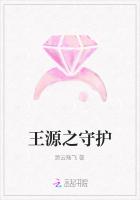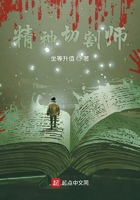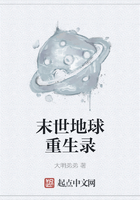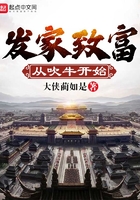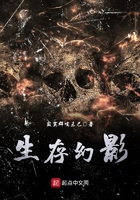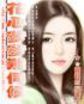从这天起,玄奘开始在玉华山弘法台上重译《金刚经》。考虑到此地远离弘福寺译场,缺乏助手,皇帝特命官员杜行顗等人做笔受。
自从在弘福寺成立译场以来,玄奘一向保持着严格的译经计划,绝非抓到哪本译哪本,也不是皇帝叫译哪本就译哪本。事实上,之前李世民也从未干涉过他的译经顺序,可能是因为谦虚,也可能是因为没兴趣而懒得干涉。如今,皇帝竟主动提出让他重译一部经,并且如此关注,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都是极为难得的。
学佛原本就无定法,所有的法,都必须同具体的因缘结合在一起。每个人的心性不同,执碍各异,悟道的方式自然也会有所不同。
玄奘完全依据梵本翻译,力求化解晦涩,校正讹谬,补上阙失,完善义理。最终所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其文字竟比旧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多出近一倍。[3]
皇帝仍然时不时地出现在玄奘面前,与他谈论佛法,内容大多是有关《金刚经》的——
“朕读《金刚经》,发现里面一直在说,是什么,非什么,是名什么。不知何解?”
玄奘道:“这是修佛的三重境界。‘是’为常境,因世人大多喜欢求是,却不知此为空执,有武断虚妄之相;‘非’为悟境,你明白了它其实并不是你所想的那个,你便步入了修行之路;‘是名’为证境,即脱缚见执,不再为诸相所迷。”
李世民认真想了想,摇了摇头:“朕真的很难想象这种境界。”
“陛下暂时不用去想象那些,等到了证性的那一天,自会明白。”
“朕,会有那一天?”
玄奘道:“陛下,你看这山峰坚实隽永,然而沧海桑田却可将它夷平。很多看似实实在在的事物,其实并非真相。一切都会改变的,只有断除执着,通达本来无我,才会走向证悟之道,从而看到真实的世界。”
“真实的世界……”李世民轻声自语,似乎有些想不通。
玄奘道:“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不真实、不完美的。或者说,这个世界本来完美,但是由于人的不完美,从而使这个世界看上去也显得不完美了。”
“可是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李世民道。
玄奘对此不置可否,而是淡淡地说道:“佛就像天上的月亮,我们的心就像地上的水。心不静,月影就映不出来。如果我们将这颗散乱的心静下来,月影就呈现出来了。所谓如水湛清,佛月自现。月本不来,因水清故。”
李世民道:“佛的本愿就是来度众生的,法师却说‘月本不来’,那岂不是说,佛就像一个影子?他根本就没有来过?”
玄奘道:“对啊,要不怎么叫如来呢?他好像来过,但其实没来。佛只是如来在这个世间的一个投影。”
李世民摇头道:“朕不相信。朕一直觉得,佛陀应该是实实在在的。”
玄奘道:“佛陀当然是实实在在的。这个世界上唯一实在的就是佛陀了,别的东西都不实在,包括佛度众生这件事。陛下觉得我把佛陀说成是一个影子很难接受,但其实陛下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只不过你以为它存在而已。就好比陛下面前的这个桌案,你以为它很实在,但其实它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一道光,或者说,是陛下心识所现的一个虚假的幻影,其存在程度与水中之月并无本质的不同。”
“如果陛下学佛念佛,佛就会在你的心中示现,如水中月一般。但是陛下放心,在陛下的眼里,他绝对实在,实在得就像陛下自己的身体一样。”
“朕的身体当然很实在!”李世民忍不住抗议道。
玄奘点头:“是啊,陛下一直以为它很实在。”
李世民愣了一下,随即长叹一声:“玄奘法师你知道吗?朕有时候真恨不得把你送到宗人府去毒打一顿,让你好好感受一下这个身体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玄奘不禁笑了:“陛下何必费这个事?沙门现在的身体就有许多障碍。这是业力所致,除了接受,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为什么?法师不是造了很多善业吗?为什么还会受苦?莫不是自找的?”
玄奘道:“佛说,有因无缘不能结果。如果说普救众生是因,那么艰难困苦便是缘。只有因缘和合,修行之人方可开悟。所以很多时候,苦难也是一种造化。”
“但是朕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李世民坏笑道,“法师前世做的孽太多了,即使今生为善,也还是要受很多的苦。”
“有这个可能。”玄奘认真地说道,“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是,无始劫以来所有的恶业种子全都集中在今生报了。”
李世民一愣:“为什么?难道法师今生就要成佛了吗?”
“因为今生我修行了。”玄奘道,“就好比扫地会将地上积累的灰尘扬起来,修行人也会将自己无始劫以来积聚的恶业种子扬起,以至于看起来会比不修行的时候还要不顺。这大概就是陛下觉得因果有时会不灵的原因吧。”
李世民默默皱眉,似在思索。
玄奘接着说道:“对修行人来说,今生报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我知道如是因生如是果,任何苦难都可以坦然接受,身苦但心不苦。”
十月初一,玄奘译完了《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上表呈给皇帝。李世民欢喜无量,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喜欢这部经。
深秋的玉华,寒意越来越浓,直到一场飞雪过后,皇帝才终于意识到山间不是久居之地,下令于十月十六日起驾回京,玄奘也跟随皇帝返回了长安。
出使归来的王玄策带着几个重要俘虏,急匆匆地赶到宫中面君缴旨。玄奘则辞别皇帝,径直回到了弘福寺。
当日没有译经,玄奘只将自己在玉华宫中新译的几部经交给译场诸德查验,让他们看看有无值得商榷之处,同时又向他们了解了一下最近译场的情况。
玄觉拉着新剃度的怀素来见玄奘,看着这个衣着整洁行为规范的少年沙弥,玄奘心中甚是喜慰。
然而,到了黄昏二时的讲经时间,玄奘却被两个突如其来的问题闹了个焦头烂额。
说起来,这也是因为李世民突然降旨大规模度僧引起的。一些高僧与朝廷高官有些联系,自然想要了解一下皇帝为什么会突然度那么多僧。此事涉及国家的宗教政策,总得给个说法,真的是诏书上写的那么简单吗?
官员们当然不知道那个中秋之夜皇帝都和玄奘法师说了些什么,有人在朝堂上询问,李世民也只随口回答:“朕前段日子身体不佳,你们是知道的。因为亲近法师,学了佛法,方才有所好转。朕想做些功德,问法师何所饶益,法师回答,度僧为最。就是这样。”
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京城的佛教徒与非佛教徒们都在为此事议论纷纷。
玄奘原本不打算在回到译场的第一天就重回讲肆的,但是今天来的人实在太多了,都说要请三藏讲经答疑,他只好出来。
结果一坐上狮子座,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当年达摩祖师去见梁武帝,武帝说:‘朕即位以来,度僧写经不可胜数,有何功德?’祖师回答:‘无有功德。’可是今上问法师:‘欲树功德,何所饶益?’三藏的回答却是:‘度僧为最。’为什么三藏的回答与达摩祖师不同?”
听到这个问题,玄奘不禁惊奇于京城道俗消息之灵通,顺口反问道:“为什么玄奘的回答一定要与达摩祖师相同呢?”
提问者说:“我们都知道达摩祖师是来自佛国的大菩萨,他的回答是一定不会有错的。三藏该不会认为自己的修为已经凌驾到祖师头上了吧?”
玄奘顿时哭笑不得:“当年佛陀讲经,弟子们同处一师座下,听到的内容却完全不同,每个人都以为佛陀是在单独为自己讲经。有时同一个问题,佛陀可能对一个人回答是,对另一个人回答否,但一定都是对那个人最有帮助的答案。以八万四千种方法对治八万四千种病,这原本就是佛陀教化众生的法门。”
这个答案一出,立刻就有人尖锐地提问道:“三藏这是在自比佛陀吗?”
“玄奘不敢。其实世间道的圣贤也是如此,比如孔子在回答弟子的提问时,也常会出现同一个问题在不同弟子处有截然不同答案的时候。这还只是同一个师尊、同一个时代、同一种情形之下,仅仅因为听讲者的不同,为师者的说法就不同。如今不仅今上与梁武帝不同,玄奘与达摩祖师不同,便是大唐与当年的大梁也不相同,仁者凭什么就认为这个问题一定要有相同的答案呢?”
提问者顿时哑然,另一边却传来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又是佛陀又是孔子,看来三藏还真是志得意满啊!”
这声音不大,却是刚好能让玄奘听见。他朝发声的地方望了一眼,只看到一群普通装束的僧侣在朝台上观望,脸上的神情甚是鄙夷。
玄奘尚未做出反应,又有人起身提问:“那么为什么当年达摩祖师对梁武帝说,度僧写经并无功德。而三藏却说有功德呢?”
这其实还是同一个问题,只不过换了一种问法而已。
玄奘心中暗叹,所谓“功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需求。莫说是几百年前的梁皇,就是在玉华山的那几个月,他对大唐皇帝所说的功德,和对尉迟洪道所说的功德就完全两样。他对皇帝说:“法须人弘,度僧为最”;对洪道却说:“功德在法身,不知真实法者,不名为功德”。两种功德,一种是有漏的,一种是无漏的,但都是他们目前所需要的。对于佛门弟子来说,这件事要理解起来真的就那么难吗?
再说,梁武帝时期的佛门是个什么情形?“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大梁的佛教已经到了“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程度,武帝度僧都恨不能把自己也给度进去,哪里还用得着达摩祖师去跟他说什么度僧的功德最大?
不过既然人家问了这个问题,可见是个困扰。身为讲经师,玄奘不愿像别的法师那样,以玄奥的语言将其应付掉。因而他只能耐心解答:“达摩祖师是从出世修道的角度讲功德,此功德乃是净智妙圆、体自空寂的性德,既非世间的努力可以达成,也非世间的标准可以评判,当然也不是世间帝王靠求就能求到的。对于这一点,相信在座的诸位同修也都明白吧?”
果然,现场的多数听者都在点头。
玄奘接着说道:“可是大乘佛法的入世之道,讲究的是应机度化。当今天子并非世外之人,他没有出世的想法,所问的功德与出世修行也完全不沾边儿。玄奘自然没有必要做出像达摩祖师那样的回答。因为那样做,就等于是放弃了他,除了让他感到失望和受挫外,并无其它意义。”
“三藏的意思是说,达摩祖师其实是放弃了梁武帝吗?”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玄奘摇头道:“达摩祖师并没有说,度僧写经一点儿作用都没有。他说的是:‘此为人天之果,有漏之因。’其实,对这娑婆世间的众生而言,学佛是需要先积累一些有漏的福德因缘的,这就像是远行的资粮,虽然沉重,却有必要。达摩祖师只是认为,以梁皇当时的情况,世间道的资粮已经不缺,没有必要再去刻意地追求这些东西了。他应该带上他的资粮,走上真正的修行之路。”
“那么,当今天子呢?”那人又问。
玄奘道:“当今天子与梁皇不同,他还没有开始积累资粮,这个时候就让他修无漏行,岂非空中楼阁?况且众生的心思差异极大,就连吃饭还有个口味不同,更惶论修行呢?当今天子所谓的‘欲树功德’,要的就是这‘人天之果,有漏之因’,这就是他的口味儿。”
见那提问的人不再说话,玄奘便接着往下说道:“如今我大唐佛门虚弱低迷,玄奘回国之时,看到很多地方寺院荒废、法侣断绝。僧是三宝之一,无僧如何兴教?如何弘法?这个时候圣上若是下诏度僧,于他本人、于我佛门都大有裨益。这难道不是莫大的功德吗?”
这一番回答下来,很多人频频点头。
然而那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再度响起:“功德未必有,顶多是对三藏本人的声望有莫大的提升罢了。”
这话一出,现场竟出现了稀稀落落的笑声,但更多的人却感到有些尴尬。
慧立再也忍耐不住,扬声道:“是哪位同门躲在人群里说话?佛门弟子,行事如此鬼祟,这是修行者所为吗?”
现场顿时鸦雀无声。
玄奘心中暗叹,摆了摆手,示意慧立退下。
这时,又有人起身提问道:“身出家易,心出家难。单纯地度僧就算有些功德,又怎么能说是最大的功德呢?”
玄奘道:“仁者所说固然不错,但对今上而言,这就是他目前所能做的最大的功德。”
“三藏这么说,未免太过武断了吧?”那人一脸不屑地说道。
玄奘道:“好吧,就算是玄奘武断了。但是常言道,山的高度取决于山坡的宽度。如今的大唐,就连身出家者都极度匮乏,仁者又能从中找到几个心出家者呢?”
那人顿时哑然,台下响起一片击节赞叹声,中间还夹杂着“嗡嗡”的议论声。
玄奘接着说道:“至于功德,梁武帝时期度僧的功德确实轻微,这不仅是因为那时的僧人已经太多,过犹不及。最重要的是,当时僧人出家不受朝廷限制,凡是想出家的,随时都可以出家。所以,梁帝的所谓度僧,不过是走个形式,并无什么实际意义;但是现在不同,现在的度牒掌握在朝廷手中,很多人想出家,没有度牒也出不成。这个时候陛下名为度僧,实为发放一批度牒,让心皈佛门之人能有机会得度。这与梁帝时的度僧完全不同。”
这时,又有更多的人上前质询,从诸如佛性等问题上与玄奘辩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是僧侣,还有一些是硕学的居士。
这时,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僧侣突然站了起来,声音洪亮地问道:“三藏方才说,我大唐佛门虚弱低迷,这话不假。可是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玄奘道:“佛法衰微,有很多原因。有外缘,但更多的却是内因。”
提问者冷冷地说道:“什么内因外缘?请三藏不要再顾左右而言他了,真实原因我们谁都知道,就是被朝廷压制的!”
此言一出,讲筵下方顿时一片哗然。
玄奘心中一阵无奈,他理解僧侣们的一片拳拳护法之心,但是在这样的场合如此口无遮拦,真的合适吗?
要知道,前来弘福寺听讲的可不光是佛教徒啊。
可是,不待玄奘回答,旁边又站起一位岁数大的,鄙夷地问道:“听说,今上对三藏荣宠有加,赠送给三藏一领价值百金的摩云袈裟,三藏今日怎么没披出来给大家看看呢?”
这位的消息未免太灵通了点儿吧?玄奘忍不住惊奇地看了面前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僧一眼。
想想也不奇怪,皇帝赠他袈裟,随驾前往玉华山的很多官员都知道这件事。还记得那天的宣序仪式,当他身披袈裟出现在庆福殿的时候,曾引起官员们一阵不小的骚动。
而很多上层僧侣都与官员有些往来,有的官员甚至专门在家中固定供养某位高僧,自然会将此事告知。
想清楚这一层,玄奘淡然一笑,回答道:“圣上确实赐我袈裟。不过,玄奘身上的这领已经披惯了,暂时不想更换。怎么,此事有什么不妥吗?”
“没有什么不妥。”那老僧一脸鄙夷地说道,“老衲只是有些不解,今上对三藏如此荣宠,三藏为何不趁此机会,奏请废除佛道先后的位次呢?”
此言一出,台下又是一片哗然。
佛道排序,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事实上,就连译场中的一些大德也想问玄奘这个问题,只是感到有些唐突不便罢了。如今既然有人主动提出,一众僧侣居士们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狮子座上的法师。
玄奘迟疑几许,方才问道:“佛道二教,孰先孰后,真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那老僧激动地说道,“此事涉及佛门尊严,也涉及到普通信众对佛门的信心!三藏你该不会是想告诉大众你不介意吧?当年智实、法琳二位大德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三藏你难道认为,他们的死都是自找的吗?”
这个问题提得甚是尖锐,以至于他说到后来已是声色俱厉。
台下那“嗡嗡”的议论声更大了,夹杂着零星的击节声。
旁边一位老僧听不下去了,起身替玄奘辩解道:“三藏回国不过三载,就改变了佛门十几年的颓势,试问在座的各位,有谁能够做到?”
说到这里,他又转向提问者:“你也是佛门弟子,怎可如此无礼,质问三藏?”
那提问的老僧轻蔑地一笑,声音洪亮,毫不退让地说道:“三藏的才华,莫说老衲不及,便是当年的法琳长老,只怕也要甘拜下风。他不过是为了护法,把自己的性命给搭进去的痴人罢了。除他以外,还有其他为护法而死的高僧大德,声望都不及今日的三藏,但是老衲敬重他们却甚于三藏!因为他们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而三藏却是明明有可为却不为!”
听到这番慷慨激昂的言论,台下顿时响起一片击节之声,震耳欲聋。
玄奘突然感到一阵疲惫,等到台下声音止歇,他才轻轻问道:“老师父,你怎知玄奘是有可为而不为?”
“难道不是吗?”老僧目光灼灼地盯住玄奘,“你不过是一个年事不高、僧腊不长的寻常比丘,出外游方前并未在京师各大寺院中担任过任何僧职。仅仅因为你外出游方了十几年,回国后就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尊崇,这可真是件很滑稽的事情啊!大唐国内有那么多的老法师,他们住持寺院、教授门徒,为护法殚精竭虑,其名望加起来居然都不及你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游僧高。只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攀附朱紫,不及你油嘴滑舌吗?既然你有这个本事,为何不为佛门解决这一大问题?你觉得你身为佛门弟子,尽到护法之责了吗?”
这个问题比方才所提的更加尖锐,台下又是一片哗然。
玄奘终于明白为什么很多佛门弟子都对自己有那么深的敌意了,并非仅仅是出于新旧学之争,还在于他在大唐毫无根基,以至于很多同门都对他不服。大唐是一个讲究论资排辈的国度,即使是出家人,也不太容易接受一个在外多年毫无僧职的中年比丘,声望突然超越很多有名望的老僧这一事实。
方才有人躲在人群中阴阳怪气地讥讽他,想必也是出于这种心理。
当然,如果他是个梵僧,那又另当别论了。毕竟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这个问题暂时无解,他也不打算对此做出回应。他是个讲经师,只回答有关义学方面的提问,顶多再加上佛门与朝廷的关系。他没有义务对自己的声望做出说明。
因而当众人的喧嚣渐渐停止时,玄奘只望着那个老僧,徐徐问道:“敢问长老上下?”
“不敢,老衲普慧。”
“普慧师父,玄奘想告诉你的是,关于佛道排位,不仅涉及佛道两教,还涉及到朝廷其它方面的问题。况且今上也曾说过,这仅仅是个排位。玄奘确实觉得,不需执着于此。”
“好一个不需执着于此!”普慧冷冷地说道,“三藏什么都不执着,难怪皇上一声令下,你就老老实实地为道门翻译《老子》了。”
底下再度响起“嗡嗡”的议论声,夹杂着一些起哄的声音。有人高声喊道:“是啊玄奘法师!那《道德经》是皇帝要你翻你就翻,怎么佛门硕德的临终心愿你却不愿意去实现呢?这对你而言只是举手之劳而已啊!”
玄奘越发感到无奈,此事若真的只是举手之劳,他又何必等到现在也不向皇帝开口?
道先佛后,是因为李唐皇室认了老子做祖宗,而这又是为提高李氏一门的高贵血统,以便同士门大族相抗衡的一种手段。佛门弟子若能平静地对待此事,皇帝其实是会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做出补偿的,比如贞观初期的造寺供僧。毕竟当今皇帝偏重儒术,佛道二教皆被他视为安定社会、淳厚民风的手段,并不会明显地厚此薄彼。一旦出现某种失衡,不需要谁主动去说,皇帝自己就会做出调整的。
但是,偏偏护法僧侣们不甘心屈居人后,反复上表请愿,还费尽心思地想要证明李唐非老子之后代,最终的结果却是适得其反。
玄奘甚至觉得,从贞观十一年开始,佛门与朝廷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僵,朝廷的打压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是护法僧侣们的急功近利恐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种急功近利还表现在其它方面,比如,皇帝刚从玉华山回来,弘福寺及京城僧众就联合上表,请求将皇帝与太子为玄奘所著的经序、述记刻之于金石,藏之于寺宇。
当玄奘从李世民口中听到这个消息时,心中不禁暗叹,想这皇帝刚刚对佛法有了一点儿兴趣,你们又何必那么心急呢?
好在这件事情李世民很痛快地敕准了。但是紧接着,弘福寺僧怀仁法师又发下一个大愿:临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的墨迹为铭,刻于碑石,以流传后世。
玄奘并不喜欢这种过于张扬的做法,他深知,越是在鲜花着锦的辉煌时刻,越是需要小心谨慎。就如同他在曲女城辩经胜利后,无论如何也不愿骑上那头大象巡众;回到长安时,也不愿参加那盛大的入城式一般。他只需要取得朝廷对译经的支持、对佛教的支持,至于他本人,则更愿意悄悄地在人们眼中化去……
但是玄奘深知,僧侣们的拳拳护法之心也需要得到安抚。
他想了想,庄重地说道:“请诸位同门相信,玄奘所为,皆是为了弘扬佛法。佛法会衰微,也会重新得到振兴和传扬,外缘的变化不足为虑。说到底,盛衰只是外相,佛理却清净永恒。”
“但是佛法在世间,世人的看法也是至关重要的!”有人大声反驳道。
玄奘道:“世人对佛门的看法,取决于佛门弟子自身的修行。”
“可是佛门弟子的修行,也应包括为佛法的弘扬尽自身最大的努力。”底下的人毫不退让地顶了上去。
玄奘很想说,他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而有关佛道排位之事,完全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他是做不到的。可是,他最终没有这么说。
毕竟到目前为止,他连提都没跟皇帝提起过,又怎敢说自己已经尽力了呢?
他只是觉得即使要提,也不是现在。时机未到,提了也没用。
但是这话也不能讲,因为人家会说,你不试试,又怎知有用没用?
迟疑了片刻,玄奘终于下了决心,对众僧道:“如果诸位同门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玄奘愿意尝试着向圣上进言。”
老僧普慧的眼睛瞬间亮了,二话不说,纳头便拜了下去。
紧接着,场内多数僧人也都纷纷拜了下去,当他们起来时,玄奘看到的是满场期待和感激的目光。
“玄奘法师。”一位年迈的老僧激动地说道,“你若真能说服圣上,改变道先佛后的秩序,便是为我佛门立了一大功啊!”
“是啊……”其他众僧也都随声附和,“此事也可慰智实、法琳二位大德的在天之灵,这才是真功德啊!”
玄奘彻底无奈了,心说这算什么真功德?但他也知道,自己已经别无选择。
恰巧这时有天使到来:“法师,圣上诏您入宫。”
听到这个消息,玄奘竟暗自松了一口气,不管皇帝叫自己入宫是出于什么目的,至少他可以暂时摆脱这里的压力了。
玄奘被引入太极殿的西暖阁中,此时已经入冬,暧阁中生了火盆,暖意融融。
“沙门玄奘,见过陛下。”
“法师来了,快请坐。”一见玄奘,正歪在软榻上看奏章的李世民立即直起了身。
再次施礼后,玄奘在皇帝身边坐了下来。
“朕这次找法师来,是有三件事要说。”
“陛下请讲。”
“一件是法师的私事。”李世民用手指点了点旁边案上一只精致的檀木匣子,“我大唐使臣王玄策给法师做了一回信使,这里面是那个天竺公主带给法师的书信和礼物。呵呵,真是天书啊,朕一个字都看不懂,问了安那怙提和尚才知道,只是一封报平安的书信。”
说这话时,皇帝的神情不无遗憾。
王玄策是大唐官员,自然不同于雪山地区那些不懂规矩的国王和使节,从外国带回的东西,不管是带给谁的,都首先拿给皇帝过目。
李世民心中毫无隐私观念,身为皇帝,他自己本身就没有什么隐私,自然也不会将臣民的隐私当回事。看到这封据说是天竺公主写给玄奘法师的信,大唐皇帝心中的好奇顿时不可遏制,想都没想就命人拆开。
可惜信上全是弯弯绕绕的梵文。看不懂没关系,叫来担任通译的安那怙提翻译给他听。安那怙提本是个睹货逻僧,对玄奘一向敬若佛陀,因而对唐皇的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只是圣命在身,又不敢不译。
信不长,完全就是做弟子的向师父报个平安,祝师父一切安好,顺便汇报了自己这些年来的修行情况,又简单说了说摩揭陀的近况。这种佛教徒之间的往来信件,李世民听得兴味索然,脸上禁不住现出失望之情。
转念一想,这安那怙提毕竟是个僧侣,又是玄奘推荐进入使节团的,难保不会在某些方面有所忌讳,关键地方少翻几句也听不出来。于是让他出去,又叫来一位俗家译员,再次翻译。
这位俗家译员的梵文能力显然比不上安那怙提,译得结结巴巴不说,有些句子前后颠倒,听得不知所云。但因为前面安那怙提先译了一遍,因而皇帝还是听懂了——仍是这些话。
既然在信上看不出花来,那就翻翻匣子里的东西吧。结果,也就是几部贝叶经外加一领褐红色长衣。王玄策解释说,这叫僧伽胝衣,是印度高级僧侣穿着的。
李世民彻底无奈了,心想这和尚真是扫兴得很。也罢,这些东西既然是带给他的,那就给他好了。
玄奘倒是松了一口气,既然有书信物品,那也就意味着罗阇室利是安全的。他立即合掌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