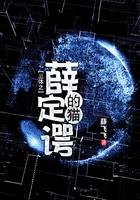在暗夜的漆黑与冰冷中醒来,他伸手探触睡在身旁的孩子。夜色浓过魆黑,每个白日灰蒙过前日,像青光眼病发,黯淡了整个世界。他的手随着口口宝贵的呼吸轻微起落。掀开塑料防雨布,他坐起来,身上裹着发臭的睡袍与毛毯;望向东方,他搜寻日光,但日光不在。醒来前的梦里,孩子牵他的手,领他在洞穴内游走,照明光束在潮湿的石灰岩壁上晃动,两人像寓言故事里的浪人,被体格刚硬的怪兽吞食,迷失在它身体里。幽深石沟绵延处,水滴滑落有声,静默中,敲响人世每一分钟,每个小时,每一日,永无止息。他俩驻足在宽广的石室里,室中泊着一面黝黑古老的湖,湖对岸,一头怪物从石灰岩洞伸出湿淋淋的嘴,注视他俩的照明灯,目盲,眼瞳惨白如蜘蛛卵。它俯首贴近水面,像要捕捉无缘得见的气味;蹲伏着,体态苍白、赤裸、透明,洁白骨骼在身后石堆投下暗影;它有胃肠,有跳动的心,脑袋仿若搏动在晦暗不明的玻璃钟罩里;它的头颅左摇右摆,送出一声低沉的呜咽,之后转身,蹒跚走远,无声无息,大步向黑暗迈进。
就着第一道灰蒙的天光,他起身,留下熟睡的孩子,自个儿走到大路上,蹲下,向南审视郊野。荒芜,沉寂,无神眷顾。他觉得这时候是十月,但不确定对不对;好几年没带月历了。他俩得往南走,留在原地活不过这年冬天。
天光亮得允许使用双筒望远镜后,他扫视脚下的河谷。万物向晦暗隐没,轻柔的烟尘在柏油路上飘扬成松散的漩涡。他审视自己所见的一切。下方的大路被倒枯的树木隔得七零八落。试图寻找带色彩的事物、移动的事物、飘升的烟迹。他放下望远镜,拉下脸上的棉布口罩,以手背抹了抹鼻子,重新扫视郊野,然后手握望远镜坐着,看充满烟尘的天光在大地上凝结。他仅能确知,那孩子是他生存的保证。他说:若孩子并非神启,神便不曾言语。
他回来的时候,孩子仍睡着。他拉下盖在孩子身上的蓝色塑料防雨布,折好,放进购物车里,再取出餐盘、一塑料袋玉米糕、一瓶糖浆。他在地上摊开两人充当餐桌的小片防雨布,把东西全摆上去,解下腰带上的手枪,放在布上,坐着看孩子睡。孩子夜里扯下了自己的口罩,它正埋在毛毯堆里的某处。他看看孩子,目光越过树林望向大路。这地方不安全,天亮了,从路上看得见他俩。孩子在毯子下翻身,而后睁开双眼,说道:嗨,爸爸。
我在。
我知道。
一小时后,两人上路,他推购物车,孩子和他各背一个背包;不可或缺的东西都装在背包里,方便随时抛下推车逃跑。一面镀铬的摩托车后视镜嵌在推车把手上,好让他注意背后的情况。他往上挪了挪肩上的背包,望向荒凉的郊土,大路上空无一物,低处的小山谷有条静静的灰色河流蜿蜒着。动静全无,然而轮廓清晰。河岸芦苇都已干枯。你还好吗,他问。孩子点点头。于是,在暗灰的天光中,他们沿柏油马路启程,拖着脚步穿越烟尘,彼此就是对方的一整个世界。
他俩顺着老旧的水泥桥过河,往前又走几英里,遇上路边加油站;两人站在马路中央审视那座加油站。我想我们应该进去看看,瞧一眼,男人说。他们穿涉草场,近身的野草纷纷倒向尘土。越过碎裂的柏油停车坪,看见接连加油机的油槽。槽盖已经消失,男人趴下来嗅闻输油管,石油的气味却像不实的流言,衰微且陈腐。他起身细看整座建筑物。加油机上,油管还诡异地挂在原位,窗玻璃完整无缺,服务站门户大开,他走进去,看见一只金属工具箱倚墙而立。他翻检每一个抽屉,但没有任何可用的。只有几个完好的半英寸长活动螺丝刀、一个单向齿轮盘。他起身环顾车库,只见一个塞满垃圾的金属桶。走进办公室,四处是沙土与烟尘;孩子立在门边。金属办公桌、收银机,几本破旧的汽车手册因泡了水而鼓胀;亚麻油布地板斑斑点点,因屋顶漏水而浮凸卷曲。穿过办公空间,他走向办公桌,静立着,举起话筒,拨了许久前父亲家的号码;孩子看着他。你在做什么呢?他问。
沿路走了四分之一英里,他停下脚步回头看。我们在想什么,得走回去,他说。他把购物车推离路面,斜斜安置在不易发现的位置,两人放下背包,走回加油站。他进服务站把金属垃圾桶拖出来,翻倒,扒出所有的一夸脱塑料机油瓶,两个人坐在地上,一瓶接一瓶倒出里面的残油。他们让瓶身倒立在浅盘里滴干,最后几乎凑到半夸脱。他旋紧塑料瓶盖,拿破布抹净瓶身,掂掂瓶子的重量:这是给小灯点亮漫长幽灰的黄昏与漫长幽灰清晨的油。你可以念故事给我听了,对不对,爸爸?对,他说,我可以念故事给你听了。
河谷远端,大路穿越荒芜炭黑的旧火场,四面八方是焦炙无枝的树干,烟灰在路面飘移,电线一端自焦黑灯柱垂落,像衰软无力的手臂,在风中低声呜咽。空地上一栋焚毁的屋子,其后一片荒凉黯灰的草原,废弃道路工程横卧原始绯红的淤积河床,更远处是汽车旅馆广告牌。除却凋零了、圮毁了,万事一如往常。山丘顶,他俩伫立寒天冷风中,呼喘着气。他注视孩子;我没事,孩子说。男人于是把手搭在孩子肩上,向两人脚下开敞无边的郊土点了点头。他由购物车取出望远镜,站在马路中央扫视低处的平原;平原上,一座城的形体兀自挺立灰蒙之中,像某人一面横越荒原、一面完成的炭笔速写。没什么可看的,杳无烟迹。我可以看吗,孩子问。可以,当然可以。孩子倚在购物车上调整焦距。看见什么吗,男人问。没有。他放下望远镜:下雨了。对,男人说,我知道。
他们给购物车盖上防雨布,把它留置小溪谷,然后爬坡穿越直立树干构成的暗黑群柱,抵达他看见有连续突岩的位置。两人坐在突出岩块下,看大片灰雨随风飘越山谷。天气很冷,他俩依偎在一起,外衣上各披一条毛毯。一段时间后,雨停了,只剩树林里还有水滴滑落。
放晴后,他们下坡找到购物车,拉开防雨布,取出毯子和夜里用得着的东西,再回到山上,在岩块下方的干燥处扎营。男人坐着,双手环抱孩子,试图为他取暖。两人裹着毛毯,看着无以名状的黑暗前来将他们覆盖。夜的袭击,使城的灰蒙形体如幽魂隐没,他点燃小灯,放在风吹不到的地方。两人往外走到路上,他牵起孩子的手,向山顶走,那是路的尽头,可以向南远望渐趋黯淡的郊野,可以伫立风中,裹着毛毯,探寻一丝营火或明灯的痕迹。但什么都没有。山壁边,山岩中的灯火只是光的微尘;过了一会儿,他们往回走。一切都很潮湿,没办法生火。吃过冰凉的简陋餐点,他俩在寝具上躺下,灯放在中间。他拿了孩子的书,但孩子累得无法听故事,他说:可以等我睡着再熄灯吗?可以,当然可以。
他躺了很久,还没睡着。过了一会儿,他转身看着男人。微弱的光线中,脸颊因雨丝敷上了条条暗影,像旧时代的悲剧演员。我可以问一件事吗,他说。
可以啊,当然可以。
我们会死吗?
会。但不是现在。
我们还要去南方吗?
要。
那我们就不会冷了。
对。
好。
好什么?
没什么,就是好。
睡吧。
好。
我要把灯吹熄了,可以吗?
好,没关系。
又过了一会儿,在黑暗中: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可以啊,当然可以。
如果我死了,你会怎么样?
如果你死了,我也会想死。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
对,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
好。
他躺着,听水滴在树林里滑落。这就是谷底了,寒冷,沉寂。虚空中,刺骨而短暂的风一阵阵来回运送旧世界残余的灰烬:推进,弥散,然后再推进。万物都失了基底,在灰白的大气中顿失所依,只能靠呼吸、颤抖与信仰存续生命。但愿我心如铁石。
黎明前他醒来,看灰茫天色向晓。缓慢且半带晦暗。孩子还睡着,他起身,套上鞋子,披上毛毯,穿过林木向外走。往低处走进岩块间的缝隙,他边咳嗽边蹲了下来,咳了很久。然后他跪倒在烟尘里,抬脸仰对愈渐苍白的天光。你在吗,他轻声说,末日时刻,我见得到你吗?你有脖子吗?我可以掐你吗?你有心吗?你他妈的你有灵魂吗?上帝啊,他低语着,上帝啊。
隔日正午,他俩经过那座城。他枪不离手,架在叠放于购物车顶的防雨布上,要孩子紧紧依在他身旁。城大体焚毁了,了无生命踪迹。街市上,汽车顶上层层厚灰,一切都蒙上了灰烬与尘土。旧时的路埋在干透的烂泥里。某一户的门廊上,一具尸体枯槁到只剩外皮,正对着天光,面容扭曲。他把孩子拉近,说:记住了,你收进脑袋的东西,会永远留存在那里,你可要仔细考虑。
人不会忘记吗?
会,人会忘了他想留住的,留住他想忘记的。
离他叔叔的农场一英里远,有一面湖。以前,每年秋天他都和叔叔到附近收集柴火。他坐在小船尾端,一手拖在冰凉的船尾波里,叔叔弯腰摇橹。老人套在羔羊皮黑皮鞋里的双脚,抵着两根直木条稳住,戴草帽,衔着玉米斗,斗钵晃挂一道稀薄的口水。他转头瞧瞧对岸,搁下船桨,取下嘴里的烟斗,以手背抹抹下巴。沿湖岸列队的白桦木,在色彩暗沉的万年青的背景衬托下愈显苍白如骨。湖水边,断枝残干交错,织成防波墙,样貌灰暗残败,都是几年前一场飓风刮倒的树。长久以来,林木被锯倒、运走,充当柴火。叔叔调转船头、架稳船桨,他俩在泥沙堆积的浅滩上漂流,直到船尾板与沙地发生摩擦。清水里,有条死鲈鱼翻出肚皮,还有枯黄的叶。他们把鞋留在漆色和暖的船舷板上,拖船上岸,抛出用一根绳子系在船上的锚,是一只灌了水泥的猪油桶,中央插圆眼钩。他俩沿湖岸走,叔叔一路检视断枝残干,一路吸着烟斗,肩头盘着一捆马尼拉麻绳。他挑中一截断干,两人合力以树根为支点将它翻过来,使它半浮在水上。裤管虽挽到膝上,还是浸湿了。将绳头拴上船尾之后,他们划桨回航,断干拖在船后。其时,夜已降临,仅余桨架沉缓间歇的拉扯和摩擦声;湖面如玻璃窗般幽漆,沿湖的灯火一路亮起,某处传来收音机声。两人默默不语。这是孩提时代的完美记忆,这一天,形塑了日后的每一天。
接下来的数日数周,他们拼命往南方赶去,孤独,然而意志坚定;穿过鄙野的山区,途经铝皮搭建的住屋,偶尔有州际公路在低处蜿蜒经过一丛丛光秃秃的次生林。天很冷,越来越冷。山里,在深邃沟谷的一边,他们停下脚步,越过溪谷向南远望,视力所及,郊土一片焦黑,形体黯淡的岩群矗立灰烬聚积的沙洲,滚滚烟尘如浪升起,往南吹拂过一整片荒地。阴郁天色背后,看不见晦暗日光流转。
他们已经数日跋涉在烧灼过的土地上。孩子找到几根蜡笔,给口罩涂上尖牙,其后继续蹒跚行走,并不埋怨什么。购物车有只前轮不稳,但能怎么办呢?没有办法。眼前万事成灰,却生不起一把火;夜晚既长且黑,又寒冷,这情势他们前所未见。严寒几可碎石,或者夺命。他抱紧发抖的孩子,黑暗中点数每一次微弱的呼吸。
他听见远处的雷声,于是醒来,起身坐定。四周尽是幽微的天光,颤抖着,未知所起,相互折射在飘移的灰雨中。他拉低覆盖着两人的防雨布,久久躺着,侧耳聆听。若淋湿了,他们没火可烘干。若淋湿了,他们恐怕就会死。
那些夜里,他醒来面对的黑暗,既不可见,也不可解,浓重得仅是聆听已伤及耳力。他不得不经常起身。除却风声穿梭暗黑的秃树,四周一片阒静。此刻,他起身,站在冰冷闭锁的黑暗里晃动,伸张双臂维持平衡,脑壳下,前庭系统疾速生产各式运算结果。古老的叙事。他挺直身体。一个踉跄,但没摔倒。迈开大步向虚空走去,回程数着自己的步履。双眼紧闭,双臂划移。挺身向谁呢?向深夜里,根源中,基底上,那无以名状的东西。之于它,男人与繁星同为环伺周遭的卫星。像神庙中,巨大钟摆循漫漫长日刻画宇宙的运行,你可以说那钟摆对其举动一无所悉,却深知自己必须继续下去。
横越那片灰白的荒野花了他们两天时间。荒野另一头,一条大路顺着山巅延伸,山里四处都有荒芜林地倾颓衰败。下雪了,孩子说。他望向天空,一片暗灰的雪花飘落;他伸手捉住,看雪在手里融化,消逝如基督教世界里最后一位慷慨的东道主。
两人披着防雨布同步向前。潮湿晦暗的雪花旋绕着,自虚空降落,灰涩的泥泞占据了道路边缘,烟尘堆浸湿了,底下流淌出污黑的水。远方山区不再出现野火。他想,嗜血教信徒必定耗尽了彼此的生命,所以这条路不再有人通行,既不见商旅,也不见盗匪。过了一会儿,他们在路边看见一座车库。站在敞开的库门里边,两人看灰蒙蒙的冰雨自顶上国度疯狂坠落人间。
他们捡了几个旧纸箱,在地板上生起一堆火。他找到一些工具,于是清空购物手推车,坐下来修整车轮。他拉出轮栓,用钻子推出栓上的夹套,拿钢锯切一段钢管重套上去,再把栓子拴回去,然后立起购物车在地面四处滑行。轮子滚动极顺。孩子坐着,看着这一切。
清早,两人重新上路,在杳无人迹的国度。途经一座谷仓,仓门钉着死猪皮,皮面残破,尾巴细瘦。仓里,三具尸体悬挂横梁上,在成束的残光之间干瘪、生灰。这里可能有东西吃,谷物之类的,孩子说。我们走吧,男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