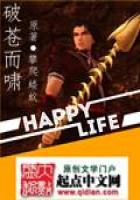不晓得过了几十日吧,我也是闲的太久了,灀风给我带那些个小玩意儿,我竟是轮着玩了个遍,好在得了他的意思罢,我倒是未曾被克扣着用度,在一众囚禁起来的小仙里,我还算是整洁干净的,若说我为何能知道别的小仙里甚么用度——这可真要多谢灀风了,他竟给了我一把传音镜,我凭着这玩意儿识得了一株仙草,名叫阿绛,我问她为何也在这云台受罚,她只道“犯了错”,我好奇,却也知不好问,便向守将说了些好话,让阿绛少受点罪。
我每每与阿绛聊上几句,但她不甚活泼,我说上十来句,她只回复我三四句,大都是不着边际的话,我问她“可认识甚么人”,她只说自己“寂寂无名”,可我若谈及上古四灵五兽,谈及灀风,谈及玄都仙人、凌介仙子和晏澄上仙,她不光知晓,还能说上几桩他们的趣事,连我都不曾知晓的。
说甚么玄都仙人埋桃花精酿极具巧思,将十来年百来年的埋在前头的桃林里,好几百年乃至千年的统统藏在一处隐蔽的好地里,嗳嗳,瞧瞧这好脾性的玄都仙人,也晓得防不了贼,便拿些次的依着,免使真真儿的遭了贼手。
凌介仙子的清荷冰露和晏澄上仙的花蜜雪酪出自南极真君所掌的蓬莱仙岛,浮于南极蓬莱山之上,常年云雾缭绕,岛上多奇珍花草,能出如此两道至真至美之食自然也不稀奇。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凌介仙子和晏澄上仙是南极真君座下弟子,他俩是师兄妹不说,更本是仙侣,只不过是因种种缘由没有正式结缘而已。
她还说灀风曾率族众欲攻朱雀一族挑起争端,我听得心惊,问她为何。灀风性子我大概明白,威正肃明,骁勇无匹,却也重情重义,易冲动易怒,他并非无故挑起战乱之人,我不知此事,不免心中有些焦急。
我还想多问几句,阿绛便说她乏了,我只能停了,可心下毫无倦意。
“阿绛……”我对着镜子悄声喊。
我见她不理,侧着身子似是睡去,抿了抿嘴,放下镜子平躺着,对着茫茫淡蓝苍穹和絮状的团云发怔。
“作何?”
我连忙抓起那柄传音镜道,“灀风为何要伐朱雀一族?”
好半晌,阿绛才轻轻说了几个字。
我脑中一片白,耳畔隐隐着嗡嗡作响,只听到她又说,“你莫以为我是把你当作朋友,不过是云台寂寞,你又肯托人与我送些什物,叫我好过些,我才愿与你说上几句。”
我愣愣道,“……云台实是寂静,平白消磨心智,若终日里不言语,我也难耐。与你说说话,徒以慰藉你我,好歹是打发打发时日的。”
阿绛不出声了,只侧身躺着,我不知她是否听进了去,便将那镜搁置在一边,后脑勺枕着双臂出神。
“兴许是为情罢。”
方才她说,灀风伐朱雀族,兴许是为情……
那么,我为何不知呢?我为何半分回忆也无?我为何也未曾听他说过有中意之人?
……我到底是忘了甚么?失去了甚么?
在我身处的这一方云台里,我竟有些怅然与茫然,难道我本不是一棵槐,难道我本不是紫槐君之女,本没有兄长,没有好友,不识得玄都仙人,也不曾有过那些记忆吗?
难道我也本不存于这天地之间……
我越想越觉惶恐,不由得惊坐起,一时又头痛难当,仿佛万般尖芒刺入我额中灵台,又扩散成无数细小的针尖无孔不入地扎着,我痛苦万分,翻滚着,却也不解痛意。
我便胡乱摸索,寻了个沉甸甸的筒状物一下又一下的往头上敲,终于随着最后一下,“砰”的一声,我眼前渐渐模糊,额中也逐渐麻木,身子便沉沉坠了下去,失去了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