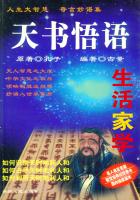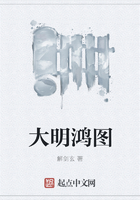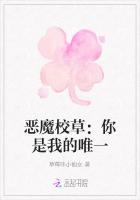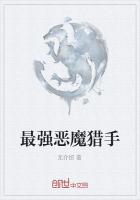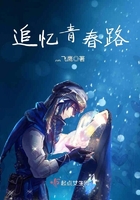——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史前史研究
从西方与其外部世界(非西方)的关系着眼,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在其《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这部巨著中认为,应当把西方现代的开端安置在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1]汤因比对现代的发生做这样的处理,主要是出于“内”和“外”两个方面的考虑:从“内”看,直到十五世纪,西方人才开始得以迈出基督教教规的重重钳制,走出了长达四个世纪之久的中世纪,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宗教的束缚和上帝的庇荫,得以把观察的视界由天上拉回到人间,并开始真正关注人类自身;就“外”而言,西方人在十五世纪已经准确地掌握了远洋航海技术,这就使得他们能够想方设法克服地理和物理上的障碍,漂洋过海,探访地球上一切有居民和可以居住的陆地。而在这项成就为西方基督教文明所掌握之前,西方旧世界文明与新大陆文明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甚至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往来。因此,远洋航海不但是促成西方人将目光投射到西方以外世界的直接条件,由此真正开始西方与外部世界的相互接触,揭开西方与非西方(包括东方)之间的关系史;同时,它也是一块鲜明的历史界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以便进行中西文化关系的研究。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中西文化关系的发生也应该定于此时此刻,中德文化关系自然不能例外。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萌芽、发展,并逐步走向复杂和深化的。
一、中国形象的史前史
汤因比在确立西方现代开端的同时还明确指出,西方于十一世纪开始进入中世纪,其间曾发生过震天动地的“十字军东征”(Kreuzzüge)事件。所谓“十字军东征”,通常是指西方的几次军事远征。当时,在教皇的鼓励和祝福下,西方进行了这些带有神圣色彩的远征,旨在去争取、支持或再一次争取在耶路撒冷建立一个基督教王国。[2]“十字军东征”对东西方文化关系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使得中世纪的西方与其周边世界开始直接照面并有了初步的接触,也使得西方通过周边世界对遥远的东方形成了间接而朦胧的了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西方于隐约之中感觉到了东方古国——中国的存在,中国形象随即在西方文学作品,特别是德国文学作品中初露端倪。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在真正进入中西文化关系之前,还存在着一段比较模糊,却又值得重视的中西文化关系史前史。就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而言,这段时期则可以称为中国形象的史前史。
我们不妨先把视野放宽一些,回到西方文化的源头。我们注意到,其实大约早在古希腊时期,中国就已经作为一个神秘的国度存在于欧洲人的意识当中了。到了罗马时期,欧洲人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称中国为“Seres”(赛里斯)。据有关学者研究,“Seres”一词可能由汉语“丝绸”中的“丝”字转化而成,此后沿用了若干世纪。当然,西方人当时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与其说是出于想象或判断,毋宁说是纯属猜测。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西方人要想准确地判断中国人的地理位置和民族特征,显然是极为困难的。而把中国人描绘成“红头发,蓝眼睛,粗嗓子”等令人忍俊不禁的形象,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毕竟,我们在早先时候也是这样来想象和描述那些非我族类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德语世界。大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诺特克尔·托伊托尼克尔诺特克尔·托伊托尼克尔(Nother Teutonikus)在其关于波伊提乌波伊提乌(Boethius,约480—524)的评注著作中首次提到了“赛里斯人”,并称之为“异教徒”。1190年,受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的大公海因里希·勒弗(Heinrich der Loewe,约1129—1195)的委托而出版的《卢西达留斯》(Lucidarius)和鲁道夫·冯·埃姆斯(Rudolf von Ems,生卒不祥)大约于1240年出版的《世界编年史》(Weltchronik)也都提到过“赛里斯人”。但不管是托伊托尼克尔,还是埃姆斯,他们都是严肃的学者,其著作也都是学术性的,他们注重的是文献记载,和文学虚构还不是一回事。但这里也必须指出,托伊托尼克尔称中国人为“异教徒”,显然是出于宗教考虑,带着浓厚的神圣色彩,与当时的历史氛围有着深刻的联系,可谓是开了救世史意义上的中国形象的先河。
“赛里斯”一词最早进入德国文学想象领域,成为德国作家笔下的艺术素材,是在中世纪宫廷史诗作家沃尔夫沃尔夫拉姆·冯·艾森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约1170—约1220)的史诗《帕尔齐法尔》(Parzival)和《威廉》(Willehalm)当中完成的。但是,在沃尔夫沃尔夫拉姆眼中,“赛里斯”只是一个名称(Name),或者说只是一种装饰。至于诗人为何要选用这个名词作为自己诗作中的点缀,我们已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赛里斯”这个名称在当时还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或特定的所指。
到了中世纪后期,德国出现了一部详细描写中国的游记作品,模仿的是英国作家曼德维尔曼德维尔(Sir John Mandeville,?—1371)所著的《东方闻见录》(The voiage and travaile:which treateth of the way to Hierusalem;and of marvayles of Inde,with other iland and countryes)。德国的这部游记作品,其作者已不可考,是一部虚构作品,也是一部杂烩之作,广采有关东方的资料加以编撰。[3]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在其中已不再叫作“赛里斯”,而是被冠以“契丹”(Kitai)一名。由于曼德维尔曼德维尔的作品在当时流传极其广远,“契丹”一词在德语语境中便也渐渐地深入人心,进而广为人知。
“契丹”一词在德语世界里虽然被广泛地使用开来,但比较有趣的是,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能搞清楚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契丹”就是“赛里斯”,两者指代的是同一个国家:中国。人们不是把这两者说成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就是称中国的北部为“契丹”,南部为“塞里斯”,并不能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对“契丹”的认识和了解在深度和广度上较之于“赛里斯”的确都要进步了许多。比如,人们知道了“契丹”的君主叫“可汗”(Great Khan)。诗人汉斯·罗森普吕特(Hans Rosenpluet,约1400—1460)的《葡萄酒颂歌》(Weinsegen)一诗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上帝赐福于你,名贵的酒药!
你使我健康强壮,
因为你是一个健康的Syropel。
君士坦丁堡的皇帝,
契丹国伟大的可汗和
教皇约翰,这三位巨富;
连他们用钱都买不来你的价值,
难道我还会指责你吗?
这首诗中不无幽默与调侃色彩。在罗森普吕特看来,“契丹”犹如君士坦丁堡,是一个充满东方情调和传说色彩的陌生国度;而“契丹”的君主“可汗”堪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教皇约翰鼎足而三,成为传说中的巨富之一。
二、《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中国形象
正如德国学者哈拉尔德·布洛伊纳(Harald Br?uner)所指出的那样,曼德维尔曼德维尔只是“契丹形象的传播者;真正的塑造者应是其他的两位旅行家,即威廉·鲁布鲁克(Wilhelm Rubruk)和马可·波罗(Macao Polo)”,[4]其中又以马可·波罗更为突出。
瑞士著名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Italian Renaissance Culture)一书中指出,十字军东征不仅在思想观念上为欧洲人打开了远方未知的世界,从而引发了许许多多有关远方陌生国度的幻想和猜测,而且在实践方面唤起了西方的旅行冲动和冒险热情,激起了人们到异国他乡作实地考察和亲身认知的无穷欲望。冲出欧洲大陆,走向外部世界,寻求新的发现,成为当时的一股热潮。[5]我们稍作深究,便会发现,这股热潮的根本动机其实还是在于“求知”,具体表现为对地理知识的发现和对物理知识的获取,当然,也不排除对文化知识的好奇和猎取。
在这股热潮中,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确无与伦比。不过两相对比之下,马可·波罗同样堪称是一位“佼佼者”,否则,布克哈特也不会称赞他是当时最富有进取精神的人:
世界的另一半就好像新发现一样,展现在他面前。他被卷入了蒙古人的洪流中,被带到大可汗的朝廷上去。[6]
因此,就中西文化关系乃至中德文化关系而言,马可·波罗或许才是一位“真正的发现者”。按照布克哈特的理解,“真正的发现者不是那个第一个偶然碰到任何东西的人,而是那个找到了他所寻找的那个东西的人”。[7]就此而言,马可·波罗显然当之无愧。
汉语世界对马可·波罗一点也不陌生,甚至赋予了他深厚的神话色彩。马可·波罗出生于1254年。他的家庭既是威尼斯的富商,也是一个旅行世家。从某种意义上讲,追求地理上的发现和致力于物质上的赢利,在马可·波罗家族那里得到了较为完美的体现,并且是那么的融合和一致。早在马可·波罗之前,他的父亲尼古拉·波罗(Nicola Polo)和叔父马菲·波罗(Mafeo Polo)就曾经涉足过元朝中国的领地,而且一度非常深入。马可·波罗也是在这两位前辈的带领下到达中国的,具体时间是1275年6月。当时,马可·波罗年仅21岁。由于聪明伶俐,他深得元朝大可汗忽必烈(Kubilai)的赏识和喜欢,并多次受忽必烈的派遣出使国内外。马可·波罗在中国居留长达20年,可谓前无古人。直到1295年,他才重新回到久违了的故乡威尼斯。
长时间在中国的逗留,以及与最高层当权者的直接接触和密切交往,所有这些都使得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蒙上了一层诱人的神秘色彩,他本人也成了一个传奇人物。回国3年后,马可·波罗在威尼斯与热内亚之间的战争中不幸沦为阶下囚。在狱中,他的海外奇闻、东方奇遇引起了同狱的小说家皮萨的罗斯蒂奇罗(Rustichello of Pisa)的极大兴趣。于是,马可·波罗口述,罗斯蒂奇罗笔录,二人共同完成了一部伟大的游记,让后人受益匪浅。
《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被辗转翻译成各种文字,并且反复校勘和注解。大体而言,这部游记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讲述的是马可·波罗个人的成长历史,第二部分记载他所到过的各地的情形。我国学术界通常把这部游记分为四卷,第一卷记载马可·波罗等东游沿途所见所闻,直至到达上都为止。第二卷所记内容比较繁复,主要有(1)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2)自大都西南行至缅国,记沿途所经诸州城等事;(3)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南沿海诸州等事。第三卷记录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第四卷记君临亚洲的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案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每卷又分成数章,每章叙述一地或一事,全书共229章。书中所记录的国家和城市地名多达一百多个,举凡山川地形、气候物产、商贾贸易、风俗信仰,乃至琐闻逸事、朝章国政等,林林总总,应有尽有,展示了一幅宏大而动人的东方政治、社会和民俗画卷。[8]
《马可·波罗游记》集中记述中国的是第二卷,共82章。这一卷占全书分量最重,因而可以说是全书的核心内容,其中广泛记载了当时中国的方方面面,诸如区域、民族、政治、经济、军事、劳动生产、风俗习惯等。另外还描述了北京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城和商埠的繁荣景况,介绍了中国的科学技术、育蚕治丝、制盐造纸以及在使用货币、建筑桥梁和宫廷、城市规划、市政管理、社会救济、植树造林等方面的杰出成就和独特经验。
《马可·波罗游记》虚实相杂,在对中国的惊讶和赞赏当中,固然有内容可靠、叙述踏实的实录,但也绝不乏想象夸大之后的虚构和杜撰。概括地说,《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描绘的中国形象可谓是“高、大、全”。它给人以神秘感和新鲜感,但也有过誉之嫌。因为,在马可·波罗眼里,中国十全十美,几乎到了让人难以相信也难以接受的程度。因此,《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毁誉交加,褒贬不一,未能在短时间内引起普遍关注。至于说它发表后很快就被争相传阅和受到普遍欢迎,恐怕只是后人的臆测了。单就德国而言,这部作品很早就被翻译成了德文,但一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直到十五世纪,确切地说,直到1477年,才在德国广泛刊行开来,而这又是此书的第一个印本。但就是这第一个印本旋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四年之后被一版再版,成了欧洲第一本真正畅销的“中国读物”。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要不惜笔墨,对早已广为人知的马可·波罗及其《游记》大书特书,并非单纯考虑到“他是整个中世纪最伟大的旅行家和最杰出的观察者”[9],更多地还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我们已经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马可·波罗游记》最初是在德国公开印行的,其影响之大,由初版后不断被再版便可略见一斑,尽管我们很难具体考证出其影响的范围。其次,就《马可·波罗游记》本身而言,它内容繁博,记载生动,在当时诸多游记作品中堪称上乘。尤其是马可·波罗把中国命名为“契丹”(Cathay或Kitai),正如上文所说,更是具有某种开创意义。随后,这个名称便彻底取代了先前的“赛里斯”,成了中世纪后期有关中国的主要指称,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德国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发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马可·波罗游记》在德国乃至在西方被接受的过程告诉我们,西方真正开始了解和认识中国是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期,这与汤因比所确定的西方现代精神的开端无疑是吻合的。而且,这种吻合绝对不是简单的历史巧合,更不是被人为地拉扯到了一起,而是有其内在逻辑性和历史必然性的。
三、门多萨门多萨及其《中华大帝国史》
十六世纪之前,旅行家们的游记不管是出于实录还是出于虚构,都为西方人接受中国做好了扎实的知识准备工作;传教士和商贾们的报道则进一步推波助澜,促使人们由被动接受走向主动认知。进入十六世纪,这种认知无论是在深度上,或是在广度上,都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标志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在西方语言中一改从前的虚设符号“Seres”和模糊名称“Katai”,而被正式命名为“Tschina”。“Tschina”这种叫法一直沿袭到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那里。但是,令人颇为遗憾的是,在利马窦(Matteo Ricci,1552—1610)之前很少有人真正判断出,“Tschina”就是“Seres”或“Katai”,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China”。所以,当时的人们往往会把中国当作美洲,找到中国就像发现美洲大陆一样,堪称一大新的发现。这种把中国和美洲相提并论,或者说混为一谈的做法,其影响所及直到十九世纪,因为直到这个时候,德国仍有作家用美洲人的形象来指称中国人,譬如,德国诗意小说家施蒂夫特施蒂夫特(Adalbert Stifter,1805—1868)的《林中小径》(Waldsteig)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综观整个中世纪,我们看到,中国不断地被西方“重新发现”和“重新命名”。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浅陋知识,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西方从未放弃接受中国,而且,由不同命名的贴切程度和合理程度,我们发现,西方对中国的接受逐步走向全面和深入,从而为肇始于十七世纪、全盛于十八世纪并席卷整个西方的“中国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就在这股中国热潮欲来风满楼之际,西方出现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编撰作品,由此构成了十六世纪西方人主动认知中国的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标志。
概括地说,这类编撰之作主要有如下四部:
1.伽列奥特·彼莱拉(Galeote Pereira)的《东西印度旅行史》(History of travayle in the East and West Indies);
2.伽斯帕·达·克鲁兹(Gaspar de Cruz)的《中国概说》(Tractado em que se cotam muito por estě so as cousas de China);
3.贝尔那狄努·德·艾斯卡朗特(Bernardino de Escalante)的《论葡萄牙人远航世界东部地区,以及在远航过程中对中国特有事物的认识》;
4.冈萨雷斯·德·门多萨门多萨(Gonzáles de 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ritos ycon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
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不想对这四部著作做详细的评述,而只想对门多萨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稍作介绍。据美国学者拉赫(Donald F.Lach)研究,门多萨门多萨的这部著作除了依据传教士的一般著述之外,还着重参考了克鲁兹和艾斯卡朗特的著作。克鲁兹是葡萄牙多明我会会士,曾经到过中国,逗留时间虽然只有几个月,其传教的宏图大志也未能实现,但他的著作试图“尽其所能地叙述他在中国期间的所见所闻”。[10]此外,克鲁兹还根据阅读彼莱拉的作品来编撰并充实其著作。克鲁兹充分发挥了其想象才能,对中国的风俗人情和地理环境做了详细而生动的描写。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作品才成为欧洲最早广泛印行的一部有关中国的专著,而且也是最杰出的“中国著作”之一。所以,鲍克瑟(C.R.Boxer)在其《十六世纪的南部中国》(South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一书中认为:
说伽斯帕·达·克鲁兹充分利用了他在广州的几个月时间,甚至超过了马可·波罗在契丹逗留的所有时间,也许有些过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位葡萄牙传教士确实提供给我们一部较那位更加出名的意大利旅行家所提供的要详细和生动得多的有关中国的作品。[11]
与克鲁兹不同,艾斯卡朗特从未到过中国。他是依靠阅读包括克鲁兹著作在内的大量资料之后,单纯凭想象而完成他的“中国著作”的。艾斯卡朗特的书用西班牙语写成,但不久就被译成了英文。克鲁兹和艾斯卡朗特的书,一实一虚,共同为门多萨门多萨提供了极好的材料和参考的方法。说得再具体一些,门多萨门多萨是运用克鲁兹的实证材料和艾斯卡朗特的虚构想象相结合的方法来撰写他自己的著作的。
本来,门多萨门多萨是应罗马教皇的要求而编撰此书的,为的是向教会提供一份有关中国的参考手册,为教会到中国传教做信息上的准备。但出乎意料的是,该书发表后竟不胫而走,成为一本热门读物。由此可见,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不光是教皇和教会认识到了中国的重要性,欧洲民间也已经发觉了中国的价值。因此,拉赫把《中华大帝国史》的畅销仅仅归因于门多萨门多萨清新流畅的笔调、细致入微的洞察力以及生动活泼的风格,未免显得有些狭隘。毕竟,我们不能完全忽略当时欧洲公众的阅读口味和认知要求。
《中华大帝国史》共由三方面内容组成,第一部分包括中国的地理位置、气候、人口、产品、早期历史与国王、行政机构、城市、道路和建筑等;第二部分叙述的则是中国的宗教、婚姻、葬礼、慈善事业等;最后一部分主要介绍中国的道德和政治事务。第一部分是全书的重心。通过对中国各方面的详细介绍,门多萨门多萨得出的中国形象是一个“划分为十五个省,其中每一个省都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大得多的中华帝国”。[12]
门多萨门多萨所描绘的这一中国形象虽然是写实性的,没有太多的文学意味,但却在西方产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就罗马教会而言,门多萨门多萨的著作让他们发现中国是一个异教世界,因此,亟须向那里派遣传教士,以实行救世的策略,尽早使中国基督教化。就欧洲的各种世俗权力而言,他们看到的是中国广袤土地上所蕴藏的巨大的物质利益。因此,在殖民主义观念的驱使下,他们对中国突发好奇,也充满欲望。而就西方的广大民众来看,他们感兴趣的主要是中国的地理风貌和文化特征,即中国所特有的丰富的异国情调。由此,追逐中国的“异国情调”,更成为以后几个世纪西方民众始终贯彻的动机,尽管时隐时现,但未曾有过中断。
总之,门多萨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可谓是“一箭三雕”,分别从心理上、物理上和地理上激起了西方各阶层对中国的广泛兴趣,因而也就成了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社会各阶层构造其中国形象的蓝本。据不完全统计,门多萨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发表后,在短短十五年时间里,竟以七种语言出版了四十六个版本,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这部著作仍然不断再版。[13]而1589年和1597年,德国分别出现了该书的德文译本和拉丁文译本,对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曾未风等译,18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228页。
[3]参见Ramond Dawson:《中国变色龙》(The Chinese Chameleon—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23~25页,London,1967。
[4]参见Harald Br?uner:《异国与现实》(Exotik und Wirklichkeit),15页,München,1990。
[5]参见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28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6]参见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280页。
[7]参见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281页。
[8]我国最早介绍马可·波罗的文字,是1874年映堂居士的《中西闻见录》。迄今为止,《马可·波罗游记》已有多种汉译本,主要包括冯承钧译注的《马可波罗行记》(1936);李秀译的《马可·波罗游记》(1936)以及陈开佼等合译的《马可·波罗游记》(1981),另有若干种有关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介绍著作。
[9]参见Ramond Dawson:《中国变色龙》(The Chinese Chameleon—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10页。
[10]Donald F.Lach:《16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China in the Eyes of Europe,the Sixteenth Century),748页,Chicago,1968。
[11]参见Ramond Dawson:《中国变色龙》(The Chinese Chameleon—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30页。
[12]参见门多萨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8。
[13]参见Donald F.Lach:《16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China in the Eyes of Europe,the Sixteenth Century),Chicago,748页,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