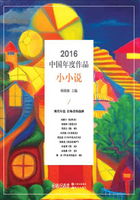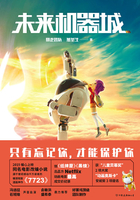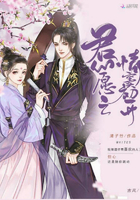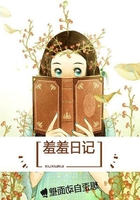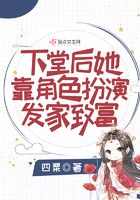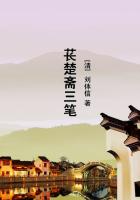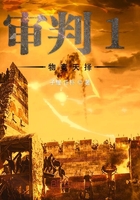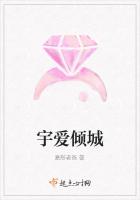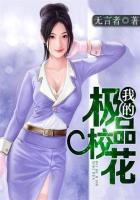王向远
一
“美学”作为一个从欧洲引进的新学科,早在明治初期就由西周等介绍引进,但从那时一直到大正时代,日本基本上只是在祖述欧洲美学,日本的美学家基本都是德国美学的翻译介绍者。因此可以说,从明治到大正年间的半个多世纪中,作为学术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日本固然是有“美学”的,但却没有“日本美学”,因为他们还没有把日本人自身的审美体验、审美意识及其相关文艺作品作为美学研究的对象。
由“美学”向“日本美学”的发展和演进,是需要基础和条件的,那就是“日本人的精神自觉”。明治维新之前的千年间,日本历史上精神文化、学术思想方面大都依赖于中国资源,明治维新之后则主要依赖欧美。不过,至少到了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江户时代,日本思想文化的独立意识也慢慢抬头了。江户时代兴起了一股以本居宣长等人为代表旨在抗衡“汉学”的“国学”思潮,本居宣长为了证明“日本之道”不同于中国的“道”,通过分析和歌与《源氏物语》,提出了“物哀”的观念,“物哀”论以主情主义反对中国儒家的道德主义、以唯美主义来抗衡中国式的唯善主义,极大地启发了近代日本文学理论家、美学家的思路。例如,为近代日本小说奠定了理论基础的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就大段地引述本居宣长的“物哀论”,并以此作为其理论支撑点之一。此后,“物哀”也就成为第一个众所公认的标识日本文学独特性的关键概念。
但是,像日本这样一个一直处在“文明周边”位置、受外来文化影响甚大的国家,要在传统精神文化中发现独特之处,在思想文化上全面确认独立性,较之在军事上、政治经济上取得自信力要困难得多,这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探索过程。从学术思想史上看,近现代日本人在这方面走过了一个由表及里、由外到内、由物质文化向一般精神文化、由一般精神文化向审美文化的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
1894年,志贺重昂(1862—1927)出版了题为《日本风景论》的小册子,首次论述日本列岛地理上的优越性,说日本的地理风景之美、地理的优越远在欧美和中国之上。第一次试图从地理、风土的角度确认国民的优越性,打消日本人一直以来存在的身处“岛国”的自卑感。这种日本地理风土的优越感的论述,很快发展为以“日本人”本身为对象的学术性阐发。1899年,新渡户稻造(1862—1933)在美国出版了用英文撰写的《武士道》,怀着一种文化自信向西方人推介日本人引以为豪的“武士道”,并且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日本人、日本国民性的文章与著作的大量涌现,其中正面弘扬的多,负面反省的也有,但无论是弘扬性的还是批判反省的著作,都在强调“日本人”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独特性”。不久,这种独特性的阐发和研究上升到了最高层次,即审美文化的层次,1906年,美术史家冈仓天心用英文撰写了《茶之书》,向西方世界展示了日本人及其茶道的独特的美,特别是指出了茶道所推崇的“不对称”和“不完美”之美及其与西方审美趣味的不同。
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日本学术界逐渐开始将日本审美文化、审美意识自身作为研究对象。1923年,和辻哲郎(1889—1960)发表了《关于“物哀”》,对本居宣长的“物哀”论做了评述。这或许是现代第一篇将“物哀”这个关键概念作为研究课题的论文。和辻哲郎肯定了本居宣长的“物哀”论“在日本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指出本居宣长的立论依据是“人情主义”的,并从人情主义的角度对平安时代的“精神风土”做了分析。他认为,平安朝是一个“意志力不足的时代,其原因大概在于持续数世纪的贵族的平静生活、眼界的狭小、精神的松弛、享乐的过度、新鲜刺激的缺乏。从当时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可以看出,紧张、坚强、壮烈的意志力,他们完全不欣赏;而对意志力薄弱而引起的一切丑恶又缺乏正确评价的能力,毋宁说他们是把坚强的意志力视为丑恶”。他进一步将平安时代的“物哀”的精神特性总结为:“带着一种永久思恋色彩的官能享乐主义、浸泡在泪水中的唯美主义、时刻背负着‘世界苦’意识的快乐主义;或者又可以表述为:被官能享乐主义所束缚的心灵的永远渴求、唯美主义笼罩下的眼泪、涂上快乐主义色彩的‘世界苦’意识。”[1]由此可见,和辻哲郎的《关于“物哀”》实际上是对平安朝贵族社会的一种“精神分析”,他的基本立场不是美学的,而是文化人类学的,由此他对平安时代的“物哀”文化做出了明确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对“男性气质的缺乏”的不健全的文化状态明确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这与后来的大西克礼以“体验”的方式阐释“物哀”美学,尽量避免做出非审美的价值判断,其立足点与结论是有所不同的。
接着,作家、评论家佐藤春夫(1892—1964)发表了题为《“风流”论》的长文,将“风流”这一概念作为论题。他认为古人所说的“风流”在今天我们身边的日本人身上仍能发现,仍具有活力和表现力,这在西洋文艺中是看不到的。“风流”就是“散漫的、诗性的、耽美的生活”,“是对世俗的无言的挑战”,认为“风流”中包含着传统的“物哀”(もののあはれ)、“寂枝折”(さびしをり)乃至“无常感”的成分。[2]现在看来,这篇随笔风的文章在理论论述上并不深刻,但作者以“风流”这一关键词为研究对象,并将“物哀”“寂”等日本独特的审美关键词统摄在“风流”这个汉语概念中,这在思路方法上对后来者是有所影响的,此后陆续出现了栗山理一的《“风流”论》、铃木修次的《“风流”考》等文章。
和佐藤春夫交往甚密、同属于当时唯美主义文学阵营的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1886—1965),在1933年至1934年间陆续发表了系列随笔《阴翳礼赞》。谷崎润一郎将日本人,特别是近世以降的日本人对幽暗、暧昧、模糊、神秘之趣味的审美追求与偏好,以“阴翳”一词概括之。“阴翳”这个词并不像“物哀”“风流”那样曾被广泛使用,而是谷崎润一郎的独特用法,在含义上应该相当于传统歌论、能乐论中的“幽玄”,但“幽玄”这个词在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基本不再使用了。对江户时代的文化无比缅怀的谷崎润一郎看出了江户时代之后的“幽玄”之美的遗存,并用“阴翳”一词称之,实际上是将“阴翳”作为一个审美观念、美学概念来看待的。还需要指出的是,谷崎润一郎和佐藤春夫都是当时日本文坛上的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与此前的冈仓天心、和辻哲郎等学者与思想家的立场与方法有所不同,他们的“风流”论和“阴翳”论完全是站在唯美的、审美的立场上的,而且贯穿着作家特有的体验认知。此后的日本美学概念研究从一般的思想史研究的立场转向纯文艺学、美学的立场,并且将纯理论思辨与体验性的阐发结合起来,谷崎润一郎和佐藤春夫是起了一定的过渡作用的。
二
此后,训练有素的专门的文艺学家、美学家登场,开始了对日本传统美学中基础性的审美观念及重要概念的研究。在大西克礼登场之前,主要代表人物有土居光知、九鬼周造、冈崎义惠等。
土居光知(1886—1979)在《文学序说》(1927)一书中,从文学史演进的角度,认为奈良时代的理想的美表现为药师如来、吉祥天女,特别是观音菩萨的雕像所表现出的“慈悲的美妙的容姿”,而到了平安朝时代,“情趣性的和谐”成为美的理想。在《源氏物语》中,“あはれ”“をかし”“うるはし”“うつくし”等词汇,都具有特殊的情趣内容,而其中最主要的是“あはれ”(哀)和“をかし”(可译为“谐趣”)两个词。他指出:“あはれ”这个词在《竹取物语》中是“引起同情的”“爱慕”“怜惜”的意思,在《伊势物语》中是“同情”“宠爱”“赞叹”的意思,在《大和物语》和《落洼物语》中又增加了“令人怀念”的意思,到了《源氏物语》中其感伤的意味则更为浓厚,多用于“寂寥、无力、有情趣”“深情”“引起同情的状态”“感动”“哀伤”的意思。而“をかし”在《竹取物语》和《伊势物语》中是“有趣味”的意思,在《大和物语》和《落洼物语》中是“机智的”“值得感佩的”“风趣的”“巧妙的”“有趣的”等意思,在《源氏物语》中又增加了“风流”“上品”的意思。在《枕草子》中将深情、寂寥之趣归为“哀”,将热烈、明朗、富有机智的事物归为“谐趣”,而且“哀”的趣味越是发达,谐趣也越是相伴相生;人们越感伤,越要求要有谐趣来冲淡。“哀”中含有“啊”的感叹,“谐趣”中含有“噢”的惊叹。[3]土居光知把“哀”置于平安时代物语文学演进史中予以考察,并把“哀”与“谐趣”两个词相对举、相比较,是有新意的,但是他显然主要是从语义学的表层加以概括,至多是从文学理论的层面上,而非“美学”的层面上的研究。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哲学家九鬼周造(1888—1941)出版了小册子《“意气”(いき)的构造》(1930),第一次将江户时代市井文学,特别是艳情文学中常用的一个关键词“意气”(又写作“粹”)作为一个美学词汇来看待,并加以研究,分析了“意气”的基本的内涵构造,认为“意气”就是对异性的“献媚”、“矜持”和“谛观”(即审美静观),[4]构成了江户时代日本人在“游廓”(花街柳巷)中所追求的肉体享乐与精神超越之间恰如其分的张力、若即若离的美感。九鬼周造将江户时代的市井文学的审美趣味、审美观念用“意气”一词一言以蔽之,这是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重要发现。自此,江户时代二百多年间市井审美文化的关键词或基础概念的空缺得以填补。次年,哲学家、美学家阿部次郎(1893—1960)的《德川时代的艺术与社会》(1931)以江户时代的文艺为例,阐述了江户时代的平民文艺如何形成,又如何对后来的日本人产生无形的巨大影响。他断言江户时代的市井文化是一种“恶所文化”,是“性欲生活的美化”和“道学化”,这部书尽管没有提及“意气”等关键词,但所谓“性欲生活的美化”基本上就是九鬼所提炼的“意气”,因而阿部次郎仿佛是从文艺学、文化史的角度,对九鬼周造的《“意气”的构造》做了很好的延伸和补充。后来,麻生矶次的《通·意气》、中冶三敏的《粹·通·意气》等一系列关于“意气”的著述和阐释,都是在九鬼周造和阿部次郎的基础上展开和深化的。九鬼周造的《“意气”的构造》在思路与方法上,对后来的大西克礼显然是有影响的。
此外,关于“幽玄”与“物哀”和“寂”等基础概念,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大西克礼作为日本美学的基础概念加以美学立场上的研究阐发之前,即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整个三十年代的十几年间,还有一系列论文陆续发表。其中被研究最多的基础概念是“幽玄”。关于“幽玄”的主要论文有久松潜一的《镰仓时代的歌论——“幽玄”“有心”的歌论》(《日本文学讲座》第12卷,1927)、《“幽玄”论变迁的一个动机》(《东京朝日新闻》,1930.1)、《“幽玄”的妖艳化和平淡化》(《国语与国文学》,1930.11—12)、《幽玄论》(《俳句研究》,1938.12);西尾实的《世阿弥的“幽玄”与艺态论》(《国语与国文学》,1932.10);斋藤清卫的《幽玄美思潮的深化》(《国语与国文学》,1928.9);富田亘的《从歌道发展来的能乐的“幽玄”》(《歌与评论》,1933.7);冈崎义惠的《“有心”与“幽玄”》(《短歌讲座》第1卷,1936.6);风卷景次郎的《幽玄》(《文学》,1937.10);钉本久春的《从“幽玄”到“有心”的展开》(《文学》,1936.9)、《“妖艳”和“有心”》(《文学》,1937.10);竹内敏雄的《世阿弥的“幽玄”论中的美意识》(《思想》,1936.4);吉原敏雄的《歌论中的“幽玄”思想的胎生》(《真人》,1937.2—3)、《幽玄论的展开》(《短歌研究》,1938.4)等。可见,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是“幽玄”的再发现的时代。说“再发现”,是因为“幽玄”这个词不像“哀”或“物哀”那样贯穿于整个日本文学史及文论史,十七世纪以后的数百年间,“幽玄”作为一个概念基本不用了,近乎变成了一个死词,以至于上述的谷崎润一郎虽然在江户时代后日本人的生活与作品中发现了普遍存在的“幽玄”的审美现象,却未使用曾在日本五百多年间普遍大量使用的“幽玄”,而以“阴翳”一词代之,可见“幽玄”这一概念是被人遗忘许久了。久松潜一、冈崎义惠等人的研究,都从不同角度呈现了历史上“幽玄”的盛况,还对“幽玄”做了现代学术上的解释和阐发。在“幽玄”之外,这个时期对“哀”与“物哀”、“寂”的基础概念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主要有久松潜一《“寂”的理念》(《东京帝大新闻》,1931.6.8)、《作为文学评论的“寂”》(《言语与文学》,1932.2)等;冈崎义惠《“哀”的考察》(《岩波讲座·日本文学》,1935.7)、《“风体”论与“不易、流行”论》(《文化》,1937.5);风卷景次郎《“物哀”论的史的限界》(《文艺复兴》,1938.7);池田勉《源氏物语中文艺意识的构造》(《国文学试论》,1935.6);钉本久春《寂》(《文学》,1936.10)、《“妖艳”和“有心”》(《文学》,1937.10);宫本隆运《“物哀”再考》(《国文学研究》,1936.11);各务虎雄《关于“寂·枝折·细柔”的觉书》(《学苑》,1936.7);藤田德太郎《“寂”“枝折”的意味》(《俳句研究》,1937.1)等等,还有一些研究“虚实”论、“华实”论、“不易、流行”等概念的文章。
在这些研究中,值得特别提及的是久松潜一(1894—1976)和冈崎义惠(1892—1982)的贡献。他们是较早、较多涉及“幽玄”“物哀”等基础概念研究的现代学者,在大西克礼的“三部作”之前的日本美学基础概念的研究中最有代表性。
久松潜一的研究的立场与视角是“日本文学评论史”,他在单篇论文和课堂讲义的基础上编写的皇皇五大卷的《日本文学评论史》(1937年后陆续出版)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久松所说的“评论”,就是“文学评论”加“文学理论”的意思,他认为文学评论的基准是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的基础是文学评论。他认为日本文学评论的基本特征是:外部形式上是随笔性的,内容上是“非合理”的,也就是非逻辑的、无体系的。例如他认为要对“物哀”这个词的言语构造做出合理的说明是极其不容易的,对芭蕉所说的“不易、流行”的概念作出“变与不变”之类的合理性的说明,也会与芭蕉本人的意思有相当距离。日本文学评论相当博大深厚、丰富多彩,但要使其成为一个体系实在太难了。[5]基于这种认识,久松潜一在《日本文学评论史》中,主要采取描述性而非逻辑的和体系构建的方法,全书虽然资料丰富,但整体上看是叠床架屋、内容板块相互重叠交织,对“诚”“物哀”“幽玄”“有心”与“无心”“余情”“雅”等一系列基础概念的性质归属与定性、定位也不免有些凌乱,或将它们看作“思潮”,表述为“物哀的文学思潮”“幽玄的文学思潮”等;或把它们看作是“理念”,表述为“物哀的理念”“幽玄的理念”等;或把它们看作是美的“形态”,表述为“物哀美”“幽玄美”之类;或把它们看作是评论用语,表述为“物哀的文学论”“‘寂’的文学论”等等。这种情况的出现表明,在“文学评论史”的架构内,既是“文学评论”的概念,又是“文学理论”的概念,还要上升为“美学”的概念,就难免会产生这样的定位、定性的诸多分歧。这也说明,这些概念还有待于放在更高的理论平台上加以凝聚和提炼。
稍后和同时,冈崎义惠从“日本文艺学”的角度对这些概念做了一定程度的提炼和进一步的阐发。
冈崎义惠是“日本文艺学”这个学科概念的创始者和实践者。那么他的“日本文艺学”与“美学”是什么关系呢?对此他在《日本文艺学》一书的跋文中指出,日本文艺学是以美学为基础的,“日本文艺学在根本上是对美学的应用,同时它又是美学的出发点。日本文艺学的研究将已有的美学研究成果作为阐释的基础,同时,美学又可以从日本文艺学的研究中开辟新的道路。……美学一旦成为一个庞大的不可驾驭的研究领域,就会失去中心点,就难以对一个个具体的审美现象加以探究和说明”。而日本美学家一直忙于译介阐释欧洲美学,未能立足于日本之美的研究,所以他提出“日本文艺学”旨在致力于研究日本的美。1935年,冈崎义惠发表《“哀”的考察》一文,开始了“日本文艺学”的实践,他对历史上的“哀”的使用做了语义学上的考察,他说:“我所要探讨的问题,并不是指出‘哀’使用中的多样性差异性,而是在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底层寻求某种本质的统一性,指出这个本质统一性到底是什么。因此要从文献上出现的最初的用例开始,依次探讨该词的用法。这样做,乍看上去似乎只是从语言学史的立场上,对词语的意义及历史变迁所进行的研究,但实际上我的目的是要把‘哀’在日本文学中如何存在、在日本文学史及文学评论中起何种作用,明确地揭示出来。”[6]为此他从最早的文献《古事记》与《日本书纪》开始,到《万叶集》等和歌,再到平安朝时代的物语文学中的“哀”的用例做了若干列举和分析。作为《“哀”的考察》的姊妹篇,次年冈崎义惠又发表了题为《“有心”与“幽玄”》(原载《短歌讲座》第1卷,1936.6)的长文,不仅发现了中国和日本文献中许多此前从未被发现的“幽玄”用例,还运用了一般日本文学研究者们所忽略的跨学科方法,指出了“幽玄”与中国诗论及与道教、神仙思想和禅宗精神的关联,展现了“幽玄”逐渐日本化的轨迹,认为“这个‘幽玄’所表示的不是优美的、现实性的情调,而是崇高和超脱的精神”。[7]如此将“幽玄”定位于“崇高”,直接启发了此后大西克礼对“幽玄”的美学定位。总之,冈崎义惠使用的虽然主要还是文献学、语言学的方法,理论概括的高度还不够,但他在“日本文艺学”的框架内对“物哀”“幽玄”的考察,为这些基础概念进入美学视阈,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三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美学家大西克礼首次明确地站在“美学”立场上,对“幽玄”“物哀”“寂”三个基础概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大西克礼(1888—1959),东京大学美学专业出身,1930年后长期在东京大学担任美学教职,1950年退休后仍埋头于美学的翻译与研究,译作有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等,著有《〈判断力批判〉的研究》(1932)、《现象学派的美学》(1938)、《幽玄与哀》(1940)、《风雅论——“寂”的研究》(1941)、《万叶集的自然感情》(1944)、《美意识论史》(1950),去世后出版《美学》(上、下两卷,1960—1961)、《浪漫主义美学与艺术论》(1969)等,是日本学院派美学的确立者和代表人物。
大西克礼在学术上最突出的贡献之一,首先在于对日本古代文论中的一系列概念进行了美学上的提炼,最后提炼并确立了三个最基本的审美观念或称审美范畴,就是“幽玄”“哀”(物哀)和“寂”。而他的基本依据则是欧洲古典美学一般所划分的三种审美形态——“美”“崇高”和“幽默”(滑稽),认为日本的哀(物哀)是从“美”这一基本范畴中派生出来的一种特殊形态,“幽玄”是从“崇高”中派生出来的一种特殊形态,“寂”则属于“幽默”的一种特殊形态。这一划分与西方古典美学加以对位和对应,虽然不免显得勉为其难,但在他看来,美学这个学科是超越国界的,“日本美学”或“西洋美学”这样的提法不过是在陈述各自的历史而已。这样划分和对位不管是否牵强,但是确实解决了日本美学范畴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在大西克礼之前,“物哀”“幽玄”“寂”等范畴通常与其他范畴,诸如“诚”(まこと)、“谐趣”(をかし)、“有心”、“无心”、“雅”(みやび)、“花”、“风”或“风体”、“风雅”、“风流”、“艳”、“妖艳”、“枝折”(しをり)、寂枝折(さびしをり)、“细柔”(ほそみ)、“意气”(いき)、“粹”(いき)、“通”(つう)等等并列在一起加以研究的。在这种情况下,诸概念之间的级差与结构关系无法理清,一级概念、二级概念、三级概念的层次模糊,日本美学的体系构建便无法进行。大西克礼在这众多的概念范畴中将这三个概念提炼出来,冠于其他概念之上,事实上构成了相对自足的“一级范畴”,而其他范畴都是次级范畴,即从属于这三个基本范畴的子范畴,这就为日本美学的体系构建奠定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
事实上,在我看来,即便不把“幽玄”“物哀”“寂”与西方的“美”“崇高”“幽默”相对位,也可以为这三个一级范畴或概念确立找到基本依据。对此,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做过简单的论述,认为:从美学形态上说,“物哀”论属于创作主体论,特别是创作主体的审美情感论,“幽玄”论是“艺术本体”论和艺术内容论,“寂”论则是创作主体与客体(宇宙自然)相和谐的“审美境界”论、“审美心胸”论或“审美态度”论。具体而言,从创作主体论上看,“哀”或“物哀”是一级范畴,而“诚”、“谐趣”、“有心”、“无心”等都属于“物哀”的次级范畴;从艺术本体论和艺术内容论的角度看,“幽玄”是一级范畴,而“艳”、“妖艳”、“花”、“风”或“风体”则属于“幽玄”的次级范畴。从创作主体与客体(宇宙自然)相和谐的审美境界、审美心胸或审美态度上来看,“寂”是一级范畴,而“雅”、“风雅”、“风流”、“枝折”、寂枝折、“细柔”则属于“寂”的次级范畴。从三大概念所指涉的具体文学样式而言,“物哀”对应于物语与和歌,“幽玄”对应于和歌、连歌与能乐,而“寂”则是近世俳谐论(简称“俳论”)的核心范畴,几乎囊括了除江户通俗市民文艺之外的日本古典文艺的所有样式。从纵向的审美意识及美学发展史上看,在比喻的意义上可以说,“物哀”是鲜花,它绚烂华美,开放于平安朝文化的灿烂春天;“幽玄”是果,它成熟于日本武士贵族与僧侣文化的鼎盛时代的夏末秋初;“寂”是飘落中的叶子,它是日本古典文化由盛及衰、新的平民文化兴起的象征,是秋末冬初的景象,也是古典文化终结、近代文化萌动的预告。[8]
大西克礼在三大基础范畴的研究中,采取的是各个击破式的相对独立的研究,但他强调其研究重心是在“美学体系的构建方面”,他在《幽玄与哀·序言》中指出:“我根本的意图是将日本的审美诸概念置于审美范畴论的理论架构中,进而把这些范畴置于美学体系的整体关联中展开研究。……我在对‘幽玄’与‘哀’进行考察的时候,始终注意不脱离美学的立场……本书只是暂且把单个独立的范畴从美学的体系性关联中独立出来……”[9]他在《风雅论——“寂”的研究》序论中,又强调指出:对于“幽玄”“物哀”“寂”,“重要的不仅仅是把它们相互结合、统一起来,而是要把它们在一个统一性的原理之下加以分化。换言之,要对‘幽玄’‘物哀’‘寂’这样的概念进行分门别类的美的本质的探究,也就是要从美学理论的统一根据中,加以体系性的分化,以便使它们各自的特殊性得到根本性的理论上的说明。”[10]换言之,三个基础概念的看似孤立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体系性的分化”。
这种“体系性”的追求,体现在三个基础范畴的具体研究中,就表现为对语义的结构性、构造性、层次性的追求。在大西克礼之前的研究中,对相关概念的语义固然也做了不少的分析,但那些分析大多是平面化的,缺乏层次感的。大西克礼则运用西方美学的条分缕析的方法,对久松潜一所说的那些“非合理”的概念内容进行了“合理”的分析与建构,将相关概念的“意义内容”如层层剥笋般地加以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剖析,从而呈现一个概念的意义结构。
例如,关于“幽玄”,大西克礼认为“幽玄”有七个特征:第一,“幽玄”意味着审美对象被某种程度地掩藏、遮蔽、不显露、不明确;第二,“幽玄”是“微暗、朦胧、薄明”,这是与“露骨”“直接”“尖锐”等意味相对立的一种优柔、委婉、和缓;第三,是寂静和寂寥;第四,是“深远”感,它往往意味着对象所含有的某些深刻、难解的思想(如“佛法幽玄”之类的说法);第五,是“充实相”,是以上所说的“幽玄”所有构成因素的最终合成与本质;第六,是具有一种神秘性或超自然性,指的是与“自然感情”融合在一起的、深深的“宇宙感情”;第七,“幽玄”具有一种非合理的、不可言说的性质,是飘忽不定、不可言喻、不可思议的美的情趣。
关于“哀”,大西克礼认为,对“哀”这个概念依次有五个阶段(层次)的意味:第一是“哀”“怜”等狭义上的特殊心理学的含义。第二是对特殊的感情内容加以超越,用来表达一般心理学上的含义。第三就是在感情感动的表达中加入了直观和静观的知性因素,即本居宣长所说的“知物之心”和“知事之心”,心理学意义上的审美意识和审美体验的一般意味由此产生。第四,“静观”或“谛观”的“视野”超出了特定对象的限制,而扩大到对人生与世界之“存在”的一般意义上去,而多少具有了形而上学的神秘性的宇宙感,变成了一种“世界苦”的审美体验。于是“哀”的特殊的审美内涵得以形成。第五,“哀”将优美、艳美、婉美等审美要素都摄取、包容、综合和统一过来,从而形成了意义上远远超出这个概念本身的特殊的、浑然一体的审美内涵,至此,“哀”在意义上达到了完成和充实的阶段。
关于“寂”,大西克礼认为“寂”含有三个层面上的含义。第一,“寂”就是“寂寥”的意思。在空间的角度上具有收缩的意味,与这个意味相近的有“孤寂”“孤高”“闲寂”“空寂”“寂静”“空虚”等意思,再稍加引申,就有了单纯、淡泊、清静、朴素、清贫等意思。第二,“寂”是“宿”“老”“古”的意思,所体现的是时间上的积淀性,是对象在外部显示出的某种程度的磨灭和衰朽,是确认此类事物所具有的审美价值。第三,是“带有……意味”的意思。也就是说,“寂”(さぶ、さび)这个接尾词可以置于某一个名词之后,表示“带有……的样子”的意思,通过这一独特的语法功能作用,就可以将虚与实、老与少、雅与俗等对立的事物联系起来、统一起来,充实其审美内涵。
在三大基础概念范畴的研究中,大西克礼明显受到了德国胡塞尔(Husserl)等人的现象学哲学与美学的影响,注重现象学美学所推崇的“直观”“静观”“价值意义”等,例如他特别注重研究三大基础概念所内含的“价值”问题,对“价值概念”与“样式概念”加以明确区分,对“价值意义”进行具体阐发;他对以往积淀起来的关于三大概念的知识特别是常识,都用“本质直觉”、“内在直观”的方法,以“面向事物本身”的审视的态度重新放到他的“美学菜板”上加以切分剖析。他践行现象学“凝视于现象,直观其本质”的主张,强调一个概念之所以能够由一般概念上升为审美概念,就在于其中包含了超越性的“静观”或“谛观”的因素。
大西克礼的“三部作”属于纯学院风格的作品,理论概括度较高,思想含量与创新意识较强,语言的哲学化倾向明显(有些表述时有学究气的晦涩),在理论思辨薄弱、容易流于常识化的日本现代学术著作中,大西克礼并不是主流,故而读者不多,更不曾成为畅销书,却具有经久不减的学术价值。后来,研究三大基础概念的著作论文不断出现,除“物哀”研究有所不振之外,如在“幽玄”的研究方面,主要有能势朝次《幽玄论》(1944)、谷山茂《幽玄的研究》(1944)、河上丰一郎的《能的“幽玄”与“花”》(1944)、草薙正夫论文集《幽玄论》等著作;在“寂”的研究方面,主要有山口论助《日本的日本完成——“寂”的究明》(1943)、河野喜雄《寂·侘(わび)·枝折》(1983)、复本一郎《芭蕉的“寂”的构造》(1974)和《寂》(1983)等著作,还有河出书房出版的《日本文学的美的理念》(1955)和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的《日本思想5·美》(1984)两书中的相关文章,都在一些方面有所推进。但总体上看,在研究规模和理论深度方面,似乎还没有出现堪与大西克礼的“三部作”相当的著作。可以说,“三部作”以其创新性的见解、体系性的建构和细致的理论分析,在日本众多的同类研究成果中卓荦超绝,对于读者深入理解日本民族的美学观念与审美趣味,有效把握日本文学艺术的民族特性乃至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都极有参考价值。
从日本美学研究史的角度看,大西克礼的“三部作”所提炼和研究的“幽玄”“物哀”“寂”,与此前九鬼周造在《“意气”的构造》所提炼和研究的“意气”这一概念,两者一脉相承又异曲同工,共同确立了日本古典美学概念的四大基础概念与范畴,使得以研究日本传统审美意识与审美现象的真正的“日本美学”成为可能,从比较美学的角度看,这些概念与中国古典美学诸概念的关系,以及两者的比较研究也很有价值,而且,从深化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如何将我们的一系列范畴,如“意境”“气韵”“风骨”“神思”等等,加以进一步提炼和分级,使得若干基础概念与其他从属概念形成一种逻辑性的结构关系,从而进一步优化以基本范畴为支点的中国美学的理论体系,相信在这方面大西克礼的“三部作”对我们也会有一定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