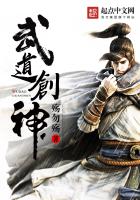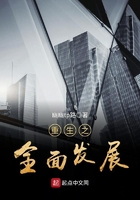今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人们很自然地要回想起当年活跃在新文化运动战场上的一些风云人物。
最近报刊上出现了几篇为李大钊、瞿秋白同志鸣不平的文章。《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预告将要披露胡适部分遗稿。这些消息表明,在解放思想激流的冲击下,学术界大胆冲破禁区,开始实事求是地评价一些历史人物了。
给历史人物以符合事实本来面目的评价,是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绝对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的典范是无须列举数说的。这种优良作风是革命导师留给我们的极其珍贵的财富。令人痛心的是,多年来,尤其是经过“四人帮”的破坏,这种老实的科学态度被远远地丢弃了。在学术研究中,因人废言、因言废人的现象相当普遍地存在。后来变坏了的人物,原先做过的好事乃至做出的贡献,也不能被丝毫肯定;后来表现好的人物,即使早先表现不怎么好也被说成是如何如何好。对人和事的评价可以不顾历史事实,仅仅为了证实某些论断的正确,历史可以被随意打扮、歪曲、涂改。
陈独秀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不能不说是个名人。他是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者之一,被开除出党。但是,他确确实实又是我们党第一任总书记,难道仅仅用“历史的误会”就能说明这个历史现象吗?在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无疑是领袖人物、主导人物。采取回避、抹杀、贬低、夸大局限性的做法,像我们已经有过的那样,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的。对他这样所谓复杂的历史人物,也只能从历史事实出发,使用既有分析又有批判的办法,从而对他的功过作出全面的评价。这绝不只是对某个人物的具体评价问题,正确地认识、评价陈独秀及其同类人物的问题,对我国现代革命史、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正如标题所标明的,本文只想就陈独秀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发表一点浅见。由于近三十年来,谈论这个问题的专门文章极少,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有意较多地援引了一些材料。至于文章观点是否合理、正确,只好期待同志们的鉴定、批评。我们坚信:历史总归是历史,与其一时得不出较为准确的结论,不如让事实本身去说话吧。
一
“五四”运动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也是一次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即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不但对当时的爱国民主斗争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创刊的《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而《新青年》杂志的主要倡导者则是陈独秀。
陈独秀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后编《国民日日报》,主张实行民主革命,反对君主专制,并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反清斗争。辛亥革命后,曾任安徽师范学堂校长,一九一三年反袁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一九一五年回到上海,九月十五日创刊《新青年》月刊[26],直到一九一七年,这个刊物主要是由他编辑的[27]。一九一八年以后《新青年》逐渐转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公允地说,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一起与胡适斗争的结果。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内容是民主和科学。《新青年》杂志一开始就高举起这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进行了猛烈的进攻。创刊号发表的陈独秀的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在历数了当时中国社会黑暗之后,便向青年大声疾呼:
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置留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迁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抉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里所陈的“六义”,实际上已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德、赛二先生”即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揭示出来了。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对民主和科学有具体的论述。民主在这里被称为“人权”:“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关于科学,他说:“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并进一步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虽然,这种民主与科学的解说,是从资产阶级那里贩来的。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这些资产阶级的学说已失去其进步性,但是,在当时中国的介绍和发现,仍具有不小的积极意义。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正是用这种“破烂的武器”向陈旧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堡垒发动进攻的。
由于袁世凯称帝、康有为反对共和等一系列封建复古活动,都是打着尊孔的旗号进行的,新文化运动的斗争锋芒便很快地指向了以维护封建专制为中心的孔子学说。陈独秀连续发表了《一九一六年》[28]《吾人最后之觉悟》[29]《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30]《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31]《宪法与孔教》[32]等政论,充满着对封建礼教和专制制度的强烈憎恨,他指出以孔教学说为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是阻碍中国人民觉醒的大敌,号召人们摆脱“奴隶之羁绊”,完成思想和个性的解放,以求政治上的进步。在这场反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斗争中,他表现了坚决的勇敢精神,他不愧是“打倒孔家店”的急先锋。
《新青年》在“五四”思想革命运动中突出的作用和巨大的影响是历史公认的。例如,当时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有学生四百人左右,有一个时期就销行《新青年》和《星期评论》四百几十份[33]。在《新青年》的影响下,许多觉悟的青年,纷纷办杂志、写文章,提倡新思想。《新青年》六卷三号载有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新声社”给编者的信,其中说:“我们从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编《新青年》的先生,实在表不尽的感谢了。”“我们这《新声》出版之后,当然是群起而攻之,所受的打击不消说得了。敬祝新青年万岁!”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王统照来信:“记者足下,校课余暇,获读贵志,说理新颖,内容精美,洵为最有益青年之读物。”[34]一位读者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今春一读大志,如当头受一棒喝,恍然悟青年之价值,西法之效用,腐旧之当废,新鲜之当迎。”[35]
《新青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和不可磨灭的功绩,决定了“五四”新文化这场斗争的主要领导人不是别人,而是陈独秀。虽然他当时还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还没有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最新武器指挥战斗,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他成为这场运动的旗手。
二
开始于“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是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也是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当时一些启蒙思想家,以《新青年》为阵地,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同时,对封建文学营垒,从内容到形式都展开了凌厉的攻势。“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36]陈独秀就是举起文学革命旗帜的第一人。
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那篇文章中,提出了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的主张,被陈独秀称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的急先锋”。可是,实际上他举的不是“文学革命”的旗帜,而是“文学改良”的旗帜。他的“八事”主张中,“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确实涉及了文学的内容,但这内容究竟是什么,并不明确。他提倡以白话代替文言,这是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对否定封建旧文学、创建白话的新文学有进步的意义。但是,总的看来,他的主张和态度,既模糊,又软弱,改良主义色彩极重。真正首先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应该是陈独秀。
一九一七年二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可以说,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揭橥文学革命旗帜的宣言。
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在“畏革命如蛇蝎”的社会中,以大无畏的精神,毅然提出:“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痛斥封建文学的“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荒谬,称“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的封建文人为“十八妖魔”,大胆宣称:“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陈独秀这种大呼猛进的革命主张,显然跨过了胡适“口欲言而嗫嚅,足欲行而踟蹰”的“刍议”,给启蒙思想运动带进了文学革命的叛逆呼声。他的这篇文章和以后的一些主张,成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纲领,在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历史潮流中,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鲜明的号召力。
文学革命的运动,不是孤立进行的。陈独秀始终注意把文学革命作为社会的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胡适的“刍议”,仅仅是从“世界历史进化的眼光”,相信“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确认白话文学必然“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他只相信“一点一滴的改良”,不敢提出思想革命和社会改革的思想。陈独秀一开始就同胡适的形式主义的文学改良划清了界限。陈独秀认为,革命是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动力。“庄严灿烂之欧洲”之所以出现,是“革命之赐也”。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政治、宗教、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中国政治之所以“黑暗未灭”,文学艺术之所以“垢污深积”,都是因为“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利器故”。因此,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37]当然,陈独秀这里所说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他的革命理想,是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它的“庄严灿烂”的文明。远在“五四”运动之前,甚至还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陈独秀不可能提出超出他生活的时代的革命蓝图。但是,他的理想的目标,在中国并不存在产生的条件。重要的不是他的目标,而是他实践的手段。他主张用改良社会政治的文学革命,来反对维护封建社会制度及其伦理道德的旧文学。打倒“垢污深积”的封建文学,是为了推翻“黑暗未灭”的封建社会。这种显然是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主张,包含了深刻的反封建的政治内容。在一个时期里,胡适形式主义文学改良的鼓噪,淹没了思想革命的战斗呼声。陈独秀等人倡导的文学革命同反对旧道德的思想革命紧密结合、蓬勃发展之后,鲁迅便热情地投入了《新青年》的战斗行列。这个事例也证明,《新青年》提倡的文学革命,开辟了文学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优良传统。陈独秀文学革命主张的战斗性,与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不同,首先就表现在这里。
其次,陈独秀一开始就没有把文学革命主张只局限于语言形式的改革,而十分重视文学内容的革命。他明确提出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使用的是文言,而是因为他们遵奉“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古法,失去了“独立自尊之气象”“抒情写实之旨”,于“大多数无所禆益也”。其形式“陈陈相因”“有形无神”;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38]后来,他又明确主张文学应该用以“改造社会,革新思想”。[39]他要求文学要表现人生,表现社会,“赤裸裸地抒情写世”,以有益于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些,还是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文艺思想。在当时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条件下,他用这种主张来反对封建的文学,努力使文学从“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工具,变成“改造社会,革新思想”的武器,这本身,不能不说是文学上的一个重大的革命。
有的论者,依据陈独秀不赞成胡适的“须言之有物”一条,便认为他主张文学应该超越政治,不应该“言之有物”。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陈独秀在给胡适的复信中确实说过:在“不作无病之呻吟”之外,不必再提“言之有物”了。因为“言之有物”一语,如果“不善解之”,“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窃以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字作用不同,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40]在给另外一个人的复信中,他又说:“‘言之有物’一语,其流弊虽视‘文以载道’之说为轻,然不善解之,学者亦易于执指遗月,失文学之本义也。”[41]不难看出,陈独秀不同意提“言之有物”,并不是反对文学表现社会现实的内容,不是主张文学超越政治。他是看到这一表述解释不清可能造成的流弊,要同“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观念划清界限。他是坚持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他说:“实写社会,即近代文学家之大理想大本领。实写以外,别无所谓理想,别无所谓有物也。”[42]他又说:“文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文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六经’,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43]他的反对“言之有物”,是反对用文学表现“圣贤之言”,载孔孟之道;他讲的文学自身独立之价值,是要文学从“攀附”圣经贤传的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他提倡文学除了“状物达意,描写美妙动人,此外不应再有其他目的”,是为了强调文学本身的艺术特征,把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区别开来。他没有反对文学描写社会和人生,更没有反对文学作为改造社会革新思想的武器。他的表述确实有不明确和混乱之处,但在这混乱和矛盾的外壳下,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主张的反封建的革命性质。
陈独秀文学革命主张的战斗性,还表现在他同封建旧文学彻底决裂的态度。胡适提出改良主义的“刍议”,唯恐有“矫枉过正”之处,对来自封建势力的反对,不敢表示一点微词。“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44]陈独秀比起胡适的这种软弱妥协态度,坚决多了。他在回信中针锋相对地提出:“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45]事实也确实如此。文学革命主张提出后,国中之人,“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其中也出现了种种折中的论调。有的主张选古文标准读本,白话可“由是以趋改进”;有的主张小学与中等以上学校分授白话和文言,以别雅俗;有的主张白话为各种文学实“矫枉过正”,“急进反缓,不如姑缓进行”。对于这种种貌似折中的论调,陈独秀始终抱着不退让、不妥协的态度,对于自己的主张,绝对地信守着,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遂不致上了折中派的大当”[46]。
陈独秀这种坚决彻底毫不动摇的态度,对文学革命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正如郑振铎后来说的那样:“他是这样的具着烈火般的熊熊的热诚,在做着打先锋的事业。他是不动摇,不退缩,也不容别人的动摇与退缩的!革命事业乃在这样的彻头彻尾的不妥协的态度里告了成功。”[47]
一九一九年底到一九二〇年初,随着陈独秀逐渐变为一个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革命文学主张也有了新的因素。如他进一步认识了文学改革同时代进步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的社会改造”,反对军阀财阀的“侵略主义和占有主义”,要求要有“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的民主政治和“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与此相适应,他提出了文学“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要创造新时代新社会生活进步所需要的文学道德,便不得不抛弃因袭的文学道德中不适用的部分”。[48]他强调新文化和新文学在“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49]方面的作用。他努力用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来解释文学革命发生的原因。他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50]胡适对这个接近唯物史观的解释十分不满,仍坚持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他说:“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51]这种意见上的分歧,反映了“五四”新文化统一战线思想分化的客观趋势,也可以看出陈独秀文学革命主张前进的足迹。
陈独秀在这个时期的革命文学主张,其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态度,是生气勃勃的,是富有战斗性的,同时,也存在许多弱点和局限。他的三种文学,缺乏明确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内容,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没有充分地阐述,带有朦胧模糊的性质。他主张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和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仍是停留在要求个性解放的反封建的高度,未能包含深入人民群众中去的内容和方向。这里的“国民文学”同周作人提出的“平民文学”一样,“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52]。他提倡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认为我国文艺“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53],但又分不清自然主义与写实主义的区别,错误地认为自然主义“视写实主义更进一步”[54]而加以鼓吹。他对于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学遗产,“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55]。毛泽东同志对“五四”运动“许多领导人物”的这一批评,也适用于说明陈独秀文学革命主张存在的严重毛病。尽管如此,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毕竟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面旗帜,“它支配了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坛,更发动了后十年的新的文学运动”[56]。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中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
三
《新青年》旗帜鲜明地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不能不引起社会上一切复古势力的忌恨。随着文学革命声势的日益壮大,《新青年》及文学革命的一些倡导者,便成了复古派文人非难和攻击的鹄的。“这面‘文学革命’的大旗的竖立是完全地出于旧文人们的意料的。他们始而漠然若无睹,继而鄙夷若不屑于辩,终而却不能不愤怒而诅咒着了。”[57]对于旧文人们的形形色色的愤怒和诅咒,陈独秀及《新青年》其他一些同人,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前后,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同封建复古派的斗争,就成了整个“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斗争中,陈独秀同样表现了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勇猛坚定的态度。
《新青年》出版以后,受到封建遗老遗少的“八方非难”,被他们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一九一九年一月,发表在《新青年》六卷一号上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就是陈独秀撰写的一篇声讨复古派的战斗檄文。面对复古派加给《新青年》的破坏孔教礼法、破坏旧伦理道德、破坏旧文学等种种罪名,陈独秀理直气壮地宣称:“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e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他引述西方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酿成“流血革命”,换来“光明世界”的教训,认定只有德、赛两先生才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他在该文最后宣告:“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科学和民主,是思想革命的旗帜,也是文学革命的旗帜。它反映了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新兴无产阶级的历史要求和时代的精神。陈独秀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痛击复古派的种种非难,揭示了对旧政治、旧道德和旧文学进行变革的历史必然性,这就把《新青年》反复古逆流的斗争提到更加自觉的高度。他那种“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的大无畏精神,不是个人的表现,它体现了《新青年》团体坚持真理的决心和勇气。这里,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思想因素在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身上产生的宝贵的影响。
后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入狱。在他出来的时候,李大钊同志写了一首题为《欢迎独秀出狱》的诗。诗里说:“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究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58]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中坚定的言论,代表了《新青年》集体坚持真理的声音。
在反对复古派的斗争中,陈独秀很少改良调和的色彩。他不局限于文学形式上的纷争,而把反对旧文学同反对旧道德的斗争结合起来。他说:“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59]又说:“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其势目前虽不可侮,将来必与八股科举同一运命耳。”[60]这里,陈独秀使用的仍是改造国民性和进化论的思想武器。但他认识到改革旧文学、旧道德与改革社会政治的依赖关系,坚信旧文学、旧道德的必然灭亡。这就是他主张的现实的革命性。
当时,封建复古派文人加给《新青年》一个恶谥:“骂人”。特别是刘半农、钱玄同的《答王敬轩书》的双簧戏之后,更激怒了一些顽固势力。他们纷纷攻击《新青年》,“不务以真理争胜,而徒相目以‘妖’”,“开卷一读,乃如村妪泼骂,似不容人以讨论者,其何以折服人心”。[61]胡适听了之后,把这些攻击视为“诤言”,责备刘半农事出轻薄,屡表不满。鲁迅则坚决支持刘半农、钱玄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战斗态度。他还建议,有些文章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同时刊登,以便“出而又出,传播更广,用副我辈大骂特骂之盛意”[62]。陈独秀的态度与鲁迅相同。有人写信反对《答王敬轩书》,攻击《新青年》“肆口侮骂”。陈独秀坚定地指出:对那些“闭眼胡说”的顽固派“则唯有痛骂之一法”,并痛斥他们是“学愿”,是“真理之贼”[63]。有人写信,劝《新青年》不要“骂人”。陈独秀复信答得好:“骂人本是恶俗,本志同人自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答足下的盛意。但是到了辩论真理的时候,本志同人大半气量狭小、性情直率,就不免声色俱厉;宁肯旁人骂我们是暴徒,是流氓,却不愿意装出那绅士的腔调,出言吞吐,致使是非不明于天下。因为我们也都‘抱了扫毒主义’,古人说得好,‘除恶务尽’,还有什么客气呢?”[64]确实如此。对封建顽固派,没有什么客气可讲。正因为有了这种坚持真理,辨明是非,不怕笑骂,除恶务尽的态度,新文化运动才能排除复古派的干扰障碍向前发展,文学革命才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
一九一九年二三月间,以《新青年》阵营为中心的新文化思潮同以林琴南为代表的封建复古派逆流,展开了一场大论战。陈独秀以刚刚诞生的《每周评论》为主要阵地,为保卫文学革命的两大旗帜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封建复古派文人林琴南及其门生、封建遗少张厚载,造谣言,编小说,写公开信,运动反动当局,妄图一举扑灭新文化运动。陈独秀针对他们的卑劣伎俩,在《每周评论》上连续发表了《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旧党的罪恶》《林纾的留声机》《想用强权压倒公理的表示》《林琴南很可佩服》等文章和随感录。他阐明了这场新旧思想斗争的实质,指出这些“迷顽可怜的国故党”之所以如此仇恨《新青年》,就是因为它“反对孔教和旧文学”;他揭露了“国故党”“依靠权势”,“暗地造谣”,向新文化运动反扑的阴险卑劣的面目;他断言顽固派“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逃脱不了最终失败的命运。在这些战斗的文章中,闪烁着锐利的革命批判锋芒。
陈独秀和李大钊一起,以毫不妥协的革命姿态,在《每周评论》上组织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战斗。周刊发表了李大钊、鲁迅思想深刻锋芒毕露的战斗文章;转载了林琴南谩骂《新青年》同人的小说《荆生》,陈独秀亲自撰写批判性的按语,“请大家赏鉴赏鉴这位大古文家的论调”。周刊刊登了对《荆生》“文法之舛谬,字句之欠妥”一一进行批改的辛辣杂文,出了这位“海内所称大文豪”林琴南的丑。他还在《每周评论》开辟《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一栏,出了两期“特别附录”,摘登各地报刊批判林琴南、声援新思潮的舆论。
这场反复古的大战,带有过去所未曾有的特点。它把新文化运动扩展成为广泛的社会新旧思潮的斗争。反对封建旧文化同反对封建军阀政府权势的斗争进一步结合起来了。斗争的结果,以复古派的惨败告终。林琴南等被斥为“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受到愤怒的申讨,新思潮却像滔滔洪流向前发展。它的胜利,使《新青年》这面文学革命的旗帜更加鲜艳夺目。陈独秀在这场斗争中表现了一个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锋芒和才能。
陈独秀还不是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姿态参加这场战斗的。他没有从阶级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来看待这场斗争的实质。这一点,他不如李大钊。李大钊在斗争中的第一篇文章《新旧思潮之激战》中,以苏联十月革命为例,从阶级斗争的规律论述了反动顽固势力及其依靠的“伟丈夫”的必然失败和新文化潮流的必然胜利。陈独秀对封建军阀的“伟丈夫”却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相信封建军阀刺刀操纵下的国会“没有干涉国民信仰言论自由的道理”,说“稍有常识的议员都不见得肯做林纾的留声机”。[65]“五四”运动之后一个时期,陈独秀仍然认为“我们不情愿阶级斗争”,要使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从而“不至于造成阶级斗争”。[66]他劝人们用“同情的热泪”,使杀人的军阀放下屠刀,“一同走向光明”。[67]这种唯心史观的局限,不能不给他反对文学上复古派的斗争带来上述的弱点。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历史事实。
四
一九三二年,刘半农编辑了一本《初期白话诗稿》。这本印得相当精致的线装书,集印了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沈尹默、周作人等人在内的“白话诗初期几位诗人的手迹”。在《序言》里,刘半农讲:“仲甫先生的白话诗作得很好,旧体诗作得很好。白话诗就我所知道的说,只有《除夕》一首。”这里说的《除夕》,原题是《丁巳除夕歌》,刊登在《新青年》四卷三号上。这确实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陈独秀的第一首白话诗。
《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是从白话诗最先开始实践的。这在文学革命中具有拓荒的意义。当时报刊载文称:“近来《新青年》杂志中,提倡这种自由白话诗,真是中国诗歌的大革命。”[68]为了壮大新诗革命声势,回击封建文人的非难,《新青年》许多同人都参加了新诗创作。陈独秀的《除夕歌》,就是这种战斗的产物。刘半农把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都算在“白话诗初期几位诗人”的行列,不是没有道理的。但他说陈独秀的白话诗“只有《除夕》一首”,就不正确了。至少,在《新青年》七卷二号上,我们还读到了陈独秀出狱后写的另一首白话诗《答半农的D——诗》。这首诗,是对刘半农因他被捕入狱而写的一首诗的答复,但思想很不高明。他宣扬用“同情的热泪”做封建军阀和顽固势力“成人的洗礼”,充满了托尔斯泰式的迂腐说教。倒是他的那首《除夕歌》写得比较好些。
“除夕歌,歌除夕;几人嬉笑几人泣;富人乐洋洋,吃肉穿绸不费力。穷人昼夜忙,屋漏被破无衣食。长夜孤灯愁断肠,团圆恩爱甜如蜜。满地干戈血肉飞,孤儿寡妇无人恤。烛酒香花供灶神,灶神那为人出力。磕头放炮接财神,财神不管年关急。”劳动人民的啼饥号寒,孤儿寡妇的呻吟无告,军阀势力的鱼肉百姓,封建迷信的虚妄害人,都写出来了。有趣的是,同期《新青年》上,也刊登了胡适的一首《除夕歌》,记叙他同一个朋友吃午饭的经过:“记不清楚几只碗,但记海参银鱼下饺子,听说这是北方的习惯。饭后浓茶水果助谈天,天津梨子真新鲜!吾乡雪梨岂不好?比起它来不值钱!”陈独秀的诗里,也有“人生如梦”的感慨。但是我们要看其主要的,同是《除夕歌》,一个是社会愤懑不平的呼声,一个是资产阶级享乐生活的津津乐道,两相比较,显示了多么不同的思想境界,也看出胡适所谓“言之有物”的真正内容究竟是什么。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中的实践,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翻译介绍外国进步的文艺思潮和作家。陈独秀同“五四”前后一些新文化提倡者一样,把介绍西方进步的文艺思潮和作家,看作是传播科学民主思想、改革中国社会现实的一种手段。正如沈雁冰在一篇文章中说的:“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69]
陈独秀的翻译介绍西方文艺思潮,贯穿了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早在一九〇三年,他曾为苏曼殊译的雨果的《惨社会》做了润饰修改工作,刊于上海《国民日日报》上,后来报纸被迫停刊,这部作品又经陈独秀补译,改名《惨世界》,署名“苏子谷、陈由己(陈独秀别号——引者)同译”,以书刊行于世。这是雨果的《悲惨世界》一书在中国较早的译本。一九一五年,他在为苏曼殊的文言小说《绛纱记》写的序里,又介绍了“以自然派文学驰名今世”的英国文学家王尔德和他的《莎乐美》。接着,他在苏曼殊《碎簪记》后序中,阐明了这些外国爱情小说的意义。他肯定了“古今中外之说部”描写自由恋爱,反对封建束缚的进步意义。“人类未出黑暗野蛮时代,个人意志之自由,迫压于社会恶习者又何仅此,而此则其最痛切者。”王尔德的《莎乐美》有极重的唯美主义色彩。陈独秀介绍它,并不是沉迷于唯美主义的艺术,是借其“最痛切”的爱情故事,鼓吹反对社会恶习的“迫压”,争取“个人意志之自由”。
陈独秀是很了解西方进步的文艺思想和作品在思想革命和社会改革中的作用的。在《新青年》创办后,这种介绍工作,成了他积极进行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陈独秀说:“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国人此种精神委顿久矣。”[70]他翻译外国作品,介绍西方文艺思潮,都是服从于用进步文艺思想改变国人精神的“委顿”,唤醒国民精神的自觉这一总的目的。他在《新青年》上,第一个用文言翻译了美国国歌《阿美利加》,是为了向中国青年传达“爱吾土兮自由乡”“自由之歌声抑扬”这种自由和爱国的声音。他用文言译了泰戈尔的《赞歌》四章,是要人们学习泰戈尔“语发真理源,奋臂赴完好”这种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他称泰戈尔是“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印度青年尊为先觉”。显然,他是想用东西文化的精神文明,唤起中国青年的觉悟。这种启蒙主义文艺思想,在当时具有的革命意义,就在这里。
从这种启蒙文艺思想出发,陈独秀介绍西方文艺思潮时,特别强调文艺与改良人生、文艺与改革社会的关系。他介绍了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当代之文豪”。他们“以明晰灵活之笔,发表其理论,于讽刺文,于小说,于记事,使不学之俗人,亦得读而解之”。他们的主张,“法兰西人民躬任实行,终之以革命焉”[71]。可见,陈独秀“极称法兰西文明之美”,是为了促进中国社会革命的到来。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连载两期的长文《现代欧洲文艺史谭》。这是新文化运动初期系统介绍西方进步文艺思潮的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叙述了“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介绍了法国的左拉、龚古尔、都德,英国的王尔德、萧伯纳,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安特列夫,挪威的易卜生,德国的霍普特曼等作家。他强调这些大文豪,“非独以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这些思想是什么?他解释道:“十九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宣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而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分不清批评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别,把自然主义看作现实主义更高的发展,这是“五四”前后新文学运动一个普遍性的弱点。[72]但是陈独秀在介绍这些作家时,不是强调自然主义的琐细描写,而是注重他们的作品暴露“宇宙人生真相”,破坏“旧思想旧制度”的进步作用。他称赞左拉对传统学说与当世社会批评“无所顾忌”的批判态度;他推崇易卜生剧本“刻画个人自由意志”的个性解放思想;他赞誉托尔斯泰“尊人道,恶强权,批评近世文明”的反抗精神。他认为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原因是“以其实现于剧场,感触人生愈切也”。总之,他认为进步的文艺潮流,是适应破坏一切“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的需要而产生的。他强调的批判社会、反抗强权、争取个性解放的精神,在思想革命和社会革命中发挥了战斗作用。
陈独秀这些介绍工作,主要在“五四”之前。他强调的社会改革还是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他所谓的文艺表现人生的“真切”,也是十分朦胧的要求。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的作家他还菁芜不分,一概肯定。他这些介绍工作,就其主要倾向来看,毕竟是对封建的旧制度旧文明的挑战和冲击。这些实践,实际上是整个“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五
谈到《新青年》和“五四”文学革命,一些论述往往只谈鲁迅与李大钊的关系,而回避鲁迅与陈独秀的交往。至于鲁迅参加《新青年》阵营的战斗,是否受了陈独秀的一些影响,那更是讳莫如深的问题了。这,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尊重历史事实的,倒是鲁迅自己。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一九三三年三月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样说过:“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73]
陈独秀办《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很注重文学创作实绩。对于那些表现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精神的白话文学作品,更是大力提倡。他对鲁迅创作的推崇和支持,就是一例。
《新青年》虽然大力倡导文学革命,但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前刊登的文艺作品,主要还是文言的小说创作和翻译作品,以及少量白话诗的“尝试”。“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地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74]鲁迅的短篇小说,是文学革命划时代的纪念碑。它喷射着猛烈的反封建的革命火焰,封建制度及其礼教吃人的历史在这里被描写得淋漓尽致。由于内容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不仅在当时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还引起了《新青年》同人的重视和称赞。这些小说壮大了文学革命的声威,成了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陈独秀成为“催促”鲁迅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一九一八年一月,鲁迅参加了改组后的《新青年》编辑部。鲁迅和陈独秀的接触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鲁迅说:“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75]“《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76]鲁迅和陈独秀之间的关系,虽然这时候就开始了,但他们之间的正式通信,却是一九二〇年秋天以后的事。这时,陈独秀已被迫离开北京,到了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往上海。催促鲁迅为《新青年》做小说,原来由钱玄同担任,现在不得不由陈独秀亲自出马了。从《鲁迅日记》上我们可以看到,自一九二〇年八月七日,到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六日,鲁迅与陈独秀信函及寄稿往来有九次之多。鲁迅给陈独秀信四封,寄稿件七次,得陈独秀信二次。除此之外,陈独秀向鲁迅催做小说,多通过给周作人的信。如一九二〇年三月十一日陈独秀致周作人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一九二〇年七月九日信又说:“豫才先生有文章没有?也请你问他一声。”就在这两封信以后,八月七日《鲁迅日记》即载:“寄陈仲甫小说一篇。”这篇小说,就是著名的《风波》。陈独秀八月十三日立即回信道:“两先生的文章今天都收到了。《风波》在这号报上印出。……倘两位先生高兴再做一篇在二号报上发表,不用说更是好极了。”这时,陈独秀已变成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新青年》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胡适不久以后就以其“政治色彩太浓”为理由,声言恢复“不谈政治”的戒约。在面临分裂的形势下,鲁迅坚定不移地继续取“遵奉前驱者的命令”的态度,积极撰稿支持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表示了义无反顾的韧性战斗精神。陈独秀对鲁迅创作的“催促”,也并非一般的编辑约稿的关系,而是《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斗争的需要。频繁的催促,反映了陈独秀对文学革命战斗实绩热切的渴望。
对于鲁迅的小说,陈独秀有热情的催促,也有敏锐的眼光。鲁迅的《风波》,以惊人的现实主义手法,再现了张勋复辟在农村引起的一场小小的“风波”,向人们提出了彻底铲除封建复辟势力的任务。它有重大的革命现实意义。陈独秀接到这篇小说之后,立即在《新青年》上刊登,同时在一封回信里对小说表示了极高的推崇。他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地佩服。”这信写在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此以前,鲁迅在《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上只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和《一件小事》五篇小说。尽管这些小说以思想的深邃和形式的新颖,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反响,但对它们的思想意义,并不是人们都认识的。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表示了这样极为心折的推崇,应该说,他的眼力是很不错的。
当然,推崇和赞赏不能代替科学的评价。说陈独秀当时已经充分认识了鲁迅小说的价值和意义,这不符合实际。他不是作为文艺家在评论小说,而是作为革命家在了解小说。他的出发点是反封建战斗的需要,是用实际成绩对旧文学示威的需要。他推崇鲁迅的《风波》,主要是看到了它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中的价值。正因为这样,《风波》刚刚刊出,他便在九月一日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这样可贵的建议:“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
陈独秀不独催促鲁迅做小说,还催促鲁迅做杂文、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文和随感录,这是他与大家取一致“步调”,所创作的“革命文学”的实绩。一九一八年底,陈独秀、李大钊主持创办了《新青年》团体另一个思想阵地《每周评论》。在筹建过程中,陈独秀写信给周作人,通知周刊筹妥及交稿日期,信中特赘一笔:“豫才先生处,亦求先生转达。”鲁迅积极支持了陈独秀的约稿盛情。他先后写了《美术杂志第一期》和《敬告遗老》《孔教与皇帝》《旧戏的威力》三则随感录,以“庚言”为笔名发表了。虽是几篇短文,却可以看出鲁迅对陈独秀及《新青年》团体的支持,看出鲁迅为了保卫文学革命发展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战斗热情。在陈独秀的支持下,鲁迅将原来被腰斩的翻译日本武者小路实笃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在《新青年》上重新刊登[77],借他人“敲门的声音”,权作“中夜的警钟”。陈独秀向鲁迅建议重印《域外小说集》,还自告奋勇张罗出版事宜。[78]鲁迅十分感谢战友的盛情,为有旧梦重温的机会而“觉得是极大的幸福”。[79]
鲁迅十分自豪地称自己的作品为“遵命文学”。他遵奉的,不是皇上的圣旨,不是金元,也不是真的指挥刀,而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这里说的“前驱者”,就包括陈独秀在内。这里说的“命令”,就是《新青年》团体所体现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要求。任何人的社会活动,都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孤立的个人活动。陈独秀以及《新青年》提倡的文学革命,适应了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要求,体现了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前后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鲁迅同《新青年》团体及陈独秀的关系,因此就带上了革命的阶级关系的性质。诚然,真正认识到鲁迅在“五四”文学革命中伟大旗手和主将地位,对鲁迅作了这样评价,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四十年代初才得出的科学结论。要求陈独秀当时对鲁迅有这样的认识,当然是不切实际的。有的论述,无视陈独秀“五四”时期与鲁迅的战友关系,无视陈独秀对鲁迅创作的支持和推崇,而依据陈独秀二十年后写的文章中的只言片语,判定陈独秀对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革命文学作品,“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价”。这种看法,恐怕不能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吧。
一九七九年二月—三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