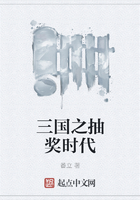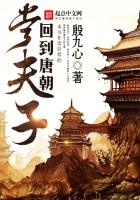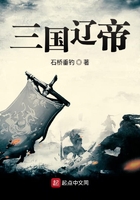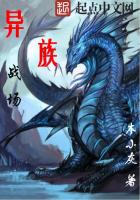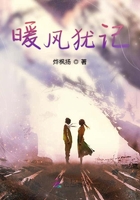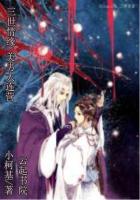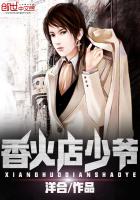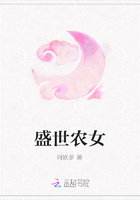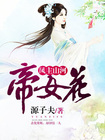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有这样著名的美妙一幕:从树林中狩猎归来,娜塔莎·罗斯托娃和哥哥尼古拉被“大叔”(娜塔莎这么叫他)邀请去他朴素的小木屋里做客。“大叔”是退休军官,品行高尚但有些古怪,和他同住的还有农庄里一个结实健壮的农奴,女管家阿尼西娅。从老人对她温柔的态度明显能看出,她就是他没有名分的“妻子”。阿尼西娅端进来一整盘俄罗斯特色家常饮食:腌蘑菇、加了酪乳的黑麦饼、蜜饯、蜂蜜气泡酒、白兰地药酒和各式伏特加。吃过饭后,狩猎随从的房间里传出了巴拉莱卡琴声。这只是一段简单的乡村民谣,按理说不会是一位伯爵小姐所喜欢的。但看到自己的小侄女几乎要随之起舞,“大叔”也就叫人拿来自己的吉他。他吹掉上面的灰尘,朝阿尼西娅眨了下眼睛,精准地踩着俄罗斯舞逐渐加速的节奏,唱起了著名情歌《在大街上》。尽管娜塔莎之前从没听过这首民歌,但她心中涌起了一种莫名的感觉。“大叔”唱起歌来就像农民那样,确信歌曲的含义就蕴含在歌词之中,只为突出歌词的曲调“自然而然就哼唱出来”。在娜塔莎看来,这种直抒胸臆的唱法让整首曲子都带有鸟鸣般的质朴魅力。然后“大叔”便招呼大家一起来跳。
“来,小侄女!”大叔向娜塔莎挥了挥那只离开琴弦的手。
娜塔莎扔掉身上的披肩,快步走到大叔跟前,双手叉腰,动了动肩膀,站住了。
这个受过法籍家庭女教师教育的伯爵小姐是何时何地、又是如何从她呼吸的俄罗斯空气中汲取了这种精神的?并且从其中得到了早已被披肩舞(pas de chale)挤掉的舞姿?而这正是大叔所期待于她的那种学不来教不会的俄罗斯的精神和舞姿。她刚一站稳,微微含笑,那神态庄严、高傲、狡黠、欢乐,顷刻之间,尼古拉和所有在场的人最初那阵担心——担心她做的不像那么一回事——就全部消失了,并且他们在欣赏她了。
她做得正像那么回事,并且是地地道道,简直丝毫不爽,阿尼西娅·费奥多罗夫娜立刻递给她一条为了做得更好的不可或缺的手帕。她透过笑声流出了眼泪:这个陌生的有教养的伯爵小姐,身材纤细,举止文雅,满身绫罗绸缎,竟能体会到阿尼西娅的内心世界,以及阿尼西娅的父亲、婶婶、大娘,每一个俄罗斯人的内心世界。[1]
是什么让娜塔莎如此本能般跟上这支舞的节奏?她为何毫不费力便能领会这个被社会阶层和教育远远隔离的乡村文化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假设,一个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可能是由各种看不见摸不着却与生俱来的情感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就像托尔斯泰在这个浪漫场景中让我们不禁想到的那样?这个问题将我们带到了本书的核心。本书虽然自称是一部文化史,但读者在其中将看到的不仅仅是《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伟大作品,也包括娜塔莎披肩上的刺绣和乡村歌曲的表达手法。诸如此类,它们融为一体,并非作为艺术的丰碑,而是民族意识的表现,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社会习俗和信念、民间传说和宗教、习惯和惯例,以及与所有其他微小的精神现象一起,构成了一种文化和一种生活方式。我要论证的不是艺术对生活的呈现,尽管种种关于这个时期的回忆表明,确实有贵族妇女就这样跳起了民间舞蹈,[2]但娜塔莎之舞不能被当作一种现实经验的文字记录来看待。我想说的是,艺术可以作为信念的承载——在这里,托尔斯泰渴求的是一个包含俄罗斯农民和“1812年的孩子”的广泛共同体;后者作为自由派的贵族与爱国者,是《战争与和平》众多场景的主要人物。
俄罗斯邀请文化史家去探寻艺术作品表层之下的存在。过去的200年间,在议会政治和出版自由阙如的情况下,俄罗斯的艺术一直是政治、哲学和宗教争论的竞技场。正如托尔斯泰在《关于〈战争与和平〉》(1868)中写到的那样,俄罗斯传统下的文学巨作并非欧洲意义上的小说。[3]它们是富含象征性的沉思,具有繁复的诗性结构,犹如抽象意义的具体再现,是检验观念的实验室;同时,与科学或宗教一样,其生命力的来源在于对真理的追求。所有这些作品的首要主题都是俄罗斯——它的人物、它的历史、它的习俗惯例、它的精神实质,以及它的命运。以一种超凡——如果不是俄罗斯独有——的形式,这个国家的艺术活力几乎全部奉献给了对把握自身民族身份的探求。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艺术家要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肩负起道德领袖和民族先知的重担,而国家对他们的恐惧和迫害又是如此之甚。在政治理念上,他们与俄罗斯当局格格不入;在教育水平上,他们又与俄罗斯农民生分;于是,艺术家全靠自己,通过文学与艺术来创建一个价值和理念意义上的民族共同体。做一个俄罗斯人意味着什么?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使命是什么?而真正的俄罗斯又在哪里?欧洲还是亚洲?圣彼得堡还是莫斯科?是沙皇的帝国,还是娜塔莎的“大叔”所住的、只有一条街道的泥泞村庄?在俄罗斯文化的黄金年代里,这些“受诅咒的问题”在每一个严肃知识分子的脑海中阴魂不散:从普希金到帕斯捷尔纳克,包括文学评论者与历史学者、画家与作曲家、神学与哲学人士。它们就是本书试图探讨的、隐藏在艺术表面之下的问题。这里所涉及的作品代表着一部观念史,包含了种种俄国借以理解自身民族的概念思想。如果我们观察足够仔细,或许可以窥见这个民族的内心世界。
娜塔莎之舞就是这样一个开场白。它的核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相遇:上层阶级的欧洲文化与农民的俄罗斯文化。1812年战争是两者第一次联手推动了民族的形成。受到了农奴爱国热情的鼓舞,娜塔莎那一代的贵族开始突破他们自身阶层的外国传统,转而寻求一种建立在“俄罗斯”原则基础之上的民族意识。他们用母语取代法语,并将自己的风俗和衣着、饮食习惯和室内设计品位都俄罗斯化了;他们走入乡村去了解民间传说、舞蹈和音乐,希望能够在所有艺术形式中塑造一种民族风格,来接近和教育普罗大众。像娜塔莎的“大叔”一样(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还加上了她哥哥),一些人放弃了圣彼得堡的宫廷文化,而试着与庄园中的农民一起过一种更淳朴(也更“俄罗斯”)的生活。
这两个世界的复杂互动,对民族意识以及19世纪的所有艺术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它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但接下来讲述的故事并不意味着,这种互动所产生的结果是某个单一的“民族”文化。俄罗斯太复杂,社会分隔严重,政治上过于分歧,地理定义太不明晰,也许还失之辽阔——这些都使得其民族传统不可能是单一文化。我的出发点毋宁说是去欣赏俄罗斯文化形态中那纯粹的多样性。托尔斯泰的这个段落之所以如此具有启发性,正是在于它用一段舞蹈将形形色色的人串联起来:娜塔莎和她哥哥,对他们来说,陌生的乡村世界瞬间展现了它的魅力;他们的“大叔”,住在这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阿尼西娅,虽说是一名农妇,却与“大叔”共同居住在娜塔莎世界的边缘;还有狩猎随从和其他家仆,无疑带着惊奇的乐趣(或许还有其他心态)观赏这位美丽的伯爵小姐跳着他们的舞蹈。我的目的,是要通过与托尔斯泰展示娜塔莎之舞同样的方式来探索俄罗斯文化:将其视为一系列的特殊经历或具创造性的社会活动,能以许多不同方式展现和理解。
通过这种折射的方式来看待文化,是对其纯粹、有机或本质观的挑战。并不存在托尔斯泰所想象的那种“纯正的”俄罗斯民间舞蹈,大多数俄罗斯“民歌”实际上都是来自城镇,就像娜塔莎随之起舞的那段旋律一样。[4]托尔斯泰笔下的乡村文化,其部分元素可能来自亚细亚草原——由13到15世纪统治俄罗斯的蒙古骑兵引入,他们大部分后来都定居下来,经营贸易、放牧牛羊或成为农场工人。娜塔莎的披肩几乎肯定是从波斯输入的;虽然1812年以后俄罗斯农民样式的披肩开始流行,但使用的装饰图案很可能参考了来自远东的同类商品。巴莱拉卡琴发展自冬不拉,这是一种起源于中亚、类似吉他的乐器(现在仍在哈萨克音乐中普遍使用),于16世纪引进俄罗斯。[5]至于俄罗斯的民间舞蹈传统,按照19世纪一些民俗学家的看法,其源头便是远东的舞蹈形式。俄罗斯舞蹈更多是以队列或者圆圈呈现,而非双人舞;手和肩膀的动作对节奏的掌握不亚于脚的作用;而且女性舞者微妙的玩偶姿态和保持头的静止也是非常重要的。与娜塔莎在她人生第一次舞会上与安德烈公爵跳的华尔兹舞相比,这真是太不一样了,她模仿这些动作的时候一定感到非常陌生——毫无疑问在围观的农民眼中也是如此。然而,如果说这乡村一幕背后并不存在所谓的俄罗斯传统,如果说这里呈现的任何文化因素都是舶来品的话,则娜塔莎之舞的意义,便在于为本书将要阐释的观点提供了一种象征,即纯粹的民族文化是不存在的,只有围绕着它虚构出来的表象,就像娜塔莎跳的民间舞蹈一样。
我的目的并不是“解构”这些表象;套用当前学院派文化史家的术语,声称俄罗斯的民族性不过是智识的“建构”,这也不是我想做的事。早在“俄罗斯”或“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这样的概念,以及任何其他民族认同神话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一种足够真实的俄罗斯。古老的莫斯科公国蕴含着某种历史意义上的俄罗斯,直到18世纪彼得大帝生搬来欧洲文明的那一套之前,它与西方迥然有异。在托尔斯泰生活的年代,赋予这个古老的俄罗斯生命的,依然是教会的传统,是商人与土地贵族的习俗,是帝国的6000万农民——他们散居在50万个遍布森林和草原的偏远村庄中,几个世纪以来生活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这就是娜塔莎之舞一幕中震撼人心的俄罗斯脉搏。托尔斯泰设想有一种共同意识,将这位年轻的伯爵小姐与俄罗斯的农夫农妇联系起来,这当然不是凭空捏造。因为,正如本书所要阐明的那样,存在着一种俄罗斯气质,它是一套本土的习俗与信念,一种内在、情感、本能。它一代代传承,有助于塑造人们的个性,维系共同体的黏合。事实证明,这种捉摸不定的气质比任何俄罗斯政府都更持久、更有意义:它让人们拥有了挺过其历史上最黑暗时刻的心灵,并给那些1917年之后逃离苏俄的人提供情感联系的纽带。我的目的不是去否定这种民族意识,而是指出,人们对它的领会要借助于各种神话(myths)。知识阶层被推动着去做欧洲人,他们与源远流长的俄罗斯渐行渐远,把祖国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忘得一干二净,以至于到了托尔斯泰的时代,当他们力图重新拾回“俄国人”的身份时,不得不借助历史传说和艺术创作来再造这个民族。通过文学与艺术,他们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俄国性”,正如娜塔莎通过舞蹈的仪式找到了自己的“俄国性”一样。因此,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揭穿这些作品的虚构性,而是去探索、去解释它们对塑造俄国民族意识所拥有的非凡力量。
围绕着对俄罗斯的民族想象,涌现了19世纪几种重要的社会思潮:斯拉夫派,他们笃信“俄罗斯灵魂”以及农民中纯正的基督性,还崇拜彼得大帝之前的传统俄罗斯,将其视为真正的“俄罗斯”生活方式的旗手——他们将这种生活方式理想化,并致力于将其提倡为18世纪以来精英阶层所接纳的欧洲文化以外的另一种选择;西化派,与前者针锋相对,他们崇拜圣彼得堡这个“通往西方的窗口”,这个在沼泽地上凭空而起的经典城市,它是其将俄罗斯按欧洲模式改造、按部就班追求自身启蒙的象征;民粹派,他们与托尔斯泰的观点相去不远,认为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其乡村组织将成为新社会的一种范式;斯基泰派,他们将俄罗斯视为一种来源于亚洲草原的文化,“富有自然活力”,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将要一扫暮气沉沉的欧洲文明,建立一个人类与自然、艺术与生命合而为一的新文化。这些神话不只是对民族身份的种种“建构”。从最崇高的个人身份、民族认同,到最日常的衣着服饰、饮食习惯或所使用的语言类型等事物,它们除了发展关于“自我”的概念,更在塑造俄国的政治理念与效忠对象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斯拉夫派就是典型。他们心中“俄罗斯”的概念是一种按照纯正基督教原则运行的父权制家庭,这在19世纪中期几十年间成为一种新政治共同体的组织核心,成员囊括了旧式的外省乡绅、莫斯科商人和知识分子、神职人员还有个别部门的政府官僚。不同的团体被这种关于俄罗斯民族的概念拢到一起,足以表明其在政治想象中的持久影响。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斯拉夫主义影响了政府对自由贸易和对外政策的立场,也影响了乡绅对国家和农民的态度。作为一场广泛的文化运动,斯拉夫派采用特定的谈话与衣着方式、社会交往和行为准则,有所区别的建筑与室内设计风格,还有他们自己的文学与艺术品位。他们穿树皮鞋和自家纺的大衣,蓄络腮胡,吃白菜汤,喝格瓦斯,住乡村小木屋,还建造颜色鲜艳的洋葱顶教堂。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这些文化样式经常被视为“纯正俄罗斯风味”。但这种认识也是一种神话:异域俄国的神话。这种印象最早是由俄罗斯芭蕾舞团输出的,他们就跳着异国情调版的娜塔莎之舞;之后由里尔克、托马斯·曼和弗吉尼亚·伍尔芙等外国作家参与塑造,他们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奉为最伟大的小说家,兜售他们自己版本的“俄罗斯灵魂”。如果说有一种神话需要驱除,那就是这种将俄罗斯视为异域和他方的观点。很长时间以来,俄国人都在抱怨西方公众不理解他们的文化,西方人只是在远远地观察,而不愿意像对待他们自己的文化那样去了解俄国文化内在的精妙之处。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抱怨是基于怨恨和受伤的民族自豪感,但它并非妄言。我们倾向于将俄罗斯的艺术家、作家和作曲家归类为某个“民族”的文化群体,不是把他们作为个体进行评判,而是看他们有多符合这个僵化的定见。我们期望俄国人有“俄罗斯风情”——他们的艺术风格就是淳朴的图饰、洋葱顶教堂钟声,以及一颗饱满的“俄罗斯灵魂”,所以好辨别得很。在1812—1917年间,这就是人们对俄国及其在欧洲文化中心地位的标准理解。俄罗斯传统中那些伟大的文化人物,如卡拉姆津、普希金、格林卡、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列宾、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佳吉列夫、斯特拉文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夏加尔、康定斯基、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纳博科夫、帕斯捷尔纳克、梅耶荷德还有爱森斯坦,他们不仅仅是“俄国人”,也同样是欧洲人。这两种身份紧密融合,互相依赖。和这些文化人一样,不管俄国人多么努力想要压抑这两种身份中的一个,这仍然是不可能的。
对那些欧化的俄国人来说,待人接物的方式有两种且非常不同。在圣彼得堡的沙龙和舞厅,以及宫廷或剧院的公开场合,他们非常“得体”(comme il faut):几乎像演员一样展示自己的欧洲风范。但是在不那么正式的私人生活领域中,也许是下意识地,他们自然而然地又成了俄罗斯人。娜塔莎对“大叔”的造访就描述了这样的一种转换:不同于她处处谨言慎行的家、罗斯托夫的豪宅或是沙皇接见的舞会,“大叔”在农村的家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这里她的天性可以自由发挥。毫无疑问,她很享受这样放松的社交场合,一曲舞蹈胜过千言万语。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变得“更俄罗斯”的惬意感觉,为娜塔莎所属阶层的许多俄国人所共享,包括她的“大叔”。造访乡间别墅(dacha),在树林中打猎、泡澡堂,还有纳博科夫所谓的“采蘑菇(hodit’po grib?)这项极具俄罗斯传统的运动”[6]——这些朴素的消遣不仅仅是对田园生活的回归,它们还是一个人俄罗斯品性的表达。解读这样的习惯是本书的目标之一。通过艺术作品和小说、日记和信件、回忆录和法令文件等材料,作者力图掌握俄罗斯身份认同的结构方式。
“身份认同”是近来时髦的一个术语,但除非一个人能指出它如何具体影响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和待人接物的方式,否则它就没多大意义。一种文化并不仅仅是由艺术作品和文学词语构成的,它还包括不成文的规矩、符号和象征、仪式和姿态,以及一种普遍情感,能赋予这些作品以共性,丰富人们的内心生活。所以读者在这里会发现,像《战争与和平》这样的文学作品,是日常生活场景(童年、婚姻、宗教生活、与大自然的呼应、饮食习惯、对待死亡的态度)的镜头交切,在其中我们有可能分辨出民族意识的轮廓。通过这些场景,我们或许得以意识到一种俄罗斯情感,它无声无息地孕育于生活之中,如同托尔斯泰在他著名的娜塔莎之舞一幕中所构思的那样。
现在该说一下全书的结构了。本书是对一种文化的阐释,而非通史,所以读者应该留心,其中讨论某些文化巨人的篇幅可能与其巨大成就并不相称。我以专题的形式,每一章分别探讨俄罗斯文化认同的不同线索,从18世纪讲到20世纪,但是为了各个专题内部的贯通,在某些地方并不一定遵循严格的时间顺序。有很短的两处(第三、第四两章的最后一小节)讲到了1917年之后的内容。个别之处涉及额外的历史时段、政治事件或文化机构,我会为普通读者提供基本的解释(更多信息或请参见大事年表)。我的故事止于勃列日涅夫时代。在那时,本书描绘的文化传统已经走到了其生命周期的尽头,之后发生的可能就是新传统的开端。最后,某些主题将在整本书中反复出现,呈现复杂的变调及系谱,如圣彼得堡的文化史,以及对两大贵族家族——沃尔孔斯基家族与舍列梅捷夫家族——的论述。这些顺序的穿插和转折意义,只有在读完全书之后方能理解。
注释
[1]L.Tolstoy,War and Peace,trans.L.and A.Maude(Oxford,1998),p.546.
[2]E.Khvoshchinskaia,“Vospominaniia”,Russkaia starina vol.93(1898),p.581即为一例。该主题会在第二章进行讨论。
[3]L.Tolstoi,Plonoe sobranie sochinenii,91 vols.(Moscow,1929-64),vol.16,p.7.
[4]Richard Taruskin对此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题为“N.A.Lvov and the Folk”,收录于Defining Russia Musically:Historical and Hermeneutical Essays(Princeston,1997),pp.3-24。
[5]A.S.Famintsin,Domra I rodnye ei muzykal’nye instrumentry russkogo naroda(St Pertersburg,1891).
[6]V.Nabokov,Speak Memory(Harmondswort,1969),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