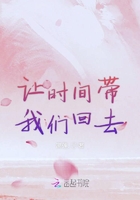用毛巾一下一下轻轻地擦拭,柔软的让人沉沦。
即使这样,我还是躲开了他的手,说:“教练,我自己来。”
“哎呀,你看看你,出那么多汗也不知道擦一下,这天儿还那么冷,就算我们这里有暖气,你也要注意点,万一感冒发烧了,我看你还怎么参加比赛。”
心中不免开始显他啰嗦,‘啰里吧嗦的老头教练,不就没把汗擦干嘛’。
我把白白净净的毛巾叠得四四方方,放在休息椅上,慢吞吞地站起来,然后问他接下来训练什么?
他叫我换上冰鞋,去滑一圈,找找感觉,然后和外面的一起训练。
有些不情愿,之前所有的志气在哪一瞬间消失了,又开始抗拒滑冰,不想去碰冰鞋,不想走上冰场,也不想去做任何跳跃动作,这一切显得那么的多余,因为做这些只是为了那个奖而已。
——
滑的过程中,我并没有去想要怎么把那段自由滑滑得更好,而是又想到小时候的一些事情。
八岁和十一岁那两年,我遇到了一些恶心的事情,但是不能说出来,因为这些事情被暴露出来以后,我基本上就不能做人了。平常戴的“皮”会被人扯掉,把我丢回最原始的地方,让我在没有皮肤的保护下,让自己跟这肉一起腐烂掉。
所以我尽力去忘记掉它,这种方法超级废脑子的,一方面,你为了忘记它而会时常性想起它,另一方面,好不容易你忘了,正在你开心之际,它又回来了。
至于是什么事情,在前几年新闻经常播报,就是某某人被潜啊,或者哪些可怜的娃被qj,现在,社会环境好很多,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恶心死人的报道。
可又有谁知道,这社会底层还有没有这些烂事。
再想起十七岁那年,险些回不了家,即使那个家我厌恶。
——
十七岁,刚升高二不久,也习惯了每晚都要晚自习。
吃饱饭后就到外面的公交站等公交。好在家离着公交站近,就在对面马路。
我站在公交牌下,微弱的灯光映着我的影子,旁边有树叶的影子触碰着它。
左等右等,始终不见公交车影。
我开始焦躁了,怕晚自习迟到被记过。
月钩挂在东北向的天空,没有车子驶过,没有行人往来,这条路只剩下我和这个路灯。
继续眺望,不远处打着灯光,缓慢朝我这边开来。我以为那是公交车,跺了跺脚,让自己不再焦躁。
到它驶近时,我才看清那是辆五菱的面包车。
司机把车开到我旁边,下来俩个人,我看到他们手里拿着捆绳,吓得撒开腿就跑,后面的人看周围也没有啥人,不紧不慢地朝我走来。
我跑得更快了,心里想着:我要完了对吧?这次,终于可以完了,那我跑什么,回去让他们做掉不就好了,如果是绑架,母亲那边——应该是不会给钱,估计直接让他们撕我票还差不多。
想着想着便停下脚步,转过身面对他们。
那俩人先是一惊,估计也没想到我会这么干。
然后犹犹豫豫地拿着绳子走过来。
我也没开口求饶,看我这架势应该能看出来,我是要求死的。
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不管怎么样,都任他们处理。
突然后面响起“叭叭”声,是公交车的喇叭。
我内心好像又抱着那飘过来的最后一根稻草,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伸出手,一边跑一边拦公交。
司机大抵看到我们是什么情况,踩了油门,距离看着有一两百米远,眨眼功夫到我面前停下来了。
我三步做两步,上了公交后,那两人贩才反应过来,赶紧溜回面包车内。
司机对我说:“别紧张,好在你大爷我远远就看到你们不对劲,才摁了喇叭,先把钱投了吧!”
自己胡撸胡撸毛儿后,掏出一块投进钱箱里。
车上乘客不多,都是刚打工回来的,插着耳机听着歌,完全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他们或许是累趴了,都东倒四歪地睡着了,伴着耳边的音乐。
学生也就只有我一个,我随便找了位,坐了下去。头抵着前面的座位,失声痛哭起来,庆幸自己还活着,庆幸自己还是想活的。
司机把车开得缓慢许多,手里拿着车载麦,向那头呼唤着:“老婆,我这班晚点交车,你先开吧!”
那头响应“好,行车安全!”
——
我滑没到一半,就停了下来,一直在回忆这些。
其他队员还在训练,没有人注意到我的不舒服。这些回忆,抹不去了,不管是差点被抓去卖,还是说被猥琐,它都会跟随我一辈子,永远困扰我。
我滑到一边,努力把气呼匀,脑子里不知什么时候起,就会自动播放这些东西。
我有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出了问题,但平时训练强度大,总能把这些东西给忘记。
教练悠哉悠哉地走了过来,说:“你没事吧?”
“没事,就是刚刚热身运动给累到了。”我狡辩着,不想让他看出我的不安。
“那我们开始你的自由滑吧,他们去做陆地训练了。”
“好。”
按照自己的感觉,一点一点的把舞蹈编出来。滑了几次后,终于确定这首歌要去怎么表达,并录好了视频,每天按照视频来滑,也不至于第二天又滑出另外一个版本。
教练也很满意,说练下去一定会变得很自然,至少不会在有人的情况下表现得很僵硬。
我们解决完这件事后,似乎放下了心里那块大石头,互相勉励对方好好干,好好滑。
回家路上,他提出要庆祝一下,我拉住他,“这有什么好庆祝的,没必要。”
“你这人能不能积极点,处理了这么大一个问题,就意味着我们往成功迈了一大步,你说,这是不是得庆祝?”
然后挠挠头又补充了一句,“年轻嘛!啥事都可以庆祝。我们晚上吃什么,我请客。”
“别吃了,走,我们去玩!”
我难得的好兴致,不管花多少钱都得表达出来。
“你上次不是没泡到妞吗?走,我带你去妹子。”
说完拿出手机打电话给阿东:“阿东,你那张卡还在不?”
那边也不知道是受什么刺激,大叫说:“姐,你要去玩吗?我跟你说,你去那家信号club,整老好了,还有弹簧的可以蹦。”
“知道了知道了,快快快,你卡在的话,放在楼下小卖部,我一会去拿。”
挂了电话后,我明显听到教练的肚子在“咕噜咕噜”叫。
“那还是先吃饭吧!”不可能带着一个没有力气,脸色苍白的人去吊凯子的吊妹子玩的。
随便钻进一家面馆,点了炸酱面吃。
教练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一看他话痨又要开始了,忙打住他:“教练,你吃完再说好吗?不够塞你嘴了这面。”
“不是说私下不用叫教练吗?”
等会儿,这人怎么跟我关注的点不一样,我是叫他安安静静吃面吧!
“行行行,个名字还揪那么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