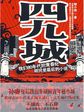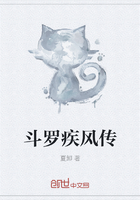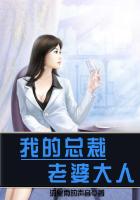西方女性主义者改造、强化了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些术语,同时也另造了一些新奇的名词,以表达女性主义的特殊诉求。政治与诗学、个人与集体、现实与先锋、本质与话语、历史的与文本的、妇女一体与策略性主体、明镜与妖妇等概念,“抗拒性读者”、“批判式阅读”、“妇女中心批评”、“女人腔”、“阴性书写”、“颠覆性写作”、“身份政治”、“身体政治”、“后殖民话语”等术语,交织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多元而繁复的图景里。女性主义的术语往往不为一般读者所理解,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也是陌生的东西。理解方面的困难使解释成为必然,术语的解说成为西方女性主义译介工作中的一个重点。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译介文本有不少涉及术语的解说问题的。大致看来,翻译的文本中对术语的解释成为许多介绍性文章的术语解释的范本,但介绍性文章在进一步的发挥中,对术语的解说有时出现些许多偏差。“阅读与写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的重要范畴,一些说法成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资源。本章对“女性阅读”方面的译介进行归类,列举译介中惯常的“阅读”词语和解说并加以评析。
一、Feminist Critique/Gynocritics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女性“阅读”的分类说来有几个方面:其一是“批判式阅读”;其二是“赞同性的阅读”;其三是研究女性阅读行为本身。前两者代表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两个阶段。对“女性阅读”的行为的研究则包含对女性所作的文学批评活动的反思,还有阅读文化内涵的关注。
“批判式阅读”和“赞同性的阅读”是相辅相成的。肖尔瓦特说:“女性主义批判”(feminist critique)着重批判,是对文学传统的解构;“女作家中心批评”(gynocritics)着眼于未来,期待可以“建立—分析女性文学的架构,发展以研究妇女经验为基础新模式”,而不是迎合男权中心文学体制的模式和价值。Elaine Showalter,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Essays on Women,Literature and Theory(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5),p。131.乔瑟芬·多诺凡有类似的观点,她说女性主义批评是辨证的,具有双重面貌:一是否定模式;二是正面或乌托邦模式。前者与肖尔瓦特的女性主义批判相当,而后者与女性中心批评相类。在否定模式的批评中,女性主义批评家审视文本中省略、裂隙、缺席之处,以批评的眼光将文本对照于其意识形态脉络(父权制),而在正面的面向(或者称作先知的模式),女性主义批评认同文本的解放向度,捕捉文本的乌托邦远景。但多诺凡也澄清,批判性的女性主义批评并不是简单地认定文本与意识形态有一对一的对应或因果关系。由于作者总是处在一种政治位置的存在,她的创造牵涉了“美学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因此,文本可视为一具有政治内涵的“欲望的寓言”。Joseph Donovan,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Exploration in Theory,preface。也许是因为多诺万的说法晚一些,另一方面其概括的是性质,不像肖尔瓦特概括那样能让人想到内容,所以并不很流行,中文译介文章中也很少有人提,但其概括还是准确的。不管怎么说,“女性主义阅读”的揭露性、批判性和“女性中心批评”的建设性、肯定性的都是为争取女性主义批评的权利、重现女作家原貌,二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
译介中引人注目的问题倒不是对上述几个词的解说。虽然中国凡是介绍西方主义文学批评的文章,鲜有不涉及“女权批评”(feminist critique)这个短语的,尽管由于对feminist一词的译名有争议而使feminist critique的译名有差异,但是译介文章、专著凡涉及这点,解说上并没有多少偏差,大同小异,都说是女性读者对男性作者的文学作品、传统经典书目的重新的、批判性的解读,或者说其“着重考察妇女作为男性文学的消费者的阅读行为,分析文学和文化中的妇女形象的塑造,批判文学评论中排斥妇女作家及其作品的倾向。”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12页。除了《性政治》外,不少译介文章提到了其他一些“妇女形象分析”的著作,朱迪·弗莱尔在《夏娃的面貌——19世纪美国小说中的妇女》(1976)指出,经常用来阐释美国文化的概念完全是男性化的,这种观察角度根本不考虑妇女的存在,同样男性文学批评家对文学中的妇女形象要么忽略不提,要么充满偏见。19世纪美国小说中的妇女形象是诱人的妖女、美国公主、强有力的母性和新女性。帕特里夏·斯塔布在《妇女与小说:女权主义与小说》中分析了英国18世纪中女性作为天使出现的根源,即男性生存在工业社会道德的沦丧中希望家庭能成为避风港,因而对家庭中的女性提出了较高的道德要求。
同样,译介文章对gynocritism的解释也没有多少差异。当然gynocritism译名有很多:陈志红把gynocritics翻译为“女性批评”,陈志红著:《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刘涓则将gynocriticism名为“妇女文学批评学”,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2页,第456页。谭大立称之为“女作家批评”,其他的介绍也名称不一。不少译介者在以上的专有名词的翻译后附英语原文,有的文章则不然,这就可能造成一些让人误解,甚至费解。比如,王逢振的文章中说肖尔瓦特指出“应把女权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区分开来”王逢振:《女权主义批评数面观》,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第151页。给人的感觉是中文的女权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说法有两个所指,其实读了下文对“妇女形象”为主的批评和“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才知道前面的“女权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可能是肖尔瓦特的feminist critique和gynocritics两个词的译文。然而,大多数译介文章都按照肖尔瓦特在《走向女性主义诗学》(1979)的说法中区分了“女权批评”(feminist critique)和“女作家中心批评”(gynocritics),翻译过来的文章还指出了这个词的演变,说“这个gynocritics的意思是妇女创作的文学史……后来,gynoctitics这个词被广泛采用,其含义也很快扩大到包括解读妇女创作(并不只是妇女创作的文学史)的所有方法论。”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56页。还有人特意指出,肖尔瓦特在其后来的《荒原中的女性主义批评》说gynocritics提供了理论上更多的可能性,“视女子著述为我们的首要论题,便迫使我们跃入新的概念的前沿,重新规定我们面临的理论问题的性质。现在已不是从意识形态上调和多元的修正论调的困难了,而是差异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如何将女子设立为一个独立的文字团体?女子著述的不同何在?”陈志红著:《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研究女性阅读行为本身的第一个切入点是表明女性读者受到男性阅读标准的损害。早期的译介文章中解释“抗拒性阅读”的必要性时候,多是说明妇女作为男性文学消费者曾经受到的戕害,也就是男性文学、标准对妇女读者的“改造”。为此,肖尔瓦特和其他一些著名的女性主义者的说法被翻译和引用。比如,林树明、盛宁、宋素凤在其书中都引述道,菲特莉在她所著的《抗拒性的读者》中开宗明义地说“文学是政治的”,而传统文学却以“非政治”、客观的姿态自我论述,而这种“非政治”究竟只是一种姿态,隐蔽了它背后实际上是充满男权中心结构的事实。宋素凤著:《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林树明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据信,由于渴望在男性中心的现实世界和象征秩序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获得同男人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在对女性诸方面权利的争取,妇女形象的设计、人生价值观的思考以及妇女阅读、女性研究等方面,妇女评论家的标准仍然是男性化的,对妇女作品的评论采取的也是男性美学,某种意义上否定了女性文学与创造意识的独特性,以一种普遍的即男性的批评标准来衡量妇女作家与作品,表现出与占统治地位的理性逻辑及本体价值相认同的一面。至于女性评论文学作品方法与男子一样标准的问题的例子,不少人转引下列例子:简·汤普金斯评论说,“安·道格拉斯在《美国文化中的女性化》中对1820~1870年间出现的女性作品的态度是轻视的,这正是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的学术态度。在她对女性化的批判后面,存在着‘为什么女人不更像个男人’的疑问。”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页。或者,有人引述肖尔瓦特,说“妇女期待着去认同一种代表人类完美的男性的经验的洞察力”,“女性读者共同加入了一种被明确拒斥的经验中;她被要求认同一种与她相对的自我;她被要求反对她自己。”
另一类研究女性阅读行为的形式蕴含了“文化研究”的内涵。“女性主义批判”(feminist critique)、“女作家中心批评”(gynocritics)的对象还基本上是正统文学,男性作家、女性作家多少都是已经进入文学史经典或者是被认为应该进入文学史的人物。然而,女性阅读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女性阅读与大众文学(非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翻译过来的《女性的奥妙》、《第二性》等著作均涉及这个问题,但很多人把女性的这部分阅读归类在“文化研究”中,译介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章对此很少提及。《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有文章用一定的篇幅介绍了詹尼丝·芮德伟的专著《阅读罗曼司:妇女、父权制和通俗文学》Janice Radway,Reading the Romance:Women,Patriarchy,and Popular Literature(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4)。罗曼司(Romance)是一种以吸引女读者为目标,以公式化的构思结构为特征,一度为男性读者、男性作者所歧视,在女性主义学者那里也被视为麻痹妇女的“低级读物”的通俗小说形式。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69页。美国各大超市里均有廉价的“罗曼斯”平装本销售,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并没有降低女性大量购买、阅读罗曼司的热情,怎样解释女性主义求平等、求解放的运动和读者心甘情愿地接受罗曼司“俘虏”这一奇怪的现象呢?《阅读罗曼斯:妇女、父权制和通俗文学》指出,读书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罗曼司是一种商品,它经过了市场商品流通渠道才到达读者手中,从美国图书出版发行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广告宣传、市场调查、发行销售和罗曼司热之间的密切关系;女读者之所以爱读罗曼司,是因为其使她们能暂时地摆脱为人妻为人母的琐碎事务。阅读就好比是一种自我独立的“宣言书”,为这些家庭主妇提供了逃避现实的机会,给了她们希望、安慰和知识。这一发现打破了传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罗曼司和阅读罗曼司所下的结论,以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常常把罗曼司的意义局限于文本中,以批评家的反应代替具体读者的反应。这里作者把发言权交给了读者,把她们对罗曼司的不同感受同各自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这里,大众对文化不仅仅是“消化”和“吸收”的关系,“文化是包含信仰、价值观,以及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在内的一个综合系统。这个系统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并赋予它意义……‘文化是日常生活的无形逻辑。’”罗曼司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普通商品,其受文化制约,又为文化服务;罗曼司的读者也不是一个同一或统一的整体,其消费兴趣和消费动机既受社会的影响,又与她们的个人经历、文化程度有密切关系。另外,对罗曼司进行文本分析可以发现:罗曼司标准化的语言和近似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手法,都是它吸引女读者的理想媒体。阅读罗曼司的意义由两重性:一是阅读意味着“温和的反抗”,是对社会现实不满和渴望改变现状的表现;二是阅读又抑制女性反抗意识,把她们的不满引入理想化的消极期待中,迫使她们安于现状,不采取行动。对于女性主义批评家来说,认识这种双重性的目的是引导和鼓励女读者的反抗意识,努力创造条件,让这种形式上的反抗结出成果。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63页。因而,主流文学之外的通俗女作家和其文本不可忽视。大众文化作品,其意义和美学价值不仅在于作品本身,同时在于其对不同的读者的因时、因人而异的作用。
二、Women Literature
译介文章中诸如此类的第二手资料非常之多,但对上述术语的解释倒也没有太多不妥。“女性阅读”相关术语中出现解释混乱的是women literature(“女性/妇女文学”)这个术语的译介。
对“妇女文学”最早的界定出现在翻译过来的《美国当代文学》的一章中,书中说,“妇女创作的文学作品和妇女文学当然不属于同一范畴”,伊丽莎白·詹威:《妇女文学》、郑启吟译,见《美国当代文学》,丹尼尔·霍夫曼主编,《世界文学》编辑部译,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80、483、484页。“是否属于妇女文学,这里采取的检验标准是作者对所探讨的经历的理解。要看她描述和评判这种经历时,用的是多种多样具有个性的,而同时又是妇女生活固有产物的措辞用语,还是用的是男子的原则和评价标准……严格意义上的妇女文学的作者认识到妇女的生活道路与男子的不同,她们想调查这些不同之处。至少她们下意识地知道需要一套不同度数的镜片才能清楚地看到它们,需要有一套不同的语义系统去表现它们。”“开放性和不稳定性就成为妇女文学的特征了。”
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时候,朱虹说,“‘妇女文学’是个很广泛的概念,包括好几个层次,它的含义伸延得很远,引起的联想很多……从广义上讲,古往今来文学名著中那些不朽的妇女形象……都是对妇女心灵的探幽,均可以归于妇女文学的辽阔领地。”然而,尽管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一些男性作家自觉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时候男女不平等和性压迫问题,“所有这些男性作家笔下的作品无论从文学角度还是从妇女解放的角度看都颇有意义”,但“这些作品缺了一个最核心的东西,那就是女人的主体性,因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妇女文学。”朱虹:《妇女文学——广阔的天地》,载《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第55、56、57、58页。朱虹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妇女文学也理所当然只能由女性作家自己实现。”妇女文学表现的内容有,“女人的孤独、寂寞、愤怒、怨恨、幻灭,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实现自我,要求发展,反对女性中心的文化强加于她们的角色”;“歌颂爱情,但这种爱情是基于把女人当人平等对待才能实现的”;歌颂深重的灾难下“女人的力量”;“歌颂母爱,以亲身体验写出母性的伟大,也写出作为女人和母亲两种身份的矛盾,这是一切女性的共同经验”;“女性之间的相互支持,姐妹、女友之间的真挚感情”;也塑造她们眼中的女性,“且不管这种塑造里是否也暗含了偏执,女作家跳出感伤的窠臼,敢于拿尊严的男性开心,这起码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该文结论是,“妇女文学,包括了严格意义上的女权主义作品和广义上表现妇女意识的作品,成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当然是以性别在文艺作品中的烙印为前提的;而性别在文学中的影响与作用,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又是以男性和女性社会存在的不平等、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为前提的,因而是符合唯物主义观点的。如果取消性别压迫这个大前提,妇女文学的独立范畴就难以成立。”此文作为朱虹、文美慧主编的《外国妇女文学词典》(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的序言又随书刊行。
将这两个有关“妇女文学”的界定两相对照,我们会发现,朱虹关于“严格意义”上的“妇女文学”与詹威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妇女文学”基本一致。伊丽莎白·詹威的说法中“妇女文学”的范畴很严格,基本上就是“女性写的女性主义文学”的简称;其特征也相当鲜明。而朱虹所言的“妇女文学”实际上包括了两个层面上的“广义”和“狭义”界定。一类妇女文学的“广义”内涵侧重的是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狭义”内涵强调的是作家的性别。另一类妇女文学先规定为女作家的文学作品,由其是否表现“女性生活”来划分“广义”和“狭义”。这种区分是建立在对文学/女性关系的不同层次上,由作家的性别区分,到作品所表现内容或形象的性别区分,最后到作品是否有特定的“女性风格”与“女性意识”作了或宽或窄的限定。朱虹的“广义”的妇女文学界定反映了中国原有“女性文学”或“妇女文学”的范畴和观念,是对西方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中的“妇女文学”含义的发挥。这种把包含女性形象的作品也称之为“妇女文学”的情况在后来的译介文章中也出现过,比如有人在介绍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的第一阶段特征时说,“女性主义阅读集中分析妇女形象,研究女性人物的处境和心理,批判女性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概念化及‘天使’与‘妖孽’的对立。”陈晓兰著:《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这里的“女性文学”的概念显然是朱虹所谓的“广义的”,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詹威和朱虹都强调“妇女文学”是“女性作者”对“女性经验”的有意识的描述,肯定研究“妇女文学”必要性,不过朱虹关注的是妇女文学的内容,詹威偏重介绍妇女文学的写作特色。后来的译介文本对妇女/女性文学的介绍也大致不脱离女性经验、女性主题、女性风格这几个方面。
我们的译介人员转述了西方女性主义者从各个层面对“女性文学”和“女性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看法。《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这本译文集中有文章说,文学在发挥其他功能之前,必须真实地以各种形式表达女性的体验,“女性主义批评应该鼓舞这样的艺术,它忠实于妇女的经验,没有被女性观念过滤,不受男性标准束缚。文学必须允许直率的、真诚的自我表达,写作不受与文化抵牾的预先存在的标准钳制。”玛丽·伊各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陈彩霞、林树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该译文集有多篇文章表明女性经验的价值是对男性独尊的文化体系的一种颠覆,比如,“阐明女性经验,它便可以帮助使历史上主要为男性利益服务的价值系统具有人性和得到平衡,也就是说,它能够有利于带来文化的男女双性。”同上,第300页。或者说,“女性艺术的发展是进步的,探究严格的女性现实,是纠正性别歧视的文化偏见的必要的一步。只有在我们将月亮黑暗的那一面纳入我们的世界观,我们才能开始严肃地讨论宇宙文化。”同上,第13页。在英美女性主义者那里,女性主义阅读实质上是对已有的作品进行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的依据是女性的“经验”。女性经验成为检验男性文学真实与否及女性主义批评是否片面的标准,也是女性读者喜读“大众文学”而不必感到羞耻的原因。实际上,女性文学所以成为一个文学团体,很难从本质上找到一个确定而稳固的原因。女性文学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是因为女性文化在整体文化中形成了一种集体经验,使得女作家可以超越时间与空间而彼此关联。菲尔斯基认为,“女性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不是因为女性写作和男性又什么本质上确定无疑的不同,而是因为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一个文化现象:妇女自觉地自我表述为一个受压迫的群体,反映在文学上,则出现了一大批对性别关系与妇女身份问题的探讨。”Felski Rita,Beyond Feminist Aesthetics:Feminist Literature and Social Chang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
文学是作家生活和存在、思想和感情的反映,要人们重视妇女文学中的女性体验,必须帮助人们了解女性文学如何体现了“女性经验”。一方面,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认为,历史中的妇女、文学妇女有着相同的际遇,女性文学是保存女性真实经验的储存所,是认识女性的源泉。译介文章《女权主义批评面面观》曾引用西德尼·卡普兰的说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男性文学中关于女性真实的质疑,对女性作品的认同,都是以女性读者的体验以及历史研究、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提供的“真实的妇女”存在、妇女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为参照系和出发点的。王逢振:《女权主义批评面面观》,载《文艺理论研究》,1991年第1期,第85页。这种看法倒体现了新历史主义所提倡的“跨文化综合”的策略,即在文学与非文学文本、在话语和非话语文本(如事件)的并列中阅读文字表述。也就是,阅读女性的文学作品时寻找其与日记、书信、传记、学术原则、广告、通俗文化、政治宣言、女性规范以及政治运动和历史事件的关系。这样,女性主义的“女性阅读”肯定作家对作品的直接参与,赋予那些与女性作家的经验更加接近的,具有鲜明主体意识的文类或文体如自传、书信体、日记等作品以更高的价值,认为它们代表了女性文类。
另一方面,女性文学,比如妇女小说,是艺术作品,当然和私下里创作的真情流露的自传、日记、书信不可能完全一样。汉译的文章中可以看到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chell)对这种情况的说明,小说是“用妇女的男性语言,谈论女性的经验。它既是妇女小说家对妇女世界的拒绝(她毕竟是小说家),又是来自男性世界内的妇女世界的建构。”玛丽·伊各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陈彩霞、林树明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页。米切尔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指出了女小说家的双重贡献:既塑造妇女应有的形象,又使作家通过写作,成为抗拒的妇女,来抵制这个世界。因而,对“妇女文学”的“女性主义阅读”要能解读女性作家的“双重声音”,探微索隐,阅读有利于女性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肖尔瓦特说,“我们必须通过探索女性文本的缝隙,寻找历史、人类学、心理学和我们自身中被压抑的信息,从而确定未曾被言说的女性特质。”Elaine Showalter,The New Feminist Criticism:Essays on Women,Literature and Theory(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5),p。47.不少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中文文章、著作都认可女性经验的双重性质,认为其包含了被压抑、被强迫的部分。女性的矛盾、分裂、疯狂、焦虑、双重性成为被关注的焦点。被男性排斥、为男性所恐惧的“镜中女妖”、“阁楼上的疯女人”正是女性之不可思议性的体现,更接近女性的真实性。从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子》中译本里可以看到该书形象地表现女性作家如何受到“天使”的困扰,如何在男性观念、规范和禁忌的压制下,为不能表达自己真实体验而痛苦,该文被广为引述、转述。张京媛书中编选了琼·迈卡斯的《一张扭曲的字母表——迈向妇女诗学》,她认为,女性的文本正如扭曲的字母表和身体的姿势,解读这种字母和姿势,阅读被迫沉默者的文本,正是女性主义批评的一种实践。《阁楼上的疯女人》在中外被认为是这种实践的最好范例,虽然《阁楼上的疯女人》没有被翻译过来,只有介绍的文字,但国人眼中“病”与“狂”被赋予新的意义。艾莱恩·肖瓦尔特著《妇女、疯狂、英国文化,1820~1980》(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可以稍微让国人见识一下这种文化与“病态”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译介文章说明,“女性文学”的批评在肯定、重申女性的“反面形象”,否定一切的教益,一切具有反叛性、异端性、异质性的现象都成为女性主义关注的对象;以同性恋、女性友谊、单身母亲的身份拒绝父亲的作用,扰乱整个法律、道德秩序。
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那里,妇女/女性文学的范畴随着“女性主义阅读”而扩大。从译介的文章中,还可以看出“女性文学”在西方的悠久传统。对“妇女/女性文学传统”的追溯是“女作家中心批评”(gynocritics)的重要方面。中国人写的译介文章大多数提到了《女性的想象》(1975)、《文学妇女》(1976)、《她们自己的文学》(1977)、《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等专著的主要内容,由于都是点到为止,倒也没有多少差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相关部分的小标题,如“女性传统: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张岩冰著:《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经典书目再造与文学母亲系谱的寻找”宋素凤著:《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她们自己的文学’:重建文学史”秦喜清:《谈英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载《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第81页。等,都比较典型地概括了追溯“妇女/女性文学传统”是“女作家中心批评”阶段的主题。中国人的译介文章所举的例子有的是来自一些介绍性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入门之类的书和文章,有的例子、引语来自一些诸如《一间自己的房子》等中译本,更多的则直接来自两本西方女性主义的译文集《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女权主义文学理论》。
从译介文章或章节还对重建“女性文学史”中的特色的零零散散的叙述中,有心的读者可以看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对“女性文学”的“主题”和“性别风格”的界定。“主题”研究包含了一个“再创造”式的颠覆过程。人们一般对通俗小说都持轻蔑的态度,认为其难登大雅之堂,女人写通俗文学更被认为是浅薄的人做浅薄的事情,哥特式小说、侦探小说中的恐怖和悬念被认为不过是提供刺激,罗曼司、科幻小说、乌托邦小说是女人胡乱的臆想。但新一代的批评家采用了女性主义的视角,从19世纪的妇女通俗小说中看到了女权意识的大胆流露,指出这些书揭示了妇女教育、就业、政治权利、社会地位等众所周知的问题,同时,那些当时被斥为“有伤风化”的那些部分和成分更深刻地揭示了妇女的内心。比如,恐怖和悬念都是女性心理的折射,那些蜿蜒的长廊和黑暗的密室意味更是不言而喻,乌托邦和科幻小说有时以最尖锐的形式,最大胆的想象来表现女性的理想,甚至侦探小说也能成为表达女权思想的媒介。朱虹:《妇女文学——广阔的天地》,载《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第58页。译介文章和专著有些篇目提到,莫尔斯的《文学妇女》以作者的日记和信件为据,认为玛丽·雪莱于1818年完成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里虽然没有女主人公出现,但全书萦绕的是“诞生的母题”,折射了一个母亲对诞生所怀有的期待和恐惧的双重心理,是对“诞生神话”别出心裁的改造,其意义还在于将当时的“怪诞小说”推向了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科幻小说”这个新文类。《女性小说的原型》(Archetypal Patterns in Women's Fiction,1981)的作者普拉特(Annis Pratt)指出,女作家作品的叙事结构常常呈现回旋反复的倾向,这个与许多女作家与世隔绝的生活有密切关系,而弥散其中的阴暗情绪则是妇女数世纪以来受女性限制的处境使然。
关于“女性文学”所体现的“性别风格”问题,译介的文章在不同的地方也有所涉及。妇女完全可能用男子的标准成功地进行写作,这是因为男子标准在我们社会里无处不在,它们既是男子的也是妇女的文化背景的组成部分。但是,用男子标准写作仍然要求妇女作一种调整。不少译介文章在论述到这个问题时引用伍尔夫的说法,“妇女很少有具备男人那种对于修辞学的钟爱”,批判所谓“女小说家只有在勇敢地承认了女性的局限性后,才能去追求至善至美。”伊丽莎白·詹威:《妇女文学》,郑启吟译,载《美国当代文学》,第481页。同样被援引较多的是伍尔夫对女性独特句式的赞美,赞赏女作家多罗西·理查森(1875~1957)创造了或曰发展了一种符合女性心理逻辑的句式,它比旧的句子富有弹性,可以拉得很长很长,挂得住最小的颗粒,也容得下最模糊的形态。
关于“女性文学”范畴的时效性问题,译介者的说法不同。朱虹说会变,“如果取消性别压迫这个大前提,妇女文学的独立范畴就难以成立。”朱虹:《妇女文学——广阔的天地》,载《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第58页。宋素凤也认为,“现在有女性文学研究,并不表示这个范畴会继续有效,或不会改变。至少当妇女、女性这些文化符码的所指范畴有突破性的改变的时候,女性文学这个范畴必定也要有所改变。”宋素凤著:《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7页。林树明则觉得“妇女文学”这个范畴会一直存在,因为“男女除了一些共同的物质与精神范畴外,还有他们各自独特的方面。这种差异不仅仅是由性别压迫内容组成的,它宽广得多,绵长且永恒。传统男女二元对立等级秩序的消解,并不必然产生一种抹煞了所有差别的一元化模式。”林树明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对“妇女文学”的范畴界定有所不同,一方面是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国内对文学中性别差异的看法。
三、“女性阅读”译介评析
“女性阅读”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它的目标是提高女性已有作品的地位和培养女性主义的阅读技巧。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耿耿于怀的是文学史,“在学术评价上,妇女作品并没有受到完全平等的对待。只消看一下为今天的批评家评定为优秀的和有意义的文学作品,就知道其中大多数是男子的作品。”伊丽莎白·詹威:《妇女文学》,郑启吟译,载《美国当代文学》,第481页。甚至身为女性的评论家也用男性的标准来贬低女性作品。我国也有译介文章探讨女性评论家受男性批评标准牵制的问题,“早期女性主义阅读实际表现为‘像男人一样阅读’,脱离了那种适合于她们作为女人的条件的独特经验,结果是充当了男性批判的同路人,把一些女作家和作品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陈晓兰著:《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对“女性主义阅读”作这样的介绍根本就是错误的,“像男人一样阅读”正是女性主义者所批判的,也许改为“女性曾经的阅读”更为妥当。这里的问题显示出对“女性主义”界定的概念不清,对“女性文学”问题认识上的混乱。
妇女作为一个群体的阅读策略有其历史的需要与必要性。女性主义“阅读”方面的译介影响是非常强烈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初对“真实”女性经验的诉求,揭示了男性文本所宣称的普遍经验歧视是漠视了女性经验的结果,使得仍居主要文学形式、以反映真实为主的男性作家写实主义文本窘态毕露。在“阅读”、发掘女作家如何表现受压抑和被禁锢的体验时所使用的术语——排斥、埋没、忽视、歪曲、抛弃、遗漏、隐匿、潜力、压抑、分裂、挖掘、重现、僭越、厌女症、次文本、双重性、亚文化等——冲击了文学的传统观念,业已改变了女性被遗忘的历史。另外,对女性一切的“肯定”,肯定差异,以还女性本来面目为前提,回到女性的“自然本质”。如果说,过去女性换上男性的衣服谓之解放,那么换回自己的衣服,更加女性化,谓之女性之作为女性而自豪。“女性文学”成为热点。只要是女性作者都有反抗的一面,至少是迂回曲折式样的。“女性文学史”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热点。
从上面有关“女性阅读”译介的介绍看,女性经验在女性主义批评中的权威性决定了它的文学观念、批评准则、批评的倾向、批评的视野、具体的分析操作方法及一整套批评术语。然而,女性主义批评对普遍经验的质疑是个双刃剑,在松动了男性文本对普遍经验的掌握后,也引发了人们质疑女性经验本身的普遍性和同一性。我国学者崔卫平质疑“女性阅读”这一术语,认为好作品不在于作者的性别,“女性阅读经验”并不能对作品的优劣作出判断。她宣称,“我反对从个人的经验直接上升为一种形而上的东西,如果这样我们就把一个理念或者说理想,改变为一种服从于个人利益的东西了。”崔卫平:《我是女性,但不主义》,载《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这是集体/个体之区分的视角。译介对“女性经验”的强调引起的另一种反应就是西方女性主义经验与中国妇女的女性经验不同,西方女性主义“不适用”于考察中国妇女的问题。这是国别区分的视角。
“女性阅读”的译介另一个没有明确阐述的是“女性文学”的界定问题。这个影响到中国文学批评中“女性文学史”撰写的分期问题(见第三章),也影响到文学批评的立足点。刘思谦曾言,由于“中国女性文学的发生、发展也是以较大规模的社会革命、思想文化革命为历史际遇而悄然出现悄然运行的”,女作家“并不是一支有自己的性别理论的文学队伍”,因此,对于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重要的是从研究对象的特点出发,理清思路,有分析有选择地吸收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合理部分,找到我们自己的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点。”刘思谦著:《“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心路历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后记”。这其中包含了对“女性主义阅读”理解上的偏差。其实,文学批评的根本是“诠释”,女性作家有没有“女性意识”要靠批评家的“开发”,所以“女作家并不是一支有自己的性别理论的文学队伍”不应该成为不能进行“女性主义阅读”的理由。
女性主义的文本阅读策略可以说是“男女有别”的:男性作家文本采取“修正性”、“抗拒性”立场,对女性作家文本的阅读则采取“妇女一体”的基本立场。这样,对女性经验的极度强调,也可能使女性主义批评走向了“生物学模式”的极端。译介的文章,尤其是早期的文章对“女性阅读”中的问题鲜有提及,主要是说这个那个女性主义者的说法如何如何,有的诠释出现了偏差,实际上是“双重意义、双重声音”。由此,辨析和清理可以有多种理论立场,不同的立场形成不同的角度和标准,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界兴起的“重写(重读)文学史”的一个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