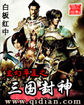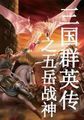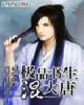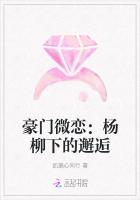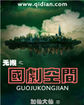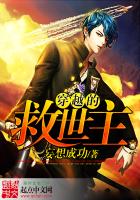走出幽深的皇宫,生活在大明帝国广袤土地上的是各色各样的普通百姓。我们常常用“男耕女织”来描写传统社会中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这种描述已经暗含了对中国历史上的家庭关系与两性差异的某种界定。毋庸置疑,婚姻与家庭是最能集中体现某个时代两性关系的一个角度。明朝皇宫中帝王的婚姻与家庭,虽然浓缩了明代君主专制权力下两性关系的特殊形态,但这毕竟只是历史面相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占有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才是构成明朝社会的主要群体,那么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婚姻与家庭呢?在日常的婚姻、家庭生活中,男性与女性保持着怎样的性别分工,扮演着怎样的社会角色,是否就是简单而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男耕女织”呢?礼制法度与现实生活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差距呢?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明代人的婚姻与家庭生活吧。
在古代中国,男女双方缔结婚姻关系,所谓“合二姓之好”,可是一件大事情,正如《礼记》所说,两性婚姻“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也就是说,在古人心目中,婚姻不仅是夫妻双方个人的终身大事,而且也是双方家庭特别是男方家庭及其宗族的一件大事,因为涉及子嗣的繁衍和宗族的传承。同时,经由男女双方缔结婚姻组成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既然婚姻和家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我国历代王朝特别重视有关婚姻方面的立法建设和调整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明王朝的统治者们也不例外。太祖朱元璋自建立明王朝后,就积极通过法制的建设来确立整个社会的统治秩序,其中也涉及对婚姻、家庭与两性关系的立法,主要体现在《大明律》以及附在律条之下的“定例”中,它们体现着明代婚姻关系、宗法等级的基本特征,也是明代人确立婚姻关系的最根本的法律依据。当然,各地的风俗习惯与现实中各种背离婚姻立法原则的现象的存在,也处处体现出国家法理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异。
1.婚姻中的等级限制
明朝社会的各阶级、阶层之间存在着森严的等级隔阂,职业有高低本末,人有三六九等,身份也有贵贱之别。在明朝时,有一些人生来就是贱民,在他们的户籍上就注明了其贱民的身份,而且父父子子世代相传。这些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无法通过读书入仕改变自己的身份。在明代婚姻立法上,有很多对这些不同等级的人群互婚的限制。
比如,明律严格限制地位卑贱的奴婢与良民子女通婚。《大明律》规定,如果奴仆的家长为其娶良人家,就是普通百姓家的女儿为妻,罚杖八十下,女家减一等受罚,如果是不知实情,则不予处罚。如果奴仆自己娶了良人家的女儿,要接受同样的处罚,奴仆家长如果知情,要减二等受罚;良人女因而入籍沦为婢女,那该奴仆的家长要加重受惩罚的力度。如果妄称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结为夫妻者,罚杖九十下,令各自离异改正。婚姻中论门第是非常重要的,主仆良贱有别,按照法律规定,是不得通婚的。这样的原则在民间也得到较大程度的认可,至少在一些比较显赫的大家族中是得到推行和强调的。比如明代休宁县茗洲的吴氏宗族,就把这样的规矩写入了他们的家规家训中,吴氏族人认为“门第不对,乡都垢笑”,认为如果与地位低下的奴仆或别的贱民缔结婚姻关系,世人会以对待奴仆的态度来对待自己,也会瞧不起自己的子孙,所以规定绝不许出现这样的族人,若出现之,“我族即不当与之并齿,生不许入堂,死不许入祠。”
2.婚姻立法中的宗法原则
明代统治者所规定的缔结婚姻关系时的诸多限制因素,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很多宗法原则。《大明律·户律·婚姻》中对亲属之间的一些婚姻关系做了严格限制,比如严禁“同姓为婚”。还有不得娶亲属的妻妾,双方虽是异姓也不能相配。元朝蒙古族有“收继婚”的风俗,即父死,子可以收其庶母,兄亡,弟可收嫂为妻,但是不准弟亡而兄收弟妇,这是蒙古族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而明朝建立以后,统治者认为这种收继婚是“胡风蛮俗”,便在《大明律》中明令禁止,规定“若收父、祖妾及伯叔母者,各斩;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妇者,各绞”。还限制了同母异父,同父异母者不得为婚,娶同母异父的姊妹或妻子前夫的女儿为妻者,都以奸罪论处和量刑。明律中将这些条款列入“尊卑为婚”目中,意思是说这些婚姻都属于尊卑相婚的形态,这种尊卑与身份的贵贱还不同,它主要是指传统宗法制度下亲属关系中的尊卑长幼之序,这是天理人伦,不可违抗。民间很多地方的风俗与习惯法也是禁止同姓、尊卑为婚的,这是传统宗法制原则在中国有深远影响的体现。
但是,民间风俗总是有与法理相悖的地方。比如关于同姓不婚的规定,民间的做法就比较有弹性,一般只限制同宗同姓的男女不得成婚,而同姓非同宗者就可以成婚。正统年间,一位知县上疏条陈民情时,就说到当地存在着一些有违宗法人伦的婚姻形态,比如将后妻所携带的前夫之女娶为自己儿子的媳妇,将后妻所携带的前夫之子作为自己的女婿,这类现象还不在少数。虽然以现在的婚姻观来看,婚姻的双方并无血缘关系,可以结婚,但是在当时的宗法制原则下,这位知县还是认为,这样的婚姻关系会导致兄妹男女之别不明,父母公婆之名不正,有“乱伦”之嫌。
3.“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按照明律的规定以及民间的传统,男女之间结为夫妇并不是依照他们自己的意愿达成的,普通百姓的婚姻缔结都要取决于“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明代的法令规定,“凡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我们可不能把这个“主婚”理解成今日婚姻仪式上的“主婚人”,二者有很大的差异。明代律令中说的“主婚”不仅仅是家中长辈主持婚礼仪式,还包括了对婚姻对象的选择、订婚程序和结婚仪式的主持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对结婚对象的选择权,这在中国古代是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婚姻双方并没有选择结婚对象的自由,选择的权力是属于双方父母或者别的长辈亲属的,这就是“父母之命”。
明律也规定,双方父母或亲属为各自的子女订婚时,不能隐瞒双方有关残疾、疾病、老幼、是否庶出或过房等情况。在情况了解后,若双方愿意,就同媒妁签写婚书,依照礼制下聘迎娶。如果女方之前已经跟另外的男家立过婚书,或者得过聘礼,即使最后未婚,若又接受另一家男方的聘礼,女家主婚人也要接受杖刑。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那些在外做官、经商的幼辈,一旦祖父母、父母等为其在家订婚,如果他们在外已经自己娶了妻子,已成婚者令其仍旧为婚,如果只是定了婚约,尚未成婚,那就听从家中长辈所定的婚约,不得按照自己定的婚约成婚,违者要罚杖八十下。
无怪乎法制史专家瞿同祖在论及中国历史上的婚姻状态和婚姻法律时说:“婚姻目的中始终不曾涉及男女本人,所以男女的结合而需顾到夫妻本人的意志是不可想象的事。婚姻所以合二姓之好,只要二姓的家长同意于其子女的结合,经过一定的仪式,婚事便成立了。直系尊亲属,尤其是男性的直系亲属,有绝对的主婚权。他的意志可以命令他的子女与任何一定的人结婚,社会和法律都承认他在这方面的威权,予以强有力的支持,不容子女违抗。于是父母的意志在法律上成为婚姻成立的要件,子女即使在成年以后,即使仕宦买卖在外,也没有婚姻自主权,除非得了父母的同意。”可谓是相当精准的描述。
至于媒妁之言,明律未作出详细的规定,但是也说明了在男女双方家长立下婚书时,需有媒妁在旁。媒妁,在民间称为“媒人”“媒婆”,她们是活跃在明代城市乡间的著名的“三姑六婆”(尼姑、道姑、卦姑;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之一,全靠着一张利辩之嘴,帮人说合姻缘,促成男女双方缔结婚姻关系。但多是只与男女双方的家长打交道,并不与男女本人沟通。有些家长甚至不亲自去对方家中,只派媒人前往说合。民间举行婚礼时,也有拜媒人之俗。
在民间婚姻关系的缔结过程中,媒人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口碑却并不甚佳。因为她们往往只图说合成功,拿到彩钱,而不管双方是否合适,满嘴的甜言蜜语,却多数都不属实。当时有一首民歌,曲中这样形容媒人:
这壁厢取吉,那壁厢道喜,砂糖口甜如蜜。沿街绕巷走如飞,两脚不沾地。俏的矜夸,丑的瞒昧,损他人安自己。东家里怨气,西家里后悔,常带着不应罪。
惟妙惟肖地刻画了明代媒婆的形象与行为,客观上反映出当时媒妁制的风行及其弊端。
4.关于婚龄
按照传统的制度,男女婚嫁必须“以时”,就是必须在适当的年龄嫁娶。一般认为,男子未及十六岁,女子未及十四岁就成婚,比合适的婚龄略早;而男子二十五岁以上,女子二十岁以上尚未成婚,就是“过时”,即超过了合适的婚龄。这是明人黄佐在《泰泉乡礼》中对男女婚龄所定的标准,大体依照宋人朱熹《家礼》中的相关规定。明代法律中的相关规定与这个传统礼制相一致,也规定“凡男子十六、女十四以上,并听婚娶”,并针对民间指腹为婚的习俗规定“凡男女婚姻,各有其时,或有指腹割衫为亲者,并行禁止”。
但是,在民间的婚恋实践中,却并不完全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实施。在明代的很多地方,如四川和徽州地区,都存在着早婚的习俗。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卷五记载其旅川见闻时,就专门记录了“蜀中尚缔幼婚”的习俗,他说,当地的男子好娶年龄更长的妻子,男子十二三岁就娶妻。他还说徽州地区的习俗也是这样,但是徽州男子在外经商,早娶妻则有利于壮志四方,至于四川地区为什么会流行这样的早婚习俗,王士性也觉得很奇怪。在20世纪80年代,四川南充地区的广安县大良乡和黔江地区彭水县善感乡两地都发现了刻于明万历九年(1581)的禁止早婚的石刻,其中一再重申“今后男婚,须年十五六岁以上,方许迎娶”,对于违犯规定者,其婚娶男子的父兄都要“重责枷号”,严惩不贷。这样立碑严禁,也可以看到当时四川地区早婚现象的泛滥。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各王朝都对男女婚龄作过相关的规定,古人对早婚可能带来的危害也有所察觉和论述。比如西汉王吉曾上疏汉宣帝,论及早婚问题,他说夫妇是人伦大纲,民间风俗嫁娶太早,这些男女尚未懂得为人父母之道就有了孩子,这样会导致子女得不到很好的教育。这一看法颇符合现代科学的观点。明代人对早婚的危害也有所认识,如明中叶人丘濬在《大学衍义补》卷五十中考察了历代关于婚嫁年龄的规定后指出,早婚不仅可能导致民间争讼增多,败坏伦理风尚,影响人口的繁殖,还可能会导致淫乱的风气。他还从生理发育的角度,认为男子十六、女子十四岁时,身体才能发育成熟,这时方可嫁娶,不宜过早。
5.关于纳妾
按明律,男女婚姻关系要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一夫一妻制,《大明律》就明确规定,如果男子已经有妻又再娶妻者,要罚杖九十下,还要与后娶的那个妻子离异,这很像现代社会对于重婚罪的定罪。但是,明代的法律同时又提供了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合法性,因此,这就在实际上认可了一夫多妻制的现实,只不过在尊卑长幼的宗法秩序中区分了妻与妾的身份,妾不属正妻罢了。明代统治者对纳妾的条件做过一些法律上的规定,《明会典》中就规定:亲王可以纳妾十人,一次选娶;世子、郡王可纳妾四人,二十五岁无子者可纳妾二人,有子即止,三十岁无子者,才可以纳足四妾;将军三十岁无子者可纳二妾,三十五岁无子者纳三妾;中尉三十岁无子娶一妾,三十五岁无子娶二妾;庶人四十岁以上无子者,许娶一妾。从这样的法令中,不难看出,明代法律对纳妾制的相关规定体现了社会各阶层间的等级区分,也体现了宗法制度下,娶妻纳妾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广子嗣,繁衍男性后代。当然,这种法理形式上的限制条件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具有真正的约束力的,而这种限制到清中叶后的法律条文中也就消失了。
因为法律上同意男子娶妾,这实际上就为男子纵欲提供了法律保证和机会,给女子带来人格、地位、爱情及家庭生活上的种种不幸。丈夫可以纳妾,就从法律上允许了他们可以在娶了妻子后又另结新欢,这对正妻而言,是种极大的伤害。而另一方面,妾在家中也是没有地位,没有名分的,她们有很多都是因为年轻貌美而被官宦或富商花钱买来的。她们不能像妻子一样获得丈夫的认可,也不能上事宗庙,在宗法社会里只有正妻才能与丈夫共同祭祀祖先。妾在法律上的地位也明显低于妻,在丈夫与妾的关系中,法律也对丈夫极为偏袒。家长殴妾比殴妻的罪刑要轻二等,杀妾唐宋律只处流刑,明律更轻,仅杖一百,徒三年。若妾殴打丈夫,则处罪较妻殴夫罪重得多。
从明人的一些笔记文集中,不难看出明中后期,纳妾在明代士大夫阶层中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当时在士人阶层中男性守一而终的情形已十分稀罕,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形,世人往往对之称奇不已,褒贬不一。比如明景泰年间的兵部尚书于谦终身独守夫人董氏,未纳别妾,为此曾备受时人赞叹;而对未纳妾的现象,不同的人往往会有不同的评价,比如明人沈德符,对龙江人沈归德无子嗣而未纳妾,就叹之为“近世罕见”,而对少保戚继光与宁夏都督萧如薰等未曾纳妾,就评说他们“俱为其妻所制”。这种少见多怪、褒贬不一的议论恰恰说明了纳妾在明代士大夫阶层中的普及与盛行。甚至还出现过父子因为争抢同一个姬妾而发生矛盾的事情,比如沈德符就记载说,宰辅焦芳的儿子焦黄中就曾为了赢得一名姬妾而与其老父争斗于室,时人传为笑谈。
明中叶以后,士大夫娶妾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他们一般会纳怎样的女子为妾呢?俗话说“娶妻娶德,纳妾纳色”,所以那些美艳风流的青楼名妓往往成为一些士大夫或者富商的选妾对象,但是更多的情形还是会首选良家妇女。明人谢肇淛有一段品评当时各地女子的言论,其中就说到,古时燕赵,即明代北京附近本多美女佳人,但到明代已经名不符实;而山西地区的女子虽然纤白足小,奈何性情粗犷,不够温柔;大同的妇女虽多美丽,却又恋土重迁,不愿嫁往外地;另外,江浙一带的南京、苏州、杭州与福建省的建阳、兴化等地,也会出产国色天香的美人,但却瑕瑜相杂,需要有眼光的人着意挑选;唯有扬州一带,居天下之中,川泽秀美,所以该地的女子也多娇美可爱,性情温柔,举止婉慧,各地女子皆不能与之相比。
也正因为这样,男子娶妾就会首选扬州女子,因为扬州女子不但有美貌,又有厨艺、琴棋之技,更因她们从小就接受过“自安卑贱,曲事主母”的教育,就是说在成为男子的妾后,要自知卑贱的身份,好好屈从于正妻,维持家庭的安宁。因此,按照时人沈德符的观察,即使是大家庭中的妒妇,会对其他籍贯的妾非常严苛,而对从扬州娶来的妾则更宽容一些。而男子娶妾,最担心的就是妻妒忌,妾争宠,但娶扬州女子为妾,就可免受此类烦恼。
于是,培养扬州女子,以作为士人、富商选妾对象的营生也就逐渐应运而生。一些精明的生意人会四处去收养贫苦人家的幼女,抚养她们长大,还会教给她们琴棋书画,培养她们的才情风韵;也会让她们学会算计账目的本事,可以管理家事。等这些女子长大成人,就找机会把她们许给那些想娶妾的男子,换取一大笔财礼,这些扬州女子时称“扬州瘦马”,这等收养调教幼女、待其长成后卖给他人做妾的生意俗称“养瘦马”。一旦有贵官富商到扬州,稍微透露出娶妾之意,马上就有各色媒婆前来牵线,这些媒婆心里都有一本美女册子,哪家的“瘦马”资质怎样,她们心中都清楚得很。相“瘦马”一般都是由媒人出面领着,一旦相中,男方就会根据“瘦马”姿色、才智情况,付一笔或多或少的财礼,这些钱大多进了那些“养瘦马”之人的囊中,算做抚养教习的谢礼。
“扬州瘦马”在晚明几乎成为一种“专业”的妾,这种特殊群体的出现,也可见当时娶妾现象之盛。当然,这种现象主要还是在士大夫、官僚、富商等有权有势有钱的上层社会中流行,在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家境贫困的下层民众中,这种现象是极为少见的,因为有些穷苦人家的男子连正常的娶妻都支付不起聘礼、宴席等各种婚礼费用,即使娶了,要养活一家子人也相当困难,又哪里有能力纳妾呢?
6.对奸情的处罚
在明代法律中,男女之间的奸情可以分为两种情况,有和奸,指男女婚外自愿通奸;有强奸,指男性对女性的施暴行为。
明律对于妻、妾与人通奸的处罚非常严厉。律例规定,如果丈夫亲获奸夫奸妇于奸所,登时将奸夫奸妇杀死者,不予论罪。若止杀死奸夫,奸妇仍依律断罪,听凭其夫嫁卖与他人;如果妻、妾因有奸情而与奸夫同谋杀死亲夫者,妻妾则会被凌迟处死,奸夫处以斩刑。如果奸夫一人杀了奸妇的亲夫,奸妇即使不知情,也要处以绞刑。从这些律条中不难看出,在和奸罪中,对犯罪的女子量刑更重,对遭受耻辱的亲夫给予相当大的同情和法律上的偏袒。这是源于明代统治者对女子贞节操行和品格道德的严苛要求,当时社会上男子纳妾宿妓不会遭受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与制裁,但是女子行为稍有不检,就会备受苛责,当时社会对男女两性的道德评价标准是严重失衡的,这也势必在法律中得到体现。
明代官员对于奸案的审查也是非常用心的,在清人刘世馨的《粤屑》一书中,就记载了明代新兴县的一位李县令如何侦破一起奸案的经过,可谓精彩。相传这位李县令有一次因公下乡,见山边上有一年轻妇女,打扮得很漂亮,在墓边哭泣。李公非常惊讶,就令差役把她带回官署,仔细地加以审讯。妇人报说因丈夫病死后葬在此地,今日是穿着丧服特来祭奠的。李县令把邻居召集起来问,都说妇人的丈夫确实是生病而死的。但李县令觉得如果夫妇情深,丈夫还在丧期,妻子怎么会打扮得如此漂亮来祭奠丈夫呢?所以仍怀疑其中有诈,于是便换上便服潜往妇人的邻乡秘密查访。一日,李县令来到一间茅屋避雨,一老妇人接待了他。正说话间,一个二十来岁的汉子从外面进来,原来是这位老妇人的儿子。李县令与这位汉子对饮畅谈,很是投机。那汉子酒喝多了,便说起县令逮捕一妇人之事,一时兴起,竟道出实情。原来这汉子平日做贼,那天晚上正好溜进那个妇人家中,躲藏在暗处,见那妇人的丈夫正生病躺在床上,而那妇人却在外室徘徊,好像在等待什么。一会儿见有一个男人在夜色中悄悄来了,正是邻乡的武举人。他便同妇人亲热调笑起来,不久听见丈夫的呻吟声,妇人便端着药进去伺候丈夫服下,只听见病人狂叫一声就死了,原来那药竟是熔化了的锡,喝下立即致命。原来这对奸人认为毒药可以被检验出来,而灌锡就没有痕迹。于是李县令命开棺验尸,果然是锡填塞了咽喉。经审讯,罪证确凿,就依照法律定了奸夫淫妇的罪,后来都处以了极刑。李县令也因此受到地方百姓的爱戴,成为贤明有声的地方官,受到当时很多官员的推崇。
明律对强奸罪也有相应的处罚规定,男子强奸女子,判绞刑,强奸未成者,罚杖一百,流放二千里外;被强奸的妇女,不论罪。而特别说明被强奸的女子不论罪这点,恰恰从反面说明当时世人对强奸案件中受害女性所持的某种微妙态度。毕竟是在一个传统社会中,女性虽然是强奸案中的受害者,却似乎也被蒙上了某种罪孽感,至少会被视为是不洁之人,所以明代被恶人奸污后自尽的妇女相当多,这也是当时贞节烈女中非常典型的一类。我们会在后面专述明代妇女贞节观的部分看到许多这样的故事。
7.关于离婚
古代男女一旦结婚,女子便脱离自己父母的家庭,完全进入其夫家,归夫家所有,所以“义绝”即离婚的主导权是归丈夫所有。中国古代关于两性婚姻的法律都赋予了丈夫休弃妻子的权利,甚至丈夫的父母尊长也可以做主令夫妻离婚。中国古代关于休妻有所谓“七出三不去”的礼制规范,这些原则在汉代以后被纳入法律之中,明代法律中也有相关的规定。
所谓“七出”,即妻子有下述七种情况之一的,丈夫便可以休弃她:一、无子;二、淫佚;三、不事舅姑(即不侍奉公婆);四、嫉妒;五、有恶疾;六、口多言;七、盗窃。这“七出”的情况现在人看来似乎都颇有几分荒谬,“无子”,这并不见得是妻子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口多言”,是不允许妻子有发言权,妻子若多了些口舌,就可以成为被休掉的理由;而妻子有“恶疾”,丈夫理应照料,予以积极治疗,反而却作为离弃的借口,自然是十分不人道的;丈夫可以娶妾宿妓,妻子却不许嫉妒,否则就被休掉,这就更不近情理了。
所谓“三不去”,就是指“七出”设有一定的限制,当出现以下三种情况时,丈夫不得休弃其妻子,即:一、在舅姑丧期内;二、娶时贫贱夫后富贵;三、有所娶无所归。这是法律对休妻制做的限制性规定,在一定范围内维护了妇女的权利,《大明律》就规定,如果妻子没有犯“七出”中任何一条,而丈夫将妻子休弃,就要接受杖八十下的惩罚。即使妻子犯了“七出”之错,但是却有“三不出”的理由,此时若丈夫仍执意休弃妻子,则要比照前刑减二等受罚,并令不得休弃,恢复婚姻关系。但是在实际情况中,若妇女所犯为奸情一类,那么即使有“三不去”的理由,丈夫仍然有权将妻子休弃。
“七出”之外,离婚的另一条件是“义绝”,所谓“义绝”就是指夫妻之间发生了一些情义断绝的状况时,必须强制离异,解除夫妻关系。明律中对“义绝”包括哪些情形有详细的说明,比如妻子父母趁丈夫在远方时将妻子改嫁或另外招婿;丈夫殴打妻子至伤残者;有妻子却诈称无妻,再娶妻者;丈夫偷偷接受钱财,将妻子当做自己的姊妹典卖给别人;丈夫纵容或强迫妻子与人通奸等等。与“七出”权利全部在男方相比,“义绝”则适用于夫妻双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规定体现了男女双方在离异条件上的相对平等性,即出现了某些对婚姻中的女性非常不利的情形时,可以由官府出面,判定夫妻二人离异,若有一方不执行,则要承担法律责任。
明代的婚姻关系解除还有一种“和离”的形式,即因为夫妻感情不和而协议离异,但前提是必须双方愿意,否则二人就不能解除婚姻关系。然而,明代统治者显然又更偏袒婚姻中的男方,更维护夫权,所以明律规定若出现丈夫不愿离异,而妻子采取背夫逃亡的行为时,妻子要接受相当严苛的惩罚。如果她只是从丈夫身边逃走,那要接受杖一百下的惩罚,如果她逃走后又嫁给他人,则要被处死。相反,如果是丈夫从妻子身边逃走,三年内,妻子若不报官就自己也逃走,则要被罚杖八十下,若擅自改嫁,则要罚杖一百下。这些规定都显得对女性颇为不公平。但是,明律也在这里对女性的权利做了一点弥补,那就是丈夫逃亡三年后,若还不回家,官府就会出面发给妻子执照,证明二人离异,这位妻子也可以另行改嫁,而且不用归还夫家财礼。
8.关于僧道不婚
僧尼道作为宗教人物,因为宗教信仰之故,不得嫁娶,这在民间习俗和宗教戒律中都是严格申明的。明代法律还专门做了规定,僧道如果娶妻妾,罚杖八十,并令其还俗,女家同罪,按律令双方离异;寺观主持如果知情,与僧道同罪,不知情不论;若僧道假托亲属或僮仆的名义求娶,而自占者,以奸罪论刑。但实际上,明代的僧道多有不守宗教戒律与国家法制者,不仅娶妻生子,甚至还会逛妓院,夜宿娼妓,寻欢作乐。据时人记载,晚明时有些好事的太监,会用妓女布施给僧人,而僧人都欣然接收,享尽情色之欲。所以明中后期的僧道,被世人戏称为“色中饿鬼”或“花里魔王”。而出现这样的事情时,民间也多以传统道德标准私下对其议论褒贬,但只要未涉及人命,大多采取不举官不追究的态度,不了了之。也可见法理与世情的不相吻合。
总体上来说,明代在婚姻关系上的立法还是比较完备的,在立法原则上遵循着社会各阶层的等级分化与宗法制度下的夫权为纲,对历代婚姻关系中的传统观念和处理原则加以了继承。但是,复杂的社会现实势必出现与法理条文不相符合之处,加之明中叶后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人口流动性增强,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实生活中就出现了更多与固定的律例相悖的现象。比如明律禁止收继婚,即不许弟娶孀嫂,兄娶弟妇。但是民间一直沿袭这种风俗,不以为怪,甚至在浙江温州府一带的丐户中,因为家中贫困,无法养活这么多人,还流行弟兄“合娶一妻”的习俗,至弘治年间才禁绝。虽然明律规定了不许指腹为婚,不许早婚,但是民间指腹为婚的习俗一直很风行,早婚的现象也在很多地区一直流行。明代成化年间,礼部上疏言民情诸事,其中就说到了当时婚姻中的种种情况,颇不合成法,比如军民之家在男女订婚后,各自因生计艰难迁徙他乡,或者去边远之地服军役,又或者因出门做买卖多年不回故土,抑或任官在外,入了他乡籍贯的,使得订了婚的男女双方无法成亲;还有些则是定婚后,两方又不愿意了,便随意毁改婚约等等,这些都与法律的规定不符。这些情况的出现使得明朝统治者也一再补充和完善法律条文,但是也不可能完全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多变与复杂。